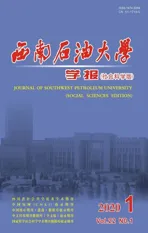试论科研工作者学术合作的持续性
2020-12-09王春雷
王春雷
广西大学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引言
随着当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学科间交叉、渗透与综合的发展趋势愈益加速,学者间的科研合作日益成为科学研究的主流方式。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合作已经成为完成研究项目的重要组织形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独挑大梁、单兵作战”的科研模式[1]。在此背景下,学术界也对科研合作的特点、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近期的研究有吴登生和李若筠[2]、谭春辉等[3]、王春雷和蔡雪月[4]等,早期相关文献综述可参见赵君和廖建桥[5]。还有不少研究者也从组织治理角度提出了一些促进科研合作的针对性建议,如王春雷[6]、高杰和丁云龙[7]等。
然而,这些文献却极少关注已经开展合作的科研工作者的合作持续性问题。多数研究者普遍或者潜意识的看法是,如果科研合作一旦发生,它持续的可能性就会很大。这是因为,如果科研工作者能够在期刊上合作发表高水平论文,说明他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沟通、协调、分工等方面的问题,科研合作的效率较高,那么科研工作者也愿意继续合作。不过,也有研究文献指出,科研工作者的利益冲突导致良好合作关系破裂的事件也并不鲜见。这些文献依据的是一些典型案例,如巴基球分子结构的发现权之争[8]、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9]。关于已经开展合作的科研工作者群体的合作持续性程度这一问题,就笔者所知,目前没有文献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有鉴于此,笔者以《科学学研究》杂志2010年发表的两人合著论文作者为样本,分析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合作持续情况,剖析科研合作的持续性及其特点。选择《科学学研究》杂志的原因,是它不仅提供了论文的收稿和修回日期,还提供了所有作者的详细信息,包括出生年份、籍贯、工作单位以及主要研究方向等,便于判断合作者之间的关系。选择2010年,是因为要充分判断科研工作者的后续合作情况。选择两人合著论文,除了因为其占比最大之外,还是为了使统计结论尽量较少受到“挂名”等假合作因素的影响。
1 《科学学研究》杂志2010年的学术论文合著情况
《科学学研究》杂志主要分为科技论坛、科学学理论与方法、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科技管理与知识管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等五个栏目,还包括少量卷首语、专稿、书评、简讯、纪要之类的文章。由于研究的是科研合作,所以列入统计的论文仅包括五个栏目的论文,共计261篇。按照论文作者人数将论文分成四类,包括独著论文、2人合著论文、3人合著论文、4人及以上合著论文,统计结果见表1。其中:2人合著论文比例最高,达到45.21%;独著论文比重与3人合著论文比重差不多,均在23%左右;4人及以上合著论文比例最少,仅为8.43%。5个栏目的论文合著情况基本差不多,2人合著论文篇数最多,而4人及以上合作论文篇数最少。
下面主要以2人合著的118篇论文作者为样本分析科研工作者的后续合作情况。笔者将合作分成老师之间的合作(简称为师师合作,下同)、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简称为师生合作,下同)以及学生之间的合作(简称为生生合作,下同)。此外,本研究还对两位作者是否属于同一个科研单位进行了区分①如果两人属于同一科研院校,但二级单位不同,也认定为跨单位合作。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表2给出的是两人合著论文情况统计表②在统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论文的作者简介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例如,简介是博士或者硕士,实际上是博士生或者硕士生。此外,在统计过程中还遇到一个关于博士后的问题。一篇论文的作者简介中说是博士,但博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后,是同博士后导师合作发表的论文。这类合作本文统一归为同单位师生合作一类,而不是师师合作。。其中,同机构合著论文88篇,占比74.58%;跨机构合著论文30篇,占比25.42%。
结果显示,师生合作是同机构科研人员进行学术合作的主要方式,虽然同单位的老师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也会经常见面,但这些人见面的主要原因不尽相同。老师和老师见面是因为院系开会或者教学方面的交流,学生和学生见面是因为上课或者一起参加活动,只有老师和指导的学生经常见面的原因是探讨学术问题。在跨单位合作中,师师合作是最常见的合作方式。因为跨单位的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见面的机会要少一些,交流学术问题的可能性就更低一些,而跨单位的老师之间见面,有可能是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讨论,而不是被动地见面,因此合作比重反而比经常见面的同单位老师们要大。因此,科研合作源于“当面交流”,科研人员经常面对面地讨论学术问题,才是科研合作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少见面或者见面不交流,是很难有合作产生的。
在统计中还发现,不少跨单位合作论文实际上应该归属于同单位合作论文。例如,2010年12月刊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阳和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王路昊的论文,第二作者论文在投稿时是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对跨单位论文作者信息进行详细审查之后,笔者将表2的统计数据进行修正,得到表3。可以看出,同机构合著论文增加了11篇,比重达到83.90%。而师生合作的比重也变得更加显著,达到了76.27%。
2 学术论文合著者的后续合作情况
针对每一篇两人合著论文,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这两位作者共同署名的论文,时间截止到2017年底。下面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术合作方式逐一分析。
2.1 师生合作的后续情况
从表3可以看到,在90篇师生合著论文中,同单位的导师与博士生合作论文篇数为61篇,与硕士生合作论文篇数为25篇,跨单位师生合作论文篇数仅有4篇。
(1)同单位的导师与博士生的合作情况
在同单位的导师与博士生合作的61篇论文中,有13篇论文的博士生作者,在中国知网上查询不到后续发表论文的任何记录。也就是说,大约五分之一能够发表高水平论文的博士生毕业之后不再发表学术论文。剩余48篇论文的作者后续合作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两位作者之后完全没有再合作发表过论文,计10篇。
第二种情况是博士期间或者博士刚毕业的时间内导师和学生共同发表了极少量的论文,通常为1到2篇,之后再没有合作过。这种类型的论文有29篇之多。这些论文基本上是博士生在读博期间与导师合作的结果,不能看作后续合作。要提及的是一个特例,即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贾卫峰与其导师党兴华在《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2017年第18期发表了一篇将导师列为第三作者的论文,是两位作者之后唯一共同署名的论文。
第三种情况是后续合作论文数量不少,但通常一篇论文都有3到4位作者。属于这样的论文有7篇,不过,论文的两位作者不再是这些新发表论文的第一和第二作者。有些论文是已经毕业的博士生与其他人合作时将导师作为第三或者第四作者,有些是导师指导的其他学生将以前毕业的学长作为第三或者第四作者,因此不能看作是以两位作者为主的持续性合作。
第四种情况是博士生和导师后续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他们也是论文的第一和第二作者。这样的持续性合作关系只有两对:一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修德和梁彤缨,第一作者博士毕业后去了广东工业大学,继续与导师合作发表了一些论文,一般是自己第一作者导师第二作者。而在导师与其他研究生合作的论文中,经常作为第三作者出现;二是湖南大学统计学院刘亦文和胡宗义,第一作者博士毕业后进入湖南商学院工作,其间在湖南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刘亦文在博士后工作期间与胡宗义合作的论文基本上是两位作者,但出站后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你一我三(互相)”的关系。
(2)同单位的导师与硕士生的合作情况
表3显示,同单位导师与硕士生合作的论文篇数为25篇。其中,22篇合著论文的硕士生毕业后不再发表论文,没有继续与导师合作的可能性①需要提及的有两点。一是华南理工大学的硕士生谢伟聪之后出现在一些论文的第三或第四作者,但从《系统工程学报》2014年第4期文后提供的作者简介来看,除了将谢伟聪的年龄弄错之外(把1983年写错为1984年),还将作者写成硕士生,实际上谢伟聪2011年已经毕业,可以认定论文并没有经过谢伟聪的认真审查;二是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硕士生高攀,他与导师在《科学学研究》2010年合作发表了两篇论文,之后在《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也发表过一篇论文,但论文的投稿日期是2010年1月,属于硕士生期间与导师的合作,之后再无论文发表。。因此,与博士生相比,能够发表高水平论文的硕士生离开学术圈的比例要大得多。剩余3篇论文中的硕士生继续读博,与博士生导师合作发表论文。需要提及的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陈颖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他的硕士生导师吴晓波。因此,陈颖只是在读博期间与导师合作又发表了一篇论文而已,不具备持续性。
(3)跨单位师生的合作情况
从表3可以看到,跨单位师生合作论文只有4篇。其中:两位学生作者王鋆、王路昊之后没有与导师合作过论文;姚小芹与合作者崔维军之后合作发表过一篇论文,但论文收稿日期在《科学学研究》杂志论文发表之前,不属于后续合作;只有华中科技大学的周莹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刘华继续合作发表论文。因此,在4对跨单位师生合作中,只找到一对持续性合作关系。在知网查阅博硕士论文发现,周莹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导师正好是刘华,因此属于师生合作的延续。
2.2 师师合作的后续情况
在表3中,师师合作论文数量有25篇,其中同单位论文12篇,跨单位论文13篇。
(1)同单位同事的合作情况
同单位师师合作的论文中,两位作者之前是师生关系的论文有4篇,剩余8篇属于纯粹的同事合作关系。4篇之前有师生关系的师师合作中,3篇论文的作者赵岑、王龙伟和印玺之后不再与导师合作②《科研管理》2012年第2期发表过赵岑第一作者导师第三作者的论文《基于与大企业联盟的技术创业企业成长机制》,但论文的收稿日期是2009年3月11日,不属于后续合作;同样,《科研管理》2011年第1期发表过王龙伟和李恒共同署名的论文《企业战略导向影响联盟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论文收稿日期是2009年3月12日,也不属于后续合作。;只有1篇论文的第二作者单子丹,经常与导师高长元合作,但所有的合作论文都是将导师作为第二作者。8篇纯粹的同单位师师同事,其后续合作呈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完全没有后续合作,或者偶尔合作过一两篇,不具备持续性;另一种是之后合作过多篇论文,这样的关系有两对:西安财经学院的胡健和焦兵以及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的仇怡和吴建军。
(2)跨单位同行的合作情况
跨单位师师合作的13篇论文中,两位作者之前是师生关系的论文有8篇,剩余5篇属于纯粹的同行合作关系。在8篇之前存在师生关系的论文中,两位作者的后续合作也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后续合作极少,要么没有合著论文发表,有也只有1到2篇,且时间跨度较长;另一种是博士刚毕业与导师合作少量论文,一般将导师列为第二作者,之后有了自己的合作伙伴,不再与导师合作。因此,跨单位师生合作不具备持续性。在5篇纯粹的跨单位师师合作论文中,有4篇论文的作者之后从来没有合作过,还有1篇论文作者是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吕一博和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康宇航,他们之后在《科研管理》杂志上面共同发表论文两篇,署名次序不变,投稿日期都在2010年9、10月份,因此他们的科研合作也没有持续性。
2.3 生生合作的后续情况
表3显示,生生合作论文数量仅有3篇,其中同单位生生合作论文1篇,跨单位生生合作论文2篇。在3篇合作论文中,只有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王栋和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生陈永广之后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作者有1篇论文发表在《研究与发展管理》杂志上,但投稿日期在2009年11月20日,不能算后续合作。由此可见,生生合作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合作关系,即便两位论文作者继续留在高校搞科研,后期基本上也不会再合作。或者说,学生毕业后会遇见新的导师、同事或者学生,会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基本上不再与旧的同窗进行学术合作。
2.4 学术合作的持续性情况
根据上面的分析结果,表4给出的是不同合作方式科研工作者的学术合作持续性情况。结果表明,在118篇两人合著论文的作者中,能够形成持续性合作关系的对数很少,只有6对,比例仅为5%。其中4对存在师生关系,而属于同单位师生合作延续的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梁彤缨和陈修德以及湖南大学统计学院胡宗义和刘亦文,属于同单位师师合作延续的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高长元和单子丹,属于跨单位师生合作延续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刘华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周莹。由于这些学生毕业后与导师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在同一个学院工作,能够经常和导师见面进行学术交流,因此之前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才可能得以持续。
从表4可以看出,剩下2对属于同事关系,分别是西安财经学院的胡健和焦兵、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的仇怡和吴建军。但是,他们的合著论文署名方式差别却很大。胡健和焦兵合作始于2007年,一直持续到2017年。胡健永远是第一作者,焦兵永远是第二作者,署名次序表面看是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排列,在中国看重“第一作者”的学术环境下,焦兵能够连续十余年担当胡健的“绿叶”,这种持续性合作原因也许要从其他方面考量。仇怡和吴建军的合作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5年,共计合作发表了22篇论文,只有3篇论文有硕士生参与其中。在他们两人合作的19篇论文中,吴建军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有9篇,仇怡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有10篇,论文署名看起来要更加合理。
3 结论与建议
笔者从科研合作持续性视角出发,以《科学学研究》杂志2010年发表的118篇两人合著论文作者为样本,对已经开展合作的科研工作者群体的合作持续性特征进行系统性分析,结果表明:只有6对科研工作者形成了持续时间较长的合作关系,其中4对属于师生关系,2对属于同事关系。这表明,即使科研工作者能够在高水平期刊上合作发表论文,显示出良好的合作效率,但这一群体的合作持续性程度也不容乐观。
师生型合作不容易持续主要是因为现有科研评价体系看重“第一作者”。我国科研院校一般实行“导师制”,一个学生主要由一位导师负责,而毕业通常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的论文可被计算在内,而导师可以依据这些论文获得一定的奖励或者达到一些招生资格、岗位聘任方面的要求,对学生和导师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但是,当学生工作之后,由于评职称或奖励都要求第一作者,合作就非常容易中断。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促进学术合作的有效持续,可逐步建立一个署名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学术惯例;另外一种做法是论文署名按照贡献大小确定,但在合著论文中要清楚标明各自的贡献率;还有一种做法是通过抛掷硬币来决定论文的署名顺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与同事特沃斯基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10]。对于最后一种做法,除了论文作者外,学术界的其他研究人员是不知道论文作者的排序是抛硬币决定的,他们可能会认为论文署名是按照贡献排序,特别是当论文署名不是按照字母排列更是如此。因此,有研究者建议用一个带圈的字母r(random的首字母)来表示论文署名是随机排序[11]。
同事之间的合作不容易持续主要是因为“晋升竞争”。同单位的科研人员往往面临职称、职位方面的激烈竞争,在学术研究上也经常有意识地选择“各自为战”,缺乏开展合作的动机,更谈不上建立有效的长期合作关系。而且,之前竞争过的同事,即使以后不存在竞争关系,也会心存芥蒂,不愿意开展合作。想要促进同事之间的长期合作,可以从职称评定制度上做一些改变。现在的做法是“晋升锦标赛”,即按照总人数设定一个比例,按照科研工作者的相对表现决定谁获得晋升,这无疑强化了同事之间的竞争关系,使持续性的合作不易达成。笔者认为,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可以采用“达标赛”来决定职称晋升,即职称评定部门设定一个晋升标准,只要科研工作者达到了要求,都可以晋升职称。为了控制晋升人数,这个标准可以定得相对高一些,只要达到标准就能获得晋升。但是,若科研工作者达不到晋升标准,就保留其原有职称位置。不过,这一点与国内外一些大学采用的“非升即走”的做法存在显著差异[12]。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师生还是同事之间的科研合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这些科研工作者研究方向相近或者学术思想相似,不易碰撞出新的火花,导致学术创新不足。因此,应该周期性地开展不同科研院所科研工作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创造一个让研究领域各不相同的科研工作者交流学习的环境,让科研工作者不但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能够倾听并吸收新的学术思想。这不仅能够提高科研院校的学术声誉,也有利于科研工作者开展持续性的学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