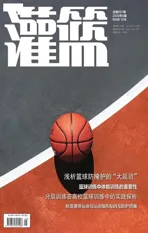竞技体育中过失伤害行为的刑法评价
2020-11-24翟子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翟子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竞技比赛中过失伤害犯罪认定
为了建立竞技比赛中过失行为“罪”与“非罪”的论证根据,笔者将竞技体育的伤害类型进行了归类划分。对于纯粹的体育竞技伤害,应当同正常的犯罪行为划开界限,这种伤害的认定应当依据体育法或是侵权责任法。而对于故意违反比赛竞技的规则进行故意伤害并导致伤亡的行为应当归类为“罪”与“非罪”的问题,依据刑法认定。在权衡责任的严重程度时,也应考虑事件发生的缘由性质,对于承担罪责所需的时限以及惩罚进行斟酌。
二、纯粹的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之非罪分析
(一)非罪化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
将竞技体育中纯粹的过失伤害行为进行非罪处理符合刑法谦抑性。尽管社会中的每一种犯罪行为以及罪责所发生的性质以及轻重程度都是伴随着社会群众的发展存在的,是由外界条件所触发的,但是在刑法谦抑性的内在要求中,制定法律的人首先就应该以最小的力度甚至是与刑罚无关的惩罚措施来进行有措施的预防犯罪以及抵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刑法是一把双刃剑,立法不合格不严谨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伤害[1]。
对于竞技运动而言,它有独立的鉴赏性以及相互对抗性,通过一种对于心底情绪的发泄让人们热爱生活中的美好。但是同时也因其自身竞技的危险性以及对抗的高强度性,在规范其罪责时首先应该从体育竞技比赛规则的角度出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不应动用刑法进行处罚[2]。利用刑法规范体育竞技中的过失伤害未免不近人情以及所带来的诸多不好的结果。对于比赛竞技过程中过失伤害的行为采用体育法或是竞技规则进行处理能够在不利用刑法的条件下,让过失伤害得到适当的解决。针对竞技体育这一行,笔者认为要明确刑法可以使用的条件,不能够一味地使用刑法,也要保证体育竞技行业中也是受刑法保护的。[3]因此,纯粹的过失行为妥善处理与刑法谦抑性相一致。
(二)非罪化有利于体育竞技业的发展
刑法过度干预体育竞技业对于体育竞技本身也并没有好处,不仅限制了这个行业本身的发展方向,缩短了范围,而且如果以刑法的名义进行对纯粹过失伤害的罪责规范,那么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也只是一种伤害,原因在于,运动员可能因恐惧承担竞技风险而发挥不出其真正的实力,进而影响体育赛事的正常开展和体育精神的传播。
(三)非罪化是充分考量阻却事由的结果
将竞技体育中的过失伤害进行非罪化处理也能够符合竞技体育中当事人责任能力减弱的性质。在我国的有关刑法的传统观念规范中,“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刑法上的辩控能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4]对于辨认能力的定义,也就是行为事件发生的主动方对于自己产生行为的性质以及后果有一个宏观上的理解,这种理解规范为认知能力;而对于控制能力,就是说人在理性思想下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防止更加糟糕情况发生,当然,最好的状态就是尽量不动作;责任减弱的概念是,当活跃的一方处于激动情绪时,无法正确控制自己的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从而导致相对严重的后果。虽然可以理解这种状态,但是仍不能有效地控制它。这样运动员将承担更多或更少的责任能力减弱的状况。以篮球为例,比赛中运动员移动的总距离约为5-10公里,其中约20%需要每个篮球运动员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准确计算能耗:在高水平篮球比赛中,篮球运动员的血乳酸含量可以达到7-9mmol/L,平均有氧代谢能力是最大耗氧量的70%,ATP-CP和糖效供应账户对于总能量供应的约85%,有氧代谢和糖效供应占总能量供应的15%,并且还消耗大量谷氨酸和Y-氨基丁酸以维持神经中枢。该系统的能量消耗引起的兴奋和抗疲劳。结果是身体中的血液乳酸增加,并且血液乳酸的积累增加了乳酸性酸中毒的后果,例如视力模糊,昏迷,休克和其他症状,意志无法有效控制你的身体,而且竞技体育的风险很高,很容易造成疏忽[5]。
根据以上论述,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运动员会因为生理指标的变化而出现辨认、控制能力异常的情况,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两种能力均丧失。并且就算是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能够在主观上要求自己保持理智,但是在中期或者是后期体能的大量消耗下想要保持正常的身体支配运动也是十分困难的,从而也就伴随着控制能力以及辨认能力与主观意识的分离。我们应当首先从生理学的原理上对运动员进行身体检查,其次将检查结果上交到相应犯罪研究机构中。虽然单纯地比赛过失伤害已经具有违法性,但是也存在着责任争议,在实践中,也许某一项事实,就能够防止犯罪的成立。尽管观念不一致,但是笔者仍然认为“要承担责任,首先得有责任”。假若不满足这种责任的成立,属于犯罪构成的阻却事由之一,那么也就无法构成犯罪。
三、竞技过失伤害行为之入罪分析
(一)竞技体育过失伤害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在比赛过程中,成立故意过失伤害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致使过失行为发生的主动方故意违反比赛规章制度,有违反竞赛规定的事实,也就是出现了伤害的动作,这种行为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其他已经引起了违反社会危害的后果,因而具有刑法谴责性。虽然主动方一直认为这种过失伤害的行为是可以避免的,在主观上否认其造成侵害结果,但是其负有保护运动员双方的注意义务,而上述过失伤害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这种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属于竞技体育规则的一部分,基于竞技规则而存在,所以所有违反比赛规章制度的规则都必须是行为成立的,是不被允许的,更别说故意违反比赛规则的了。同时参加比赛的其他运动员也应该具有专业素质,了解竞技规则,在相应竞技规则的技术性规范下开展体育竞技,以最大程度履行比赛中保护运动员的义务。体育比赛本身的性质导致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失伤害具有很高的概率。因此,有必要制定比赛规则在比赛过程中限制运动员的行为。因此,意外伤害在竞技体育领域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满足客观要求。
(二)竞技过失伤害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在竞赛过失伤害行为中存在故意行为的,行为人无法依据上文所提到的责任能力减弱的理论进行抗辩。该理论的含义为,行为者对行为的认知程度以及掌控力度程度降低。上文已经提到,由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运动员在竞技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体能消耗过多的情况,其相应的控制能力等,都会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就极容易造成过失伤害。可若是竞技人员出于自身的意愿主动不遵守竞技规则,责任能力减弱理论将不会在对其有任何适用性。因为当竞技人员选择主动不遵守竞技规则时,该行为是可以被自己所掌控的,该行为的错误性也是可以被清晰辨认的。这种情况下,行为发生人可以清晰的辨认出自己的行为,同时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较好的控制力,因此我们不会判定其处于责任能力减弱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符合入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三)竞赛过失伤害行为违背竞技体育理念
故意的竞赛过失伤害行为同我们发明竞技体育的初始目的相距甚远。竞技体育最基本的性质应该是公平性。我们在发扬竞技体育精神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将竞技体育的道德规范一同发扬,使遵守比赛规则成为人们的共识,尊重对手是竞技运动员的基本素质,坚决制止欺骗或野蛮行为的发生[6]。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出于自主意愿不遵守竞技体育规则的行为,同竞技体育真正的核心价值相距甚远。此类行为在球类运动中较为多发。球类运动员常常因为替团队争取更多的时间,或者想方设法的对对方的优秀运动员造成干扰,而违反竞赛规则。这种行为曾经被很多球队所采用,并美其名曰比赛策略。实际上这种行为是为真正的体育运动员所不齿的,因为其不仅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不符合体育道德准则,还使整场比赛都失去了意义。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人们都将竞技体育中的伤害同一般的伤害分隔开来,强调竞赛体育的特殊性。可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竞赛体育的特殊性被过分夸大,造成故意伤害行为,被长期纵容,使人们对竞赛体育的追求逐渐与其建立之初的最终目的相违背。过失伤害与故意对人造成伤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因此笔者提倡,将过失伤害与普通伤害分隔开来,故意伤害按照我国法律标准进行处罚,但若是过失伤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应给予相应的处罚。由于上述类别的分类,故意违规引起的过失伤害行为,造成运动员的伤害也不同,对于无意伤害运动员的行为,可给予一定的包容。对于对运动员充满恶意,会造成他人受伤的行为,按照我国法律标准给予其应有的惩罚。
在竞技体育比赛中,由于运动员的违规行为造成的过失伤害的情况占绝大多数竞技体育中的伤害。竞技运动员基于过失心态犯规造成他人重伤的情况可以适用过失致人重伤罪进行刑法处理。在主观过失方面的认定上,判断伤害一方对伤害结果是否是过失心理主要是通过对该运动员是否有意违反规则的考察来实现[7]。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竞技体育是伤害事故的高发活动。且由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在该活动中发生的侵权事件普遍按照其内部的规则进行处理,抑或者根据体育协会的相关制度给予过失人员相应的处罚。不过出现情节行为较为恶劣的过失事故,则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进行制裁。
虽然竞技体育中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存在着一部分可以避免的风险。文中将此类风险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以刑法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建立起避免伤害的意识,尽可能的减少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