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铠甲的形制与复原研究
2020-10-26温陈华冯子建周佳伟炼铠寺文化浙江海宁314400
|温陈华 冯子建 周佳伟|炼铠寺文化,浙江 海宁 314400
自中国古代文明诞生起,战争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作为冷兵器军事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铠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独有的形制和风格。
我国古代铠甲,保存下来的实物极少,有关文献也不多,且比较零散。近些年来,随着文物考古的挖掘和整理,获取了相当数量的信息,相应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古代铠甲的复原与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具备时代特点的中国铠甲研究也走向更深层次、更新的领域。[1-6]
一、 中国古代铠甲形制的演绎
根据《周礼·春官·司服》记载,西周已出现“兵事之服”,也称为“练甲”。春秋战国时期除大量使用皮甲胄外,也使用青铜铠甲;汉代开始出现锻铁铠甲,不同官阶装备不同形制的铠甲;魏晋南北朝时期铠甲得到进一步发展,有代表性的有两当铠,并配有兜鍪、胄、盔等;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据《唐六典》记载,唐代铠甲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锤、白布、皀娟、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等十三种,其中明光、光要、锁子、山文、乌锤、细鳞是铁甲,其他则以制造材料命名;元代有柳时甲,铁罗圈甲等;明代甲胄大多为钢铁制造,技术先进,种类繁多,如罗圈铠、罩甲、锁子甲等。总而言之,中国铁质甲胄基本演绎为:秦汉——铁扎甲,魏晋——筩袖铠,南北朝——两当铠,隋唐——明光铠,宋代——步人甲,明朝、清朝——布面甲、棉甲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改变,铠甲的形制也在不断地变化。
二、 中国古代铠甲的功能分析
说铠甲就必须要说到古代战争,讲古代战争又绝对离不开铠甲。有人说现代战争铠甲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已经是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战争中总要有进攻的一方和防守的一方,进攻的一方想要消灭自己的对手,防守的一方则一定是要抵挡住对方的进攻或者伺机消灭对手。在战争中最大程度地消灭对手,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是亘古不变的准则。今天大到某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小到保安身上穿的防弹衣,原理跟铠甲一样,都是要最大程度保存自己。铠甲是人类早期保护自身肉体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从最早的兽皮甲壳到后来的用金属以及其他适用的材料制造的铠甲(如古代中国的皮夹纻、纸夹纻,古希腊的亚麻甲,古代中东地区的棉甲等),铠甲伴随着人类走过了整个文明的绝大部分时光,仿佛铠甲是脱离所有护具本身,单独被赋予了时代和精神的一种工具,乃至今天我们在雕塑绘画文艺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铠甲的身影。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现象呢?这个答案只能是实用性,任何人类制作的工具只有实用才能普及或者被大批量制造,只有这些工具最终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最后才能被发扬光大。
中国关于盔甲的最早记载是炎黄和蚩尤的战争。据称蚩尤有81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暗示他们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制作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后来到了商周时期皮质和金属制铠甲开始逐渐普及,到了战国和秦汉铁制盔甲也开始陆续出现,均有出土文物证明。然而自西汉周亚夫案后,对铠甲陪葬的限制越发严格,至后世唐时已有律条管控,于是这一时期只有周边地区及少数民族中有铠甲实物留存。
据唐律:“诸私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故唐律疏议·擅兴》曰:“‘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若有矛、矟者,各徒一年半。”唐律又规定“弩一张,加二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领及弩五张,绞。私造者,各加一等”(下注:“甲谓皮、铁等,具装与甲同即得阑遗,过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造未成者,减二等。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余非全成者,勿论”。还有打完仗不归还的“征戎事讫,停留不输者”也要受罚。
铠甲在战场上能为装备铠甲一方带来巨大的收益,装备铠甲更多更精良的一方总是能主宰战场。在远东,汉朝的军队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除了具备强大的国力以及文明带来的组织力、战略、战术等最直接的优势外,就是汉军装备有铁甲。匈奴人骨制或青铜制的箭头根本无法对汉军的铁甲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所以后面就有了“胡骑五不敌汉军一”的说法。虎牢关之战,李世民更是带3 500名骑兵,其中有1 000名装骑兵进行多次冲击,击穿了窦建德10万大军的军阵,最终击溃窦建德,大杀四方。如在西方,亚历山大帝国也是靠着自己的冲击部队击溃敌人,后来十字军东征中的阿斯卡隆战役,十字军以1 200名重装骑士为主力击溃了五倍于己的法蒂玛王朝大军。历史凭借铠甲坚固和与之相辅相成的正确战法获得胜利的战役数不胜数,以至于铠甲被人们逐渐搬上了神坛。
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开始装饰铠甲,商周均有金属皮革铠甲出土,如出土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的商代兽面青铜胄,同时还发现了盔甲上用来装饰的兽骨玉石等,可见早在3 500年前甚至更早人们就已经开始对保护自己身体的盔甲进行装饰了。后来的朝代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装饰华丽甚至奇怪的盔甲,如我们熟知的东周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马甲,山东西汉齐王墓出土的金饰铁甲(图1),唐朝敦煌流传下来的各种各样身着华丽铠甲的武士像和以双林寺韦驮像为代表的身着铠甲的神仙塑像,以及各种水陆画中的武将形象,等等。看上去好像时间距离我们越是接近,盔甲就越华丽,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图1 山东省淄博市西汉齐王墓铁甲胄复原(图片来源:《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开头部分汉甲)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实物的消失,就有一些朋友开始产生怀疑,是否是一代代画工和工匠在臆造?怀疑这些盔甲的真实性后随之出现了仪仗甲一词,即是说那些雕塑绘画中形象华丽的盔甲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是作为仪仗而存在,这些形制的盔甲根本没有防御力,根本上不了战场。
就以上几个问题我们来作一些探讨:
(一) 中国铠甲的发展
中国铠甲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华丽又从华丽到相对简单的一个过程。要知道人类的进步并不是一条单线,而是一棵非常复杂的进化树。狩猎能力、畜牧业能力提高后才有足够的皮用来制作皮甲,有了漆才能做漆皮甲,有了铜、铁和相应的金属加工工艺才能拥有后来的金属铠甲。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战争的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化。从用木棒石斧,到各种切割或盾击的金属武器弓箭标枪等再到后来的火药武器,防具也从最早的兽皮甲骨到后来的青铜钢铁复合材料等,各种战法更是层出不穷。唐宋火药武器出现,到了明朝,面对火药武器的不断普及,中国的盔甲就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明朝早期与宋朝如出一辙的步人甲形制,骤然变为了明中晚期各种绘画中的布面甲(参考河南巩义宋陵石刻,四川明蜀世子墓武士石像(图2),广州南海神庙内明武士石像(图3),对比《出警入跸图》《平番得胜图》)。这显然是从华丽反转为简单,这种由华丽到简单是由战争形势决定的。其一,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巅峰,也是冷兵器时代的巅峰,当时的盔甲需要给武士们提供全方位乃至对不同武器的防护。例如大家争议非常大的肩吞,它的诞生的确不只是为了装饰,而是有其特别的功能,如可以起到保护胸部和手臂之间盔甲缝隙的作用。其二,唐宋时期非常流行非切割类武器,也就是鞭、锏、锤这样直接隔着金属铠甲就可以打碎人骨头的武器,而肩膀绝对又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这个时候肩吞表面并不平整的形状最大的可能是减缓打击力的传达(雕塑壁画中的肩吞、腹吞多为彩色,出土的唐宋甲又出现了除金属甲甲片外,残留的、不知具体成分的、黏在一起的混合物,结合流传至今的传统夹铸面具等工艺品的制作技术,作者怀疑肩吞、腹吞是由皮、布、纸做的夹铸彩绘品)。它的原理就像今天汽车上的保险杠一样,通过自身的变形和空腔来最大限度地吸收传达过来的力。还有那些华丽和夸张的包边(从壁画和雕塑上能看出有些是布的,有些是皮毛),它们在不同部位的连接处形成一道道像烟雾弹一样的视觉干扰物,挡住了铠甲的连接处,以混淆对方对进攻位置的判断。

图2 四川成都明蜀世子墓武士石像(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宋甲参考)

图3 广州南海神庙内明武士石像(图片来源:《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 明朝铠甲参考)
明朝中后期的盔甲几乎全是布上打着铆钉的“衣服”, 这就是因战争方式的改变而带来的改变。随着火药武器的普及,武士们越来越不需要近身肉搏了,原来只能通过钝器、锥类武器才能对当时的重型盔甲造成伤害,现在只需要用火药武器在近战距离外就能完成。沉重的华丽盔甲逐渐成为了武士们的负担,慢慢退出了战场,而复合材料的甲胄虽然对火药武器以及其他武器仅有着有限防护的功能,但是大大加强了机动性且降低了价格,更适宜大规模装备部队,让整支部队披甲率更高。所以,布面甲主宰了明中后直至铠甲退出近代战场。虽然对华丽的甲身作了削减,但是戴在头顶的头盔,反而被做得更加华丽,或者说是更高。这也是当时的作战方式造成的,当时的火药武器(黑火药)发射或者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烟雾,而且精度极差,这就需要在烟幕漫天的情况下辨别出敌我,这个时候高高的头盔就显得有意义了。同时期西亚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亲兵们手持火器时戴着造型更夸张的帽子,同样都是在烟雾弥漫中告诉队友“我在这里,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告诉指挥官“我们在这里战线没有问题”。显然这个时候的华丽造型的实用性目的性已经不再相同。外表的“华丽”其实都有其实用性,这个实用性并不止防护力,更有加工上的可操作性,以至于有一些我们看上去比较花哨,可能会被误解成装饰的东西,实际上是为了方便加工才成为我们看到时的那个样子。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瓶子形状或者云头以及乌骓状的扎甲甲片,这种类型的甲片在很多的壁画和雕塑中都有出现,它们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就是在方形金属末端都有一块类圆的延伸体。作者在参与铠甲复原以及甲胄抗击打测试时发现这种末端多出的一块甲片冷锻或者热锻时方便用钳子夹住,在上漆的时候也可以用两根木棒一次性夹住很多这种甲片以实现大批量快速着漆。在抗击打测试中,这种甲片的绳子也更不容易断裂,因为翘起来的原型部分刚好会挡住最容易被砍断的上下排甲片的连接绳子。在复原铠甲和测试铠甲的实验中,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神像和壁画铠甲上原来我们以为只是装饰的其实并非装饰品。2018年作者温陈华先生和冯子建先生带着一些盔甲参加一个展示会的时候,因为路远难走,车又不能通过,就用绳子把盔甲像包大闸蟹一样扎了起来,后来联想到这些临时用来扎盔甲的带子跟古代塑像和壁画中武士身上缠绕的带子有相似之处,如双林寺的韦陀、山西惠济寺宋代雕塑等。可以设想古代武将身上的这些飘带不就是古代武士们用来打包铠甲的工具么?甚至可以作为攀爬或者捆绑俘虏的绳子?就是这些看似装饰的实用品不就集合成了我们看到的华丽的铠甲实体吗?这些部件的实用性给了我们视觉上的极大震撼,可以想象,能够制造和装备这些华丽复杂装备的武士自然也是十分强大的,在作战时一开始就给对手深刻印象,知道碰上了狠角色,从而起到另一个作用——震慑!
(二) 震慑作用
阅兵无疑是所有大国秀肌肉、秀力量的方式,各国把最先进最强大的武装拿出来走秀,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别惹我,你惹不起!古代阅兵,必然是让部队里最精壮的汉子穿上最炫耀最坚固的盔甲, 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以震慑前来观摩的邻国、各种使臣和内部的藩镇。从宋朝的《大驾卤簿图》[图4(a)]和明朝的《出警入跸图》以及清乾隆众多的阅兵图上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端倪。 例如宋的《大驾卤簿图》[本文作者冯子健有幸参考复画过几个人物如图4(b)所示]中旗帜不下几十面,这些旗帜有些是代表部队番号,有些则是用于指挥,指挥官的命令就是通过这些旗帜以及金鼓声层层传达给每一个士兵的。古人曰:“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画中的具装骑兵并没有像我们以往在汉砖唐俑中看到的那样持实用近战武器,如矛、戟、槊等,而是扛着硕大的神臂弩,据《武经总要》记载这种弩的射程可以达到二三百米。[7]《大驾卤簿图》中的骑兵人马具甲,马甲的头部有青色兽头的马面甲,青色兽头除了给马面甲提供额外的防御功能外,还能震慑恐吓敌军的战马和士兵(城濮之战中晋军就是以马蒙虎皮,吓得楚军战马狂奔,阵容大乱)。画中马的装具为炫目的红色,人也是全副铠甲,只有头戴着冠,相当于今天的礼帽

(a) 原图(局部)

(b) 冯子建复原临摹
(作战时是要换成盔的),加上白色的绒毛包面看上去华丽无比。而当时的具装骑兵就相当于二战时期的重型坦克,是无敌一般的存在。在这里装饰华丽的铠甲的作用是要让敌人发现自己,并且通过震慑的方式避免直接的冲突。把这么多的具装骑兵等武装力量集中在一起,检阅的同时也是在炫耀国力的强大 ,从而从更高层面上达到避战、免战,最终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技术的进步,有些装备不断改造和升级,以适应不同形态的战争所承载的作用。一些装备从最早的只具有实际防御作用逐步变为具有实际防御作用和文化象征双重意义的部件。
(三) 文化和传承
古代铠甲的文化传承首先还是离不开战争, 远古时代的猎人们就会把他们战利品的头骨、皮毛等作为装饰挂在身上,以彰显自己的勇武和力量,震慑对手或者迷惑猎物(如15、16世纪欧洲殖民者初到美洲时,印加帝国和阿兹克特帝国最英勇的武士会把美洲虎的头一整个地套在自己的头上,或者是用羽毛、金属等把自己打扮得像雄鹰一样,以彰显自己的勇猛,激励战友震慑对手。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也有相似的情况,武士直接把狼或者狮子的头戴在头上作为装饰,如亚历山大直接在其所造的钱币和雕刻中,将自己彻底打扮成头戴狮皮帽的赫拉克勒斯经典形象)。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唐代画家画的《八公图》中长孙嵩那套盔甲的头盔,能看出是在金属头盔上加了一个青面赤发张着獠牙的狮头,除此之外,此甲其他部位更有多达七个兽首形象。山西双林寺韦陀的头盔也是一个兽头装的盔体,另外的例子还有收藏于河北内丘县邢窑博物馆的唐朝武士俑等众多的虎头盔帽俑。直到十九世纪,和英军作战的清军还拥有大量把自己打扮成老虎形象的精锐虎衣藤牌兵,虽然火器已经普及,传统盔甲已经基本退出战争,但是作为精神象征和为震慑的目的这种装饰还是保留了下来。
在战争中把铠甲装饰得非常华丽乃至夸张的国家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邻国日本。日本从东汉开始向中国称臣,学习中国先进的技术,以至于从石木时代跃过青铜时代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而他们的盔甲也从龟壳兽皮切换到铁甲。大家可以从日本现存的文物中看到日本早期的铁甲跟朝鲜半岛的铁甲外形非常相似,铠甲表面只有少量花纹。但是在和唐朝白村江一战之后至室町幕府时代乃至更往后的战国时代,日本的铠甲明显发生了巨变。平安时代的大铠很明显是受到了唐宋时期兽首盔的影响,与四川泸县宋墓出土石碑中的一尊不全的武士雕像十分相似(图5),作者有幸写生过那尊雕像和画过复原设想图(图6)。后来的日本随着自身文化的发展又衍生出了其他样式的装饰,比如真田家的武士会把家徽六个铜钱作为抹额(日本叫前立)装饰在头盔上。根据古代传说,人死以后要过奈何桥,守桥的鬼差会索取六个铜钱的过桥费,真田家的武士们随身携带这六个铜钱的意思就是时刻作好了赴死的准备,从而彰显他们家族不畏生死的气概,既震慑敌人也鼓舞自己的士气。同理,盔甲上的其他华丽装饰也绝对不只是为了好看,都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切合实际的作用。那么有人会说了, 头顶个兽头或者装饰六个铜钱什么的能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呢 ?它们真的可以提高防护力么?答案是可以的。古代的头盔并不像我们现代的军盔一样做得比较大,内部悬挂、头部隔开以避免钝器伤害;古代的头盔无论是出土的中国盔还是传世的日本盔,作者有幸见到的都比较小,那么面对对方除切割伤害以外的盾击怎么防御呢?就上述长孙嵩的头盔而言显然是和上文中所描述的夹铸肩吞同理,硕大的兽首和盔体之间必然有空腔,以达到缓冲和抵消伤害的目的。我们可以把抹额想象成立面支撑体,它会以横截面的形式用它的高度挡住攻击者的武器,就好像你要把一面墙从上到下劈开后才能接触地面一样。抹额保护了正上方,侧面我们就不得不提另一项中国铠甲特有的造型了:那就是凤翅。凤翅像鸟的翅膀一样侧面张开, 在侧面对头盔形成像抹额那样的保护。关于凤翅的来源以及作用有很多的说法,在这里我们不一一阐述。这些看似装饰的配件还祈祷或象征着对武士身体、勇气和灵魂的保护。而凤翅肩吞这种形式则成了中华民族盔甲的典型特征,或者说是唐、宋、明时期盔甲的典型特征(图7)。

图5 四川泸县宋墓锁子甲持弓武士(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藏)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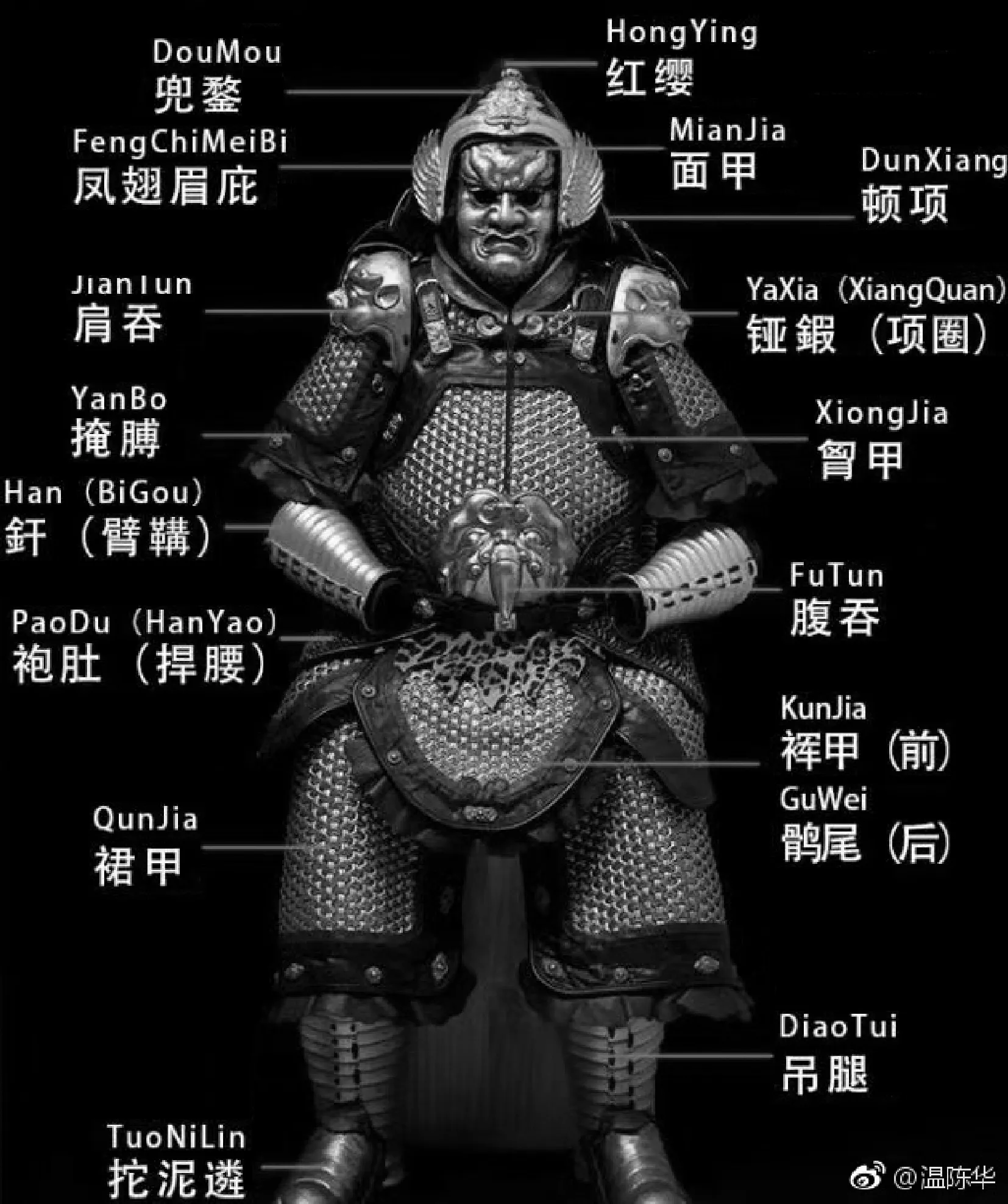
图7 “炼铠寺”出品宋式大全装黄金锁子吞头凤翅将校铠
(四) 雕塑和绘画
在许许多多的绘画和雕刻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带有这些典型特征的铠甲。因为出土的盔甲只剩金属残片,其他复合材料都已经朽坏,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铠甲必须从古代雕塑和绘画入手。
首先要说的是古代的工匠并非今天大家理解的艺术家,他们没有自由发挥创作的能力,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个才华和技巧,而是说他们都是被当时的统治者或者权贵雇佣来为自己服务的,用来记录这些统治者或权贵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功绩。而且当时无论绘画还是雕塑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先不讲绘画所需要的颜料和工具的费用(如古代绘画中含各种宝石粉末或贵重金属粉末的天价颜料),一个人脱离生产长期专注创作的开支十分巨大,一般人无法承受。还有就是在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诞生前,画家和雕塑家都是画自己实践过和看到过的东西,就像大学时教我们画画的老师会不停地跟我们讲画画要有生活一样,有生活感受才能画得好。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毕加索、达利等画得那么扭曲但却是艺术大师的缘故。令人敬佩的是,他们画的东西他们自己都没见过。哪怕像莫奈那样的印象派画家,画画也只是画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例如睡莲系列,那几十幅不同时间、不同光线下的睡莲,给人以深刻的艺术享受。中国古代的绘画也一样,那些工匠并不是画写意山水的士大夫,水陆画、寺庙神像壁画和雕塑作品极少署名,而士大夫的写意绘画皆有署名,甚至有收藏者的姓名花押等。还有就是,一些跨地区的同期作品极其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山西惠济寺宋代木雕武士,四川泸县宋墓石刻武士,河北王处直墓中的武士像,宋燕子窝神道石刻武士 ,宁波南宋石刻公园、 广州南海神庙内明石刻武士,重庆大足石刻三皇洞南宋天王像,安岳塔子山毗卢洞宋代石刻武士,等等,虽地分南北,相隔千里,同时期的雕塑作品却形制相同、造型相近。那个时代并没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这样全国性的美院去统一教授大家雕塑的技法和雕塑的主题,例如长江上游的重庆大足石刻和大陆最东端的宁波南宋石刻公园中宋代石刻的铠甲形象就极度相似,而它们相隔了大半个中国。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大量实例证明,所塑造的形象并非出自工匠或者画工的臆造,作品中形象相似的前提必然是他们见过这些武士身着的盔甲。这里还有必要阐述一下中国传统的绘画和雕塑中的写实问题。大家看到西方从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塑绘画直到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的艺术,一直都是在走一点透视的写实主义道路,大家可以记住关键词:一点透视。直到毕加索创造了立体主义,其实也并没有完全改变一点透视这个看画和雕塑的角度问题,你看画用什么角度就决定了你绘画雕塑的时候去塑造什么样的造型。中国的绘画和雕塑从写实到抽象这个过程显然要比西方走得快得多,在西方还在发动十字军东征画呆板木讷的宗教画的时候,在东方的我们就已经开始既有写实的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嵩的《花篮图》,又有浪漫主义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还有带着后现代感的《泼墨仙人图》,等等。那么,为什么后来我们就没有西方画得“像”了呢?其实并没有不像,比写实我们一点也不弱,我们看一看李嵩的《花篮图》和五百年后卡拉瓦乔的《水果篮》,简直太像了。还有晋祠圣母殿、保国寺大殿等的宋代泥塑写实手法简直超凡入圣。但是不得不提的还是透视的问题,中国乃至受中国影响的整个远东地区都是采用散点透视法。散点透视属多点透视法,即不同物体有不同的消失点,这种透视法在中国画中比较常见。传统的中国画讲究散点透视法。散点透视法不拘泥于一个视点,它是多视点的,在表现景物时,它可以将焦点透视表现的近大远小的景物,用多视点处理成平列的、同等大小的景物。散点透视法可以比较充分地表现空间跨度和比较大的景物的方方面面,这是传统中国画一个很大的优点。如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的《出警入跸图》等。
因为许多人对绘画和雕塑不了解,所以造成了很多人看不懂、搞不清古代绘画和雕塑所塑造的实物应该是什么样子。即便是系统学习过绘画和雕塑的甲胄复原工作者,在工作和交流中也经常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大众往往需要的是一个具体的一点透视的照片或者一点透视的写实素描,但是当你拿出这些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古代应该拥有的东西,久而久之中国古代的甲胄就被称作仪仗甲,实际上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五) 美学与战争
首先,形象的塑造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文化理念的问题,无论是古代铠甲还是现代武器,越好看的其实越有价值。其发展就像现代的战斗机一样,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最佳气动外形的过程,在不断减少空气阻力的过程当中,飞机逐渐进化出了优美的线条。其次,高颜值是制造工艺的体现,如果说战机的外形是一个人的“身材”与“外貌”,那么战机的蒙皮就是这个人的“皮肤”。良好的“蒙皮”制造工艺不仅会让整架飞机看上去光滑流畅,更显示着这架飞机诞生背后优良的生产工艺与制造水平。古代也是一样,越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外部轮廓就越是好看;越是强壮健康的士兵就越显得匀称;越是美丽的色彩和质感,就越能让人产生好的或者是美的情绪,更能激励人心。就像大家都喜欢的老虎、骏马、雄鹿一样,在动物界中只有拥有足够资源和能量的动物才有资格进化出那些“没有用”的装饰物。然而,老虎美丽的花纹其实是保护色,骏马强壮身躯的流线线条是为了使它具有超凡的速度而不会被其他捕食者捕捉,雄鹿巨大的角则象征着自身的地位,也是和其他雄鹿争夺交配权时的武器,这些所谓的“好看”无不说明极度的实用就是极度的美丽。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古代战争和制作仿古甲胄,可以深切感受到铠甲装饰中文化的传承体现在雕塑和绘画的各个方面。关于中国古代绘画、雕塑中那些装饰华丽的所谓“仪仗甲”究竟能不能打的问题,结论是所谓“仪仗甲”不仅能打,而且绝对是作为军中尖刀一样的存在。
三、 中国古代铠甲的设计、复制与实践
中国古代铠甲有数千年的历史,历经朝代变更而得以存续,为历朝历代所认可,绝非偶然。然而,一方面是内涵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留存的资讯和实物又十分短缺。作者及“炼铠寺”设计与研发团队一起,对中国古代铠甲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在探索和复制的道路上,在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后,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
对中国古代铠甲进行仿古复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严谨科学起见,我们采取了软件工程的方法。
(一) 路径
(1) 深入细致地研究现有的文献资料;
(2) 到古战场实地观摩,结合不同历史年代,对南、北铠甲的差异性进行比对,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3) 赴全国各地相关名胜古迹进行考察,对有铠甲符号的石雕、石刻、泥塑、彩塑、碑文等进行认真的研究学习;
(4)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出土文物进行认真的学习领会和探究,对文物的形态、结构、材料、相关物等进行金相学(金属材料学)、材料学、结构学等多学科分析研究,并与专家、学者进行广泛交流合作,以求结果的最佳化;
(5) 对古代铠甲元素从艺术设计、美学、形态学等专业方面进行研判与攻关;
(6)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入物理实验和复原工作。
(二) 设计与实验
铠甲的设计建立在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涉及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物理学等学科;铠甲制作实验同样建立在多种工艺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涉及材料学、精密加工、特种工艺加工等集合技术门类,在此仅作个例阐述。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瓶子形状的甲片或者云头以及乌骓状的扎甲甲片,这类甲片在很多壁画和雕塑中都有出现,它们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就是在方形金属末端都有一块类圆的延伸体。当瞻仰这些中国著名古代雕塑时,不禁就会让人设想古代武将身上的这些飘带就是古代武士们用来打包铠甲的工具,甚至还有攀爬、捆绑的功用。就是这些看似装饰的实用品,带给了我们视觉上的震撼和复制思维上的启迪,而携有这些华丽复杂装备的武士在历史的当时应该是很强大的。
“炼铠寺”团队对中国古代铠甲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进行了大量的古代铠甲复制实验,取得了大量数据和实验成果,限于篇幅,以下择要介绍(图8~图12)。

图8 “炼铠寺”出品宋式飞彩锁子甲

图9 “炼铠寺”出品宋式黄金锁子甲

图10 “炼铠寺”铠甲剧照

图11 作者温陈华先生在复原唐代绢甲护臂

图12 全甲格斗运动员陆奇身着中国铠甲和日本队员比赛
四、 结语
伴随着历史的车轮,中国古代铠甲走过漫漫数千年风雨历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辉煌,也确立了中华铠甲在历史中的地位。缘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代铠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进了人类博物馆。然而,现代的铠甲仍以其他的形式在发展,铠甲的初始命题至今仍得以沿袭。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铠甲现存文献记录不多,文物稀缺,资料贫乏分散,这给复原工作造成诸多困难,加之铠甲复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炼铠寺”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研发、设计、实验工作;特别是在铠甲形象学、结构学、材料学、美学、精密加工等方面取得可喜成果,这为今后深入研究与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铠甲历经数千年的沧桑,经历若干朝代变更而得以存续,而且被历朝历代所认可,绝非偶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一种传承,它所积淀的智慧和文化十分厚重,内涵十分深邃,更是一种民族文化自觉。
时至今日,民族文化复兴已成为国家战略,对中国古代铠甲文化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取其优秀内涵进行传承和弘扬,显然是一种使命,也是非常难得的文化遗产课题集,拓展空间非常广泛,值得学界、专业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