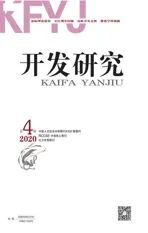“双评价”中主体功能分解与传导的理论机制
2020-10-19谭乃榕
马 涛,谭乃榕,王 昊
(哈尔滨工业大学 a.城市水资源和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b.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00)
提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为“三区三线”划定、空间规划制订与管控实施提供了基础支撑。主体功能区的基础性作用在“双评价”中的空间分解与传导过程尚不清晰。为适应国土空间开发中跨区域尺度、跨层级治理、跨时期统筹中的管控需求,探讨建立了主体功能空间分解与传导的理论机制。从降低不确定性和容纳复杂性两个维度,更新了主体功能在分区管控、底线管控、弹性管控、量化管控4个环节的实施原则。选取区县层级空间规划试点阿城区作为基于管控需求的“双评价”调整的应用案例。结合规划衔接、发展时序、动态反馈、空间承载等治理需求探讨“双评价”的应用。
我国空间规划以主体功能区制度作为战略引导的上位规划,国土空间开发中多重功能属性[1]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空间规划问题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这些在主体功能区由大尺度向小尺度至市县层面分解与传导中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明确指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方式只适用于全国和省域大空间尺度,在下层位需要根据评价单元情况做出差异化的具体功能规划。部分省(区、市)创新了规划实施的传导机制[2],《武汉市主体功能区实施计划》《清新县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方案》等细化至以街道(乡、镇)为基本单元,或是根据发展需求细化或新增主体功能类型[3]。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以下简称“双评价”)作为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既要有效衔接宏观目标并由上至下向市县尺度分解,也要有效反映基本单元的要素情况与发展需求。
主体功能的落实过程需要更加的精准化、差异化、弹性化,“双评价”未能提供充分合理的科学评价依据,来引导主体功能区划降尺度分解、传导与落实。“双评价”指标体系、方法与主体功能类型紧密关联,但是尚未存在统一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来应对不同类型地域功能。目前“双评价”在“三区三线”划定、统筹与落实上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参数支撑,通过格网单元对地方环境承载力和空间适宜性宏观态势有较为准确的判断[4]。科学推进“双评价”,准确刻画各类要素与主体功能,反映各空间尺度的开发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5-6],是落实空间规划效果、制定差异化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的关键[7]。
随着跨区域、跨层级、跨时期开发活动的增加,评价单元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双评价”需要在政策评估与协调治理方面加强反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双评价”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基于底线管控的关键与基础作用[4]。在浙江、广东等各省[8]、市[9]、县[10]的工作实践中尝试回答“双评价”在国土空间的“传导-划定-评价”环节的作用机制。2020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版)》正式发布,明确要求“下位评价应充分衔接上位评价或成果,并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有针对性地补充和深化评价”。“双评价”中各层级评价内容的衔接与协调反馈机制的尚未完善也制约了空间管控与治理的效果。
一、“双评价”分解、传导与国土空间管控
新时期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强调充分认识、精准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土开发适宜性,“双评价”如何调整以辅助主体功能制度有效分解、传导、落实,为国土空间管控与治理提供系统性、科学性的评价支撑(见图1)。

图1 基于“双评价”的空间规划框架
(一)分区管控
衔接宏观战略需求。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分别对应了我国经济与人口集聚、粮食供给、生态功能供给等功能承载。三大空间布局与结构的基本要求是有助于发挥地域功能,促进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保障“粮食安全”目标与农产品主产区的规划制定,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粮食安全为红线设定我国整体的粮食总量目标,并以各地区农业功能优势差异化降尺度分解为地区目标。而空间整体性要求空间单元应与空间战略格局、空间结构优化相衔接,中心城市、城市群的点空间应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重点开发轴相协调,生态空间布局应与重点生态廊道网络[11]、黄河[12]等流域保护相协调等。
精准化差异化分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判断空间开发方式的刚性约束,可能不利于存量增长、增量增长差异化发展模式下资源的合理配置[13]。本地化、特色化的评价因子选择及分级阈值的确定才能更好地表征评价区域的资源环境禀赋特征[14]。如面临水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又亟待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西北地区,除了水资源总量评价还须研判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及问题,利用农业灌溉和城镇产业、居民用水需求共同解析水资源的约束作用[15]。
增加主体功能细化的辅助指标。细化生态脆弱/敏感区、能源资源地区等特殊地的划分亚类,海岸线、浅山区等特殊区域的空间管制措施,编制针对性的制度和政策。发展时序可能造成分区的变更,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准入条件、退出机制、空间转换规则等[16]。北京市分区规划在编制思路上加强了《北京市总体规划2016—2035》刚性约束的有效传导,进一步厘清了时空关系、市区规划事权。
增加陆海统筹评价。考虑到我国经济优势地区同时又是与海洋资源环境临近地区,优势地区的高质量增长需要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适应,侧重管理目标与阈值的联系[17]。但是海洋空间规划工具和土地规划工具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临海地方政府之间也缺乏有效协调[18]。因此有必要将对海域的单项评价拓展为海陆统筹评价,避免不同主体功能在海洋空间的冲突[19]。同时为海洋生态补偿提供依据,如海洋生态补偿涉及了行政边界跨越了功能边界,而流域生态补偿是功能边界跨了行政边界;沿海地区的财政转移六省一市同时作为海洋生态补偿的支付方、受偿方时生态补偿应当如何划定等问题。
(二)底线管控
空间比例与“三线”划定。城镇、农业、生态三类功能空间比例反映了“双评价”评价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根据三大空间结构所产生空间效益差异评价规划成果,由此探索可持续发展战略下最优的空间组织方案。但应用于强调底线管控实施性、用途管制落地性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中时,往往出现农业生产适宜与城镇建设适宜用地在地势平坦、灾害风险低、水资源丰富的土地上重叠的结果,难以支持市县国土空间规划落实。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根据承载力状态的变化诊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限制性和约束性政策(见图2)。因此,“双评价”对于底线划定这类中短期甚至长期不变更的红线规划决策需要更精细化与差异化,将发展方式及技术进步决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趋势变化及时反映在评价结果之中,如生态修复干预程度应取决于生态系统退化和恢复水平,才能保证规划的连续性和实施效果。

图2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精细化需求
辅助区际生态补偿的边界。我国国土空间中划定的生态脆弱地区往往重叠着亟待发展的贫困地区。对于牺牲部分发展机会而又亟待发展的生态功能地区,“双评价”难以评价不同时空尺度上补偿主体和客体的作用边界、传导机制以及功能之间的替代关系、补偿关系。
(三)弹性管控
“双评价”需要有效评价-管控-未来开发的不确定性,利用趋势预判对中长期国土开发活动进行弹性管控(见图3)。经济、人口高度集聚城镇空间与适宜农业空间重叠,发展困难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重叠等问题,要求空间划定应当充分考虑中长期建设用地不断更新的需求,有利于生态与城镇、农业的动态更新与空间转化。

图3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与弹性管控
有效反映产业的空间布局。经济规模、人口总量在“双评价”的体现,反映城镇开发发展预测及更新需求;同时粮食主产区与生态功能区等功能划定对于产业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引性。加强生态系统单元与行政单元、经济单元的尺度融合,确定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主导产业和初步工业区布局方案。特别是涉及产业规划的重大问题,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产业发展时序及空间布局指引、存量产业土地利用及增量土地结构、新型基础设施等。
有效反映要素的空间布局。由于国土空间承载了多种由彼此相互作用及内在机理性联系构成的复杂要素系统[20],“双评价”须有效植入空间要素并反映要素效率,尤其是要素是否可替代,是否能够进行区际交换等,如区域间土地要素市场[21]、依托生态网络的空间要素配置[22]。面对存量工业用地转型困难与城市闲置用地现象并存,需要限定城市工业、居住用地、留白用地范围及规模[23],如《北京市战略留白用地管理办法》是区县尺度弹性应对长期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的重要实践,有效缓解当前用地需求增加而可用地量趋紧、低效用地挤占战略性功能性用地的问题,并通过用地置换优化集中布局。
(四)量化管控
主体功能降尺度开发过程中,需要“双评价”提供有效的量化手段。要适用于不同资源开发利用类型、不同空间尺度条件和不同功能复合叠加下的国土空间管控需求,尤其是特大城市要考虑内部和外部元素之间的交互强度,以及受主要内部和外部控制元素影响的巨型城市集聚系统中本地和远程耦合的机制模式[24]。主体功能定量研究能够为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制定和分解提供操作性强的技术方法,可将“双评价”体系结合生产、生活、生态主体功能定量刻画[25],辅助宏观尺度空间规划目标转化为经济、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匹配关系[26]。市、县单元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也要利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开发活动的耦合关系,量化统筹国土空间合理配置[27]。
二、基于管控需求的“双评价”调整:以阿城区为例
哈尔滨市阿城区在2014年《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被列为“多规合一”试点市县,是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区县级尺度的重要改革探索案例。阿城区是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中的重点开发区,试点工作将产业布局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建设规划、生态保护规划有机融合,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形成合理的城镇、农业和生态空间布局。探索完善市县空间对宏观目标传导、衔接、落实过程,是建立功能互补的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基础。选取阿城区的主体功能核算案例,进一步探讨市县层级的管控需求与“双评价”调整思路。
(一)分区管控与量化管控
从分区管控角度来看,阿城区是国家以及省域尺度的重点功能开发区,也是黑龙江省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区域。阿城区生态空间用地占比全区面积50%以上,农业空间用地占比全区用地40%左右,承担了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功能。阿城区功能空间划分(见表1)分为3个大类以及7个亚类空间,以其空间需求为导向划定了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以及生态保护红线三大红线。当前,生态-农业-城镇开发空间比例为53∶40∶7。

表1 阿城区三区三线概念界定
量化管控方面则根据发展适宜性评价结果和用地限制性分析结果划定三大空间,划分结果结合2014年数据对生态、生产、生活功能进行核算(见表2)。

表2 阿城区三大功能核算结果
1.借鉴谢高地等[28]的当量因子法,结合阿城区粳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近5年利润平均值测算生态功能价值。因阿城区空间规划试点工作以2015年数据为基础,生态功能核算所用数据选取的是2011—2015年《哈尔滨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利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将每年价格转化为2010年的不变价格,得到当量因子值为2 875.27元/hm2。阿城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0 427万元,其中以水文调节、气候调节为主的生态调节功能占比达到69.75%,功能价值为7 274.86万元,以及以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为主的生态支持功能占比21.61%,功能价值为2 253.04万元。阿城区42.90%的耕地与45.75%的林地作为主要生态系统类型提供了大部分的生态功能,分别为1 221.62万元、7 343.55万元。
2.生产功能以2014年阿城区地区生产总值与一、二、三产值数据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2014年阿城区生产功能总量为2 762 522万元,仅占全区6.01%的城镇空间承载了87.25%的生产功能。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2.78∶27.99∶59.24。其中,农业生产功能中耕地生产的比重为53.71%,有45.81%的农业功能由生态空间提供。由此体现了农业空间与生态空间在生产功能角度能够一定程度相互替代。
3.生活功能以地区人口总数进行表征。目前阿城区人口57.97%集中在中心城区,其余42.03%分散于玉泉镇、平山镇、蜚克图镇、料甸满族乡、杨树镇等城镇,而城镇化率为40.8%,还须进一步向中心城区聚集,加深城镇化程度。
(二)底线管控与弹性管控
面向国家-省市-城区的发展目标定位,阿城区侧重不同目标进行空间划分的调整。依据图4a、4b所示,“三线”划定是底线管控的基础,在底线刚性约束的情况下还存有部分弹性管控空间,即图中的留白区域可根据情景目标的设定调整空间功能,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阿城区三大空间的划分调整

图4 阿城区三区三线规划情况
情景1:加强生态保护,增加生态空间。阿城区以生态功能为主、同时兼顾产业发展与人口承载。在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约束下只有可能从城镇发展空间中挤占。目前城镇发展最大边界范围是基本农田保护区及生态红线基础上向外扩展0.5千米设定缓冲区;如果现状建成区与基本农田或生态区相邻或距离小于0.5千米,则城镇发展最大边界为现状建成区的界线。
情景2:空间划分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扩容增效。人口和经济持续向重点开发区域有序集聚,空间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性逐步增强,有效实现了产业有序集聚,城镇布局合理,人口密度提升。阿城区将引导农业空间及生态空间人口向城镇空间转移,强化城镇空间对外来人口的接纳能力,提升人口承载力。整合农村用地规模,借助村屯撤并,引导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重点向中心村集中。
(三)管控调整与空间承载功能量变动
三大空间的转换主要表现之一是空间主体功能的转型,即生产、生态、生活三大主体功能间的转化,是有限的空间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在各种功能之间进行数量和空间再配置的动态过程。根据增加生态功能、空间不变下扩容增效的不同目标情景设定对三大空间的划分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情况核算三大主体功能(核算结果如表4所示),分析三大空间变动对其承载的功能的影响。

表4 阿城区空间划分调整对三大功能的影响
情景1:加强生态功能,增加生态空间。根据阿城区空间规划2035目标,生态空间面积不少于国土总面积的53.33%,农业空间面积不少于39.81%,其中基本农田面不小于36.44%。使农业空间中的耕地、园地按比例缩减3.36%,城镇空间中的村庄用地缩减0.97%,缩减部分主要转化为生态功能价值较高的林地。该情景下,新增面积103.67 km2的林地,使得生态功能增加了666.54万元,但功能密度从8.67万元/km2下降至8.49万元/km2。生产功能并未发生改变,主要原因是新增林地不仅提供生态功能,还提供了林业产品、木材原料等弥补了农业空间减少所损失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在承载人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缩减村庄用地,使功能密度从3 876.34人/km2上升至4 625.41人/km2。
情景2:空间划分不变的情况下扩容增效。作为哈尔滨主城区重要组成部分,阿城区经济、人口变动受哈尔滨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未来持续集聚作用的影响。在对阿城区人口历史增长分析基础上,综合考虑哈尔滨人口变动趋势和阿城区人口变动条件,预测2035年阿城区人口达60万人,功能密度从3 876.34人/km2上升至4 075.28人/km2,人口向中心城区以及玉泉镇、平山镇等几大城区聚集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生产功能根据人口增长比例与哈尔滨市人均GDP进行估算,生产功能总量增加141 675.50万元,功能密度从1 127.76万元/km2上升至1 185.59万元/km2。
结果表明,通过增加生态空间的方式增加生态功能,并不一定带来生态效率的增加,退耕还林的方式虽然使生态功能总量增加但是生态功能密度有所降低。然而生态效率的高低还需要考虑跨地区比较与更大尺度生态边界的复杂系统稳态与突变理论[29]才能得出有效结论。同时,农业空间向生态空间转换并不一定导致生产功能降低,表明了不同空间有一定程度上的功能替代作用,主要取决于农业空间所种植的农产品与生态空间的林产品之间是否能够替代,尤其是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二者之间的替代作用较小。
三、“双评价”的治理应用与讨论
(一)分区管控衔接规划目标
“双评价”体系与各层级规划方案存在脱节现象,不利于实现主体功能的降尺度传导、分解。如阿城区在进行目标功能定位时,基于国家宏观战略视角,兼具以国家重点开发区、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为核心的多重功能定位。但从省市发展来看,其作为黑龙江的重点工业化、产业化区域需要以生产功能为主要落位目标,从阿城区自身发展来说则是要推动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等目标,区县层面则难以协调宏观战略目标与自身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
增加“双评价”指标的精细化和差异化,实现分区管控。“双评价”尚未根据主体功能类型、城镇化、农业和生态地区等不同发展类型而选择差异化的指标体系。各层级规划目标应当在统一框架的“双评价”体系中予以表征,当上层规划目标发生变化或与下层规划需求冲突时,才能给予量化反映和及时调整。现阶段评价结果后置导致对资源的保护、开发、配置,以及在多方博弈中的平衡作用不足。
(二)利用量化管控提高空间承载力
“双评价”应当增加主体功能区规划尺度与生态系统尺度关联,尝试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发展需求的空间转译与定量化指标[25]。仅从自然地理和生态角度开展生态脆弱性评价及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难以真实反映现状生态空间内耕地、人工商品林、镇村、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战略性矿产资源区域等功能承载情况。在阿城区,根据增加生态功能、空间不变下扩容增效的不同目标情景设定对三大空间的划分进行调整与功能核算。阿城区三大红线之间的过渡空间(林地为主)被划为生态经济区,即可同时承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利用主体功能核算量化空间转化带来的效率变化,探讨如何调整以实现功能总量最大化[30]。
(三)以底线管控为约束统筹发展时序
辅助统筹长远目标与开发时序的关系。“双评价”集成各类要素,综合发展基础、潜力、风险集成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传统承载力评价多是单一空间尺度的静态评价,缺乏必要的时空尺度转化,而且未考虑经济社会因素作用下对外开放与资源依赖导致的国家安全问题[31]、面临用地更新的经济发达地区都需要进行跨时开发需求与资源利用研究。以跨时期生态服务系统与自然资本[32]着手考量,可以一定程度兼顾空间的多功能性、适应性和弹性。
适当融入发展潜力分析。现阶段国土开发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国土开发强度接近或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33-34],而自然禀赋相对较好的中西部地区尚有较大潜力。长江、黄河流域跨越了多个省市,连接了我国的生态脆弱区至经济高度密集区。以增长极限为理论基点的预警模型[35]可适当将反映产业发展的趋势性因素纳入评价体系,辅助制定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等。
(四)增加动态反馈,实现弹性管控
“双评价”对国土空间开发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反映不足。“双评价”实践过程中并非动态可调整,评价结果难以有效反馈。“双评价”指标大部分依据某一时间节点进行评价,空间划分依据尚未考虑功能空间随着发展需求与目标调整可能产生的变化。在国土空间规划15~30年的实施期间,新技术进步与新要素产生随时可能改变区域资源禀赋特征。因此“双评价”需要对规划效果的动态反馈,通过弹性管控指引区、县尺度国土空间的产业布局、要素布局,围绕主体功能目标配置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形成新的区域比较优势。
“双评价”需要从静态的绝对性评价转向关联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资源环境承载之间的动态相对性评价,辅助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目前,生态支付区与生态受偿区、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之间的权、益失衡问题严重[36],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功能弱化但无法及时通过市场途径得以补偿。比如以国家粮食以及生态安全为主的东北地区,其合理补偿金额应当多于其通过粮食产品、生态产品贸易获得的货币收益,尤其是生态产品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缺乏生态多样性等跨期价值的有效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