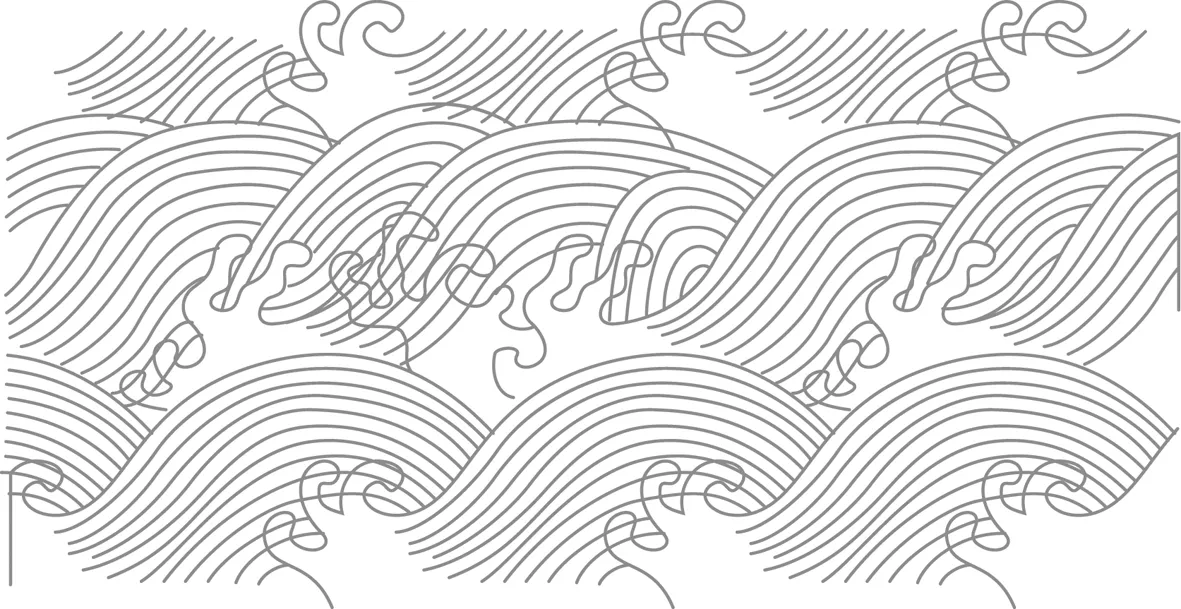考古学视野中的区域史开掘
——李昆声先生对云南历史、文化研究的贡献
2020-08-31杨泽宇刘金泉
杨泽宇,刘金泉
(1.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2.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李昆声先生是云南著名的考古专家,祖籍湖南张家界,194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安徽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大学等处工作,曾担任云南省博物馆馆长、国家社科基金会特别委托项目首席专家,并受聘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教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台湾艺术大学、逢甲大学、大理大学的客座教授,多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资助和奖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50余年的学习、工作和教学生涯中,先生潜心钻研、勤于笔耕,撰文达50篇之多,主编或著述《云南文物古迹》《云南艺术史》《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等学术著作共25部。2016年,学界将先生的作品全面推广,整理、出版四卷本的《李昆声文集》,但此后对先生学问的研究略显停滞,目前,除云南大学陈果老师《中国西南及东南亚考古的集大成之作——<李昆声文集>读后》和蒋珊珊在硕士论文《滇文化学术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探索》中提到李先生在考古学领域的贡献外,并无专文详述先生的学术硕果。笔者颇觉遗憾之余,认为先生的研究领域虽以考古学为主,但其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云南区域史中,为云南艺术史、农业史和民族文化史注入新血液、打开新思路,拓展了滇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回顾先生学术成果,既能从中总结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经验,也能勉励和鞭策当今学子效其学、承其志、传其业。
一、 艺术考古视野中的云南艺术史研究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李昆声先生主要从事青铜器的考古开掘与青铜文化的解析;同时,兼顾对其他艺术载体和艺术学通史的探讨,在云南古代史和青铜艺术史研究中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以铜鼓为中心的研究
铜鼓中的云南艺术史。先生关于铜鼓研究的开山之作,是1980年与黄德荣先生共撰的《谈云南早期铜鼓》,其最早提出“铜鼓可能起源于滇中至滇西区域”[1]的观点,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许,现已成为学界在铜鼓起源地问题上的共识。
1990年两位先生在《考古》上的合著《论万家坝型铜鼓》,讲述万家坝型铜鼓从发现、分布到传播的历史际遇,确定存在年代区间是春秋早期到战国末期,在铜鼓分类中属于最古老的一类,依据出土形态分为四种鼓式;并通过对云南、贵州两省的现代民族学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万家坝型铜鼓成对埋藏,究其原因,乃是鼓分雌雄。”[2]随着万家坝型铜鼓出土数量的增多,新的发现与收获也与日俱增,为作进一步补充,先生又撰《再论万家坝型铜鼓》,该文相对于前文有三方面的补充:第一,将新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从体高、束腰、足界、扁耳、圈纹、外饰等方面再做分式;第二,从铜鼓的金属成分中检测铅同位素含量,以此判断铜鼓的起源、产地以及铸造方法;第三,涉及对越南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的比较研究,认为纹饰是越南出土铜鼓分辨类型的主要依据,“纹饰越复杂,年代越古老”[3],并从历史与艺术的角度分析其格式化风格与越南古代环境的关系。
在《释早期铜鼓鼍纹》中,先生从贾兰坡和甄朔南教授的相关研究中认为,早期铜鼓中的“菱形网状纹”“四足爬虫纹”就是甲骨文中的“鼍”,即鳄鱼,代表部族首领的权力和力量,“鼍”作为纹饰在“音色”“鼓皮”“鼓钉”和“写实”上“深受中原文化影响”[4]213。
《云南文山在世界铜鼓起源研究中的地位》则在分析文山州出土的铜鼓数量、类型和特质后,认为该地极有可能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之一,并根据铅同位素和遗传花纹的双重证据说明文山铜鼓在从万家坝型到石寨山型嬗变中的重要作用。
在《试论黑格尔I型铜鼓的三个亚型——以中国西南为中心》中,介绍了奥地利考古学家弗朗兹·黑格尔采用类型学方法将东南亚地区的古代铜鼓划成“4个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的分类模式,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创造性将黑格尔Ⅰ型铜鼓进一步细分为“石寨山式、文山式、东山式”3种类型,并对三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辨析,认为万家坝型铜鼓是“铜鼓之祖”,不仅“石寨山式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文山式“祖型也是万家坝型铜鼓”。[5]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黄二位先生编著出版《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以全球史视野,从欧美、日本、中国和越南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分析、归纳当前铜鼓发掘的学术现状;也从分布地、标准器、年代、分式纹饰、金属成分和铸造工艺的角度介绍了国内和越南出土铜鼓的实况,力图在学术前沿中,探讨中国万家坝型铜鼓、石寨山型铜鼓、越南东山铜鼓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有关铜鼓之间从共生到裂变的关系,成为先生铜鼓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当前考古学界在早期铜鼓源流、演变研究中的权威作品。
(二)铜鼓以外的云南艺术形式探索
先生在艺术史研究领域除关注铜鼓之外,也重视对云南其他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形成了以铜鼓为主,其他考古艺术多花齐放的研究态势。《云南原始社会艺术初论》,从云南新石器时代艺术的内容、分类、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云南原始社会的艺术兼有欣赏和实用意义,一方面精美绝伦的动物和人物造型带来审美愉悦和快感;另一方面,以血缘标志、图腾符号和民族习俗为装饰的原始艺术,最初富涵象征权力、财富的实用、功利性目的。[4]130
在《云南青铜时代的音乐、舞蹈和杂技》中,先生基于对商代末年至战国西汉时期出土文物的考察,揭开云南青铜时代音乐、舞蹈和杂技的原貌:在音乐上,详细介绍“葫芦笙、葫芦箫、錞于、钟、羊角钮钟、铃、锣、钹和鼓”9种云南古代民族制造的乐器,根据测音标本、敲击部位和音节结构的区别研究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的音程关系和生律法倾向;在舞蹈上,分别揭示出以“翌舞、旄舞、人舞和干舞”为形式的“商周庙堂舞蹈”和以“葫芦笙舞、翔鹭舞、圆圈舞、巫舞和刑牛舞”为娱乐方式的云南人民自创的“滇族舞蹈”;在杂技上,通过对云南青铜器纹饰图案研究后发现,汉代云南存在投壶、角抵、驯兽、鬼竿等杂技和马戏表演。[6]
《云南古代青铜动物造型艺术》则从《牛虎铜案》《猪搏二豹》《三水鸟铜饰物》等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案为着眼点,探讨动物形象的代表类型、艺术内涵以及滇人原始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观念,认为这些神形兼备并涵有夸张色彩的动物图形“体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风格”[4]258。
《绚丽多彩的古代青铜文化瑰宝》一文,记述1986年“云南省博物馆青铜器展览”代表团赴瑞士、奥地利、德国展出的文物,详尽描述“滇王之印”的历史渊源和精美质地,“青铜贮贝器”的类型、用途和雕铸场面以及“青铜装饰物品”的表现场景和蕴含寓意,总结云南青铜器艺术“主题明确、构思巧妙、热情奔放,以写实为主,又注重内心世界刻画”[7]的特点,向世界展示历史悠久、光彩夺目的云南青铜文化。
在艺术通史研究上,李昆声先生借助考古学的视角独撰的《云南艺术史》一书被誉为“云南艺术考古学的开创”[8]之作,以原始社会时期的石器、陶器和原始绘画、舞蹈、建筑为开篇,根据朝代顺序依次将商至西汉的青铜艺术、舞乐技艺、杂技马戏,东汉至隋的碑刻、书法、绘画艺术,唐宋时期的石窟摩崖、音乐舞蹈、建筑艺术,元明清的陶瓷工艺、建筑雕刻以及近现代各民族艺术纳入云南艺术考古的视角,方法上别开生面,为云南考古注入艺术学的学科活力,亦为读者了解云南区域艺术的演变历程提供方便。
二、农业考古与云南农业史研究
在农业史研究领域,李先生将考古材料和民族学资料相互印证,根据已发掘的耕作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及农具,青铜器图案上有关农作的场景以及文献的记载,从农业考古的角度探究云南农业科技史的发展过程。
(一)对云南农业史的概述
作为李先生云南农业史研究的提纲、总览之作,《云南农业考古概述》在分析考古发掘获得古代农业实物资料的基础上,从作物品种、农具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讲述自新石器时代到唐南诏国时期云南农业的概况,并强调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农业科技史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云南农业对开发西南边疆和发展祖国经济具有的深远且特殊的价值。[9]
《试论云南上古农业经济的特点》通过解读云南上古时期悠久的稻作文化、多种的经营模式和发达的畜牧养殖层面,认识到当时云南的经济发展方式比其他地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并从考古遗存和史籍记载考证,发现云南古代农业经济中畜牧业比较发达,约在二千五百年前,云南的“六畜”品种即已齐全。[10]
《先秦至两汉时期云南的农业》则以先秦到两汉时期的云南农业为研究对象,从农具、牛耕、作物和水利等方面进行介绍:在农业生产工具上,梳理云南从青铜农具向铁农具的过度,认为西汉中期云南出现铁农具,及至东汉,铁农具已在云南大部分地区普遍使用,青铜农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牛耕上,通过昭通东汉墓中发现的画像砖初步判断,东汉初中期云南就已经出现用牛力代替人力进行耕垦的生产方式;在粮食作物品种上,根据《蛮书》记载和云南出土的大量野生稻谷分析出云南粮食作物品种繁多,稻、大麦、小麦均是其常见作物且以粳稻需求量最大、种植面积最为广泛;在水利灌溉上,认为云南最早的水利设施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的洱海西岸的“缓坡”和“台地”[11],而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出现“穿龙池”“陂池”以及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圆筒形青铜锄”均被视作水利工程和与水利有关的农具。
《南诏农业刍议》从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和养蚕业三方面探明唐代云南的农业发展水平:南诏农作物品种丰富,“五谷”齐全,水田、梯田兼用,稻、麦作物轮作,农业种植理念先进、方式科学;经济作物主要有“柑橘、甘蔗、橙、柚、李和杏”等,种类繁多,可以补充农作物之不足;家畜饲养上,“战国时期云南的畜类品种已很齐全”[12],牛马猪羊鸡犬“六畜”兴旺;同时,南诏养蚕业也比较发达,《南诏德化碑》《蛮书》《新唐书》均有所载。
(二)对农业考古出土作物、农具的具体分析
上述论著均是先生在立足和把握整体性的基础上对云南农业史的梳理与概括,而从以“小问题”分析“大内容”的方法入手,通过作物、农具等探求云南农业发展全貌方面的研究,先生亦有建树。
在出土农作物的分析上,《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百越——我国稻谷的最早栽培者》姊妹篇,相辅相成,都致力于证明古代百越民族是最早驯化野生稻谷的民族。前文从年代和分布地域出发,将古代记载野生稻的文献和国内已发掘的52处人工栽培古稻遗址结合研究,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遗传学的材料,得出“中国南部到中南半岛间的地区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居住在此的古代百越族人民,最先将野生稻驯化成功并大面积种植”[13]的结论;后文论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考古学视野中古稻的分布范围研究,以甲骨文中的“稻”字为线索,依次解读出土过籼、粳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二,从地理学和生物遗传学的角度推敲人工栽培稻的类型,进一步梳理出野生稻分布与出土古稻之间存在遗传关系;其三,历史学视野中对百越先民育稻起源的考察,通过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民族学族际识别的方法,厘清我国东南地区古代居民的民族成分,进一步明确“我国南方古代百越族群的先民是我国稻谷的最早栽培者”[4]51。
《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则结合考古学、民族学和农学的知识,分析云南滇池、元谋县大墩子、宾川县白羊村、剑川县海门口和宁洱县凤阳公社五处出土的碳化古稻,对亚洲栽培稻起源地的问题进行探究,认为“云南是最早驯化野生稻为栽培稻的地区之一”[14]的判断毫无疑义。
在出土农具的研究上,《云南牛耕的起源》围绕“犁”与“牛”两个要素,对云南牛耕的出现时间和最早使用地域加以探索,以战国西汉时期云南出土的铜犁和牛在云南的用途为线索,在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史料的相互证实下,确认云南牛耕最早出现在东汉初中期,由四川传入,并率先在滇池、昭通地区得到推广。[15]
《唐代云南“二牛三夫”耕作法民族学新证》作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剑川县沙溪公社白族“二牛抬杠”的耕田方法与《蛮书》《新唐书》中记载云南“二牛三夫”的垦殖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畜力数量相同的情况下,人力数量却从文献中的“三人”变为现实中的“二人”,作者认为随着云南人民在长期农业劳作中知识经验的丰富和积累,“二牛三夫”的耕作法也在不断改进,“千余年后,使用熟牛耕作时让‘郭阿’增加一项职能”[4]435,也因此节省下一个劳动力,形成现在见到的“二牛二夫”操作搭配。
在《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播种图”补释》中,先生认为以往学界将晋宁石寨山铜鼓形贮贝器上的花纹视为“巡狩”有所不妥,他更认同冯汉骥先生将图案上手持的“执杖”看做少数民族耕田时使用的“点种棒”[16],因此考释该图应是云南少数民族“播种”的场景,而非象征权威的仪式。
三、以民族考古为视野的文化史研究
在文化史研究领域,先生立足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分布的社会现实,对发掘出的少数民族文物、遗迹进行探勘、识别,借助民族考古的手段,在探析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方面亦有成绩,主要贡献包括:单一民族的文化溯源、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勘探三个方面。
(一) 民族考古与西南百越、彝族和氐羌的历史文化
《百越文化在云南的考古发现》和《百越先民对中国金属史的一个重大贡献——云南元江铜锑合金斧研究》两文在跨学科的视角中基于不同的研究侧重,对百越民族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是近30年来国内百越文化梳理与专研的佳作。前文中,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林惠祥等前辈的百越文化研究成果上,依据当代更为成熟、更加专业的考古学方法,推断出百越民族在生产上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青铜农具并善于纺织,饮食上喜食异物,军事上以铜钺、一字格剑,经济上以贵重海贝为商品交换媒介,住宿上居住干栏式房屋,文化上有文身绣脚的传统、使用象形文字“以图代文”、崇拜孔雀、以铜鼓为礼器和采用猎首祭祀,生活用具有羊角钮钟、且以跣足佩环为装饰,出行惯用水路“习水操舟”等文化特征。后文则从金属锑在国内外的考古发掘和云南元江铜锑合金斧的金属测定与定量分析中发现,早在商末周初之时中国就已炼制出铜锑合金,纠正以往学界“锑在我国明代出现”的误判,并根据古文献和民族史考察出该斧出土地红河流域在商周时期以前百越民族聚居和分布区,以此确认古代百越民族是云南红河流域青铜文化的缔造者。在元江出土的商周时期百越民族所使用的铜斧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检测后证明是铜锑合金铜斧,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金属史上在青铜时代没有铜锑合金的空白”[4]370,同时也证明了百越对中国金属冶炼技术产生的巨大贡献。
《疑似彩霞天际来——云南彝族服饰与文化一瞥》则以楚雄、红河以及哀牢山、小凉山地区出土的彝族服饰为研究内容,从色泽、纹饰、帽子、头饰的角度对彝族服饰中蕴藏的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加以梳理与解读,并根据彝族史诗《祖神源流》的记载,说明彝族服饰既包含驱灾辟邪、祈福祷告的宗教元素,也蕴涵先祖崇拜的人神意识和祖宗信仰,经漫长岁月洗涤而沉淀的服饰文化实则是保留彝族历史文化记忆的百科全书。[4]390
《从云南考古材料看氐羌文化》是根据古籍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氐羌的文化特征进行尝试性探索,主要从丧葬习俗、生活方式和宗教崇拜几个方面力图勾勒氐羌民族生产生活原貌,其中,葬俗以翁棺葬、火葬为方式,居住在半地穴式或平地起建木构房屋中,穿衣喜披毛毡,出行善于骑马,发式多为披编,体质特征“深目长身、黑面白牙”[17],并且存在以葫芦为崇拜物的自然信仰和以虎为对象的图腾崇拜。同时,先生认为因古代民族迁徙之频繁和文化之传播,并不能将氐羌文化简单的归结为氐羌民族的文化,而是应该综合考虑地理、人文等多重因素,在分析具体问题之时,将氐羌文化和氐羌民族区别分析,这种批判性的族群文化研究在当前民族史、民族学文化研究中也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二)族群的文化比较以及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史探究
《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主要通过论述夏商周三代时期,氐羌、百越和百濮三大族群在云南的历史痕迹与文化遗留,依据考古学强调不同类型原始文化的区域特征,将三大族系在云南的活动范围和文化分布详加厘定,认为原始社会时期,氐羌先民主要活动在滇西北地区、滇池及滇东北地区,百濮居民主要集中在澜沧江中游地区,百越族民分布在滇东北、滇东南及西双版纳等地,亦有交错杂居之现象,[18]正是在三大族群的共同努力下,形成新石器时代时期灿烂辉煌的云南原始文化。
《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从石器时代、春秋时期、战国秦汉之世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出发,认为“东南亚国家有的铜鼓是直接接受中国云南铜鼓文化的影响,有些则是间接影响,通过越南东山文化,再影响到东南亚其他国家。”[19]同时,作者指出,东南亚国家对云南的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以贸易、交换和赠予为主要模式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互惠,使双方在文化上兼顾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
《百越与弥生文化》一文以寻找百越文化与日本弥生文化之间的相同习俗为重点,从“文身、黥面和漆齿”的人体装饰、“徒跌、蹲踞、贯头衣”的行为习惯和“南稻北麦”的农业结构上,[20]探讨古代云南与日本在文化交流上的过程与原相。
《“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比较研究》依据考古知识对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代金印“滇王之印”和在日本北九州博多湾采集的“汉委奴国王印”在来源、印文、印纽、成色、制作工艺和大小规格上进行对比,一方面运用文献学和史料学对两印的历史渊源、质地真伪进行考证与辨识;另一方面,在其相似的艺术特征中发掘“汉代时期云南与日本北九州在文化、习俗上有着共通与相同之处。”[21]
(三)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信仰与宗教文化的研究
《天菩萨、傩面具、甲马纸、金马碧鸡——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一文通过文物遗存和文献典籍的对比分析,论述了彝族器物上“天菩萨”“察尔瓦”文物图案、驱鬼逐疫的傩戏祭仪、彝族向神快速传递信息的甲马纸以及“金马碧鸡”神话传说等文化事项,在经数千年的历史洗涤中的保存、继承与传播。
《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为例》在将国内出土的陶祖、石祖、玉祖和木祖视为代表男性生殖器和象征原始“性”魅力的基础上,结合云南考古发现的“祖型器”以及崖画上出现的酷似女性阴部的图案,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的云南,存在对生殖器官的崇拜,既有以男根崇拜为外在表现形式,实质上代表父系氏族社会中对男性优越地位的推崇,也蕴涵人类渴求通过生育达到繁衍子嗣、生产劳动与再生产的目的,又有以女阴信仰和孕体信仰为内容的生育崇拜,自然而然成为当时无法解释受孕繁殖条件下,人类的粗浅认识和原始认知。
《权杖、驯象长钩、图腾柱——云南考古三题》经过对青铜杖头饰、石窟壁画中的驯象钩、贮贝器上铜柱图案的考察发现,云南青铜杖上的装饰物,多是象征权力大小与级别高低;云南的驯象长钩图像与中原地区所见图案一脉相承,可断定“云南古代民族以长钩驯象之术,系传自中原”。[22]
在《南诏大理文物精粹——赴瑞士“中国云南古代佛教艺术展览”巡礼》中,先生回忆了1991年5月5日至9月15日在瑞士举办的“中国云南古代佛教艺术展览”的盛况,从历史传承、宗教寓意、外形特征、制造技艺和艺术价值等方面,介绍了赴展的南诏、大理时期以“密宗阿嵯耶观音造像”“写本和刻本佛经”“塔模和经幢”和“铜镜、铜钱、影青瓷”为代表的佛教文物;并赞誉该会展是“我国首次在国外举办以南诏大理国时期文物为主”[23]的一次重要展示,既彰显我国历史久远、璀璨绚丽的古代佛教文化艺术,又多维度的呈现出云南文化的风格与特色。同时,从中原与西南地区的宗教文化的共性更能看出中原王朝与南诏、大理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证明西南边疆自古就是华夏民族、中原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余论
从求学到治学,从立志到立业,经50余年风雨历程,李昆声先生在研究上孜孜不倦的摸索、深究,为西南考古做出巨大的学术贡献;在教学上,勤勤恳恳的教书、育人,为云南乃至全国考古学界培养出大批后辈俊才。从先生众多的考古学论著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先生学术经历之丰富,近半世纪以来云南考古的成就均伴有先生努力之身影,所取得累累硕果不言自明,可以说先生为云南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奉献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学术造诣之深厚,先生专攻考古发掘之余,将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学、民族史、民族学的相关知识结合,将“二重证据法”引入具体的学术探寻中,一定程度上打破历史学者擅长整理、分析文献史料,却常常忽略用考古资料论证、解决问题的研究瓶颈。总言之,在云南区域史研究上,先生尝试运用考古学视野,探索云南区域历史与文化,以多层面的理论方法、多学科的认知视野揭秘云南区域社会中的历史迷云,阐释西南边疆地区的纵横文化,体现出一位考古学家的文化情怀,在云南艺术史、农业史和民族文化史均建树颇丰,贡献甚伟,不仅是云南史学乃至全国史学界的杰出人物,更是值得后辈学子学习、效仿的学术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