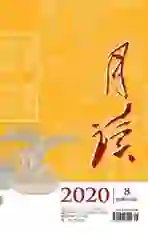刘禹锡:试茶解得其中味
2020-08-25杨多杰
杨多杰
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莞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
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
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
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
炎帝虽尝未解煎,桐君有策那知味?
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
木兰坠露香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
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嘉客。
不辞缄封寄郡斋,砖井铜炉损标格。
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
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跋石人。
——[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
判断一个诗人是否懂茶,不能只看他写了多少首茶诗。大诗人白居易一生写了六十余首茶诗,自然是茶事的行家里手。可是,像白居易的老友刘禹锡,一生只写了两首茶诗,却也在茶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刘禹锡的两首茶诗,其中一首题目为《尝茶》;另一首是《西山兰若试茶歌》,这首诗堪称唐代茶诗中的经典之作,凭借这首茶诗,刘禹锡加入了懂茶人的行列。
原因何在?我们读了便知。
老规矩,还是先从作者聊起。
刘禹锡,字梦得,祖籍洛阳,后迁居荥阳。他生于公元772年,比茶圣陆羽小将近五十岁。二人之间,相差了两辈人。所以从茶文化的角度看,刘禹锡生活在后《茶经》时代。
据刘禹锡自己说,他这个刘姓很高贵,是汉中山靖王之后。换句话说,刘禹锡与刘玄德是同气连枝的近亲。当然,他的这种说法也不太靠谱。
唐玄宗天宝末年,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刘禹锡跟随其父刘绪到江南避祸,所以他的童年在嘉兴等地度过。也正因为这样,少年刘禹锡得遇高人,跟随诗僧皎然、灵澈等人学习。请注意,释皎然是陆羽的好友,更是精于茶事的僧人。很可能从那時起,刘禹锡便在皎然那里接触到了茶事活动,但并不_定十分热衷。毕竟,十多岁的少年意气风发,哪会静下心来饮茶呢?总之,刘禹锡虽不是王侯之后,却是名师之徒。
唐贞元九年(793),刘禹锡登进士第,又登吏部取士科,授弘文馆校书郎,算是正式步入了仕途。那一年,他不过21岁,可谓少年得志。但是,接下来的宦海生涯却充满了凶险和艰辛。
永贞元年(805)正月,唐顺宗即位。不久,刘禹锡迁屯田员外郎兼德宗崇陵使判官,判度支盐铁案,积极参与王侄、王叔文的革新活动。同年八月,顺宗退位,革新夭折。十一月,革新参加者都被贬谪,刘禹锡被贬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行至江陵(今属湖北)时,朝廷追来一道圣旨,将刘禹锡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而且在制词中有“纵逢君赦,不在量移之限”的狠话。也就是说,即使之后大赦天下,也没你刘禹锡的份儿。
时隔多年,刘禹锡终于回到了首都长安,随即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文如下: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但此诗骨子里却另有所指,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靠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刘禹锡不仅看不起那“桃千树”般的新贵,更藐视那些“看花回”的趋炎附势之流。
由于这首诗过于辛辣,再一次刺痛了朝中的权臣。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再度贬为远州的刺史。从司马到刺史,官职看起来是升了,可政治境遇却没有丝毫改善。他们这几位仍然是职场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自此以后,刘禹锡历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等职。直到唐大和元年(827),才北归回到洛阳。这距离他永贞元年被贬,整整过去了二十三年。就连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也在《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中感叹道“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这二十三年,实在折得过多了。
大和元年,在宰相裴度等人的关照下,刘禹锡授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大和五年冬,出为苏州刺史。在苏州任上因为赈灾有功而被赏赐。八年秋,调任汝州(今河南临汝)刺史。次年,迁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同州是四辅之一,唐代往往作为临时安置要员的地方。但这时的刘禹锡已是64岁高龄,而且他很快看到了长安上演的“甘露之变”——宦官与朝官相互倾轧,十多位宰相、节度使同时被族诛的惨剧,于是在次年,即开成元年(836)秋,辞官回到洛阳,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和已在洛阳的裴度、白居易诗酒酬和。直到会昌二年(842)秋病逝。
了解清楚了刘禹锡的境遇与性格,我们再来看题目。
关于这首诗作于何时,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王威廉、周靖民在《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作于何地》(《中国茶叶》1982年第5期)中认为,该诗作于朗州司马任上。但是文章多是推测,并未举出有力的证据,恐不足为信。
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中,将这首茶诗的写作时间定为在苏州刺史任上,则有一定道理。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六八一“苏州府物产考”记载:“茶多出吴县西山,谷雨前采焙,争先腾价,以雨前为贵也。又虎丘西山地数亩,产茶极佳,烹之色白,香气如兰,但每岁所采不过二三十斛,止供官府采取,吴人尝其味者绝少。”
当然,哪个城市都可能有一座西山。所以此诗作于苏州的说法,也只可看作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罢了。至于“兰若”二字,则确实是佛寺的名字。宁采臣与聂小倩的故事,不也发生在兰若寺吗?当然,此兰若寺非彼兰若寺就是了。
除去地点的考据,题目中的这个“试”字,也值得玩味与推敲。试,可以组词为尝试,这显然是针对不太熟悉的事情而言。如今的爱茶人,拿到一款新品后一般也会试茶。那么,到底是什么茶值得刘禹锡一试呢?这便是本诗的重点。我们还是到诗文中去寻找答案吧。
第一部分,自“山僧”至“新茸”,讲的是试茶的起因。
这里的山僧,呼应的是题目中的兰若寺。一杯清茶,既符合青灯古佛的生活,也可以结交往来的香客。因此,从古至今,许多寺院都有茶园。但是兰若寺的茶园,显然规模不是很大,仅仅有“数丛”而已,并且是散落在竹林当中。
诗中的一个“抽”字,极为巧妙,将茶芽萌发时的姿态描写得活灵活现。若是用“长”字,则过于平淡无奇。可要是用“冒”或“钻”,则又过于浅白庸俗了。只有用了这个“抽”字,竹下茶树欣欣向荣的长势才跃然纸上。
第二部分,自“莞然”至“沙水”,讲的是新茶的制作。
原来刘禹锡要试的茶,不在老和尚的坛坛罐罐中,而是在后檐的竹林里。这里的“振”字,应解释为整顿。所谓“振衣”,就是整理衣衫。由此可见,刘禹锡与山僧很可能已经脱去了拘谨的服饰,正在禅房中闲谈。偶然聊到寺中有茶树,大家一时兴起,这才准备走出僧房,亲赴茶园。
众人摘下的“鹰嘴”,指的便是尖细的茶芽。刘禹锡在《尝茶》一诗中也有“生采芳丛鹰嘴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二句。由此可见,唐代还是很流行嫩采的。
按照陆羽《茶经》的记载,唐代流行的应是蒸青绿茶。但是,兰若寺的僧人却是不蒸而炒。鲜叶下锅,不消片刻,便已满室飘香。这样的做法与唐代主流制茶工艺不同。所以,刘禹锡在兰若寺不光试了新茶,而且试了新工艺的茶。明确记载了锅炒杀青,这才是这首《西山兰若试茶歌》的史料价值所在。
这边在炒茶,另一边已在备水。金沙,是湖州的名泉。据说,唐代时就用金沙水造紫笋茶而进贡了。当然,刘禹锡没有到过湖州,所以这里的“金沙”二字,应该泛指优质的泉水。好茶配好水,这才是行家。
第三部分,自“骤雨”至“襟开”,讲的是试茶的过程。
所谓“骤雨松声”,当然不是真的刮风下雨,而是指水开时的声响。至于“白云满碗”,则是描述茶皂素产生的沫饽。日本平安时期的《和出云巨太守茶歌》中,有“饮之无事卧白云”一句。可见唐代人非常喜欢将饮茶与白云联系在一起。后来我有一陈年普洱茶饼,取名就叫“闲卧白云”,灵感便是来源于这些茶诗。
其实,“骤雨松声”也好,“白云满碗”也罢,都是对于茶事活动的艺术化描述。由此可见,刘禹锡应是爱茶之人。李太白愛酒,不也写出了“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的诗句吗?如果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是写不出这么美的句子的。
兰若寺僧人制出的茶,香气直喷鼻腔,连宿醉都能消除。胸中的忧愁,自然也都消散到九霄云外了。这几句诗文读起来会让爱茶人心生赞叹,同样是喝茶那些事,怎么就写不出人家这层意境呢?的确,刘禹锡的诗不像韩愈等人那么奇崛,也不像白居易那么平畅浅易。他的诗风干净明快,不过分雕琢,也不流于俗滑油腻,在中唐诗坛可谓独树一帜。
第四部分,自“阳崖”至“知味”,讲的是试茶的闲谈。
茶叶质量的高低,与茶树的生长环境有很大关系。就算是同一片茶山,即使是阳坡与阴面,成品茶的风格也大有不同。但是兰若寺的茶好喝,更因为种在了竹林莓苔之地。唐代韩鄂《四时类要》中关于茶树种植写道“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这与如今人们提倡的人工复合茶园生态系统的原理极为相近。
这一部分还引入了两个典故,此处要特别说明。炎帝,即神农氏。他虽是尝茶,怕也是生嚼的鲜叶。因此,炎帝自然不知道,茶还可以这样做,这样煎,这样品。《桐君录》的内容可见于陆羽的《茶经》中。炎帝与桐君,都是茶界的前辈人物。但是,按刘禹锡的说法,这二位可没他有口福。
其实,从古至今茶树品种在不断遴选,制茶工艺也在不断提升,茶汤味道自然也愈加鲜美。陆羽虽贵为茶圣,却没喝到乌龙的馥郁、白茶的鲜灵。所以,我常常讲,当下的爱茶人才是最幸福的!
第五部分,自“新芽”至“不如”,讲的是试茶的赞叹。
在这一部分,刘禹锡赞叹了兰若寺僧人制茶手艺的高超。采摘精良,自然不必多说;但是自摘下鲜叶到煎茶出汤,不过片刻,这才是真正让诗人大开眼界的地方。纵观全文,鲜叶摘下来只有炒这一个处理,后面也没有晒干或烘干的过程。正因为只是炒制,才可以达到“自摘至煎俄顷余”的速度,并且做到“悠扬喷鼻宿酲散”的香气。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西山兰若寺的僧人不光是锅炒杀青,很可能就是朴素的炒青绿茶。
时至今日,炒青绿茶已是我国茶区最广、产量最多的绿茶种类。要真是追根溯源,工艺的源头还得从刘禹锡的这首《西山兰若试茶歌》算起。刘禹锡恐怕也是第一个喝到炒青绿茶的文人了。
第六部分,自“僧言”至“标格”,讲的是僧人的惋惜。
自摘至煎,片刻已成。宾主把盏言欢,共享茶汤之乐。这时的僧人不禁感叹,茶本就是性格幽寂之物,像刘大人这样的贵客来到敝寺,我便自采自炒奉上香茶一碗。也有一些沽名钓誉之辈,听说了西山兰若寺出好茶,但他们可没心思探古访幽,而是直接“下单让我快递”,拿到手后根本不懂得珍惜。本该用“金沙泉”般的好水,他们却只打“砖井”之水;本该用“宝鼎”这样的好器,他们却只拿“铜炉”煎煮。结果自然是风味大减,格调全无。
第七部分,自“何况”至“石人”,讲的是诗人的心声。
僧人话说至此,刘禹锡不由得暗自称赞。诚如山僧所讲,那些权贵追求的是茶名而非名茶。只要是有名气的茶,不管是顾渚紫笋还是蒙顶甘露,都要想办法弄到手。哪怕茶山与京城远隔万里之遥,也要求白泥赤印封装好,再披星戴月送往京城。
但是,那些天天嚷着要喝好茶的贵胄豪富们,真的会好好品赏一碗茶汤吗?恐怕不会。他们有权搞到好茶,有钱买到好茶,可就是没有心思去品味一杯好茶。他们的心思,都在尔虞我诈的职场斗争上了。
所以全诗最后,刘禹锡指出要想体味茶汤的美妙,便“须是眠云跛石人”。这里的“跛”通“倚”,也有版本写作“卧”。所以“眠云跛石人”,就代指隐士高人。在这里,刘禹锡点破了饮茶的关键,不只在于茶,更在于人。
很多人的一生,都在职场努力打拼。而目的,是追求幸福与快乐。但是,近在眼前的幸福与快乐,他们却总是忽视或弃之不顾。
其实,生活中自有美感:街边的花草,天空的飞鸟,杯中的茶汤……这些美好,—直在那里,只是我们常常对它们视而不见,没有感触到蕴含在它们之中的那种美。我们能够发现美、欣赏美的心,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深处,本来就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常常丢失了它。
苏东坡曾说:“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文章的本意,是呼吁大家欣赏自然之美。但这几句话,用在茶事上不也很合适吗?
耳得之而为声,便是“骤雨松声入鼎来”。
目遇之而成色,便是“白云满碗花徘徊”。
烧水之声,茶汤之色,乃至于香气、口感、韵味,不都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吗?这样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茶事趣味,又有谁能享受到呢?
刘禹锡告诉我们:须是眠云跛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