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奇回来了
2020-06-27李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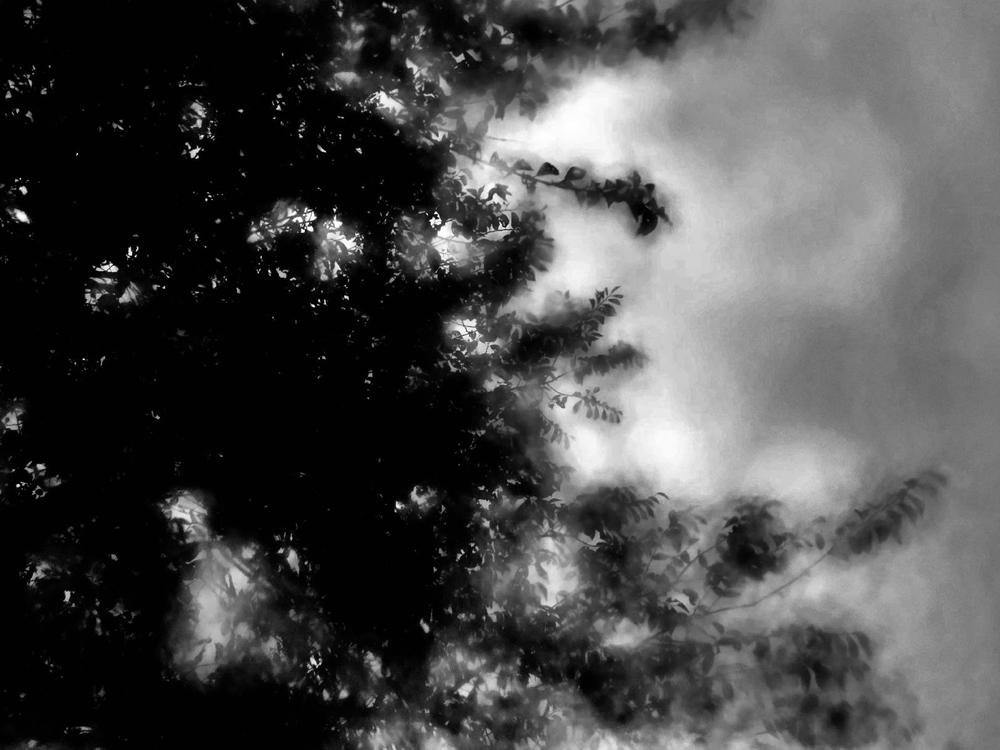
李启发,贵州独山人,1972年10月生,布依族,现供职于独山县教育局。小说作品主要发表于《贵州作家》《山花》《芳草》《小小说》《微型小说选刊》《短小说》《文学港》《夜郎文学》等。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班学员,贵州文学院第一、二届签约作家。曾获黔南州政府文艺奖。
我跟箩筐说,哈拉奇是一个湖,已经干了300多年了。
秋阳照在箩筐仰起的脸上,他问:“那300多年前,哈拉奇的水一定挺多的喽?”
我知道箩筐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而我们的肚子已经饿极了,必须赶快去弄点吃的。我边向屋外走去,边大声叮嘱他不要乱跑。
“哥,那你早点回,我怕!”箩筐在那堆破棉絮里缩成一团。
到这地方虽然没多久,但我已经踩好了点,穿过草地,经过一个工地,就到了街边一个包子店。那胖乎乎的女店主总是板着脸,每天早上,她都要抽空送娃娃去不远的幼儿园,那时正好下手。我本来无意盯上她家的,可是,我第一次经过她店门前时,她正红着脸,狠狠扯她娃儿耳朵,嫌娃儿出门时的动作慢了些。当时听着那娃儿杀猪般的嚎叫,我决定今后想吃包子了,就专门吃她家的。
店主前脚刚走,我就从容地走过去,揭开屉笼,迅速抓起热乎乎的包子,两个,四个,六个,往棉外套里塞。我还想再抓两个,看到街对面小店里,一个老头儿愣神向这边张望。我心里有些紧张,忙把怀里六个包子顺了顺,揣好,转身就跑。
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盘算,我和箩筐一人吃两个,留下两个,防备晚上找不到吃的。
我眼前浮现出箩筐吃包子的模样,双手捧着,闻个够,然后大口咬开,嚼着,黑里透红的脸,笑得像朵花。
箩筐跟着我快两年了。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白白的脸蛋,随便一笑就是两个可爱的小酒窝。现在,无论他怎样努力地笑,再也看不到那酒窝了。营养不良,加上不常洗脸,皮肤已变得很粗糙,根本不像个十岁的娃儿。
我有点后悔给他取名叫箩筐。见到他时,他正在一只箩筐里睡得香,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擦着泪花说叫罗小狗。我说,那还不如叫你箩筐。后来,我发现他的饭量比我还大,我吃一个盒饭,他吃两盒。我甚至怀疑就是因为我叫他箩筐之后,他的小肚皮才那么能装的。我倒不是嫌他吃得多,而是担心弄不到东西吃的时候,他会饿得慌。
又经过工地时,我放慢了脚步。我发现这里工人不多,都在不紧不慢地做着活,应该是在打地桩,或许这地方今后要造几栋高楼。地上很随意地摆放着一堆一堆的钢筋和扣件。我经常听人说,那些造高楼的商人心里都是黑的。于是我心里有底了,我想,我和箩筐至少一两个月的吃喝应该能有着落了。
包子很热,我拉开衣服上的拉链,香味清晰地蹿进我的鼻子。我想,等一下,我和箩筐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包子,一边继续给他说哈拉奇。一抬头,却看见草地那边的房顶上有个小人影,细细一看,正是箩筐。他也看见了我,一边挥着手叫着哥,一边蹦跳起来。
我急坏了,这几天我注意观察了,这房子所在之处虽然偏僻安静,但房子太旧,三间房垮掉了一间半,剩下一间半的墙上已满是裂缝。我这几天正在到处物色新住处,住在这房里太危险。
我一阵风似的跑到房子下,大声吼叫起来:“你个死娃崽,快给我下来,快给我下来!”
箩筐被我的吼叫吓住了,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吼他,而且吼得这么凶。箩筐犹豫了一下,才撅着屁股,顺着断墙一点点往下爬。
籮筐的脚刚一着地,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抬手就是一耳光:“叫你别乱跑,你爬这么高!”
箩筐哇地哭了起来,眼泪像山泉水一样往外涌。
突然,轰隆一声,那一间半平房在箩筐身后瞬间坍塌,腾起一团团烟雾。
我拉着箩筐,一下跑出好远,一把抱住他,放声哭了出来:“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让我还怎么活?”
箩筐伸出又凉又脏的手,为我擦拭眼泪:“哥,今后我不乱跑了,我一定听你的话!”
我们坐在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树下吃包子。我本来打算继续给箩筐讲哈拉奇的,但找到新住处才是眼前最要紧的事。
要离开的时候,我又去那堆废墟前站了好一会儿。前不久,在一个小摊上,我给箩筐弄了件皮夹克,很厚实,里面都是毛,过段时间入冬了,他穿着应该不会冷。我真的想一块砖一块砖地扒,把那件皮夹克给扒出来。但看着小山似的碎砖头,我放弃了,箩筐能好好的,一件衣服算什么,想法再弄就是了。
天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在那个工地的另一边找到了又一处废弃房。
其实,如果进城去的话,废弃房很容易找到,而且条件会更好,但那样很容易被人们发现,发现了就很容易被送到派出所或是救助站,然后那些人就会想法找到你的家,把你送回去。我和箩筐都不想那样子。
这处废弃房共两间,还挺结实,里面居然还有两条旧沙发,估计主人才搬离不久。
我把怀里剩下的两个包子都掏出来,咽了一下口水,全给了箩筐。箩筐只接下一个。我哄他说,早上弄到包子时,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现在饱得很,一点不饿,就把另一个也塞他手里了。
看着箩筐吃好后,天已全黑了,远处的灯火全都亮了起来。我该行动了,就说:“箩筐,你在这等着我!”
箩筐往房间的黑暗里瞄了一圈,又抬头看了看窗外的灯光,赶紧一把拉住我,说:“哥,我跟你一起去!”
我本想把他往沙发上摁的,但一想到白天他受到的惊吓,就打住了。平时,我要干活是坚决不会带上他的。他当然知道我干的是什么活,但我很不想在干活时让他看到。
我没说话,站起来就往门外走。没走几步,身后的房里传出来嘤嘤嘤的哭声。以前,每当我要出去了,他总会哭,但我都是硬着心肠迈步就走。
可是这次,箩筐的哭声比任何一次都要响,让人压抑得很。我叹了一口气,住下了脚。箩筐的哭声立马止住了,哧溜一下钻了出来,拉住我的衣角。
我牵着箩筐,在黑夜里向工地摸过去。
夜风有些冷了,我把身上的棉外套脱下来,反手就给箩筐穿上。箩筐没有挣扎,他知道挣扎也没用,乖乖地让我把拉链拉得严严实实。这件外套长了些,穿上之后反而把他衬托得更加瘦小。记得刚见到他时,他是胖乎乎的,两年过去了,他不但没长得更高更胖,反而变得更单薄了。我鼻子隐隐有些发酸,决心想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但箩筐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工地边上,几个吊塔上的灯都亮着,照得四处雪一样亮,偶尔还听到有人在干活,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夜色中显得更加清晰。我们还是来得早了些,只好先在一处暗影中躲起来。
天上的星星很多。平常这时候,我和箩筐,仰望着星光,无边无际地聊着。我们会更多地聊到哈拉奇。
哈拉奇是我还在上学时,在一本书里看到的,书里写了很多神秘的地方,很吸引人,但我唯一记得清晰的就是哈拉奇。这是一面消逝已久的湖,我没弄清楚它在哪里,但我知道它一定也在我所看到的星光之下。本来,今晚该借着这满天的星光,说一说哈拉奇里的湖水到底都去哪里了,可我们这时候都不能说话,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看近处的灯塔,又看看天上的繁星。
箩筐的大眼睛在暗夜里忽闪忽闪的,很亮。十岁的他,此时最应该靠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可他却没有家。箩筐五六岁时,记些事了,印象中的爸妈是一对冤家,一见面就大打出手,打了差不多一年,两个人就离婚了,谁也不愿意带箩筐,双双消失了,再没来看过箩筐一眼。他跟着爷爷生活了两年之后,爷爷一场大病撑不住去世了。孤苦伶仃的箩筐跟着叔叔生活了几个月,实在受不了叔娘的狠毒,在一次连吃了她的几个大嘴巴之后,箩筐离开了那个家,四处流浪。中途,箩筐被人送到派出所一次,被警察辗转送回了老家,但爸妈依然毫无音讯,他只在叔叔家呆了三天,又逃了出来,没多久就遇到了我。
工地上终于安静下来了,塔灯灭掉了好几盏,不再那么亮堂了,只有深秋的风刮得什么地方的铁皮咣当咣当响。
我按了按箩筐的头,说:“等着我!”然后猫着腰,很利索地翻过围栏,摸进了工地。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白天物色好的那堆铁扣件旁。我撑起一只蛇皮袋子,一件一件往里装。很快就装了半袋子,提起一试,足有百把斤,我狠狠心,又装了几件,一咬牙,抡到肩上,往回摸去。
我虽然还有两个月才满14岁,但个头至少比同龄人高出一头。在外面混了六七年,虽然没长肉,力气倒长了不少,一袋一百斤的水泥,我能轻松扛起来跑得飞快。
毕竟一整天只吃了两个包子,我感到手脚有些发软,走到箩筐身边时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我放下袋子想歇歇再走,箩筐叫了一声“哥”,然后咣咣咣地给我捶起背来。
见我终于喘平了气,箩筐扒开口袋,把几个扣件往外扒。我压低声音喝道:“箩筐,你干吗?”
箩筐说:“我拿几个,哥你少累点!”
“住手!”我的声音提高了些。但箩筐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一阵火起,抬手就扇了过去,很响的一声“啪”,箩筐歪倒在蛇皮袋子上,捂着脸抽泣起来。
我在夜色中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扳过箩筐的脸,使劲抹了几下,一把将他抱在胸前,长叹一声,说:“箩筐呀,你不能碰啊……你不能像哥这样,知道吗?你要做个好人!”
回到房里时,我已是一身汗水,躺在沙发上好长时间了才回过神来。肚子里更空了,我拎起可乐瓶,猛灌了一气。可乐瓶是路边捡的,水是公共厕所里的水龙头灌装的,有些异味,一点也比不上小时候家里的山泉水。
天刚微亮,我就爬了起来。肚子饿,根本睡不着,同时也要赶早出货。
籮筐睡得正香。我背起蛇皮口袋,轻轻走了出去。
我把扣件分成三份,只扛出来一份。每次出货不能太多,一是太显眼,二是太重了不方便赶路。几年下来,我卖过的东西可不少,主要是工地上的铁货。我是不敢直接对着钱下手的,毕竟那要面对人,我一个小孩子,没那方面手艺,也没那个胆。
十来天前,我和箩筐刚到这个城市。一出汽车货运站,拐个弯,钻进一片参差错落的居民区里,在一条巷子尽头,我看到了这家废品收购站。正好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四处望望之后,从怀里掏出一卷崭新的电缆,交给那个面无表情的店主老头。老头随便掂了掂,摸出几张纸票子拍在他手上。我当时想,这就是我和箩筐吃饭的路子了。
店主老头用眼睛挖了挖我,把蛇皮袋子提起来掂了掂,问:“捡的?”
“是!”我虽心虚,却把胸脯往上一挺。
“要是敢哄我,当心我敲死你!”店主老头的目光朝一把铁榔头瞟了一眼,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哗啦啦一下,把蛇皮袋子里的东西全倒进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中间。然后,又痛痛快快地拍给我一小叠钞票。我数了数,居然差不多两百块。那一刻,我突然对这个店主老头充满了感激,要不是他这小店,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弄到钱。
在路边一个摊上,我连吃了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粉,又痛快地灌了一瓶矿泉水。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是采买一些吃的东西。我想,我都吃上了羊肉粉,必须给箩筐带上些更好的东西。
我连跑了几个店,先后买了几个汉堡包,几包火腿肠,两挂香蕉,几个熟鸡蛋,外带一大袋粗面包。最后,在一个烤肉摊上烤了好几串牛肉串,箩筐好久没吃上肉了,得让他好好解解馋。我把这些东西拢在蛇皮袋子里,已经足足小半袋了,挺沉。
就要往回赶时,我看到一个和箩筐差不多大小的男娃子,穿了件火红的皮夹克,还有雪白雪白的毛领子,特好看,也觉得特暖和。
我扭身走进附近一家商场,照着那皮夹克的模样到处找。几趟转下来,终于在一家童装店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但我没选大红色的,而是选了款黑不溜秋的。没法子,我和箩筐这样东躲西藏,穿那大红大红的,太显眼。不过,一问价格,死活要三百多。
我盯着那件皮夹克,看了好久,越看越觉得这衣服就是为箩筐量身定制的,穿上去肯定再合适不过了。
我咬了咬牙,忙往回赶。回到住处,没跟箩筐多说,放下吃的,背起剩下的铁扣件又往废品店里赶。这次,那店主老头给了我两百多块,不过,他恶狠狠地说:“下回,你捡点别的,不要再捡这个了,人家哪有这么多给你捡,是不是?”
我顺利地买到了那件皮夹克。我想起我们那房子背后有个水凼子,于是又买了块香皂,心想着就在水凼边,把箩筐的脸和手洗干净了,再穿上这件黑夹克,里里外外透着香,那他该有多开心啊!
箩筐一见到新衣服,果然两眼放着光,把脸埋进去,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闭着眼睛笑嘻嘻地说:“安逸,舒服,巴适!”
“哥,你的呢?”箩筐眨巴着眼睛问我。
“我是大人了,身体好,这一身也足够厚!”我边说边把他的新夹克叠好,装进袋里。冬天已经不远了,但我心里很踏实。
那水凼其实是一口废弃了的水井。蹲在井边,我给箩筐洗脸洗手。他说他自己洗的,可我不让。其实是我很享受给他洗脸洗手时的感觉。我边洗就边给他说着哈拉奇。
我拿着香皂,在他臉上抹几个来回,抹出了一层泡泡,我说:“之前的哈拉奇,里面汪满了水,水里都是鱼,那些个鱼啊,像你的脸蛋一样溜溜的滑,又滑又好看!”
我拿着香皂在箩筐的左手上抹,抹出了一层泡泡。“哈拉奇的四周啊,都长满了绿油油的草,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要是箩筐你在那里,采啊采啊,一下子就采了一大把,手里都拿不过来了。”
我又拿着香皂在箩筐的右手上抹,抹出了一层泡泡。“哈拉奇的四周啊,飞着一只只小鸟,鸟们都长着好看的羽毛,要是箩筐你在那里啊,手一抬,一只鸟就站到你手上了,呀呀呀,多好看的鸟啊!”
箩筐咯咯咯地笑着,露出小小的白白的牙,整个脸蛋透着一缕很好闻的清香味道。
洗了脸和手的箩筐,呆呆地望着水凼里的水,问我:“哥,你说,哈拉奇有水时真的也这么清这么亮?”
我说:“哈拉奇有水的时候,可比这清多了,白天洒满了阳光,像是下了一湖的金子,晚上,撒满了星光,像是铺了一湖的银子!”
此后好几个晚上,我们都坐在水井边,看天空的星星,看城里的灯火,继续着哈拉奇的话题。
读到《哈拉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我还记得我们班上的那个女老师,长得很好看,见我喜欢看书,特意给了我一本,书中写了好多漂亮的地方。这本书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一篇文章都很美。其中一篇写的是一面叫哈拉奇的湖,我一直在想,那么漂亮的湖,为什么后面就消失了呢?也许就是因为心中这个疑问,我对这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其他的全都模糊了。
我喜欢看书,是因为我的爸妈。
刚上幼儿园那会儿,爸妈一吵架,我就哭,一哭就要挨打。爸用鞋底板扇,妈用衣架抽。爸不敢打妈,妈发起疯来敢操菜刀。妈也不敢打爸,爸冒起火来敢把房子给点了。两个人就都拿我出气。后来,我不敢哭了,只要这两个人一吵架,我就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小人书,后来看童话书。我识字用的是拼音,奶奶教我的。这些书都是奶奶买给我的,可惜她死了,别人都说是被我爸妈给气死的。别的娃娃上小学时认的字很少,可是我已经开始看整本的书。
就在老师把那本书送给我的当晚,回到家时,爸和妈正在吵架。喝了酒的爸像头狮子,一酒瓶敲在妈脑袋上,顿时就满头是血。妈也不示弱,操起砧板上的菜刀就挥了过去,一刀砍在爸的手臂上,溅了一地的血。我当时被吓晕过去了,等我醒来时,这两个人都不见了,我以为是到医院去了,结果很多天也没回来,等我上完了那个学期的课,还是没见回来。爸的弟弟和妈的弟弟两人干了一架之后,再也没人管我了。
没多久的一个晚上,我悄悄跑回学校,把那本书从那个老师的门下塞了进去,然后一个人悄悄扒上一辆开往外地的货车后厢,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几年下来,我都记不得我到底到过几个城市了。
冬天很快就到了。
风像刀子一样往房里钻,一天到晚呼隆隆呼隆隆吼叫着。我和箩筐整天整夜地躺在房子里,饿了就吃干粮,渴了就喝矿泉水。我们偶尔也会出门活动活动。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说这地方要是下雪了会是什么样,也说下雪后的哈拉奇会是什么样,说大雪过后的哈拉奇是不是就会有水了。箩筐白天黑夜都穿着那件新买的黑夹克,把手插在衣袖里,他说真暖和,比烤大火炉还要暖和。
备下的干粮应该足够个把星期,但不能坐吃山空,我每隔几天就要出去走走,想法子把吃的喝的好好补充补充。我出去的时候,箩筐就一个人呆在房子里,前些天我在集市的旧货摊上淘到了一些小玩具和小人书,他可以用这些打发时间。
玩玩具需要我们两个一起玩,可那小人书就不同了,他可以一个人看,每次看起来都很专注,每本都要翻看好几回。从我们在一起以后,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教箩筐识字,他挺聪明的,两年下来,已经能看一些简单的儿童书籍了。我甚至打算,明年春天,就开始教他写字,都十岁的娃儿了,可不能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
一天下午,我在街上逛了好一会儿,还没有弄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了,要是能弄到小废品店需要的东西最好,换了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如果实在弄不上钱,就只有顺货了。顺货时,总要找一些看起来面相凶狠的,总是板着脸的,喜欢斜着眼睛看人的,说起话来像是训人的,总是对着顾客双手叉腰的,张口就随地吐痰的,特别是动不动就凶小孩子的。看到这些人,我禁不住心里恨恨的,总是想着法子顺他们的货。
转到天黑,才顺到了几个面包,几根火腿肠,几个水果,几小包酸奶,还有一小袋怪味胡豆。顺怪味胡豆时,还差不多被逮住了。当时,那横眉竖眼的店主人正在埋头看手机,我悄悄走近了,一只手抓起那袋怪味胡豆,另一只手随着也伸了出去,想要再捞点别的,没想到那人抬起了头,大喝一声,就蹿了出来,那人个头挺高,一步就蹿到了门口,眼看就要逮住我了,没料到他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差不多摔倒了。我一锉身,早钻进了人群里。
回来路上,我心想,看来,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是哪天真的被逮住了,箩筐怎么办?想着想着,我就想到了将来。我总要长大的,箩筐总要长大的,难道我们就这样流浪一辈子?不行,箩筐得到学校读书,我只能带着他读点小人书,别的我可就教不了他了。我也要学干点正事了,既然是箩筐的哥,就要给箩筐做个好的榜样。还有十来天,我就满十四岁了,我决心从生日那天起,就洗手不干这些顺东西的事了,从此干干净净地做人。
回到住处,天已黑,站在门口,我叫了声“箩筐”,没声。又叫了几声,还是没人应。我吓了一跳。平时无论多晚,我回来时不用我叫唤,箩筐都会从黑暗里蹿出来,一把抱住我,一个哥接一个哥地喊着,粘上好半天。
我扔下怀里那堆东西,就在黑暗里摸索起来。我摸到了箩筐的腿,但他没动。我心里一紧,就往他脸上摸去。脸好烫,再摸摸额头,更烫。我赶快把他整个人抱起来,感觉他全身像是着了火,像是刚从火膛子里捞出来的。我拼命地晃着箩筐,带着哭腔大声唤他。
“哥,你回来了!”箩筐终于出了声,但声音很弱。
“筐,你怎么啦?是不是感冒了!”
“天黑了,我怕,一直在门口等你回来……我怕你不回来了!”
我脸上已满是泪水。我在黑暗里摸了一瓶水,摸索着给他灌了几口。又在角落里拉起几件旧衣服给他盖上。但箩筐吃力地说:“哥,我冷!”
我感到箩筐的身子开始发抖。我上学时,有个同学是个瘸子,说话也不利索,听说就是感冒后打摆子给弄那样的。
我哭出了声音:“筐,你别吓我!”
我奔出门去,门外更黑了,远处的灯光有气没力地亮着,风吼得更来劲了,那样子似乎要把这房顶给揭了。泪水在我眼前横着飞,我不再觉得冷,心里急得上了火。
我转身冲进房里,扶起箩筐,往背上一拉,就往门外奔去。
在夜色里,我的脚步迈得飞快。以前还没遇上箩筐时,我外出顺货大都是在晚上,练就了夜行的功夫。
走出草地,穿过工地,城市的灯光照亮了脚下的路,我走得更快了,发疯似的往前奔,口里一直唤着:“筐,筐,你不要睡着好不?跟哥说句话好吗?”但箩筐昏沉沉的,一句话没说,只听到他越来越粗重的呼吸。
终于,在一处街角,我发现了一家诊所,虽然已是半夜,但灯居然还亮着。
我挟着一股寒风,咣当一下撞开了诊所的玻璃门,然后和箩筐一起重重地摔倒在里面的一条沙发上。
里间走出一个六十来岁样子的老医生,架着一副四方眼镜,宽松的白大褂套在又瘦又细的身躯上。
老医生没有说话,轻轻把我拉开,伸出枯瘦的手,给箩筐摸摸脸,捏捏手,看看眼睛和舌苔,问了句:“烧这么厉害,咋才来?”
我没说话,只是紧紧地握住箩筐的手,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医生。
老医生问我:“姓名?你是他什么人?”
我说他叫箩筐,我是他的哥。
“你们父母呢?”
我低下头,半天才说话:“我们没有父母,我们是孤儿!”
老医生盯着我俩看了好一会儿,不再说话,示意我把箩筐抱到里间一张病床上。
老医生不紧不慢地配药,皮试,挂瓶,插针,给箩筐输液。
箩筐本来只是似睡非睡,这下沉沉睡去了。我握着他火烫的手,一动不动地看着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流。
相邻的一张床上,一个病人刚好输完了液,对那老医生说:“感觉好多啦……这都输了一天了,该多少钱?”
老医生用笔在一张单子上划拉了一会儿,抬头说:“差不多600块!”
我在旁边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摸了摸放钱的地方。我想,箩筐这液输下来,估计也是几百块,但我的兜里已分文全无。
快天亮时,箩筐终于退烧了,但医生说:“再观察一早上,应该还要再输一次液!”
东方夜空上露出一丝亮光的时候,箩筐醒过来了。我摸了摸他的脸,说:“你好好再睡会儿,我给你弄早餐去!”
箩筐从兜里摸索着掏出一块面包,说:“哥,这有呢,一人一半!”
我哄他说:“你身体虚,我给你去弄点热乎的。”
我俯下额头,贴了一下箩筐的脸,拉开玻璃门,扑入寒风里。
天还太早,街上行人很少,开门的店子不多。我漫无目的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路过几个开了门的店子前,店主不是眉开眼笑的,就是慈眉善目的,或者干脆就是可怜巴巴的。
一家挺大的电器商店,一溜长的电卷门已经打开,一男一女走出来,拿着扫把清扫门前道上的落叶。男人魁梧的身躯背对着我,粗壮的手臂看起来很有力气。看样子这应该是个凶巴巴的男人,我想,就是这了。
我正盘算着怎么瞅个机会,猫着腰,钻进他的店里去,他转过身来,看到了我,抬起头,笑了笑,对那女的说:“你看看,这小兄弟多勤快,这么早!”他笑着的时候甚至现出来两个隐隐约约的酒窝,不但看不出来半点凶相,反而让人觉得很亲切很温和。
我赶忙加快脚步往前走。街面上的人稍微多了些,都在风中使劲缩着脖子。可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我的目光四处梭巡,希望尽快找到目标。
我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
正当我完全失望的时候,在一条巷子前,似乎听到从里面传出来小孩子的哭声。我驻下足,往巷子里面张望,没见到人影,但那哭声却越来越分明。
我犹豫了一下,就向巷子里跑去。
巷子尽头,哭声停了,却听到有人在大声嚎叫。
那是一座小院子,一栋三层楼前,一辆小轿车,一男一女两个大人站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小女孩肩头一抽一抽的,正在抹眼睛。
女人抖着手指头,戳著小女孩的额头,比一只母狗还凶:“再哭,我撕破你的嘴!”
那男的双手叉着腰,两眼刀子似的直盯着小女孩。
那女人继续对小女孩吼道:“我不是你亲妈,你在这个家,你就得听我的话!”
那男的似乎失去了耐性,也指着小女孩吼了起来:“你到底上不上车?”
小女孩没动,继续抹眼睛。
那男的一抬脚,把小女孩踹倒在地,抓起她,拉开车门,扔了进去。
两个大人随后骂骂咧咧地上了车。那车一声吼叫,蹿出院门,卷起一阵落叶,很快消失在巷子的另一头。
我禁不住歪进院门,围着那栋楼房转起来。
没转完一圈,我突然发现有一扇房门是开着的。我蹲在不远处的花坛后面,从一个盆景里捡起一块石头往门里扔。里面传出来啪啪两声,然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我又捡起一块,又扔了一次,还是没动静。一定是那一男一女忙着训小女孩,气头上就忘了关门了。
摸进房里后,我很准确地找到了主人所在的卧房。只翻到了第二个抽屉,就发现了一沓钱,全是红通通的百元大钞。
钞票用一个长尾夹夹着,足足有一指头厚。我从里面迅速抽出六张,把剩下的夹好,放回原处,关上抽屉。我正要蹿出门,脑子里又浮现出小女孩抽泣的模样,她的两只小羊角辫伤心地颤抖着。
我驻下脚,打量起这个屋子来,才发现这是个极奢华的所在,叫不上名儿来的高档家具,处处透露出让人畏惧的富贵气。可是,靠墙边上的一口鱼缸里,水早已干涸,缸壁上满是污迹,缸底一层鹅卵石上覆着几具死金鱼的灰白尸体,让这个又大又漂亮的屋子了无生气。也许,那小女孩每天都会看着这个空空的金鱼缸悄悄流泪吧。多可怜的小女孩。那两个大人为什么对她那么凶呢?
我一咬牙,扭过身,又钻进了那间卧房,拉开抽屉,把钱全部拿了出来。离开时,我重重地把屋门给摔了一下。
我回到诊所,箩筐还在输液,他气色好了许多。我才记起竟然忘了给箩筐买吃的东西。箩筐说:“哥,我吃过东西了,好香好香的面条,热乎乎的!”箩筐边说边指了指在一张躺椅上睡得正香的老医生。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阳光,金闪闪一片。
看着箩筐好了起来,我打算结了账离开这里,到外面好好享受享受这暖暖的冬阳。
吊瓶里的药液即将滴完时,老医生醒了,给箩筐拔了针,说:“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我把手伸进怀里,问:“医生,多少钱?”
老医生本来已摘下了眼镜,听我这样问,又戴上了,从又薄又亮的镜片后面盯着我和箩筐看,说:“看样子你们也没钱……不要了,走吧……多穿点衣服,不要再来了就行!”
我拉着箩筐,深深地向老医生鞠了个躬,然后就出了门。没走几步,我从怀里抽出一小叠钞票,也不知道有多少,转过身,塞进了玻璃门,拉起箩筐就跑。
我和箩筐买了一堆吃的,又到农贸市场买了一袋子木炭。
冬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回到了住处。生起炭火后,整个屋子立马变得异样的暖和起来。风照样灌进来,但不再那么凶狠了。看着箩筐,看着红红的炭火,我感觉这个破门破窗的地方仿佛就是我们的家。
围着火堆,我们饿了吃东西,累了就在沙发上睡,睡不着的时候就说话。说大街上的汽车,房子,好看的衣服,飘着香气的北京烤鸭。但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哈拉奇。
“哈拉奇会下雪不?”箩筐问。
“应该不会吧,那样的话,应该就会有水了!”我想了想说。
“那哈拉奇会有这么冷不?”
“没到过咋知道?”
“那等明年春天了,我们看看哈拉奇去!”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哈拉奇,就这样一直过了好几天。
这天早上,我看吃的东西该补充了。刚一出门,才发现到处都白了,厚厚的一层雪,踩上去没掉了脚背。
箩筐闹着要我和他玩会儿雪。拗不过,只好和他扔了会儿雪球。扔他的时候,我故意扔偏了,怕把他弄疼了。他扔我的时候,我尽量迎上去,让雪球在我身上簌簌簌地开花。箩筐开心得止不住地笑。只要他开心了,让我怎么做都可以。
当我抟好一个雪球又要扔出去的时候,箩筐突然住了手,止住了笑,愣愣地望着我。我正莫名其妙,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哟嗬,玩得很开心哩!”
我转过身,是两个人,一高一矮。我再定神一看,吓得尿都出来了,他们全都穿着青蓝色的警服。我每次见到警察都会绕着走,以前是怕他们把我送回老家去,现在是怕他们把我扔到里面去,如果那样,箩筐怎么办?
我想撒腿就跑,可脚下根本不听使唤,高个子警察跨前一步,揪住了我的胳膊,矮个子亮出一张照片,对着我比对了一下,说:“没错,应该就是这小子!”
派出所里,暖暖的热气让人很是舒服。
矮个子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对他说我没名字,或者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又觉得不妥,想了想,说:“我叫哈拉奇!”
“哈拉奇?哪个哈?哪个拉?哪个奇?”
“哈拉奇的哈,哈拉奇的拉,哈拉奇的奇!”我说。
两个警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这两个警察其实一点都不凶,好像还很喜欢逗小孩子。特别是那高个子,在来派出所的路上,笑盈盈地给箩筐说过好几个笑话,还好几次抚过他的头。
我解释说:“笑哈哈的哈,拉拉扯扯的拉,奇奇怪怪的奇!”
矮个子问高个子:“有这个姓?”
高个子也是一脸茫然:“没听说过!”
“那你父母叫什么名?”矮个子又问。
我低下头,不说话。我不想再提他们。
矮个子把笔的一头含在嘴里,偏着脑袋看着我。
我不知道沉默了多久,才仰起脸,看着天花板说:“我没有爸,也没有妈,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娃儿怎么这么说话?”高个子有点生气了。
无论他们再怎么问,我不再说话。
在我这里问不出啥名堂,两个警察便去了另一个房间。我知道,他们问箩筐去了。
我根本不用擔心箩筐,两个警察对他很好,从一进派出所,不光买饭,找小人书看,还给他往手上擦蛇皮膏,说他的手都冻裂了。
我身上剩下的钱,都退了回去。那两个人来领钱时,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执意要给我和箩筐留一些,但被我回绝了。高个子让我向那两个人道个歉,我使劲把脖子一梗,把头往后一拧。
最后,我听到箩筐在隔壁大声说:“叔,姨,我们错了……那天,如果你们不打你们家小妹妹,我哥肯定不会拿你们的钱!”
第二天一早,两个警察带着我和箩筐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理发店。
“像个小刺猬一样,蓬头垢脑的!”高个子警察说。
嚓嚓嚓,电剪子的声音轻匀而响亮。
“这么一打理,其实也挺好看的!”矮个子轻轻捏了一下箩筐瘦瘦的脸。
店里墙面上有台液晶电视,正播着新闻节目:“……干涸了300年的哈拉奇又回来了,形成了五平方公里左右的湖面,沿河芦苇等植被恢复了生长,又呈现出了一片绿色的气息……”
“哈拉奇又回来了,哥!”箩筐向我扭过头来,两个小酒窝若隐若现。
我的眼前升起一片片盎然的绿意,仿佛听到了一阵阵潺潺的水声。
两个警察又是你看我,我看你。
我扭过头去,笑着对箩筐说:“是的,哈拉奇回来了!”
这一天,正是我十四岁生日。
责任编辑 婧 婷
哈拉奇回来了
李启发
李启发,贵州独山人,1972年10月生,布依族,现供职于独山县教育局。小说作品主要发表于《贵州作家》《山花》《芳草》《小小说》《微型小说选刊》《短小说》《文学港》《夜郎文学》等。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班学员,贵州文学院第一、二届签约作家。曾获黔南州政府文艺奖。
我跟箩筐说,哈拉奇是一个湖,已经干了300多年了。
秋阳照在箩筐仰起的脸上,他问:“那300多年前,哈拉奇的水一定挺多的喽?”
我知道箩筐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而我们的肚子已经饿极了,必须赶快去弄点吃的。我边向屋外走去,边大声叮嘱他不要乱跑。
“哥,那你早点回,我怕!”箩筐在那堆破棉絮里缩成一团。
到这地方虽然没多久,但我已经踩好了点,穿过草地,经过一个工地,就到了街边一个包子店。那胖乎乎的女店主总是板着脸,每天早上,她都要抽空送娃娃去不远的幼儿园,那时正好下手。我本来无意盯上她家的,可是,我第一次经过她店门前时,她正红着脸,狠狠扯她娃儿耳朵,嫌娃儿出门时的动作慢了些。当时听着那娃儿杀猪般的嚎叫,我决定今后想吃包子了,就专门吃她家的。
店主前脚刚走,我就从容地走过去,揭开屉笼,迅速抓起热乎乎的包子,两个,四个,六个,往棉外套里塞。我还想再抓两个,看到街对面小店里,一个老头儿愣神向这边张望。我心里有些紧张,忙把怀里六个包子顺了顺,揣好,转身就跑。
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盘算,我和箩筐一人吃两个,留下两个,防备晚上找不到吃的。
我眼前浮现出箩筐吃包子的模样,双手捧着,闻个够,然后大口咬开,嚼着,黑里透红的脸,笑得像朵花。
箩筐跟着我快两年了。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白白的脸蛋,随便一笑就是两个可爱的小酒窝。现在,无论他怎样努力地笑,再也看不到那酒窝了。营养不良,加上不常洗脸,皮肤已变得很粗糙,根本不像个十岁的娃儿。
我有点后悔给他取名叫箩筐。见到他时,他正在一只箩筐里睡得香,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擦着泪花说叫罗小狗。我说,那还不如叫你箩筐。后来,我发现他的饭量比我还大,我吃一个盒饭,他吃两盒。我甚至怀疑就是因为我叫他箩筐之后,他的小肚皮才那么能装的。我倒不是嫌他吃得多,而是担心弄不到东西吃的时候,他会饿得慌。
又经过工地时,我放慢了脚步。我发现这里工人不多,都在不紧不慢地做着活,应该是在打地桩,或许这地方今后要造几栋高楼。地上很随意地摆放着一堆一堆的钢筋和扣件。我经常听人说,那些造高楼的商人心里都是黑的。于是我心里有底了,我想,我和箩筐至少一两个月的吃喝应该能有着落了。
包子很热,我拉開衣服上的拉链,香味清晰地蹿进我的鼻子。我想,等一下,我和箩筐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包子,一边继续给他说哈拉奇。一抬头,却看见草地那边的房顶上有个小人影,细细一看,正是箩筐。他也看见了我,一边挥着手叫着哥,一边蹦跳起来。
我急坏了,这几天我注意观察了,这房子所在之处虽然偏僻安静,但房子太旧,三间房垮掉了一间半,剩下一间半的墙上已满是裂缝。我这几天正在到处物色新住处,住在这房里太危险。
我一阵风似的跑到房子下,大声吼叫起来:“你个死娃崽,快给我下来,快给我下来!”
箩筐被我的吼叫吓住了,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吼他,而且吼得这么凶。箩筐犹豫了一下,才撅着屁股,顺着断墙一点点往下爬。
箩筐的脚刚一着地,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抬手就是一耳光:“叫你别乱跑,你爬这么高!”
箩筐哇地哭了起来,眼泪像山泉水一样往外涌。
突然,轰隆一声,那一间半平房在箩筐身后瞬间坍塌,腾起一团团烟雾。
我拉着箩筐,一下跑出好远,一把抱住他,放声哭了出来:“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让我还怎么活?”
箩筐伸出又凉又脏的手,为我擦拭眼泪:“哥,今后我不乱跑了,我一定听你的话!”
我们坐在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树下吃包子。我本来打算继续给箩筐讲哈拉奇的,但找到新住处才是眼前最要紧的事。
要离开的时候,我又去那堆废墟前站了好一会儿。前不久,在一个小摊上,我给箩筐弄了件皮夹克,很厚实,里面都是毛,过段时间入冬了,他穿着应该不会冷。我真的想一块砖一块砖地扒,把那件皮夹克给扒出来。但看着小山似的碎砖头,我放弃了,箩筐能好好的,一件衣服算什么,想法再弄就是了。
天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在那个工地的另一边找到了又一处废弃房。
其实,如果进城去的话,废弃房很容易找到,而且条件会更好,但那样很容易被人们发现,发现了就很容易被送到派出所或是救助站,然后那些人就会想法找到你的家,把你送回去。我和箩筐都不想那样子。
这处废弃房共两间,还挺结实,里面居然还有两条旧沙发,估计主人才搬离不久。
我把怀里剩下的两个包子都掏出来,咽了一下口水,全给了箩筐。箩筐只接下一个。我哄他说,早上弄到包子时,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现在饱得很,一点不饿,就把另一个也塞他手里了。
看着箩筐吃好后,天已全黑了,远处的灯火全都亮了起来。我该行动了,就说:“箩筐,你在这等着我!”
箩筐往房间的黑暗里瞄了一圈,又抬头看了看窗外的灯光,赶紧一把拉住我,说:“哥,我跟你一起去!”
我本想把他往沙发上摁的,但一想到白天他受到的惊吓,就打住了。平时,我要干活是坚决不会带上他的。他当然知道我干的是什么活,但我很不想在干活时让他看到。
我没说话,站起来就往门外走。没走几步,身后的房里传出来嘤嘤嘤的哭声。以前,每当我要出去了,他总会哭,但我都是硬着心肠迈步就走。
可是这次,箩筐的哭声比任何一次都要响,让人压抑得很。我叹了一口气,住下了脚。箩筐的哭声立马止住了,哧溜一下钻了出来,拉住我的衣角。
我牵着箩筐,在黑夜里向工地摸过去。
夜风有些冷了,我把身上的棉外套脱下来,反手就给箩筐穿上。箩筐没有挣扎,他知道挣扎也没用,乖乖地让我把拉链拉得严严实实。这件外套长了些,穿上之后反而把他衬托得更加瘦小。记得刚见到他时,他是胖乎乎的,两年过去了,他不但没长得更高更胖,反而变得更单薄了。我鼻子隐隐有些发酸,决心想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但箩筐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工地边上,几个吊塔上的灯都亮着,照得四处雪一样亮,偶尔还听到有人在干活,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夜色中显得更加清晰。我们还是来得早了些,只好先在一处暗影中躲起来。
天上的星星很多。平常这时候,我和箩筐,仰望着星光,无边无际地聊着。我们会更多地聊到哈拉奇。
哈拉奇是我还在上学时,在一本书里看到的,书里写了很多神秘的地方,很吸引人,但我唯一记得清晰的就是哈拉奇。这是一面消逝已久的湖,我没弄清楚它在哪里,但我知道它一定也在我所看到的星光之下。本来,今晚该借着这满天的星光,说一说哈拉奇里的湖水到底都去哪里了,可我们这时候都不能说话,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看近处的灯塔,又看看天上的繁星。
箩筐的大眼睛在暗夜里忽闪忽闪的,很亮。十岁的他,此时最应该靠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可他却没有家。箩筐五六岁时,记些事了,印象中的爸妈是一对冤家,一见面就大打出手,打了差不多一年,两个人就离婚了,谁也不愿意带箩筐,双双消失了,再没来看过箩筐一眼。他跟着爷爷生活了两年之后,爷爷一场大病撑不住去世了。孤苦伶仃的箩筐跟着叔叔生活了几个月,实在受不了叔娘的狠毒,在一次连吃了她的几个大嘴巴之后,箩筐离开了那个家,四处流浪。中途,箩筐被人送到派出所一次,被警察輾转送回了老家,但爸妈依然毫无音讯,他只在叔叔家呆了三天,又逃了出来,没多久就遇到了我。
工地上终于安静下来了,塔灯灭掉了好几盏,不再那么亮堂了,只有深秋的风刮得什么地方的铁皮咣当咣当响。
我按了按箩筐的头,说:“等着我!”然后猫着腰,很利索地翻过围栏,摸进了工地。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白天物色好的那堆铁扣件旁。我撑起一只蛇皮袋子,一件一件往里装。很快就装了半袋子,提起一试,足有百把斤,我狠狠心,又装了几件,一咬牙,抡到肩上,往回摸去。
我虽然还有两个月才满14岁,但个头至少比同龄人高出一头。在外面混了六七年,虽然没长肉,力气倒长了不少,一袋一百斤的水泥,我能轻松扛起来跑得飞快。
毕竟一整天只吃了两个包子,我感到手脚有些发软,走到箩筐身边时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我放下袋子想歇歇再走,箩筐叫了一声“哥”,然后咣咣咣地给我捶起背来。
见我终于喘平了气,箩筐扒开口袋,把几个扣件往外扒。我压低声音喝道:“箩筐,你干吗?”
箩筐说:“我拿几个,哥你少累点!”
“住手!”我的声音提高了些。但箩筐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一阵火起,抬手就扇了过去,很响的一声“啪”,箩筐歪倒在蛇皮袋子上,捂着脸抽泣起来。
我在夜色中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扳过箩筐的脸,使劲抹了几下,一把将他抱在胸前,长叹一声,说:“箩筐呀,你不能碰啊……你不能像哥这样,知道吗?你要做个好人!”
回到房里时,我已是一身汗水,躺在沙发上好长时间了才回过神来。肚子里更空了,我拎起可乐瓶,猛灌了一气。可乐瓶是路边捡的,水是公共厕所里的水龙头灌装的,有些异味,一点也比不上小时候家里的山泉水。
天刚微亮,我就爬了起来。肚子饿,根本睡不着,同时也要赶早出货。
箩筐睡得正香。我背起蛇皮口袋,轻轻走了出去。
我把扣件分成三份,只扛出来一份。每次出货不能太多,一是太显眼,二是太重了不方便赶路。几年下来,我卖过的东西可不少,主要是工地上的铁货。我是不敢直接对着钱下手的,毕竟那要面对人,我一个小孩子,没那方面手艺,也没那个胆。
十来天前,我和箩筐刚到这个城市。一出汽车货运站,拐个弯,钻进一片参差错落的居民区里,在一条巷子尽头,我看到了这家废品收购站。正好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四处望望之后,从怀里掏出一卷崭新的电缆,交给那个面无表情的店主老头。老头随便掂了掂,摸出几张纸票子拍在他手上。我当时想,这就是我和箩筐吃饭的路子了。
店主老头用眼睛挖了挖我,把蛇皮袋子提起来掂了掂,问:“捡的?”
“是!”我虽心虚,却把胸脯往上一挺。
“要是敢哄我,当心我敲死你!”店主老头的目光朝一把铁榔头瞟了一眼,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哗啦啦一下,把蛇皮袋子里的东西全倒进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中间。然后,又痛痛快快地拍给我一小叠钞票。我数了数,居然差不多两百块。那一刻,我突然对这个店主老头充满了感激,要不是他这小店,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弄到钱。
在路边一个摊上,我连吃了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粉,又痛快地灌了一瓶矿泉水。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是采买一些吃的东西。我想,我都吃上了羊肉粉,必须给箩筐带上些更好的东西。
我连跑了几个店,先后买了几个汉堡包,几包火腿肠,两挂香蕉,几个熟鸡蛋,外带一大袋粗面包。最后,在一个烤肉摊上烤了好几串牛肉串,箩筐好久没吃上肉了,得让他好好解解馋。我把这些东西拢在蛇皮袋子里,已经足足小半袋了,挺沉。
就要往回赶时,我看到一个和箩筐差不多大小的男娃子,穿了件火红的皮夹克,还有雪白雪白的毛领子,特好看,也觉得特暖和。
我扭身走进附近一家商场,照着那皮夹克的模样到处找。几趟转下来,终于在一家童装店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但我没选大红色的,而是选了款黑不溜秋的。没法子,我和箩筐这样东躲西藏,穿那大红大红的,太显眼。不过,一问价格,死活要三百多。
我盯着那件皮夹克,看了好久,越看越觉得这衣服就是为箩筐量身定制的,穿上去肯定再合适不过了。
我咬了咬牙,忙往回赶。回到住处,没跟箩筐多说,放下吃的,背起剩下的铁扣件又往废品店里赶。这次,那店主老头给了我两百多块,不过,他恶狠狠地说:“下回,你捡点别的,不要再捡这个了,人家哪有这么多给你捡,是不是?”
我顺利地买到了那件皮夹克。我想起我们那房子背后有个水凼子,于是又买了块香皂,心想着就在水凼边,把箩筐的脸和手洗干净了,再穿上这件黑夹克,里里外外透着香,那他该有多开心啊!
箩筐一见到新衣服,果然两眼放着光,把脸埋进去,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闭着眼睛笑嘻嘻地说:“安逸,舒服,巴适!”
“哥,你的呢?”箩筐眨巴着眼睛问我。
“我是大人了,身体好,这一身也足够厚!”我边说边把他的新夹克叠好,装进袋里。冬天已经不远了,但我心里很踏实。
那水凼其实是一口废弃了的水井。蹲在井边,我给箩筐洗脸洗手。他说他自己洗的,可我不让。其实是我很享受给他洗脸洗手时的感觉。我边洗就边给他说着哈拉奇。
我拿着香皂,在他脸上抹几个来回,抹出了一层泡泡,我说:“之前的哈拉奇,里面汪满了水,水里都是鱼,那些个鱼啊,像你的脸蛋一样溜溜的滑,又滑又好看!”
我拿着香皂在箩筐的左手上抹,抹出了一层泡泡。“哈拉奇的四周啊,都长满了绿油油的草,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要是箩筐你在那里,采啊采啊,一下子就采了一大把,手里都拿不过来了。”
我又拿着香皂在箩筐的右手上抹,抹出了一层泡泡。“哈拉奇的四周啊,飞着一只只小鸟,鸟们都长着好看的羽毛,要是箩筐你在那里啊,手一抬,一只鸟就站到你手上了,呀呀呀,多好看的鸟啊!”
箩筐咯咯咯地笑着,露出小小的白白的牙,整个臉蛋透着一缕很好闻的清香味道。
洗了脸和手的箩筐,呆呆地望着水凼里的水,问我:“哥,你说,哈拉奇有水时真的也这么清这么亮?”
我说:“哈拉奇有水的时候,可比这清多了,白天洒满了阳光,像是下了一湖的金子,晚上,撒满了星光,像是铺了一湖的银子!”
此后好几个晚上,我们都坐在水井边,看天空的星星,看城里的灯火,继续着哈拉奇的话题。
读到《哈拉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我还记得我们班上的那个女老师,长得很好看,见我喜欢看书,特意给了我一本,书中写了好多漂亮的地方。这本书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一篇文章都很美。其中一篇写的是一面叫哈拉奇的湖,我一直在想,那么漂亮的湖,为什么后面就消失了呢?也许就是因为心中这个疑问,我对这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其他的全都模糊了。
我喜欢看书,是因为我的爸妈。
刚上幼儿园那会儿,爸妈一吵架,我就哭,一哭就要挨打。爸用鞋底板扇,妈用衣架抽。爸不敢打妈,妈发起疯来敢操菜刀。妈也不敢打爸,爸冒起火来敢把房子给点了。两个人就都拿我出气。后来,我不敢哭了,只要这两个人一吵架,我就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小人书,后来看童话书。我识字用的是拼音,奶奶教我的。这些书都是奶奶买给我的,可惜她死了,别人都说是被我爸妈给气死的。别的娃娃上小学时认的字很少,可是我已经开始看整本的书。
就在老师把那本书送给我的当晚,回到家时,爸和妈正在吵架。喝了酒的爸像头狮子,一酒瓶敲在妈脑袋上,顿时就满头是血。妈也不示弱,操起砧板上的菜刀就挥了过去,一刀砍在爸的手臂上,溅了一地的血。我当时被吓晕过去了,等我醒来时,这两个人都不见了,我以为是到医院去了,结果很多天也没回来,等我上完了那个学期的课,还是没见回来。爸的弟弟和妈的弟弟两人干了一架之后,再也没人管我了。
没多久的一个晚上,我悄悄跑回学校,把那本书从那个老师的门下塞了进去,然后一个人悄悄扒上一辆开往外地的货车后厢,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几年下来,我都记不得我到底到过几个城市了。
冬天很快就到了。
风像刀子一样往房里钻,一天到晚呼隆隆呼隆隆吼叫着。我和箩筐整天整夜地躺在房子里,饿了就吃干粮,渴了就喝矿泉水。我们偶尔也会出门活动活动。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说这地方要是下雪了会是什么样,也说下雪后的哈拉奇会是什么样,说大雪过后的哈拉奇是不是就会有水了。箩筐白天黑夜都穿着那件新买的黑夹克,把手插在衣袖里,他说真暖和,比烤大火炉还要暖和。
备下的干粮应该足够个把星期,但不能坐吃山空,我每隔几天就要出去走走,想法子把吃的喝的好好补充补充。我出去的时候,箩筐就一个人呆在房子里,前些天我在集市的旧货摊上淘到了一些小玩具和小人书,他可以用这些打发时间。
玩玩具需要我们两个一起玩,可那小人书就不同了,他可以一个人看,每次看起来都很专注,每本都要翻看好几回。从我们在一起以后,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教箩筐识字,他挺聪明的,两年下来,已经能看一些简单的儿童书籍了。我甚至打算,明年春天,就开始教他写字,都十岁的娃儿了,可不能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
一天下午,我在街上逛了好一会儿,还没有弄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了,要是能弄到小废品店需要的东西最好,换了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如果实在弄不上钱,就只有顺货了。顺货时,总要找一些看起来面相凶狠的,总是板着脸的,喜欢斜着眼睛看人的,说起话来像是训人的,总是对着顾客双手叉腰的,张口就随地吐痰的,特别是动不动就凶小孩子的。看到这些人,我禁不住心里恨恨的,总是想着法子顺他们的货。
转到天黑,才顺到了几个面包,几根火腿肠,几个水果,几小包酸奶,还有一小袋怪味胡豆。顺怪味胡豆时,还差不多被逮住了。当时,那横眉竖眼的店主人正在埋头看手机,我悄悄走近了,一只手抓起那袋怪味胡豆,另一只手随着也伸了出去,想要再捞点别的,没想到那人抬起了头,大喝一声,就蹿了出来,那人个头挺高,一步就蹿到了门口,眼看就要逮住我了,没料到他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差不多摔倒了。我一锉身,早钻进了人群里。
回来路上,我心想,看来,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是哪天真的被逮住了,箩筐怎么办?想着想着,我就想到了将来。我总要长大的,箩筐总要长大的,难道我们就这样流浪一辈子?不行,箩筐得到学校读书,我只能带着他读点小人书,别的我可就教不了他了。我也要学干点正事了,既然是箩筐的哥,就要给箩筐做个好的榜样。还有十来天,我就满十四岁了,我决心从生日那天起,就洗手不干这些顺东西的事了,从此干干净净地做人。
回到住处,天已黑,站在门口,我叫了声“箩筐”,没声。又叫了几声,还是没人应。我吓了一跳。平时无论多晚,我回来时不用我叫唤,箩筐都会从黑暗里蹿出来,一把抱住我,一个哥接一个哥地喊着,粘上好半天。
我扔下怀里那堆东西,就在黑暗里摸索起来。我摸到了箩筐的腿,但他没动。我心里一紧,就往他脸上摸去。脸好烫,再摸摸额头,更烫。我赶快把他整个人抱起来,感觉他全身像是着了火,像是刚从火膛子里捞出来的。我拼命地晃着箩筐,带着哭腔大声唤他。
“哥,你回来了!”箩筐终于出了声,但声音很弱。
“筐,你怎么啦?是不是感冒了!”
“天黑了,我怕,一直在门口等你回来……我怕你不回来了!”
我脸上已满是泪水。我在黑暗里摸了一瓶水,摸索着给他灌了几口。又在角落里拉起几件旧衣服给他盖上。但箩筐吃力地说:“哥,我冷!”
我感到箩筐的身子开始发抖。我上学时,有个同学是个瘸子,说话也不利索,听说就是感冒后打摆子给弄那样的。
我哭出了声音:“筐,你别吓我!”
我奔出门去,门外更黑了,远处的灯光有气没力地亮着,风吼得更来劲了,那样子似乎要把这房顶给揭了。泪水在我眼前横着飞,我不再觉得冷,心里急得上了火。
我转身冲进房里,扶起箩筐,往背上一拉,就往门外奔去。
在夜色里,我的脚步迈得飞快。以前还没遇上箩筐时,我外出顺货大都是在晚上,练就了夜行的功夫。
走出草地,穿过工地,城市的灯光照亮了脚下的路,我走得更快了,发疯似的往前奔,口里一直唤着:“筐,筐,你不要睡着好不?跟哥说句话好吗?”但箩筐昏沉沉的,一句话没说,只听到他越来越粗重的呼吸。
终于,在一处街角,我发现了一家诊所,虽然已是半夜,但灯居然还亮着。
我挟着一股寒风,咣当一下撞开了诊所的玻璃门,然后和箩筐一起重重地摔倒在里面的一条沙发上。
里间走出一个六十来岁样子的老医生,架着一副四方眼镜,宽松的白大褂套在又瘦又细的身躯上。
老医生没有说话,轻轻把我拉开,伸出枯瘦的手,给箩筐摸摸脸,捏捏手,看看眼睛和舌苔,问了句:“烧这么厉害,咋才来?”
我没说话,只是紧紧地握住箩筐的手,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医生。
老医生问我:“姓名?你是他什么人?”
我说他叫箩筐,我是他的哥。
“你们父母呢?”
我低下头,半天才说话:“我们没有父母,我们是孤儿!”
老医生盯着我俩看了好一会儿,不再说话,示意我把箩筐抱到里间一张病床上。
老医生不紧不慢地配药,皮试,挂瓶,插针,给箩筐输液。
箩筐本来只是似睡非睡,这下沉沉睡去了。我握着他火烫的手,一动不动地看着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流。
相邻的一张床上,一个病人刚好输完了液,对那老医生说:“感觉好多啦……这都输了一天了,该多少钱?”
老医生用笔在一张单子上划拉了一会儿,抬头说:“差不多600块!”
我在旁边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摸了摸放钱的地方。我想,箩筐这液输下来,估计也是几百块,但我的兜里已分文全无。
快天亮时,箩筐终于退烧了,但医生说:“再观察一早上,应该还要再输一次液!”
东方夜空上露出一丝亮光的时候,箩筐醒过来了。我摸了摸他的脸,说:“你好好再睡会儿,我给你弄早餐去!”
籮筐从兜里摸索着掏出一块面包,说:“哥,这有呢,一人一半!”
我哄他说:“你身体虚,我给你去弄点热乎的。”
我俯下额头,贴了一下箩筐的脸,拉开玻璃门,扑入寒风里。
天还太早,街上行人很少,开门的店子不多。我漫无目的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路过几个开了门的店子前,店主不是眉开眼笑的,就是慈眉善目的,或者干脆就是可怜巴巴的。
一家挺大的电器商店,一溜长的电卷门已经打开,一男一女走出来,拿着扫把清扫门前道上的落叶。男人魁梧的身躯背对着我,粗壮的手臂看起来很有力气。看样子这应该是个凶巴巴的男人,我想,就是这了。
我正盘算着怎么瞅个机会,猫着腰,钻进他的店里去,他转过身来,看到了我,抬起头,笑了笑,对那女的说:“你看看,这小兄弟多勤快,这么早!”他笑着的时候甚至现出来两个隐隐约约的酒窝,不但看不出来半点凶相,反而让人觉得很亲切很温和。
我赶忙加快脚步往前走。街面上的人稍微多了些,都在风中使劲缩着脖子。可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我的目光四处梭巡,希望尽快找到目标。
我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
正当我完全失望的时候,在一条巷子前,似乎听到从里面传出来小孩子的哭声。我驻下足,往巷子里面张望,没见到人影,但那哭声却越来越分明。
我犹豫了一下,就向巷子里跑去。
巷子尽头,哭声停了,却听到有人在大声嚎叫。
那是一座小院子,一栋三层楼前,一辆小轿车,一男一女两个大人站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小女孩肩头一抽一抽的,正在抹眼睛。
女人抖着手指头,戳着小女孩的额头,比一只母狗还凶:“再哭,我撕破你的嘴!”
那男的双手叉着腰,两眼刀子似的直盯着小女孩。
那女人继续对小女孩吼道:“我不是你亲妈,你在这个家,你就得听我的话!”
那男的似乎失去了耐性,也指着小女孩吼了起来:“你到底上不上车?”
小女孩没动,继续抹眼睛。
那男的一抬脚,把小女孩踹倒在地,抓起她,拉开车门,扔了进去。
两个大人随后骂骂咧咧地上了车。那车一声吼叫,蹿出院门,卷起一阵落叶,很快消失在巷子的另一头。
我禁不住歪进院门,围着那栋楼房转起来。
没转完一圈,我突然发现有一扇房门是开着的。我蹲在不远处的花坛后面,从一个盆景里捡起一块石头往门里扔。里面传出来啪啪两声,然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我又捡起一块,又扔了一次,还是没动静。一定是那一男一女忙着训小女孩,气头上就忘了关门了。
摸进房里后,我很准确地找到了主人所在的卧房。只翻到了第二个抽屉,就发现了一沓钱,全是红通通的百元大钞。
钞票用一个长尾夹夹着,足足有一指头厚。我从里面迅速抽出六张,把剩下的夹好,放回原处,关上抽屉。我正要蹿出门,脑子里又浮现出小女孩抽泣的模样,她的两只小羊角辫伤心地颤抖着。
我驻下脚,打量起这个屋子来,才发现这是个极奢华的所在,叫不上名儿来的高档家具,处处透露出让人畏惧的富贵气。可是,靠墙边上的一口鱼缸里,水早已干涸,缸壁上满是污迹,缸底一层鹅卵石上覆着几具死金鱼的灰白尸体,让这个又大又漂亮的屋子了无生气。也许,那小女孩每天都会看着这个空空的金鱼缸悄悄流泪吧。多可怜的小女孩。那两个大人为什么对她那么凶呢?
我一咬牙,扭过身,又钻进了那间卧房,拉开抽屉,把钱全部拿了出来。离开时,我重重地把屋门给摔了一下。
我回到诊所,箩筐还在输液,他气色好了许多。我才记起竟然忘了给箩筐买吃的东西。箩筐说:“哥,我吃过东西了,好香好香的面条,热乎乎的!”箩筐边说边指了指在一张躺椅上睡得正香的老医生。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阳光,金闪闪一片。
看着箩筐好了起来,我打算结了账离开这里,到外面好好享受享受这暖暖的冬阳。
吊瓶里的药液即将滴完时,老医生醒了,给箩筐拔了针,说:“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我把手伸进怀里,问:“医生,多少钱?”
老醫生本来已摘下了眼镜,听我这样问,又戴上了,从又薄又亮的镜片后面盯着我和箩筐看,说:“看样子你们也没钱……不要了,走吧……多穿点衣服,不要再来了就行!”
我拉着箩筐,深深地向老医生鞠了个躬,然后就出了门。没走几步,我从怀里抽出一小叠钞票,也不知道有多少,转过身,塞进了玻璃门,拉起箩筐就跑。
我和箩筐买了一堆吃的,又到农贸市场买了一袋子木炭。
冬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回到了住处。生起炭火后,整个屋子立马变得异样的暖和起来。风照样灌进来,但不再那么凶狠了。看着箩筐,看着红红的炭火,我感觉这个破门破窗的地方仿佛就是我们的家。
围着火堆,我们饿了吃东西,累了就在沙发上睡,睡不着的时候就说话。说大街上的汽车,房子,好看的衣服,飘着香气的北京烤鸭。但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哈拉奇。
“哈拉奇会下雪不?”箩筐问。
“应该不会吧,那样的话,应该就会有水了!”我想了想说。
“那哈拉奇会有这么冷不?”
“没到过咋知道?”
“那等明年春天了,我们看看哈拉奇去!”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哈拉奇,就这样一直过了好几天。
这天早上,我看吃的东西该补充了。刚一出门,才发现到处都白了,厚厚的一层雪,踩上去没掉了脚背。
箩筐闹着要我和他玩会儿雪。拗不过,只好和他扔了会儿雪球。扔他的时候,我故意扔偏了,怕把他弄疼了。他扔我的时候,我尽量迎上去,让雪球在我身上簌簌簌地开花。箩筐开心得止不住地笑。只要他开心了,让我怎么做都可以。
当我抟好一个雪球又要扔出去的时候,箩筐突然住了手,止住了笑,愣愣地望着我。我正莫名其妙,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哟嗬,玩得很开心哩!”
我转过身,是两个人,一高一矮。我再定神一看,吓得尿都出来了,他们全都穿着青蓝色的警服。我每次见到警察都会绕着走,以前是怕他们把我送回老家去,现在是怕他们把我扔到里面去,如果那样,箩筐怎么办?
我想撒腿就跑,可脚下根本不听使唤,高个子警察跨前一步,揪住了我的胳膊,矮个子亮出一张照片,对着我比对了一下,说:“没错,应该就是这小子!”
派出所里,暖暖的热气让人很是舒服。
矮个子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对他说我没名字,或者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又觉得不妥,想了想,说:“我叫哈拉奇!”
“哈拉奇?哪个哈?哪个拉?哪个奇?”
“哈拉奇的哈,哈拉奇的拉,哈拉奇的奇!”我说。
两个警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这两个警察其实一点都不凶,好像还很喜欢逗小孩子。特别是那高个子,在来派出所的路上,笑盈盈地给箩筐说过好几个笑话,还好几次抚过他的头。
我解释说:“笑哈哈的哈,拉拉扯扯的拉,奇奇怪怪的奇!”
矮个子问高个子:“有这个姓?”
高个子也是一脸茫然:“没听说过!”
“那你父母叫什么名?”矮个子又问。
我低下头,不说话。我不想再提他们。
矮个子把笔的一头含在嘴里,偏着脑袋看着我。
我不知道沉默了多久,才仰起脸,看着天花板说:“我没有爸,也没有妈,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娃儿怎么这么说话?”高个子有点生气了。
无论他们再怎么问,我不再说话。
在我这里问不出啥名堂,两个警察便去了另一个房间。我知道,他们问箩筐去了。
我根本不用担心箩筐,两个警察对他很好,从一进派出所,不光买饭,找小人书看,还给他往手上擦蛇皮膏,说他的手都冻裂了。
我身上剩下的钱,都退了回去。那两个人来领钱时,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执意要给我和箩筐留一些,但被我回绝了。高个子让我向那两个人道个歉,我使劲把脖子一梗,把头往后一拧。
最后,我听到箩筐在隔壁大声说:“叔,姨,我们错了……那天,如果你们不打你们家小妹妹,我哥肯定不会拿你们的钱!”
第二天一早,两个警察带着我和箩筐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理发店。
“像个小刺猬一样,蓬头垢脑的!”高个子警察说。
嚓嚓嚓,电剪子的声音轻匀而响亮。
“这么一打理,其实也挺好看的!”矮个子轻轻捏了一下箩筐瘦瘦的脸。
店里墙面上有台液晶电视,正播着新闻节目:“……干涸了300年的哈拉奇又回来了,形成了五平方公里左右的湖面,沿河芦苇等植被恢复了生长,又呈现出了一片绿色的气息……”
“哈拉奇又回来了,哥!”箩筐向我扭过头来,两个小酒窝若隐若现。
我的眼前升起一片片盎然的绿意,仿佛听到了一阵阵潺潺的水声。
两个警察又是你看我,我看你。
我扭过头去,笑着对箩筐说:“是的,哈拉奇回来了!”
这一天,正是我十四岁生日。
责任编辑 婧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