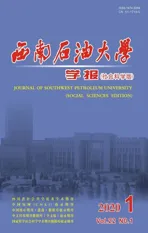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与想象
2020-06-06曾繁健
曾繁健,潘 星
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引言
近年来,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日益兴起,研究范围也由政治经济层面拓展至文化层面,却少有丝绸之路的形象研究。以“丝路形象”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搜索,搜索结果仅有58条,且多聚焦于分析中国文学中的丝路形象,难以知晓外国人对丝路的印象与评价。2013年中巴两国达成一致,共建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乃一带一路协议的重要项目。走廊建设工程遭俾路支等省人民的袭击与破坏,他们对一带一路建设持敌视态度,视这一建设为洪水猛兽,只为掠夺与控制当地资源。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显然目前仍有许多人对丝路建设存在怀疑与误解,若以英语诗歌中的丝路形象为窗口,在他者中见自我,可以躬身自省,一定程度上利于消解疑虑。念于此,以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为研究对象,以Nvivo质性分析软件为研究工具,中国文化也可借丝绸之路及其蕴含的中国文化要素,展开卓有成效的西渐传播,亦可为丝绸之路复兴、丝路文学的景观发掘,提供软体实力的文化支持。
1 丝绸之路的文学记忆与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
丝路文学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丝路文化传播与丝路形象的传递离不开丝路文学的研究。丝路文学既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亦是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在中外丝路文学中找寻文学记忆,挖掘丝路文学景观,重走文学活动与文化交流之路,有益于促进丝路复兴。
中国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其中《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大宛列传》对张骞凿空西域的事迹予以了明示,这促使中国发现了欧洲。然而,中国史学家在描叙这一历史事件时,“西域”一词频繁提及,而非“丝绸之路”。事实上,广义的西域包括新疆、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与非洲东部等国家。但有学者认为,东西方商贾之旅的历史远早于西汉,西周《穆天子传》对此有所揭示。文中提到周穆王驾八骏西巡,自宗周(洛邑)北渡黄河,出雁门,抵包头,经贺兰山,过天山,至西王母之邦(乌鲁木齐),又北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哈萨克斯坦。天子沿途赠答玉石、马匹、牛羊、黄金、贝饰、工布等物。《穆天子传》虽颇具传奇色彩,其中不乏虚构成分[1],但其时东西方玉石器物的贸易往来有迹可循。
西方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大致始于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伊西多尔撰写的《帕提亚驿程志》。那时伊西多尔等人受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所托,前往波斯湾进行实地调查与情报收集;帕提亚波斯王朝记载的有关美索不达米亚至中亚的交通图示在该书也有记载。这一地理信息与汉文史籍有诸多竞合,即经安息(帕提亚)至大秦(罗马帝国)的路况记录。古希腊地理学家克劳德·托勒密对“丝绸之路”也有述及,他在《地理志》一书中记载了自幼发拉底河流域至“丝国”(一般指中国)的路线,其中提到敦煌和洛阳[2]。
丝绸之路在欧洲的历史影响如此之深,及至当代,有关它的记忆符号在英诗中大量存在。因此,本着源于文学形象,但又与现实中国形象产生联系的思辨立场,从英诗域场入手,针对当代英诗丝路形象及其想象的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和跨文化形象学为源头理论,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内容分析为方法的文学研究思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以文本为中心,注重文学文本的细节研究;跨文化形象学则以观念史为中心,注重问题研究,关注社会、思想、文化及历史趋势中的重大现实主题。因此,研究既分析构成“他者”形象的原始成分,如英诗中的词汇、情节和等级关系,也关注形象的套话。至于形象的等级关系,想象诗学的代表人物保罗· 利科和萨特认为,想象性的形象塑造具有创生性的本质。因此形象学的研究重点不在于追问形象塑造本身的真实,而在于寻觅异质形象折射的心理倾向和价值评判等,从中研究者便可发现“自我”与“他者”之间隐藏的等级关系。而形象的套话与“铅版”及老俗套存在隐喻式的认知关系,它历久弥坚,凝聚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丰富的历史内容,成为了解异国、异族形象的认知媒介[3]。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英诗有关丝绸之路的形象建构,成为丝路沿途各国想象性地了解中国、认知自我的极佳参照。通过英诗描述的丝路形象,他们或对中国充满好感,或对中国排斥有加,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当代英诗对丝路的描述,皆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事实,而只能是想象、虚构的事实,它本质上只是各国民族、道德、文化、国家及政治意识的决定物。因此,当代英诗的丝路形象存在一定的范式特征。那么,它们呈现何种形象范式?这些形象范式的分布情况如何?上述答案皆可以内容分析为方法、以Nvivo为质性分析软件,加以数据获知和印证。
一方面,笔者在前期大量阅读丝路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丝路元素的关键词;借助谷歌浏览器、Poem Hunter和Australian Poetry Library等数据库,以“Silk Road”“silk routes”“The road of jade”“Zhang Qian”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抽取30首丝路英语诗歌为样本。另一方面,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与跨文化形象学及其他跨际学科知识的互文指引下,逐字逐行阅读当代涉及丝路元素的英诗文本,并对其编码赋值。然后依据质性数据,推导当代英诗蕴含的丝路形象,且在丝路元素与丝路形象之间建立关系,最终对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元素及其内置的丝路形象展开主题叙事[4]。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理论将现当代英语诗歌中的丝路形象划分为乌托邦化、意识形态化与褒贬并生三大形象范式[5],本研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主节点,并在主节点之下建立关联的亚节点,逐字逐行阅读后对文本展开编码赋值,得出编码参考点统计表,如表1所示。

表1 _英诗丝路形象的范式节点编码参考点统计表
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的统计结果表明,乌托邦化丝路形象占比最大,共有100个参考点,意识形态化与褒贬并生的丝路形象占比较小,且与乌托邦化的丝路形象形成断崖式的落差。这一质性数据表明:“乌托邦化”丝路形象是当代英诗最为稳定的文学范式,丝路各族借助诗歌的崇高,抒发了他们对丝绸之路的历史好感,评价正面。
2 乌托邦化的丝路形象
通过在对涉及丝路元素的当代英诗阅读并编码赋值之后,质性与文本数据表明,乌托邦化丝路形象呈现出5大次阶类型,即:治愈圣地、浪漫遐想、异国情调、思想文明交流、东西沟通枢纽。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数据显示,异国情调这一亚节点在乌托邦丝路形象中占比最大,节点数高达59个。文学的异国情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异国情调强调文学创作者对“异”的心理感受和表述,是文学家对异域文化的向往之情,是其审美情趣和审美风格的表达。广义的异国情调则体现了文学创作的一种乌托邦理想,表达了人们想要躲避文明的桎梏、寻找异域异国和奇异的自然社会环境的愿望,本质上隐藏着对自身文明的某种怀疑和批判[6]。博岱(Henri Baudet)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指出,西方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的文化心理动机,是一种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对异域乌托邦的向往[7]。爱德华·赛义德则在《东方学》一书中表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8]笔者将结合相关诗歌对之展开论述。
诗歌《丝绸之路札记》(Notes from the Silk Road)为美国诗人斯蒂芬·坎内托(Stephen Barrowman Canneto)所作,他在诗中将丝路之旅视为一种朝圣,一段治愈心灵的旅程。爱普· 蕾妮· 泰勒(April Renee Taylor)则以“丝路”为题,想象爱人身着丝衣、佩戴珠宝的模样,将浓浓的爱意与归家的心切娓娓道来;此时,丝路与甜蜜的爱情、浪漫的遐想紧密相连。华人诗人李良(Liang Li)称赞丝绸之路打破了东西方原有的隔阂,使东西方得以自由贸易、交流思想与文化。伊朗裔诗人纳西·法沙拉奇(Nassy Fesharaki)的诗作《丝绸之路》(Silk Road)堪称乌托邦丝路形象的集大成者:男耕女织、采桑纺绩、孩童嬉戏的祥和图景一览无余,诗中蓊蓊郁郁的桑树遍地可见;伊斯兰教的托钵僧(Dervish)经由此道前去修行;各种民族的文化之花在丝绸之路上竞相开放,它们和而不同。但诗人又潸然感慨,认为以喷气发动机(jet engines)为代表的当代科技打破了丝路的宁静与和谐。诗人出生于伊朗伊斯法罕的一座名为法沙拉奇(Fesharak)的村庄,当地群山环绕,地形较为崎岖,诗中描写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或许是诗人早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加拿大诗人格里·吉本森(Gary Gibbens)在《丝绸之路》(Silk Road)一诗中描绘了一行人骑着雪白的骆驼(snow white camels),后转乘碧绿的玉船(green jade ship),从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出发,踏上海上丝绸之路。旅途天高海阔,风从神秘的远方传来,梵音(sutras)入耳,令人内心变得沉静。实际上,阿勒颇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间,是古代商路的重要枢纽,历史悠久,是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奥斯曼时代,阿勒颇的商人走丝绸之路从波斯等地进口棉花、羊毛和丝绸,后销往欧洲和奥斯曼各地,当时该城发达程度仅次于君士坦丁堡与开罗。追古抚今,阿勒颇在叙利亚内战之后,生灵涂炭,早已成为激进主义与宗教暴力的代名词。在挪威诗人奥斯卡· 汉森(Oskar Hansen)的笔下,费尔干纳盆地(Farghana valley)犹如乌托邦一样的存在,那里山川秀美,气候宜人,既无洪水猛兽,也无恶病流行,当地人过着宁静恬淡的生活。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处,西汉旧称大宛,古丝绸之路蜿蜒穿行而过,东方圣地的丝绸、玉器和文化汇聚于此。诗人不禁无限感叹,文明与宗教总有兴衰,费尔干纳却能幸免于历史车轮的碾压,成为屹立不倒的标志。但现实却是,这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圣洁之地,与历史名城阿勒颇一样,遭受了无尽的浩劫,一群野心勃勃、利欲熏心的投机政客、好战分子和毒品贩子,无端插足当地的政经发展,制造了大量的恐怖、冲突与动乱。诗中乌托邦化的丝路形象,无疑充当了费尔干纳的一面镜子,它不仅折射了诗人对古丝绸之路的怀念,因为它曾经给沿途各国带来了繁荣,而且还言说了诗人对当代自我文化的鞭笞——战争摧残了当代的文化,也让文明折戟沙场。
美国诗人利安·埃尔(LeighAnn E.Heil)在《丝绸之路》(Silk Road)一诗中以笔杆喻罗盘,引领读者想象性地重回丝路。故地重游的丝路以忽必烈大汗的大陆为起点,途经威尼斯,经由意大利西北部港口热那亚(Genoa),跨过印度的安达曼群岛(Islands of Andeman),最终抵达伊朗的内沙布尔(Neyshabur)。诗中的内沙布尔夜色如绿松石一般静谧美妙,诗人目及之处,尽是东方风情,沿途所见的奇闻秘事,比《天方夜谭》中苏丹新娘谢赫拉莎德(Schaerazade)讲述的故事还要真切。澳大利亚诗人凯瑟琳· 盖勒(K atherine Gallagher)的诗作《我——迹象》(I—Signs)的每一个字母,无不彰显出古丝绸之路的异国情调,如加德满都的神社(s hrines in Kathmandu),泰姬陵(Taj Mahal),老虎和骆驼,印度西北部城市阿姆利则(Amritsar),阿富汗的青金石(Afghanistan’s lapis-lazuli mountains),通往伊斯坦布尔的丝绸之路(Silk Road to Istanbul),佛香(incense)与麝香(musk),茉莉、小豆蔻(C ardamom)、藏红花(saffron)及印度咖喱(massala)等。其中,青金石是古代西域国家文化交往的重要媒介,在丝路的商贸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代两河流域,小亚细亚,新疆克孜尔石窟与敦煌石窟出土的文物,皆以青金石为镶嵌材料和绘画颜料。在罗马语中,青金石被称作“来自海洋那一边的蓝色”。冯承钧译本的《马可波罗行纪》第46章“巴达哈伤州”对此也多有记述——“而境内别有一山,出产瑟瑟(azur),称其莹泽为世界之最”,“瑟瑟”即青金石。因此,历史上形成了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西直到地中海的“青金石之路”,它与于阗往东的“玉石之路”沟通对接,形成了今日的丝绸之路[9]。
《丝路故事》(Story Of The Silk Road)由印度诗人拉迦· 南迪(Raj Nandy)所作,他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再现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细说了从秦朝到明朝时期中国与丝路国家的历史往来,诗中书写了三大文明古国的盛况,即:古希腊米诺安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中亚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与古波斯王国(Old Persian Empire)。诗人称赞了古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的纽带连接作用,为读者展现了集思想、文化、科技和宗教交流的丝路画卷。全诗气势恢弘,尘封的历史扑面而来,诸多丝路意象贯穿始终,谱写了一部大气磅礴的丝路史诗。其中,诗人带领读者,想象乘坐神奇的飞毯,重回丝路之旅:苏美尔人(Sumerians)的楔形文字(cuneiform writing script),克里特岛(island of Crete),费尔干纳(Farghana),中亚名城撒马尔罕(Samarkand),布哈拉(B ukhara),锡兰(Theran),“中亚之门”(The gateway to Central Asia)梅尔夫(Merv),伊朗西北城市大不里士(Tabriz),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通道的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等,无不显露出异域他乡的万种风情。丝路带来了中国的丝绸、玉器、漆器、纸张、火药和瓷器(Chinese silk,jade,lacquer,paper,gunpowder and porcelain goods),而波斯红枣、藏红花粉和开心果(d ates,saffron powder,and pistachio nuts from Persia),索马里的乳香、沉香和没药(Frankincense,aloes and myrrh from Somalia),印度北部的檀香木、莲花和佛教(sandalwood,lotus,and the great Religion of Buddhism from Northern India)也经由丝路抵达了中国。据《圣经》记载,耶稣诞生之日,东方三哲赠黄金、乳香和没药为贺礼。乳香在西方的宗教场合颇为常见,古埃及和古罗马的祭司曾大量使用乳香以制造异香缭绕的神秘气氛。没药产自古代阿拉伯及东非一带,象征生命的短暂与死亡的馨香。《博士献礼》赞歌中吟诵道,“献乳香芬芳四溢,救主恩爱万民受益,祈祷感谢赞美颂扬,当作馨香之祭,献没药味苦难尝,忧伤悲叹流血舍身,主有得胜力量”。此外,汉唐时期,南海的林邑国(今越南中南部)、中亚的伽毗国(今阿富汗境内)、安国(今布哈拉)、南亚的天竺国、西亚的波斯等国多向当朝天子进贡沉香香料,以作焚香、熏衣和建筑用材[10]。可见,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东西方的枢纽,各种科技成果、文化产品和宗教圣物在此互通有无,这给沿线国家与城市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丝路的人们也因此共享丝路甘甜的果实。
3 意识形态化的丝路形象
与前文神秘浪漫的乌托邦化丝路形象氛围截然相反,在意识形态化的当代英诗中,丝路不是沟通欧亚双方的桥梁,而是罪恶之源,是军事化、殖民化的路径推手;沿线国家与地区也不再是令人向往的乌托邦,而是贫穷落后、肮脏堕落的地狱,它们备受他国的压榨和剥削,毒品、罪恶与死亡充斥着这些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英国诗人阿· 哈维(Aa Harvey)在《欲望》(Lust)一诗中写道:“你灵魂空空,因为你在丝路将它沽换了钱财”(Empty inside is your soul/Sold in exchange for money along the silk road.)。诗中的丝绸之路向世人伸出恶爪,引诱人们贩卖灵魂,堕向地狱。英国诗人罗伊· 巴拉德(Roy Ernest Ballard)在《古丝绸之路上》(On The Old Silk Road)一诗中从老者与青年对话的内容入手,以警示的口吻,告诫后生勿深入戈壁荒漠,以免招致不测。诗中出现了诸多丝路形象,驼夫(camel-puller)、大篷车(caravan)、戈壁(Gobi)、罗布泊(Lob)、大旅馆(caravanserai)与阿尔卑斯山脉(Alps)等纵横组合,构成一幅荒凉悲切的文明图景。在诗人笔下,中国抵御外敌入侵的万里长城成了地狱之门(Gate of Demons means a gate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美丽神秘的罗布泊成了臭名昭著的食人之地,丝绸之路黄沙漫天、风声呼啸,交响成了海妖塞壬之歌;而遗落的瓜皮也能诱人走向死亡,诗性的丝路因此遍野横尸,一旦踏上,便意味着客死他乡,无人生还。这些描述,无疑塑造了一条意识形态化的魔怪的丝绸之路。
印度诗人拉贾尼· 阿迪卡里(Rajani Adhikary)在诗作《丝绸之路》(Silk Road)中刻画了负面排他的丝路形象。在诗人看来,无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新丝绸之路,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它们皆是沿线民族的国殇之路。古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为了方便各国掠夺糖料、香料与丝绸等资源;而新丝绸之路则沦为“被动全球化”的帮凶(Their silk road-now called colonization,/genocide,military bases or globalization),也致使中亚国家惨遭军事占领,甚至种族灭亡。在加拿大诗人斯蒂芬妮· 卡尔柏克(Stephanie Kjaerbaek)的笔下,新丝绸之路充斥着毒品、犯罪与死亡,它成了中东地区圣战组织(mujahideens)的聚集之地,是“黑金”石油(black gold)、猫眼石(opal)和毒品(poppies,opium)走私的滥觞之路。澳大利亚诗人凯斯· 特雷斯特雷尔(Keith Trestrail)借由《咆哮》(Rant)一诗,对丝路形象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塑造。他认为毒品、高利贷、战争、畸形审美等人类恶习,皆随丝路而来;因为新丝绸之路的肇起,当代科技借道丝路,冲击甚至毁灭了沿线国家的宗教信仰,资本腐蚀了众人的灵魂,致使人们道德沦丧,享乐至上,站街女、皮条客和高利贷“大行其道”(the whores of dystopia,pimps and moneylenders)。显然,该诗指称的新丝绸之路并非当代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而是美国向沿线国家强制输出美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丝绸之路;美国借由这一路径,多次发动海湾战争,侵吞资源。因此,诗中曾经的小镇与田园随风而逝,故乡已是一条不归路(a place and past of no return),哀悼乌托邦之死(ravenous jackals and wolves feed on the carcass of idyll idealism)。
4 褒贬并生的丝路形象
若将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视作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钟摆的两端,褒贬并生则是中点。例如,当代英诗对作为丝路形象的长城予以赞扬的同时,也对它冠以了血肉工程的标签。在当代英诗中,既有诗人一方面肯定丝路东西方贸易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又给它背上了疾病与强盗的骂名;既认同丝路对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又担忧丝路成为文化入侵与文化同质的推手。
英国诗人埃德温· 摩根(Edwin Morgan)借助《身处荒漠》(In the Stony Desert),诗性记述了一位马夫在罗布泊旅行险些迷路的侠客故事。但诗中的丝路并没有马可·波罗描绘的那般美好:沙丘与石山掩身其中,狂风裹挟着黄沙,鼓声、马嘶声和挽具的撞击声混杂在一起,前路漫漫,风沙掩盖了大篷车(caravan)的轨迹,无处可寻;诗境的“他”惴惴不安,即便向灯神祷告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历经艰辛之后,他找到了亮灯的帐篷,最终渡过一劫。于是,埃德温在诗中写道:“灯神微微笑着,却不现身”(The djinn laugh softly,don’t materialize.);这里的“djinn”(又作“jinn”)意为阿拉伯神话中的灯神[11]。可见,诗人笔下的罗布泊险恶万分,稍有不慎便会丧命,向神灵祈祷也不全然奏效。诗中蕴含诸多丝路意象,颇具异国情调和别样风味,既有罗布泊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有夸张的魔化他塑。
美国诗人詹姆斯·麦卡勒姆(James Bradley McCallum)的丝路心迹在《丝城》(Silk City)中得到了袒露。他借助一些丝路形象,对君士坦丁堡过去的圣洁繁华进行了凭吊,但他又称如今的伊斯坦布尔早已沦为了堕落颓靡之城,它藏污纳垢,有人在街头巷尾干着皮肉的营生,可谓“成也丝路,败也丝路”,诗中褒贬并生的伊斯坦布尔由此显山露水。伊斯坦布尔最初名为“拜占庭”,后罗马帝国定都于此,改称“君士坦丁堡”。该城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当时世界商路汇合于此,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如今,也因丝绸之路带来的多重冲击,而饱受责难。
5 结语
如果以跨文化形象的思路,跳出文学的藩篱,对当代英诗的丝路形象进行跨际跨学科的思索,那么,历史过往及当代国际政经角力的丝路形象,能够从中得到部分印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揭示的一样,中亚曾是世界的中心,历史上的丝路,可概括为以下7个方面:信仰之路;变革之路;天堂、和睦、妥协及重生;贸易之路(皮毛、黄金、白银、黑金之路);战争与危机之路,具体包括奴隶、铁蹄、殖民、霸权、帝国、纳粹之路;小麦香料之路;驿站之路等[12]。这刚好与Nvivo数据的显现大抵一致:“神秘未知、迷梦冒险、宁静恬淡”等高频形象词,多与乌托邦化的丝路形象联系在一起;而“罪恶之源、堕落贫穷、犯罪死亡”等高频词,多指向意识形态化的丝路形象;当然,褒贬并生的丝路形象则在极点的两端适时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