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
2020-06-03王东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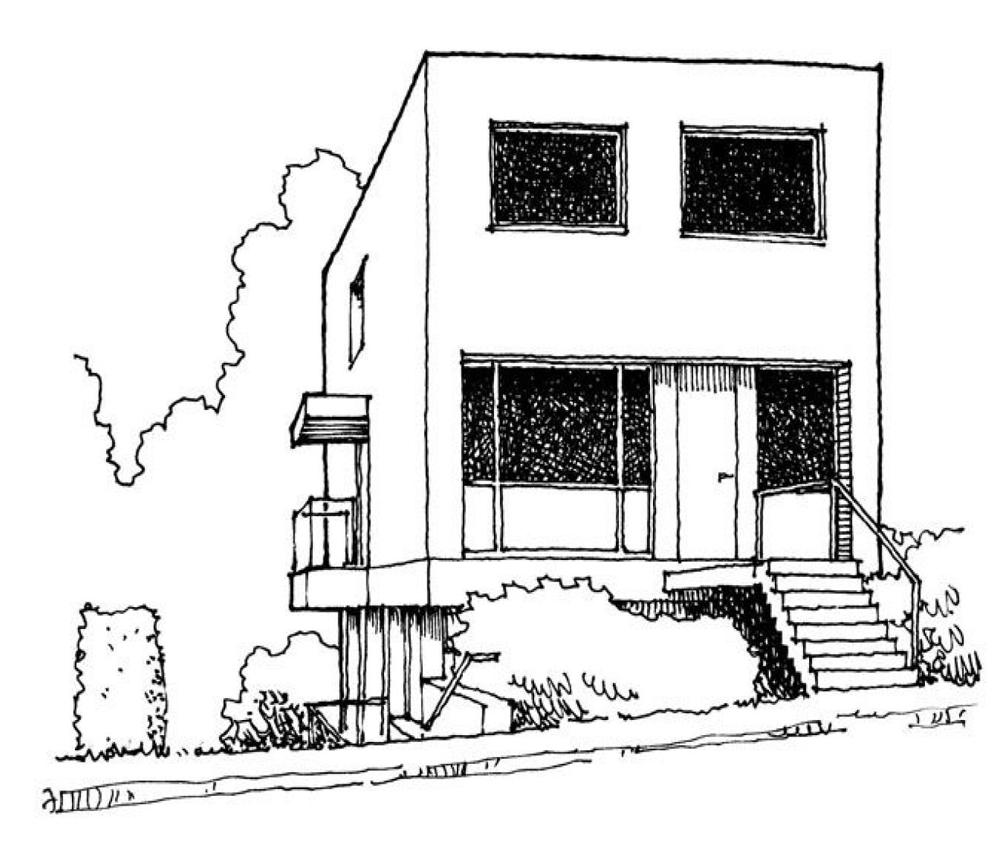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王东梅,现居重庆。爱好文学,近年在数十家地市级文学刊物发表散文、小说、诗歌等作品多篇。
上篇
周漫若又坐到那辆汽车上。之前,这两个人已经很少说话,彼此都无法想象曾有过连续交谈数小时以上的时候。那天午后,他给周漫若发了一条微信:“我们去墨山吧!”
此刻,他们就在去墨山的路上。车子已经开出城区,开到一条乡间小道上,那道路居然有名字,路边竖立的杆子上写着“幸福小径”几个字。小径两旁各有一排简陋的棕色花箱,上面开着那种紫色、黄色的角堇花,蝴蝶形状,艳丽而欢快。与那条道路的名字一样,给人一种俗气的喜感。
沿途还有一堵灰色水泥背景墙,上面嵌着几扇中式花格窗,两排飘逸的红灯笼,是时下流行的混搭风。这些景物从周漫若眼前一一浮掠而过,最后,他们的车子穿过长长的“幸福小径”,拐过一座陡坡,驶到那条平整、宽阔的柏油大路上,速度加快。
郊区的冬天是一片单调的苍黄色,一种江南冬季特有的灰蒙感,房屋和树木都是灰色调,暗沉、肮脏、含混不清。周漫若微侧着脑袋,略有些拘谨地坐在副驾驶座上。他则像往常那样,专注于前方的道路,两人并没有说话。
空调出风口就近放射出热气,喷在周漫若脸上,暖烘烘、热乎乎。周漫若的目光慵懒地扫过车窗右侧及前方大部分区域,却无任何聚焦,甚至产生一种临睡前躺在眠床上的昏昏欲睡感。但周漫若知道,自己此刻绝无入睡的可能。
周漫若闭上眼睛,竭力想要理出个头绪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坐到这车上来。刚才,一上车,周漫若就对那个人宣布,她累了,能不说话最好别说。周漫若的不耐烦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好像事实本该如此,她不是一个饶舌的人,一点也不喜欢在车上说话。而那个人居然也一声不吭地接受了。
他们都有些反常,但彼此都对此无动于衷,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反常是何种原因导致的。尤其是周漫若,动作、神态比往常更多了一份骄横和跋扈。周漫若原本不是这样的人,她从来也不允许自己这样,那个男人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周漫若坐在这车上,那神情好像是凭空被空降到此处。外面温度很低,车子里面却闷热不堪。周漫若的身体越来越感到热,那些热在不断地积聚、扩散,包裹着她。表面上却无动于衷,哪怕汗流浃背,周漫若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好似她的身体与意识是分离的。
周漫若看着窗外,想要从那些灰暗的景物中,获得一些清冷的感觉,一种真实感。哪怕是一种强烈的不适感,也好过此刻。自从坐到这车上后,周漫若一直处于恍惚之中。
车子继续在柏油大路上行驶,如同停驶一样悄无声息。途中,大概是意识到什么,他问周漫若是不是热了,要不要脱掉件衣服。他的神情有些迟疑,似乎张口说话时,才忽然想起周漫若初上车时的声明,她要安静,不想说话。可听到他的话时,周漫若并没有发作,只微微点了点头,双手摆弄了几下钮扣,随即放弃了。
周漫若实在不想动,甚至不愿让车子停下。此行,他们要去一个叫“墨山”的地方。两年前,他们去过那里。也是冬天,天气也这么冷。周漫若还记得那个地方,那间农家乐饭馆,那些胖乎乎、圆滚滚的鳗鱼,她似乎吃了不少。
他们去的那天,饭馆里除了服务员,几乎没有别的顾客。他们坐在二楼包厢里。包厢对着一片连绵的湖水。那些鳗鱼,在放了红糖、大蒜、黄酒、生抽、老姜和葱丝之后,已经尝不出鳗鱼本身的滋味了。
他用周漫若的筷子给她搛了河鳗。他一共给周漫若搛了三次河鳗。对他的这种行为,周漫若虽谈不上反感,但也没有被感动。
因为他多次提及那些鳗鱼,周漫若知道它们的滋味大概是很不错的,但此刻完全想不起来。曾经吃过的鲈鱼、鲑鱼什么的,也一概想不起来了。不用说鱼,太多人,那些浮动的面孔,都让周漫若无从记忆。
可有一样,周漫若是记得的。她记得那个房间,农家乐饭馆里的房间,就像周漫若老家的房间一样简陋而昏暗。那张轮廓丑陋的床,白色而来历不明的床上用品,那种被过度漂洗过的白。那些白色里藏着的黑色和灰色,它们丧失了织物本身的光泽,只是一堆冷冰冰、硬邦邦的东西。
在此之前,周漫若并不知道那种地方还会有供人休息的“房间”。在那个房间里,他踌躇满志地对周漫若说:“明年五月我们再来吧!”那时候,周漫若并不明白他想说什么,为什么是五月,而不是别的月份。
后来,下楼的时候,周漫若看见了那些枇杷樹。周漫若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说那些树,也没有问。当然,那年五月,他们并没有再去那里。他们去了西山、菇城、古堰,还有别的地方。
现在,那些地方周漫若一个也想不起来了。好像都差不多。不是山就是水,要么就是些简陋的小餐馆,稀稀落落的外乡人。他们总是去那些人少的地方,陌生人待着的地方,旅游风景区的外围。他带周漫若去的尽是那种地方。
周漫若从口袋里摸出一粒东西,发现是一枚皱缩的山楂果,由艳红转为深褐色,已经变得像石子一样硬。周漫若捏在手里,细细地看着,想不起来这是哪次出游的“馈赠”,居然还留在口袋里。周漫若无意识而反复地揉搓着它,嘴里喃喃着什么,好似对着幻想中的某个人说着话。
你怎么了?一旁的男人关切地问道。
周漫若瞥了那男人一眼(似乎不再认识他),流露出小动物似忧伤的表情,抱怨他打破了她的清静,或是发现了她的秘密。直到车子驶离省界,沿着湖岸开了许久,抵达那个露天停车场,周漫若还沉浸在那种表情里。那种强烈而奇特的表情,被某种东西带走的表情——这让周漫若身边的男人感到棘手。
周漫若从汽车上下来。那间农家乐饭馆,苍茫的湖水,以及那些芦苇丛,似乎让周漫若想起了什么。直到那一刻,周漫若才想起了一切。那天午后,周漫若从那个“房间”里出来,浑身软绵绵、轻飘飘。周漫若看见端坐在门厅椅子上的老板娘,似笑非笑的,望了周漫若一眼。那颇富意味的一眼,好似在谴责什么,又好似在提醒周漫若一些事。现在,周漫若再次来到这里,并清清楚楚地记起了这一切。
周漫若在河边洗衣,奶奶托人带话来说要打周漫若。周漫若既惊惧又不解,不知自己犯下什么错误,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当走在通往家中的路上,做了一半的梦醒了。此后,周漫若一直等待命运将她再次带人那个梦境,但从未如愿。
当走进饭馆,周漫若毫无征兆地,忽然想起那个童年时做的梦。昏暗的厅堂,桌子、椅子乌泱泱堆了一屋子,因为是阴天,那些颜色更显得暗沉。周漫若开始头晕,浑身颤抖不已,她似乎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了。
时间仿佛在后退。他们再次点了河鳗,所不同的是,这回他们坐在二楼外面的露天平台上。太湖水就在眼底,如此之近,好像随时可能漫浸上来。周漫若心里忽然起了一种莫名的悸动,甚至还有点害怕。随着时间流逝,那种感觉变得强烈。鳗鱼上桌后,周漫若再次闻到那黏稠而浓郁的鱼香,她低着头,嗅着那气味,一口、一口,谨慎地剔除鱼肉里的刺。
那个坐在周漫若对面的男人,缓慢而赞许地说:河鳗的味道一点也没变!——说那话时,其神情里带着微妙的笑意。周漫若听见了,点点头。那个人继续说:简直可以说是鲜美!他的语气有些夸张,带着邀功的意味,好像那些河鳗是他亲自捕捞上来的。
他又要往周漫若的碗里搛鱼了。周漫若想阻止他,可已经来不及了。这回,他用的是自己的筷子,兴奋之下,没来得及纠正过来。
周漫若在心里发出一声惊叫,可那个人什么也没有听见,还在往她的碗里搛鱼。眼看着就要“堆积如山”了,周漫若急得干瞪眼,却说不出任何话。
鱼肉在周漫若嘴里嚼动着,逐渐融化,缓缓下沉,进入胃囊深处。一项机械的唇齿运动,根本不知其味。周漫若想着那个“房间”,那张简陋的床,白色床单,荒野一样寒冷。
鱼还未吃完,周漫若就已经快震缩成一团了。恐惧逼近,寒冷从身体内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那个房间在向周漫若招手。他一定会带周漫若去那里,俗气的化纤窗帘、肮脏的白色床单,轮廓丑陋的床,散发出一股橙红色的铁锈气息。
对面那个人早早搁了筷子,剔着牙,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这时候,那个老板娘进来了,她一眼就认出周漫若来。
周漫若身体一软,险些滑至餐桌底下。男人起身,不明所以地望了周漫若一眼,随着老板娘走到里屋,下楼去了。大概是去结账了,或許还会把那个“房间”的钱也一块付掉,周漫若想。
男人回来的时候,周漫若已经不再吃鱼。周漫若再也咽不下那些鱼肉,它们塞满了她的口腔、食管、胃囊,让周漫若说不出话来。男人站在那里,充满期待地望着周漫若。为了避开那目光,周漫若仓皇地往远处眺望。
那圈水泥栅栏外就是太湖水了,今天没有阳光,近处之水暗绿沉沉,还有些微波轻漾的感觉。再远些,那一大片深暗、凝滞的水好似铁板一块,被焊接在一起,永不分开。
周漫若的脑袋又开始痛起来。那些小而细微的痛意,丝丝缕缕,薄如蝉翼,好像是过去那些大痛苦的碎片和残留,是一些顽固和难缠的疼痛的卷土重来。
周漫若如愿移步到露台上喝茶,但心底的焦灼并没有得到缓解。那个“房间”还在那里,它张开大口等在那里,等着从他嘴里吐出来。迟早,他会这么做的。周漫若目光游移,东张西望,气息吁吁,好似有什么大事要发生。那因疼痛而涨大的脑袋,变得重如磐石。
当再次抬头,周漫若似乎看见了树,它们宛如长在水中央,而不是岛上。其实,她并不确定那就是树,它们只是一些苍黄而模糊的绿,一些驳杂的色块。周漫若的目光全方位扫射,唯独没有在他身上停留,似乎对方身上的某个按钮会因自己的凝视而随时启动。
茶水很快喝完了,连热水瓶里的水也被倒空了,可服务员一直没有出现。这里不是茶馆,他们本没有续茶的义务。他们在闲聊,或许还在“观察”他们,那个老板娘也在其中。
周漫若想对他说:我们快走吧!哪怕去湖边散步也好,她不怕冷。现在,她什么也不怕了。
而那个人也明显按捺不住了,他微微扭动的身躯、游移的眼神,已经泄露了一切。某一瞬间,他体内那紧绷的弹簧似乎弹了起来,就那么一下,让他猛地站立起来;好像不是他自己要站立起来,而是那架弹簧的主意。那句话几乎脱口而出,其实是酝酿了太久,带着一股恍惚的气息。他说那话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看周漫若的脸。
那一刻,周漫若也站了起来。
有一刹那,周漫若感到自己也是想去那个“房间”的,尽管是同一个房间、尽管会遭遇同样的事,可有不一样的东西也说不定。周漫若甚至安慰自己,就算那个女人认出她,也不会知道她是谁、叫什么名、来自哪里。
这时候,他显得过于迫切了,他肯定以为周漫若已经同意了。周漫若怎么会不同意呢?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他眼神里那种胶状的物质硬生生地全倒了出来,要去黏住周漫若。那个女人听见自己嘀咕了一声,可今天不方便呢!
连周漫若自己都吃了一惊。居然真的说出口了,而且是那么自然而然地说出,就像是真的。周漫若低着头,自说完那些话后,周漫若一直低着头,偶或抬头望一眼湖景,又立刻将眼神收回。
周漫若脸上是那种迫切地想要转移话题的表情,同时又极力掩饰着——这只能让人更感到愤怒。他站在那里,脸庞涨得通红,双手紧紧攥着,握成拳,好似感受到了某种奇耻大辱。但那表情一闪而过,他马上又谈笑自如了。
后来,当他提议去湖心岛,周漫若似乎长舒一口气,马上从饭桌前站立起来。终于可以离开了。那一刻,周漫若感到有某种力量即将引她进人多年前那个被中断的梦境。
下篇
他们是下午一点半左右上了古小民的船,好像是从对面那间农家乐饭店里出来。男的穿一身黑色衣裤,帽子也是黑的,脚下穿的是布鞋。帽子和衣服的款式古小民记不清楚了,古小民特地留意了下那双鞋子。现在,很少有男人穿布鞋出门了,连古小民这个划船的也开始穿皮鞋了。后来,古小民才知道那个男人的鞋子并不是布做的。
待他俩上了船,古小民才问:老板你这布鞋多少钱一双?改天我也去买一双穿穿,看着很暖和呀!
没错,古小民就是喜欢主动和客人聊天。聊着、聊着,就把钱给赚了,多好的事啊!再说,摆渡这活儿生意清淡,一天也接不了几单,冬天更是淡季,寒风萧瑟的,没事谁会去岛上吹风啊!
当然,对谈恋爱的男女来讲,找个地方躲清净也是有的。一开始,古小民以为这一对也是这情况。
再接着刚才说那鞋子的事。男人见古小民注意到他的鞋子,显得很高兴。他笑眯眯地说:老人家您可看仔细了,我这鞋子是牛皮鞋,和你一样的。它是牛皮做的,货真价实的牛皮鞋。
这一说,古小民还真凑近着,仔仔细细地研究了那鞋子半天,确实不是那种廉价的布鞋。原来它是皮鞋,是看着像布鞋的皮鞋。
男人大概是被古小民的表情给逗乐了,马上说他脚上的鞋还没有古小民的高级,愿意跟古小民换着穿。古小民一看那女人在边上皱眉,就知道他说笑了。古小民再一瞧,女人也穿着那种款式的鞋子。不同的是,男人穿的是黑鞋,女人的鞋子是灰色的,鞋帮也比男的略高些。可它们无疑是同一家店生产的。
古小民的脑子里描述着那女人的相貌:长得很白,高鼻梁、大眼睛,也戴帽子,灰帽子。女人身上也是清一色的灰,没有别的颜色,一点也不好看。可她的眼睛好看,女人有一双好看的眼睛,这让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姑娘。况且,她长得也不高,足足矮那个男人一个头,看着就像是那个男人的女儿,如果那个男人再老上十岁,就更像了。
古小民一看就明白他们是什么关系。古小民见过不少这样的男女,他们坐到他的船上来,都有些遮遮掩掩的,不太自然。当然,那男的还算大方,和古小民也说说笑笑的,女人则一声不吭。无论那男的说什么,女人就是不答腔。起先,古小民还以为是女人害羞,在他这个外人面前不好意思说话。
后来,古小民才发现那女人在偷偷地抹眼泪。显然,那男人什么都看见了,可他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继续和古小民扯闲篇,问古小民岛上好不好玩。古小民说好不好玩,那要看跟谁一起玩了。
男人笑了,又问今天有多少人上岛。古小民说,一个也没有。男人诧异地说,这么冷的天,那你还等着啊!古小民说,我必须得等着啊。等着就是我的工作嘛!你看,我不是等来了你们吗?要是没有我,谁为你们服务呀!说完这话,古小民得意地笑了。他想,要是他死去的老伴知道他这么会说话,肯定会夸他的。毕竟撑了那么多年的船,古小民也开始学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就是为了互相取暖吗?说点让彼此都开心的话,没那么难呀!再说,古小民也喜欢和客人聊天,什么样严肃的客人一坐到他的船上,离开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
可那个女人一直不吭声,哪怕古小民费尽口舌,她还是老样子,更不用说赔个笑脸啥的。不知道为什么,她越是皱着眉、越是不说话,古小民就越想听她说。古小民想听听她的声音,古小民想知道那么一个女人,会有什么样的嗓音。在船上,古小民听过许多女人的声音,绝大多数人的相貌已经记不得了,只有她们的声音还存在古小民的脑子里。古小民也搞不清楚那种奇怪的感觉是怎么来的,一直觉得,只有听过一个人的声音,才算是真正认识了这个人。
船已经开出一半水路了,那女人还是不吭声。当然,她已经不抹眼泪了,可还是那副表情。看她那样子,好像不是去岛上玩,而是去受难。古小民要是那个男人,干脆掉頭回去算了,去那荒岛上干么呀?除了风,那里什么也没有。
古小民估摸着,他们可能刚刚起过口角,可看着男人笑眯眯的样子,也不像。古小民就没话找话,问那个男人以前去岛上玩过没有。男人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上岛,以前每次来都只在岸上看看,觉得那岛挺神秘,也不知道上面有些啥。今天恰巧有空,就想着去看一眼。
说到这里,男人望了那女人一眼。这是上船之后,男人第一次关注那女人的存在。男人继续谈论那个岛,从他的谈论中,古小民知道他对那里一无所知。自上船后,女人似乎是第一次露出侧耳倾听的表情。她在偷听他们的谈话。这时候,古小民才感到这女人完全被男人控制住了。男人伸出手,试探性地在女人的肩上拍了几下,女人毫无反应。男人马上不再聊岛上的事情,好像那是一种禁忌,特别是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提及。
男人跟古小民说,他做的是自由职业,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作。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了工作,因此获得了自由。他说自己享受这份自由已经十几年了,有时候也会觉得无聊,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男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些洋洋自得。古小民思忖着,他应该是个有钱人吧!只有有钱人才会这么说话,只有有钱人才穿那种鞋子。那种像布鞋一样的皮鞋,肯定很贵的。
男人的这些话,古小民并不爱听。古小民心想,他敢说谁都不会喜欢听那种话。于是,古小民就没有吭声。男人也不在意,掏出手机对着天空、湖水和岛上的树,上下左右地移动着,他在拍照。男人一边拍照,一边还要和古小民说话,古小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喜欢说话的男人。
但让古小民纳闷的是,这个活泼的男人怎么会喜欢这种木头一样的女人呢?就算是一块木头,你拿东西去敲,它还会发出点声响的,这女人完全是……怎么说呢,反正没有一个正常的男人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看得出来,那男人急切地想要和那个女人说话,他好像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而那女人完全无动于衷。她好像不是坐在古小民的船上,而是独自坐在自家屋子里。
她的嘴巴紧紧地闭着,不知道是怕风吹进去,还是怕露出她的牙齿,或者是怕那藏在牙齿缝里的舌头会自己搅动着说话。上船这么久,古小民实在想不起来那个女人到底说过什么。大概是船快要靠岸的时候,她嘀咕了一句:这就到了呀!也有可能那只是古小民的幻觉。古小民老是想着让她说句话,哪怕是一句也成。
下船的时候,男人掏出两百块钱递给古小民,跟古小民说这船他们包了,叫他不要再去对岸接客人过来了。古小民乐得同意了,反正这种大冷天,也不会有什么人来。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古小民问男人大概几点回去。男人愣了愣,反问了古小民一句:你有急事吗?古小民说那倒没有。男人就说他们兜一圈就出来,很快的。
“警察同志,我信了他的话,就在那里一直一直等。等到五点钟,连一个影子都没等到。我想我已经等了三个小时,这两百块钱差不多也该花完了。如果要走,那也是可以的。可是,我眼前老是浮现出那女人的模样,尽管她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也没正眼瞧过我。可我心软,想着那女人的模样,特别是那对眼睛,我说不出那种感受。”
或许,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吧……那船夫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
就这样,古小民的船戈0到一半,又划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古小民还挺高兴的,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那是一个孤岛,如果没有船,是出不去的,即使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总不能让他们在岛上过夜吧!那是要冻死人的。
“警察同志,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應该讲出来。”
那女人的意识好像是不清醒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下船的时候被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了。
“你问我有什么凭据,我能有什么凭据啊?我只是瞎猜的。他们又没有跟我说什么,那女人连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过。”
古小民把船划到原地,左等右等不见他们来,而天快黑了,怎么办呢?古小民想着还是去岛上看一看吧!其实,古小民早就想上去了,又怕他们忽然出现,一下子找不到他。说起来,那岛古小民也上过几次。没想到,这次居然迷路了。
一踏上那条路,古小民就感到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进去了。沿途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什么也没有发现。古小民本以为风大,岛上会很冷,也没有什么风景好看的,他们没有理由逗留那么久。
可古小民错了。古小民完全没想到那岛上的树会那么茂密、高大,全是大树。人走进那树丛里,就好像走进温暖的屋子里,什么都忘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见湖水、看不见堤岸,你只能看见那些大树。人在低头、抬头时,看见的都是树。那时候,古小民还想他们可能躲在某个树丛里玩,忘了时间。
古小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会出事,一男一女能出什么事呢?这岛上又没有别人。根本没有人。古小民就没往那上面想。那男的肯定是个有钱的主,模样也不错,人也开朗周正,好端端的,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来?古小民还是不信,打死他也不信。
“警察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是知道那男人是这种人,怎么也不会让他上我的船。我是有原则的,坏人我不载,给再多的钱也没用!”
对,是古小民发现了那两双鞋,一灰一黑,整齐地摆在那块大石头上。
一看到那鞋子,古小民的心就凉了半截。完了、完了,古小民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到船上,将船划到湖中心,才给警察打电话。打完电话后,古小民扔了手机,差点把桨也丢进水里。上岸后,古小民还在发抖。古小民整个人抖得不行,双腿就像折断了似的,怎么也站不直。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除了那两双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别问我。老天啊,太可怕了!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一”
说到这里,那船夫一脸惊恐,发出一声哀号。
“是我把那女的害死的。是我把她送上岛。下船的时候,她被绳索绊了一下,老天原本是要阻止她上去的。可我没有阻止,我还扶了她一把。警察同志,她叫周漫若,是吧?那一把是我扶的。周漫若是在我的搀扶下才上了岛。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那个男人,我认识的那个男人在我船上的时候,一直笑眯眯的。他有钱,有很多很多钱,不可能做出那种事。他没有必要去做那种事,他有那么多钱。”
下船的时候,他跟古小民说,他是做古董生意的。他一说古董,古小民就想到了鸡缸杯。古小民在电视上看见过,那么一个喝酒的杯子居然要卖两个多亿。
“所以,他不可能做那种事。我没有亲眼看见,我不信。他对那女人不错,我敢说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能对她这么好。他是带她出来玩,想让她散散心的。这个女人看上去太陇郁了,会不会是得了抑郁症?我没有见过得那种病的女人,所以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只是出来玩一趟,马上就要回去的。或许还是偷偷摸摸跑出来的呢!我知道,他只是想让那个女人开心、开心。老天哪!……”
——那船夫一屁股坐在地上,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责任编辑/乙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