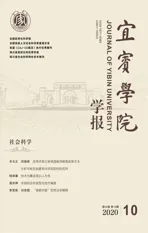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圆美”
——以书法文化为例
2020-02-22徐惠
徐 惠
(曲阜师范大学 杏坛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圆”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意义,“圆”是会意兼形声字,《说文·口部》:“圆,圜全也。从口,员声。”马叙伦考证:“圆”的本字为“圜”,而“圜”的最初写法为“”,本义为方圆之“圆”。[1]130《周易·说卦》:“乾为天,为圜(圆)。”《淮南子·本经训》:“戴圆履方”,高诱注:“圆,天也;方,地也”[2]。在此,“圆”有了“天”的涵义。甲骨文中“天”字的写法,是在人的头顶上加一个圆圈或圆点。上古时代,先民从晨昏往复,四季循环的自然变化中感知到“圆”的存在,从而产生“盖天说”“浑天说”等观念。先民认为“天”的态度决定了农业生产、田猎战争等,主宰了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理应受到无以复加的虔诚膜拜。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认为:“者,无极而太极也”[3],王夫之在《周易内传发例》中补充道:“太极,大圆者也。”在此,“圆”成为太极之圆,上升为“道”的层面,具有了象征意义和丰富的哲学文化内涵,频繁出现在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中,用以阐释古典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调和流转、圆融自足的审美品质。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以圆为美”的思想已经有所关注。但是,对中国书法“圆美”的发展及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还尚属少见。“圆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这原本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要再追问:“圆美”究竟怎样影响了中国书法?“圆美”在书法美学中居于何种地位?却没有多少人深入思考过。前人的研究中,书法之“圆美”仅仅是文学、戏曲等学科探讨各自领域的“圆美”时一种可有可无的举例和补充。然而,只要深入研究书法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就会发现中国书法中的“圆美”意识是一以贯之的,从见于记载最早的书论——东汉崔瑗《草书势》所载“方不中矩,圆不中规”开始,到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明确使用“圆美”一词:“当行草时,尤宜泯其棱角,以宽闲圆美为佳。”“圆”在历朝历代书论中使用达到最高频次,它几乎贯穿了书论的每一个篇什。以收录《历代书法论文选》的书论为统计对象,其中对“圆”的阐述大约有342次之多,具体表现为圆畅、圆备、圆通、圆劲、圆浑、圆和、圆满、圆足、圆活、圆融、圆转、圆静、圆整、圆明、圆稳、圆熟、圆正等几十种“圆美”形态。不少书论家也曾专门探讨过“圆美”问题,如陈绎曾在《翰林要诀》中著有专门的“圆法”篇。与此同时,与“圆”相对的“方”范畴论述极少,且大多数情形下与圆并称方圆,其余有方正、方阔、方整、方严等说法。项穆《书法雅言》认为:“圆为规以象天;方为矩以象地。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4]863在“技”的层面上,“方圆互用”可以阐释书法作品中的用笔、结体、布局等一系列技法问题,“道”的意义上,“阴阳互藏”则折射出中国古典艺术孜孜以循的最高法则。再如姜夔《续书谱》中的“方圆”篇:“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在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中,“方”主要适用于隶书和楷书两种书体,并且在多数情形下是刀刻在碑碣上带给人的审美错觉,而“圆”的审美需求则贯穿了全部书体。然而,书法“圆美”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简单地概括为“自然美”和“自由美”,其独立品格被忽视或遮蔽。然而我们发现,难道这不是中国美学最普遍的审美追求吗?书法之“圆美”的内涵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书法原始史料进行认真地梳理、系统地考辨,尤其对前人忽略的书法“圆美”的种种作出新回答。
一、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形式圆”
书法的“圆美”可从最基础的层面分析——艺术语言,即书法工具的选择、点画的分布、执笔的方法、章法的运用、布局的技巧等方面需表现出恰当、和谐的审美感受,我们称之为“形式圆”,这是艺术作品最基本的因素,没有这些因素的调和,便难以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圆美”。
(一)毛笔之“圆健”“圆正”
中国书法的毛笔具有异于其他艺术门类工具的特殊性——“唯笔软则奇怪生焉。”这是书法的根本,但“软”还无法涵盖毛笔的全部特征。因为西方绘画的油画笔、漆刷也有类似特性。毛笔本身的笔管圆而空心,笔毫也是圆形聚扎,这决定了书法工具上“圆”的特性。朱履贞《书学捷要》:“考造笔之法,兔毫为最……纯用紫毫,则软而圆健。”[4]603包世臣《艺舟双楫》:“能手之修笔也,其所去皆毫之曲与扁者,使圆正之毫独出锋到尖,含墨以着纸,故锋皆劲直……”[6]674书家强调毛笔需“圆健”“圆正”。圆柱形的毛笔在纸上平行运动的过程中,笔毫具有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接触面,诉诸于视觉的线条也具有了四面的效果。以横画为例,左右两侧笔毫分别构成了线条的上下,而前后方向的笔毫构成了线条的中骨。前后笔毫行笔之时经过的方向一致,同一位置经历了前后笔毫的重叠“涂抹”,因此墨的淤积增加了一倍,这就是“徐铉式线条”中端不透光的效果。
圆柱形的毛笔表现了书法线条强烈的“立体感”,这是古今书家孜孜以求的美学目标——“圆”为中锋用笔提供了技巧性之外最优越的工具性条件。古代书家钟情于中锋用笔,并为此追求付出了无数的精力,而这一点首先在书法毛笔的选择上得到了明确的验证。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卷毡书、指书等,均是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在于“圆健”“圆正”等因素的缺失。
(二)执笔之“虚圆”
执笔方法被历代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所重视。只要我们翻开古今书法理论的典籍,关于执笔方法的探讨比比皆是,诸如握管法、单钩法、双钩法、握管法、撮管法、捻管法、拨镫四字法、回腕法等言之凿凿。这些方法中有的言之有理,有的则是故弄玄虚。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在《书法论丛·书法论》中说:“书家对于执笔法向来有种种不同的主张,我只承认其中之一种是对的,因为它是合理的,那就是由二王传下来的,经唐朝陆希声所阐明的:擫、押、钩、格、抵五字法。”[5]五字法的要点包含了几个要点:手指实、手掌虚、手背圆。其中掌虚如握鸡卵,形成圆形空间,手背也要呈现自然的圆弧状态。虽然书写者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会发生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而执笔需“圆”是书家历来共同遵守和推崇的执笔最佳状态。
欧阳询在《传授诀》中论道:“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4]105执笔须在一种“圆正”“如对至尊”的静穆氛围之中。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提到,张公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这是书家创作之前,身心与执笔处于高度的融合、协调,达到物我合一、心手双畅,胸中丘壑满营的境界。解缙更是将执笔视作书家“书之美”的第一要素,《书学详说》:“今书之美自钟、王,其功在执笔用笔。执之法,虚圆正紧,又曰浅而坚,谓拨镫,令其和畅,勿使拘挛。”此外,周星莲《临池管见》:总之执笔须浅,浅则易于转动。其法先拓大指,使虎口圆,则掌心自虚,大指为捺,食指为压……[6]728上述书家在对执笔法的论述中,无不处于执笔须遵守“圆美”规则的笼罩之下,执笔符合“圆正”的要求,“执之法,虚圆正紧”,手指之间的分布要求符合“圆”之特征,“使虎口圆,掌心自虚”,不难看出,书家们对于执笔要求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即使在一定意义上违背了人自身的生理规律,但也必须做到“虚圆”。
(三)中锋用笔之“圆”
在书法创作的实践和书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中,书法用笔构成了书法艺术的核心命题。书家对书法用笔理论的阐发中,一直对中锋用笔津津乐道,米芾言:“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这是书法用笔的基本原则,讲求有来必有往,有去必有回,有放必有收,有行必有止。大化流行,书道沿时,书法用笔处在这回环往复中。这种中锋用笔产生的审美效果是什么?就是“圆”。见于记录最早提出笔法问题的是汉代的蔡邕,《九势》谈九种用笔技巧其中就有“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这一说法大概以陈槱“锋常在画中”观点为源头。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写道:“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李宗玮先生在《悟对书艺》中这样评价:
赵孟頫在用笔理论上有深刻的见解,他从悠久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本体规律中,剥开繁复庞杂的层层迷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了‘用笔千古不易’的核心命题。这是基于对书法技法的人文思考,是基于对书法艺术形式特征的审美思考而断然发出的绝论。[6]325
虽然“笔笔中锋”的审美要求有些极端化,确是书家通往成功最大的捷径,中锋是书法用笔的正宗,也是书法美学线条美的正宗。从索靖的银钩虿尾,到王羲之的锥画沙、印印泥,到张旭的折钗股,再到颜真卿的屋漏痕,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无不将中锋用笔奉为圭臬。笪重光《书筏》:古今书家同一圆秀,然惟中锋劲而直、齐而润,然后圆,圆斯秀矣。[4]561刘熙载《艺概·书概》:中锋画圆,侧锋画扁。舍锋论画,足外固有迹耶?[4]709从书法美的角度看,中锋用笔的美是绝对的,是必须遵守的。上述书家在阐释中锋用笔时,都无一例外地倡导中锋用笔要“圆”,也就是说,中锋用笔最核心的审美追求就是“圆美”。笪重光在《书筏》中竟然发出此般感慨:“善运中锋,虽败笔亦圆,不会中锋,即佳颖亦劣,优劣之根,断在于斯。”[4]562用笔贯中锋,字便能贯圆,懂得这个道理,即便是破笔写字也可列入佳品。
卢携《临池诀》:纯刚如以锥画石,纯柔如以泥洗泥,既不圆畅,神格亡矣。[4]295中锋用笔产生的直接审美效果就是使书法的线条呈现“圆浑”的立体感,不但生发出“圆足”的厚度,同时也有“圆劲”的力量感,使线条有隐隐约约“圆满”的“骨”的存在,符合人们追求圆畅含蓄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继而上升到韵味、境界等无穷范畴。王羲之《书论》:“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点银钩,方圆周整。”这就是中锋不用笔不激不厉,方圆相宜的审美效果。按照人的审美习惯,立体的事物会令感官和心理产生愉悦的快适。相反,如果违背了中锋用笔,则是另一番体验了,窦臮《述书赋》提道:“薄阙于圆备曰薄。”李世民《指意》:“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4]120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用笔的真谛——中锋,它的核心美感就是“圆美”,中锋的圆浑、圆足、圆畅、圆劲、圆满在历代书家的评论中俯首即是。
二、 “目所绸缪,身所盘桓”:“流动圆”
方东美谈论中西哲学差异时曾言:“希腊人较为着重存有之静止自立性,印度人与中国人则往往赋予存有一种动态流衍的特性。”[7]283中国哲学强调生命的流动性,世界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空间被时间化、节奏化、流动化。这种哲学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影响至深。《南史·王筠传》:“谢脁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8]611南北朝诗人谢朓最早把“圆美”作为独立的美学范畴提出来,“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诗论品评话语在后来的唐宋文论中频频出现。明末徐上瀛《溪山琴况》:“五音活泼之趣……全在圆满……于是欲轻而得其所以轻,欲重而得其所以重,天然之妙,犹若水滴荷心,不能定拟。神哉圆乎!”[9]其在音乐品评中使用 “圆美”来谈左手拨琴的吟猱技法,认为弹琴者内心表达之意完满表达并与琴音连贯圆融为一体,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好的音乐婉转动荡,无滞无碍,不多不少,以至恰好是为“圆”。我们把中国书法推崇圆转、圆活、圆通之气称之为“流动圆”。流动的线条是书法艺术诉诸人们视觉的独特符号形式,优秀的书法作品不是纸和墨组成的僵死之器,更非与人的存在毫不相干的冰冷之物,而是灌注着流动的气韵和灿然的生命气息,蕴含着宇宙天地运行生生不息的玄机。流动的“圆美”得益于书家善于运用藏露、疏密、黑白、虚实、大小、粗细、浓淡、枯润、方圆、奇正、向背、呼应、顺逆、刚柔、疏密、揖让、巧拙等富于变化和辩证精神的艺术手段。《易传》载“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传》对事物阴与阳、柔与刚等因素的阐发,直接影响到中国美学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对立统一观的形成和发展。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定然“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符合张弛结合、刚柔相济审美理想。同时,《易传》又主张在“阴阳”的对立统一中,“阳”处于支配的位置,故中国传统艺术往往又倾心于追求阳刚之美。阳刚之美总体上是进取的、尚动的、昂扬的,而书法意象之“圆美”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流动性。
宗白华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形式,其根本精神在于乐,乐是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跳舞,这是线条的舞蹈,是一种圆转流动之美。朱履贞论书法则强调“书贵圆活”,《书学捷要》道:“书贵圆活,圆活者,书之态度流丽也。”[4]604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有“圆动之处,了不关心,纵才藻灿然,终成下格,不可另着眼乎?”[10]在此,“圆动”与“圆活”的内蕴是一致的。“圆活”之美在于宛转流动,有生动灵活之趣,所以不少理论家又提倡“宛转”或“圆转”。项穆《书法雅言》:“书不变化,匪足语神也……固不滞不执,有圆通之妙焉。”“释氏怀素流从伯英,援毫大似惊蜿,圆转牵掣则其诡秃矣。”书家在此强调了书法的“圆转”之美的重要性,并从“变”的角度,阐释了书当“变化”而“圆转”“神化”,好变者方奇,道出书法需“不滞不执”,方可“圆通”,这无不昭示出书法追求圆美的品格——不固守、不滞怠,求圆活,求流转,时时刻刻吸收源头活水,于平淡中务求新奇,“不滞不执”,从善如流,如“太极”一样滚滚行进、健运不息、运转于无穷。
笪重光《书筏》:“活泼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滞者共机圆,机致相生,变化乃出。”[4]562笪重光自称郁冈扫叶道人,晚年居茅山学道,因此他的书论中渗透了浓重的道教色彩。上文他提到“共机圆”“机致相生”“机”,道家谓万物所由发生的虚无状态。《庄子·至乐》曰:“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唐代道教学者成玄英疏:“机者,发动,所谓造化也。造化者,无物也。人既从无生有,又反入归无也。”笪重光拈一“机”字,在此可理解为书家作书只有把握了道之机,也就把握了书法圆美的关键,于是则能产生自由任运、存亡无间的万千气象。《庄子·齐物论》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郭象注:“与变为体,故死生若一”。天地运行的根本规律在于变化,书法创作要把握宇宙这种变易精神,加入这种流动的节奏中,使书法意象虚实相生、刚柔相济、变幻莫测与万物相优游。
解缙《春雨杂述》:“上下连延,左右顾瞩……形圆而不可破。昔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纵横曲折,无不如意,毫发之间,直无遗憾。”[4]526钟、王何以尽善尽美?书家在此给出了精彩的回答。书法家在其作品中尤其注重外在的形式上平和、含蓄的审美追求,提出“体和势均,平正安稳”的审美原则。王书善于布置,《兰亭》中书法各种对立、统一的形式因素,在此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展示,各得其所,主体与客体达到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契合,形成了一种内心世界的共鸣,仿佛享有着同一的生命、感情和生命的节奏,从而生发出一个圆融的、和谐自由的圆形整体。这种感受并不神秘,因为“书圣”参透了宇宙人生的秘密,人与自然,艺术与人生,在书法作品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和统一,书法的线条在这里成为书家情感和人格的化身,洋溢着脉动的生命情调和文化精神。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能偃仰顾盼、阴阳起伏,如树木枝叶扶疏而彼此相让,流水之涟漪杂见却前后相承,从而形成循环不息的生命之流、激情四射的生命舞蹈,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等气象万千的审美意象。
此外,宋儒周敦颐《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冯友兰解释:“太极属本体界,永恒之中,涵有动静两潜能,而其外貌是静。至其发生功能,则入于现象界。其始为动,动之反为静,静又复动,如钟摆然,彼此相续,无有已时。”[11]299书法作品飞动的韵律是在静谧中求得,其意象世界的圆美不仅是流动的,它同样体现为圆静、圆稳、圆和、圆满、等阴柔静态之美,这种美的形态是相对保守的、尚静的、安稳的。如梁巘《评书帖》:“欧以劲胜,颜以圆胜。欧书力健而笔圆……文书整齐,少嫌单弱,而温雅圆和,自属有养之品”。包世臣《艺舟双楫》:“逐字移看,大小两中宫皆得圆满,则俯仰映带,奇趣横出已。”[4]648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刁遵》为虚和圆静之宗”。[4]828上述诸家强调的“圆和”“圆满”“圆静”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完满感和充实的审美感受,由字的充实上升为生命终极体验的快乐充实。孟子语:“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大而化之之谓圣……”[12]332这种“大”不是体量上的巨大,而是人心包容之大,是人对于自身所受局限的提升和超越。至此,书法艺术一动一静、一阴一阳的生命结构被连贯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气脉酣畅的“太极”之“圆”,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哲学精神。
三、 “胸罗宇宙,思接千古”:“意境圆”
叶朗先生认为意境“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13]。书法作品的境界与绘画和影视呈现出直观的视觉形象不同,与文学作品展示的间接想象的形象也不同。书法作品表现的文字内容本身的美感固然是不能忽略的,但其美感却是十分有限的,书法史中的经典大作往往只是在谈论“肚痛”“食鱼”、食“韭花”等人间日常琐事,其表达的文本本身不具有惊天动地的意义和文学史价值。这种美是被文学所引导的,但又不是文学所能如此直接、真实、强烈地表现出来的。因而,书法意境是因其具有超文字的、超文本的独立的形式意义。书家正是通过运用书法艺术中的经典技法手段,凝铸现实与人生、艺术和宇宙的体悟、沉思于特定的书法作品中,呈现给欣赏者充满诗性的精神空间,在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妙之作中,往往涌动着激动人心的力量,它启迪个体生命进入一种形而上的、充满诗性智慧与创造的独创性的精神空间。书法作品脱离了笔墨线条而达到纯粹精神意义上的“圆美”,我们可称之为“意境圆”。这种“圆美”表现为意境超旷远逸、虚实相间,境界浑大无际、包容无限,折射出大道、至理的浑全渊深,使欣赏者也能自觉超越一切,进入一个物我合一、圆融无碍的神妙世界。
(一)“圆美”之妙造自然、技道两进
书法“圆美”的“意境圆”首先体现在书家创作前浑然天成、心手双畅的美好状态。孙过庭言:“阴惨阳舒,本乎天地之心”“同自然之秒有”,书家作书要契合自然阴阳变化之道。李世民《指意》:“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4]120也强调“心神”之合,方可“同乎自然”,达到物我相忘得“不知所以然而然”。王僧虔《笔意赞》:“剡纸易墨,心圆管直。[4]62陈绎曾在《翰林要诀》云:“大凡学书,指欲实,掌欲虚,管欲直,心欲圆。[4]480二人共同提出书家作书需“心圆”方可“入妙通灵”。项穆《书法雅言》云:“然后审其神情,战蹙单叠,回带翻藏,机轴圆融,风度洒落;或字余而势尽,或笔断而意连……书之能事毕矣。”[4]534在这里,不论“心圆”还是“圆融”,一言以蔽之,就书家豁然贯通,忘情笔墨之间,心手调和,已然不知孰物孰我?完全处于自身生命活动的自由状态,获得了极大的快适。
书法“意境圆”又体现为书家的技艺圆熟、速成,出神入化。魏源语:“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亦可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14]5苏轼《题二王书》语:“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15]2170技艺圆熟是书家成功的第一要素,经过逐年累月的沉淀,往往会无意抵达一种化境,如风驰雨骤,鬼神出没,满眼空幻,满耳飘忽,突然而来,倏然而去,这种突然而至的文思,使书法作品浑然而就,毫无雕琢的痕迹而臻于化境。这种作品往往出自灵机透悟,出神入化,凭着突发的灵感天然成就,这偶然得之、自然天成之作往往精美无比,非人工揣摩、推敲所及。彪炳史册的“三大行书”,无一不是书家的神来之作。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中有言:“古人为诗,有语语琢磨者,有一气浑成者。语语琢磨者称工,一气浑成者为圣……一气浑成者,兴趣所到,忽然而来,浑然而就,不当以形似求之。”[16]“一气浑成者为圣”难道不是对王羲之最真实的写照吗?
(二)“圆美”之中和圆满、天人合一
书法的“意境圆”也体现于书法的赏评中,体现为书法风格、甚至是渗透着书家人格的中和圆满。清代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说道:“落笔要面面圆,字字圆,所谓圆者,非专讲格调也。一在理,一在气。理何以圆:文以载道,或大悖于理,或微碍于理,便于理不圆。气何以圆: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百转可也,一戛即止亦可也,气贯其中则圆。”[17]36历代书论在品评书家的过程中,以“圆美”相标举,形成诸种卓然的流派。在书法时代风格的划分上,不论“晋尚韵”“唐尚法”还是“宋尚意”,都是当朝书家们共同追求、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至美境界,而“圆美”的理念涵盖了这书法美的历程。晋人“尚韵”,是一种澄明的“圆韵”, 药、酒、姿容、神韵,华丽的文采词章,构成了魏晋风度。书法此时更是达到了“散怀抱、恣性情”的高度,书之“韵”是“圆动”的活泼泼的生机之美,是胸中脱尽尘浊的“圆明”之美。宋人“尚意”,强调表现“圆博”的学识,“圆和”的性情,“圆足”的意趣,“圆通”的哲理。无拘无碍的创作心态,认为“心不知手,手不知笔”的境界最堪嘉尚,追求任情适性的天然和自由,因此更接近艺术的本质。然而,书法发展至唐代开始标举“尚法”,构成了“圆美”最为集中和辉煌的阶段,这与唐代初年儒学的复兴息息相关。唐代是中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向复兴的重要阶段。统治者认为儒家思想乃“盛衰是系,兴亡效在”,并发出“有国有家者可不慎软”[18]809的慨叹。而唐太宗的“雅好儒术”,已昭示着儒学复兴的不可避免。这为书法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论字体和风格都在唐代迅速全面地封顶结壳,达到书法史的巅峰。当时官吏铨选标准: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书法与科举挂钩使唐代参与书艺的人群空前绝后地广阔,书学论著质量和数量也超越了前代,并多为后世所祖述。唐太宗在《王羲之传论》中亲自制定了“尚法”的至高标格:“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4]122他标榜王书不激不厉、阴阳相调、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的“圆美”品格,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尚法”何为?唐人在法度面前并不窘迫,而自信潇洒地展示:我即是法——唐人“尚法”是“《祭伯父草》,字字皆有规矩,不失常度”(《书林藻鉴》录陈敬宗语)的“圆备”之美;是以欧阳询为代表的“每秉笔必在圆正”体貌丰伟的庙堂衣冠、正色立朝、气象雍容的君子名士形象;是敢于在帝王面前和出:“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盛德君子之正气与坦诚。“尚法”的实质是“尚圆”,在根本上是中国艺术对于“中和之美”的崇尚与认同,不仅是书法作品要求适中、中正、不偏不倚、体式均和,更重要的是对书家“圆美”人格的追求。这就是“书圣”的意义,也是为什么后人在技法上可以模仿甚至超越王羲之,但“书圣”高贵超脱、典雅纯净的人格却永不可复制,成为后世心中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这更是书法境界追求的“圆美”留给我们永恒的话题——书如其人。因此,是唐代树立了书法“圆美”的最高“法度”,是唐代发现了王羲之。于是“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这是历史的选择。
结语
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世界的本原,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之间在本质上都是数学关系。该学派从数理逻辑分析出发,认为圆形、球形的各个部分都极为对称,具有最恰当的比例,完美体现了数量关系的和谐。他们得出结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19]15柏拉图也认为 “(世界)是旋转的,因为圆的运动是最完美的……”[20]190此外,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提到,恩培多克勒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球,处于无穷的循环之中。回望西方文艺理论的源头,西方学者对“悲剧”“崇高”等美学和哲学范畴尤为倚重和偏爱,而并未给予“圆”的研究以足够的重视。因此,产生的影响也远不及中国,这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差异有着巨大的内在关联。“圆”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范畴,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其对“圆”的尤其偏爱,古人在对“圆”的观照中呈现了他们对宇宙人生和文学艺术的深层体验,“圆”是探寻中国艺术精神的源头,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生命张力。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艺术来说,对“圆”的崇尚与追求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对“圆”进行艺术考察和美学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