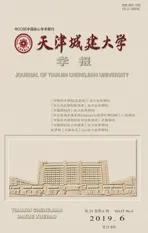农业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互动影响机制分析
2020-01-07何疏悦王祝根季建乐
何疏悦,王祝根,季建乐,徐 振
(1.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南京 210037;2.南京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南京 210028)
新的城市空间在科技进步推动的生活方式的变革中生长出了复杂动态结构肌理.由此,农业景观在其间获得了更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机遇.这些动态的结构肌理中的某些节点会演化成影响区间内社会互动频率的关键要素,它们的活跃度正向关联整个城市空间网络的结构连接强度,尤其是核心空间.农业景观空间有着能够成为这样的关键要素的能力,能激发具有结构性网络功能的弹性社会互动链接,亦能适应所在空间中不同人群及相邻空间的群体活动的差异性需求[1].将农业景观从城郊规模化的营造模式转变为城市结构空间内的点状分布模式,研究视角的转变重点在于:将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属性主导策略转换至农业生产的社会行为属性主导策略,进而实现农业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互动价值机制的构建.
1 城市空间中的景观社会互动化趋势
人类是作为一个群体共同成长的,这个群体共同参与了各类生产行为,由此建立了群体性的社会关系,与他人间的互动协作是人类的标志性特征.
1.1 城市空间要素的“减物质化”
在低价同质化的工业产品和相对高价差异化手工制品间,得益于日渐充裕的物质基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群选择了后者.与为了节省十元钱而花费一小时相比,在社区的公共空间中漫步或交谈半个小时对于生命的益处,显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社会互动对于城市空间的价值由此得以受到关注——培育实质空间中的城市生活.
城市从生产具体的物质资源转向生产服务,物质资源的消耗就会降低,社会互动的形态在此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互动的方式的重要性,开始追赶并超越人们对物质本身的渴求[2].与过去数百年的城市形态相比,今天的城市无论是在表象中的个人行为方式,还是深层次的城市发展的价值观,都在知识和信息不断累积的当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同样也要求农业生产传统适应于城市变化的需求.农业景观在城市空间中优化的区域定位,由此从边缘转向核心,而主导功能则由“产量”转为“互动”.
1.2 农业景观要素的“社会互动化”
农业景观结合城市内广泛应用的观赏性景观,能够共同适应现代城市按需即时性:更偏向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的生活方式,以租赁的方式运营及管理,不同的人群根据差异化的需求申请,城市社会互动机制得以在原有的结构空间中被重新定义[3].
可预期的未来,私人花园的数量在高密度的城市核心空间中将会逐渐减少.碎片化的时间参与是当下生活中最可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与自然互动的方式.办公场所中的农业景观、校园农业景观、屋顶农业景观甚至公园农业景观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见图1).它们只需少量的专职人员进行日常看护照料,更多的将是租赁者与随机参与者,以协同共享的方式参与照料及收获(见图2).

图1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学院建筑内庭农业景观互动区

图2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内4-H 儿童教育园
2 农业景观的社会互动介质效应
城市核心区的公共空间并不是越多、越大对城市越有益,她必须位于有效的位置和服务于尽可能多样化的人群,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活力指标[4].小尺度的空间互动能够有效减少由于缺少高质量社会连接对城市人群造成的精神压力[5].城市农业景观兼具适应碎片化空间及创造社会互动的特质,因此能够很好地成为这些空间形式中被人群乐于感知的景观要素.
2.1 契合城市空间中社会生活方式
城市居民的社会性表现在他们会比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更容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扩散程度远超居住密度较低的乡村及城郊[6].当农业景观改变了传统形态,以一种设计构思精巧的邀请姿态重新出现在城市中的时候,人们下意识的偏好则更多是尝试性的接纳,传播的影响也是正向效应,并且能够持续.
今天,城市核心区中的很多居民喜爱并接纳农业景观出现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及公园,多数不属于城市设计者们的理想规划期望,诸如对生态环境或生态足迹的担忧,也不仅是因为对于传统农业的怀念,甚至食品安全都不是首要原因.城市生活中直观感受引发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带动了意识形态的变更,视觉的参与感唤醒和社会行为的引导示范成为引发进一步参与的起点.
农业景观在“种菜达人”等潮流词汇面前可能显得过于学术,但是学术的定义并不能直接左右城市居民的主观意志,一旦此类行为在城市中因为友善谦和设计而变得时尚,它就获得了更大的生长契机.让传统变得轻松甚至有趣,才可能更好地对接今天城市空间的结构肌理[7].
2.2 培育生态教育的社会基础
耳濡目染的熏陶和现场学习是“在环境中教育”的根基.有别于“为了环境的教育”以及“关于环境的教育”,常态化的社会互动行为是“在环境中教育”得以存在的土壤.如果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这种形式的自然互动感知过程,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减少额外提供的景观生态课程[8].离开自然互动,即使安排专项的课程,效果也会非常有限.不是基于实践行为的生态价值观的感知培养,即使能够辅助言辞上的熟练精巧、科学上的严格准确,都无法弥补情感体验上的匮乏和空洞.对于儿童而言,这是打开他们关于生态启蒙教育的一个契机,在此之中,城市中的农业景观扮演着比课堂理论传授方式更为重要的角色(见图3).

图3 环境教育模式
当管理者和规划者亟待城市藉己之手变得更加的可持续之际,单纯禁止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并且通常情况下执行管理的成本会很高.提升社会互动性,以言传身教的互动,引导市民作出更为明智的决定无疑是优化的策略之一.很多时候,教育的实施往往只是比其他的方法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耐心而已[9].但是改变一旦发生,它所产生效用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那些立竿见影的措施所无法比拟的.
3 社会互动机制下的城市农业景观价值拓展
在一种积极的社会互动共生的机制结构中,某些特质间是可以相互加强的,由此产生更多类型的有效城市活动形式.
3.1 优化城市空间效率
城市,尤其是对效率追求几乎到了极致的一线城市,绝大多数都能因接触农业景观空间而获益,特别是从事对专注力要求较高的工作领域.农业景观的优势在于除却观赏性景观的自然审美价值外,其社会互动的属性更为其在帮助那些从事对专注力要求较高的工作的人群进行精神自我修复提供了额外的价值.他们自己活动了身体的同时更得到了精神上的放松[10].参与的人们对于农业景观本身的照料、管理的同时也成为了农业生产性景观向周围观望及路过的人展示的城市活动形态.
让农业景观出现在城市日常生活的毗邻地,例如街道、建筑边缘地带、学校里的开放空间以及社区内的公共空间等,就很容易使得接触到它的人群获得注意力修复的契机.办公楼顶以及楼宇内部的农业景观的出现也是由此而生,即使只是以为获取更高效率和价值为目标,这仍然是城市中令人可喜的转变趋势[11].参与者的专注力获得了提升,城市的运转效率也由此获益.而对于城市农业景观的管理和运营,效益评估,也是极为重要的前提之一.
3.2 创造新的社会连接
能够帮助达成实质性社会连接的城市空间主要有公园、商业区、街道以及社区等.这些区域的特质可以帮助催生一些基于陌生人产生社会互动的行为.基于陌生人群体的连接对于今天城市的重要性在于不断地创造新的协作机会,这是能够帮助这个城市以一种富有活力的方式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1)强连接:校园、企业生产及写字楼等城市空间,培育了城市中大量基于熟人群体的社会互动行为.社区、校园尺度下高频的重复性互动行为会让社会群体中局部生成强连接关系,即亲密的内聚性关系.这些强连接会让其中的人群形成小范围的圈子,圈子内紧密联系的人群基由反复的社会互动逐渐塑造了共同的目的、行为、兴趣和价值观[12].
(2)弱连接:相较于强连接,农业景观创造的城市新聚集场所更容易培育的是较弱的连接形式.空间内外的弱连接缩短了内部与外部不同人群间的联系路径,进而促进了城市区间内外的信息交流.不断生成的弱连接加厚了场所的边界,形成另一类开放的聚落.诸如被农业景观管理及维护行为吸引,进而前来参与的随机人群.在这样的空间中,有着全新的可达性、多样化,且具有更强的适应力,边界的低排他性催生了对待各类外部连接尝试极高的宽容度(见图4).
3.3 城市消极空间的更新
Michael Ableman,北美最大的城市农场Sole Food Street Farm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一次专访中说道:真正让这一切实现的英雄们是社区的居民.他曾经对那里的低收入者特别是吸毒者存有偏见,但是“正是我曾经评判过的那些人,却是有着热心肠、正直灵魂的人,他们拥有不同寻常的创造力、智慧,以及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渴望,我们的农场只是给了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13](见图5-6).

图4 农业景观为城市创造的新的有效连接

图5 温哥华Downtown 区Sole Food Street Farm(部分)[14]

图6 温哥华城市轻轨下Sole Food Street Farm(部分)[14]
传统的国内城市建设对于消极空间的处理简单而直接.但是,单纯的拆除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座城市获得本质性的成功.它们从一个角落被消灭,又会顽强地从另一个区域萌发出来,凋敝依旧.培养一类安定且满足最低城市生存需求的生活方式,引导农业景观参与消极空间的更新,孵化一种低成本、易操作、低维护且低技化的社会空间修复模式,让脆弱破碎的社会关系借由简单的景观构建及社区生活营造,重构局部空间的默认秩序,恢复常态化、正向的社会互动及信任机制,整个城市区域的安全稳定的发展才有实现的可能.由此帮助并协同其他相关政策、方法途径,缓慢培育城市消极空间由内而外的改善及再生[15].
3.4 参与缓解城市贫穷
行之有效的城市设计应该向贫困的人群而非贫困的地区倾斜.农业景观可以引导生活在贫困中的城市人群,培育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策略(粮食种植),与城市结构中的其他部分产生互动(粮食出售).并且,这一策略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启动资金较少,且后续资金的需求量同样易于承受.实施贯彻的重点在于城市管理者的政策倾向,推进力量部分可由市民团体或相关企业介入参与.但是,导向性的支撑必须来源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执行者.
旧金山市区的NGO 组织Farming Hope 招募城市流浪者及低收入者,对其进行简单的培训后,让他们从事城市农业景观种植[16].收获的食物经由组织方协同慈善组织机构中的专业厨师,共同烹饪并组织定期的社区主题聚餐,向社会开放售票.这个组织建造的主旨为开辟并经由一个食物系统,让低收入的人群有机会工作,教会他们需要和想要的技能.其中,组织者特别强调:“在社区里,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意义远大于种植本身.”(见图7)
此类城市农业景观对于城市贫困地区的渗透,其正面效应同样已经在西班牙、古巴等国家获得成功[18].这不仅有助于增加就业、创收,并且为贫困家庭提供了清洁卫生的食物;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结构中的一部分灰空间也由于这一行为附带转化成了城市中必不可少的社会互动介质,由此与城市中的其他区间构建链接,获取收益,焕发了全新的活力[17].

图7 旧金山Farming Hope[18]
当然,这种理想的构建策略实施起来也会遇到很多实际的困难,贫民区的居民是否同意就是首要的问题.如果是简单的意见征询,此类人群更多的倾向是工厂或者是直接性的土地开发项目,农业景观的培育显然不是首选,因为这不是能够最快获得最大收益的办法.可持续、环保、文化存续、协力互助的理念无法以说教的方式参与缓解城市的贫穷,只有先实施,以过程为教育,切实的引导,自主地参与劳动力的投入,培育良好的劳作习惯才能获得参与者真正的认同,城市农业景观才可能切实地促使改变的发生.
4 结 论
颠覆性的更新是现有城市空间结构的变革发展难以承受的.点状分布的城市核心区农业景观需要包容,而不是限定城市中的各种日常社会活动,具备足够的弹性和适应性的同时,拥有对于变化做出良好应对反应和培育机会的能力.在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中,以农业景观为基质,生长出差异化且具有区域特征属性的社会互动机制,融入当前的城市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进而创造并延伸新的社会连接.与此同时,原有的城市消极空间也能够获得低成本、可持续改善的契机.这种影响机制及其温和渐进的正向社会经济效应,是促成城市农业景观在今后被纳入城市规划改造整体建设框架的理论及实践依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