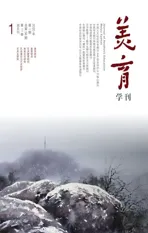观念艺术的知识谱系及其表意机制
2020-01-02汤克兵
汤克兵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在现代艺术“风格”更替演化的脉路中,至少存在着还原论与观念论这两种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如果说以格林伯格和弗雷德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将形式美学主导的艺术还原论推向极致,那么作为“反美学”先锋的现成品艺术以及战后由此衍生出的波普艺术、过程艺术、身体艺术、行为艺术、概念艺术、现场性艺术等广义上的观念艺术(1)艺术史家阿纳森认为,从艺术追求观念表达方式来看,观念主义适用于偶发艺术、电视艺术、大地艺术、人体艺术、波普艺术、光效艺术和光艺术的要素;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这些形式都互相作用。观念艺术近乎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70年代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主要艺术类型,可以视为对非绘画或非雕塑的其他艺术形式的简称。参见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邹德侬等译,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698-699页。本节所考察的就是这种广义上的观念艺术。,则一开始就挑战了自莱辛以来的传统艺术的分类和各门类艺术之间的界限,强调让生活直接成为艺术,或者借用戈登·布朗的话说是“生活本身成了艺术品”。格林伯格和弗雷德等现代主义者把以绘画或雕塑的惯例为前提的“艺术本质”等同于“艺术品质”,将所有价值判断归为形式的知觉问题,然而那只是美学上的形而上演练,实质从一开始就抑制了艺术作品的观念和思想因素。观念艺术主要针对“艺术”概念本身进行思考与突破,艺术的思想或观念永远比艺术作品的物质形式重要,或者说艺术创作过程往往比作品本身更加重要,以致最后演化为通过纯粹的语言文字来彰显艺术表现的“事件性”或“过程性”。
一、艺术的“界限”问题:现成品与空画布
我们知道,传统绘画或雕塑的“美学价值”之所以等同于“艺术品质”,是因为艺术主要以技术与情感配合作为保证,艺术自身的观念性因素因而作为一种“先验的概念”而被掩藏了。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解构了技术层面的形而上价值等级序列,通过一种心理学的内省方法,强调主体意志的胜利和内在情感的外化,艺术的问题转变为媒介的纯粹性问题以及对媒介象征意义的探索,然而艺术的“观念”和“思想”只是作为审美判断的外围支撑存而不论(例如格林伯格对“空画布也是一幅画”的审美判断就是一种独断论)。这种形式主义理论更注重视觉经验的审美表达,直到现成品艺术的出现突破了绘画与雕塑界限,对内在情感的视觉抽象表现才转化为艺术本质所关切的观念表达(对外在事物的情感或看法),艺术才开始真正发挥自身的功能。正如约瑟夫·科苏斯在《哲学之后的艺术》一文中所说,艺术之功能问题,首先由杜尚提出。自此以来的所有艺术都是概念性的,艺术仅仅是概念性的存在,艺术将其焦点从语言的形式转向内容。这意味着艺术的性质从形态学的问题转到功能的问题。这种从“表象”到“概念”的转换,正是“当代”艺术的开端,也是概念艺术的开端。[1]149
毋庸置疑,现代艺术从视觉表征到观念表达的转变,始于达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尚。杜尚的《自行车轮》(1913)、《瓶架》(1914)、《泉》(1917)等现成艺术品通常既非绘画也非雕塑,却同样能够更为简省地表达自己的观念。《泉》只不过是一件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便器,除了杜尚亲笔签名的“R.Mutt”以外,它看上去和普通的小便器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它并不能引发“美还是不美”的趣味判断。当艺术家把一件批量生产的物品当作艺术品放在美术馆里展览时,当我们所熟悉的物体进入到独特的、陌生的关系之中时,也就挑战了理性的现实模式。杜尚正是通过在经验层面无法“分类”的“现成品”来引导我们思考艺术的本质:如果视觉形式上无法区分普通物品与现成艺术品,那什么决定了艺术品的独特属性或品质?由此,艺术不再属于审美判断的疆域,反而被视为一种认知判断来对待。艺术家的选择和意图成为艺术的分析命题,对艺术的解释将有赖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命题,“意义即用途”。也就是说,特定的用途、使用方式将决定事物、物品的具体性质和意义。对艺术家而言,关注物品在不同使用方式中产生的不同意义,是艺术的观念和思维表达。
某种程度上,杜尚对艺术材料的选择行为即是一种认知判断,这表明了艺术作品诞生的语境乃是艺术的“艺术条件”。如果普通物品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就清除了“艺术”这个范畴的所有意义,但同时用一种新方式揭示了艺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们将注意力从特定物品的形式特质转向了概念的、语言的、制度的以及文化的因素的整个集合体,后者正是我们和物品打交道所采取的方式的条件[2]。达达主义不仅挑战的是美学的鉴赏趣味和视觉感知特征,而且直指艺术本质的问题:艺术只有与美分离,艺术的“语境”化问题才能浮出水面。阿尔普认为,达达主义的创造性的、实验性的反判冲动在针锋相对地质疑传统“艺术”的同时,也揭示出某种“艺术的原初的根基”。这种根基在审美上既难以理解又难以加以定义的所谓艺术的原初根基[3]174,实际上是指艺术作品与“真实”的原初关系,即艺术的“艺术条件”或艺术作品诞生的最初语境。艺术家渴望占有生活的真实,这需要废除所有的中介物。因为一位想要接近真实的艺术家,就要怀疑艺术品的物质形态。当寻常之物变得神秘难解,习惯的趣味备受揶揄,那么现成品就为杜尚追问艺术的本质提供一个契机,他与达达主义者们共通的地方在于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杜尚曾经承认,他最重要的概念是:一件艺术品从根本上来说是艺术家的思想(idea),而不是有形的实物——绘画或雕塑,有形的实物可以出自那种思想。[4]697事实上,包括《自行车车轮》《瓶架》《泉》等在内的大部分现成品“原作”早已遗失,如今收藏展出的其实都是复制品,但这并不影响作为艺术作品的观念表达,有形的实物可以不断复制,但作为观念的艺术的创造性体现了艺术家的唯一意图。达达主义者志在拥抱全部的现实,但是他们所试图获取的东西紧紧附着偶然、平淡、形态各异的经验世界的偶然性事件之中。所以艺术渗透到生活之中,生活也渗透到艺术之中。结果,一方面是“没有艺术的事实”,另一方面,混合、关联和相互渗透产生了一种从属于表现领域的语言形式,这种形式可以称为“没有艺术的艺术”,即所谓“反艺术”。[3]175
自杜尚发明了现成品艺术之后,艺术创作活动主要表达思想观念或者注重过程的体验,艺术作品不再拘囿于个人独特风格的审美判断,而是追溯其诞生的语境并将其转化了意义或观念。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美国和欧洲艺术延续了对艺术本质的探索。尽管这些作品多半都还停留在现代主义的“主流”之外,而且并不被热衷于绘画和雕塑的专业人士圈子所接纳,却代表着达达主义的这种“反艺术”精神在欧美的复苏。这股被称为“新达达”的运动思潮明显地带有观念艺术的特征。约翰·凯奇创作了一首叫做《4分33秒》(1952)的“无声”音乐作品,演奏者在这段严格的时间里不发出任何声音,无声作品表达了环境声音的真正任意性。凯奇的“无声音乐”受到罗伯特·劳申伯格“白色绘画”的影响,他取消了作品中的任何东西,除了时间(声音与沉默共同的一个特征)和环境中偶然的声音。罗伯特·劳申伯格后来做了一件更有挑衅性的事情,他将德·库宁的一幅素描擦掉,然后当作自己的作品装框展出。贾斯珀·约翰斯将一些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东西制作成雕塑,如啤酒罐和手电筒,重构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正如绘画没有“内容”,音乐没有“声音”,艺术的内涵显得“空洞”。新达达们不断挪用生活中的“非艺术”材料来展示“没有艺术”的事实,艺术充斥着生活本身的无序、突兀、乏味而显得“空洞”,这种“抽空”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既有担负超越性功能的“象征架构”的颠覆和否定。如果波洛克或者德·库宁的作品是“完整”的艺术,那么在莫里斯的作品《无题(板)》(1968)中由较低的矩形夹板所形成的空白,安德烈“拥抱地板”系列中排列建筑砖块所呈现出惊人的简洁性,或是贾德的作品《无题》中那些涂上他最喜欢的浅镉红的盒状木质结构所体现的恪守成规,都必须被看作十分“空洞”。[5]46艺术作品中的“空白”或艺术内容的“空洞”戳穿了艺术幻象的虚假伎俩,拒绝了形式主义美学观念,让观者获得了思考的自由。
波普艺术通过非个性化,类型化制作以及单调、重复的选题来远离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情感表现。艺术家们致力于非个性化,甚至发展了商业艺术技巧,以便唤起一种强烈的大批量生产的感觉。安迪·沃霍尔希望自己变成一台机器,在其艺术“制作”生涯中,他反复使用光丝网来印刷复制美钞、可口可乐瓶、汤罐头以及玛丽莲·梦露等一系列“空洞无物”的东西;利希滕斯坦的广告漫画并不注重形式感,甚至不加改变地取自商业印刷品和机械式轮廓画,他的画作具有“一种很重要的巨大感和粗俗感,这是工业化的,它代表了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真实世界”[6]342;詹姆斯·罗森奎斯特用广告牌的风格来作画。其图像大多来自杂志,它们被并置在一起的风格,用朱迪斯·格尔曼的总结语就是“嘈杂的、迅速的、粗俗的、重叠的、公开的、可见的”[6]344。尽管波普绘画的巨幅尺寸和粗俗趣味使人们相信艺术脱掉了“高贵”的伪装,但波普艺术任意地挪用商业文化中的现成图像或物品,却使人们看上去它似乎又不像是“艺术”。波普艺术家们把生活中现成图像“复制”到绘画中并不能改变这种艺术内容“空洞”的事实。实际上“波普艺术在博物馆以外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因为它一跟塞满信息的环境接触,马上就变得平凡了”。[7]然而,作为一种策略,波普艺术恰恰是在挪用商业文化形象或媒体图像过程中彰显了物品在使用中的意义。与杜尚的现成品艺术类似,普通物品在波普艺术中被直接放到艺术的位置上去,在生活环境中,这些实物只不过是寻常物而已;在艺术语境中,这寻常物就成了艺术。普波艺术毫不掩饰艺术中的寻常物的“身份”,相反还竭力呈现这种艺术的“集合”状态。这里的“集合”一词中有两个重要的观点对后来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其一,无论多少确切的图像和物品被结合在一起构成艺术作品,这些图像和物品从未丧失它们源于日常世界的功能性身份;其二,如果一个人毫无顾忌,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连接性使他可以使用很多迄今为止和艺术创作毫无瓜葛的材料和技术[5]12。在普波艺术家看来,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艺术经验与日常经验也并不是对立隔绝的,艺术经验只是对日常经验的延续。
从新达达派艺术作品的“空白”或“无物”,到简·迪贝茨和迈克尔·阿舍将“空白画布”当作艺术作品来展现;从杜尚的现成品装置,到波普艺术中的流行文化符号,现代艺术变得越空洞,也就越接近一种界限的边缘。正如“现成品”是艺术作品的临界点一样,“空画布”也成了绘画的临界点,“这样的艺术作品跟空画布一样,拒绝开口说话;二者都是模糊的和没有意义的”[8]。观念艺术正是借助“现成品”或“空画布”这一剥离了叙事框架的临界点,促使“艺术作品”或“绘画”这类先天概念解域化,从而让我们以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去看待艺术。
二、制造“事件”:观念艺术的意义表达机制
从杜尚的《泉》到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现成品艺术凸显了艺术的意义乃是“暴露”进而“假借”艺术的条件或语境。小便器本身不是艺术作品,但是杜尚的行为造成了“小便器是艺术品”的陈述,因此,杜尚关于小便器的看法或想法才是作品,即表达了一种观念。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更是强化了寻常物在“使用”过程中的意义,波普艺术对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与图像的挪用,使得艺术与日常生活边界的消失。如果说波普艺术用艺术来作一个“生活也是艺术”的陈述,那仍然是观念上的想象或解释。艺术和生活还是不同。真正要让艺术与生活的边界消失,不仅要让艺术和生活在形态上相似,还要让它们在存在方式上相似。这就是说把艺术的创作活动与日常活动融为一体,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以“事件”为艺术内容的“偶发艺术”(Happenings)[9]。偶发艺术是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一种较为短暂的艺术现象,这类艺术是一种没有中心意义和不经任何预演的表演活动。这种表演活动在诸如大街巷角、商店橱窗或者乡村这些非传统表演场地进行表演。这种偶发艺术综合了几种艺术形式于一体,如音乐、绘画和舞台表演。观众可以参与表演,表演者也可进入观众中,使艺术贴近生活。当表演结束,表演者有意识地使其表演不留下任何结果。[10]偶发艺术极富戏剧性和表演性,最早可以追溯至意大利和俄国的未来主义、苏黎世的达达主义和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这些前卫艺术家们纷纷抛弃画室和艺术陈列馆,走向演讲厅、剧院和街道,以各种表演的形式来宣扬他们的艺术观念。这些前卫表演活动一开始就受惠于流行戏剧,并以“能动性、对抗性、虚无主义和主动性”(波吉奥利语)为准则制造艺术“事件”。[11]某种程度上讲,后来的行为艺术、表演艺术甚至身体艺术都可以从这些前卫表演活动中找到各自的渊源。不过,偶发艺术的真正发展还是要得益于美国的波普艺术运动,因为大多数主要的波普艺术家创作或参加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偶发艺术,例如纽约的波普艺术家奥尔登堡和吉姆·戴恩也是“偶发事件”的首创者,他们甚至成了偶发艺术的主要成员。
根据偶发艺术的核心人物阿兰·卡普罗的解释,“偶发艺术,简言之,就是事件的发生”。[1]66一件偶发事件是一件包含了在一个特定情景或环境下,人们与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家艾·汉森看来,偶发艺术的核心理念是艺术与生活的真正融合。好比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一样,偶发艺术是一种可能性和机遇性的艺术形式。他坦承自己将行动素材、商品、条目、音效整合进一件偶发事件中,如同那是那生活中的一部分[12]。以偶发艺术为典型的“事件型”艺术拒绝现代主义艺术那种封闭的自我指涉性,通过事件或过程的“生成”来追求作品意义的无限增值。在德勒兹看来,一个对象、一件事情或事实要想成为真正的事件,它必须有超越“可见”的力量。[13]杜尚的小便器只是一个现成物品,它本身不是“事件”,只有把它放在艺术馆里当作艺术品展览时,这个小便器就超越了其物质形态而发生了某种转变,这种转变也是“视线”的转变,它意味着“事件”的发生。
姜宇辉根据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总结出“事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这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包括偶发艺术、行为艺术和身体艺术等这类“事件性”艺术的特质。首先,“事件”的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单独性。这就使得它不能成为单纯的事实性的状态,它不从属于任何现有的分立的存在领域和体系,我们只能从它的“单独性”来认识它,而这种单独性又并非是一个空洞的完全缺乏规定的“点”,而是说它的丰富性已经溢出了我们现有的存在体系。其次,一个事件与另一事件之间存在着难以被最终抽象化和同一化的差异,我们不能将不同的事件归属于其中的普遍的或者一般的概念,也就是说不存在“事件”的“类”。再次,“事件”虽然发生在特定的时空点上,却是一种能动的状态,是一个戏剧性的奇点,它的发生使得在这一点上的现有的时间和空间状态发生变化,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最后,“事件”的这种改变时空结构和向度的状态使得它成为不同的存在系列和层次的交叉点,而它自身又包含了这样的可能,即向着更为差异化的方向开放关联。德勒兹用“断裂”(rupture)甚至“爆裂”(crack)来形容“事件”点上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总的来说,“事件”既是“一”(“单独性”“独特性”),又同时是“多”(开放性、可能性)。[14]
偶发艺术与后来的身体艺术、行为艺术等更为惊颤的艺术类型,通过把艺术生成的“事件性”或“过程性”推向极端,来表达某种概念或意义。伊夫·克莱因的飞行实验,艺术家自己从高墙上旋转坠落的几幅照片,代表了首批由个人记录下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观念艺术作品特征的表演或人体艺术;阿尔曼1960年的展览,在巴黎一个画廊塞满了两卡车垃圾;还有荷兰艺术家斯坦利·布朗1960年的宣言:在阿姆斯特丹所有鞋店都举行着他的作品展览;皮埃罗·曼佐尼发亮的、上面写明内装艺术家大便的圆筒,等等。[15]278道格拉斯·休布勒从1971年决定开始一项以1000万人为目标,用黑白照片记录人类目录的计划。虽然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依然没有完成1000万人的拍摄计划,但是这项艺术行为本身已经是一种概念性表达,因为作品就是他的行为本身所传达的观念。而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在过程艺术或反形式口号下创作的,虽然他们继续使用物质材料,但抛弃了客体,取消其作品中的结构、永久性以及固定的界限,代之以随意即兴、临时的分布,在室内室外撒播碎片、无固定形体、容易消失的物质——锯末、切割开的毛毯、废颜料、面粉、橡浆、雪,甚至玉米片。其他人则保留永久性而抛弃变动性,在风景区远处设计、建造巨大的大艺术作品。过程艺术和大地艺术通常只有通过照片才为人所知,这表明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对它们来说,都要求一种非物质的、观念中的存在。[15]279-280由于这类艺术是发生在开放而真实(而不是完全被演出的)环境中的不可预知的“行为”过程,用卡普罗的话说,即“在超过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的情况下,去表演或理解一些事件的集合”[4]612。因而对事件“过程”的推重无疑导致这些艺术形态具有了情境性特质。观念艺术正是诞生于情景转换中。观者通常先是本能地把某个情景当作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艺术家也正是利用了这种“前理解”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卡普罗的创作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偶发艺术的参观者时常不能确信发生了什么,它什么时候开始,或什么时候结束,甚至是什么时候出现了“差错”。然而,正是通过发生这种“差错”,某些东西反而变得更“对”了。[1]68在这里,卡普罗所说的“差错”,意味着事件的发生,即是德勒兹所说的“断裂”(rupture)甚至“爆裂”(crack),主要是来形容“事件”点上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这种转变也是“视线”的转变,与杜尚的“小便器”展览一样,都意味着事件的发生。然而,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件都是艺术,“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有时,这样的架构直接以虚构作品的方式向我们呈现,这种虚构物恰恰使我们能够间接地表达真相”。[16]“事件”的这种“爆裂”必须通过一种突如其来的瞬间击中,使主体意识中所有前经验的东西失效,使观者心灵处于暂时涣散状态,然后经由视线转变回到现场,进而有所领会。我们对艺术及其意义的获得,正是通过回溯性地撤销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差异性。艺术反映了经验能够被理智地和创造性地挪用、转换。……当艺术家对其材料的自觉态度延伸到所有经验时,即延伸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生活本身就可能变为艺术。[17]因此,艺术作品不再依赖某一物质形态才成为艺术,而是融入生活经验,一件日常事件的发生过程本身就构成了艺术。艺术让我们进入生活,而不只是表现生活。
三、结语
观念艺术强调“概念”或“观念”至上,甚至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艺术”。在观念艺术家看来,视觉经验和感官愉悦只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因此观念主义艺术提倡“反形式主义”和“去物质化”。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理解,经由审美判断过渡到艺术的认知判断。观念艺术通过“现成品”和“空画布”这两个分别关乎艺术和绘画本质的临界点,揭橥了艺术的本质只是一种“命名”的事实(绘画的本质也只是一种历史惯例使然),这就促使“艺术作品”或“绘画”的先天概念解域化,并由此确立了一套更为开放的艺术表意机制。从杜尚的“小便器”到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现成品艺术凸显了艺术的“意义”乃是成为艺术的“艺术条件”或“语境”,“小便器”本身不是艺术作品,杜尚关于“小便器”的“看法”或“想法”才是“作品”本身。同样,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更是强化了物在“使用”过程中的意义。以创造“事件”表达意义的偶发艺术、身体艺术、行为艺术等更为惊颤的艺术流派,将一件日常事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艺术,事件的发生或体验的过程即是“艺术作品”;以语言文字为本质、以文献实录为媒介的概念艺术(也就是狭义上的观念艺术),作为纯粹观念表述的概念艺术在去物质化或反形式主义方面走得更远,因而也是最为典型、最为激进的观念艺术。概而言之,在观念主义者看来,观念主义的实质永远是概念的或观念的,它无关形式或材料、媒介或风格。尽管艺术的概念需要媒介来呈现,但是艺术作品的物质载体并不具备唯一性和真实性,真正有创造性的是思维存在本身,概念永远比形式更深刻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