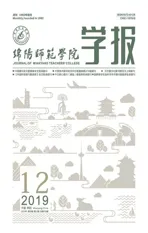最后一场南北战争
——论《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嗅觉叙事
2019-12-30冉西楚
冉西楚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人的身体具有五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在文学研究中,视觉研究处于霸权地位,而后三者往往被学者忽视。1988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恶臭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社会想象》(TheFoulandtheFragrant:OdorandtheFrenchSocialImagination)①的英文版本问世。此书独辟蹊径,从气味的角度出发,分析18-19世纪法国社会和观念史,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嗅觉沉默。自此,一向处于研究边缘的嗅觉研究逐渐引发了学者的兴趣。吉姆·杜布尼克(Jim Drobnick)编著的《嗅觉文化读本》(TheSmellCultureReader)②收录了从不同角度分析嗅觉的36篇文章。杜布尼克认为嗅觉是文化意义上的,气味区分了自我和他者,常隐含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仇外思想。其中道格拉斯的《嗅觉地景》(Smellscape)将风景研究注入嗅觉研究之中,认为正如视觉印象一样,味道在空间、地点和时间上也有分布的规律。这篇著作虽只从宏观意义上研究嗅觉,但其实验的方式科学,观点新颖,极具参考价值。德国学者丹妮拉·巴比伦(Daniela Babilon)于2017年出版的《美国文学中的气味力量:气味、影响和社会不平等》(ThePowerofSmellinAmericanLiterature:Odor,Affect,andSocialInequality)结合种族研究、性别研究、酷儿理论、创伤理论等,将气味和福柯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研究美国文学中的气味主题,其研究涵盖了麦尔维尔、惠特曼、莫里森、福克纳等。在福克纳部分,作者通过细读《八月之光》,论证南方社会的主要群体如何维持他们的性别和种族地位,并揭示了当一个白人女性的行为已经暴露了她冒犯的性行为时,她的错误是如何转嫁到身边最亲密的美国黑人女性身上的,从中体现背后权力的运作体系[1]。
比起西方,国内在嗅觉方面的研究较为滞后。与嗅觉相关的论文大多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少。2012年张世君发表在《国外文学》的《意识流小说的嗅觉叙事》从嗅觉出发,分析三部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嗅觉叙事。作者认为,气味是意识流小说心理活动的生理诱因之一,贯穿情节始终;气味唤起人物与过去经验的记忆;嗅觉叙事包含了特有的伦理隐喻和作家自身的道德批判[2]。其论证丰富,论点新颖,实为佳作。武汉大学的林翠云深受道格拉斯的“嗅觉地景”影响,认为嗅觉激发了潜意识记忆,为时间和空间提供线索,从主人公的童年、爱情及自我三方面分析,建构了主人公的嗅觉地景[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尚未找到学者对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下文简称为《献给》)进行嗅觉叙事方面的研究。正如丹妮拉所说,福克纳是嗅觉大师,擅长用气味叙事[1]154。在其经典短篇《献给》中最突出的气味为刺鼻的腐臭,其次便是大量出现的尘封之味以及隐匿在暗部的现代化气息。这些气味仅仅是偶然存在的吗?抑或是有更加深层的含义?本文拟定从隐含叙事、时间和空间、道德倾向三方面来解读《献给》中的嗅觉叙事,试图挖掘作者的隐含意图。
一、腐臭背后的隐含叙事
《献给》中最为突出的气味莫过于腐臭。小说第二节讲到,艾米丽被心上人荷默·伯隆抛弃后,众人闻到越来越严重的臭味,抱怨不已。他们一开始认为是因为黑奴没有把厨房的卫生做好,后来猜测是因为黑奴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由于不好当着贵妇人的面说她家有难闻的臭味,第二天午夜四人去撒石灰,一两个星期后,气味消失了。表面情节很是简单,但其中存在不少疑点。叙述者可靠吗?为什么镇里的居民没有怀疑过艾米丽?为什么采取偷偷撒石灰的方式处理这件事?艾米丽和黑奴如何忍受这么强烈的腐臭味?
为了重现腐臭事件,首先需要推算时间、地点和温度。根据文中的细节推测,恶臭事件发生在19世纪末,艾米丽三十出头。福克纳是密西西比州人,自幼在奥克斯富镇长大,他所塑造的杰弗生镇便是家乡的写照。文章描述“他们蹑手蹑脚地潜入草坪,钻进街道两边洋槐树荫之中”[4]122。在美国南方城市,洋槐通常在五月初进入花期,七八月树叶繁茂,秋季衰败。这里最可能的季节为夏季七八月。密西西比夏季温暖潮湿,气温多在30摄氏度左右。
人体死亡后,一般经过二十四小时左右,开始出现腐败现象。此时,机体组织中受腐败细菌的作用分解为简单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从口、鼻、肛门等腔道涌出,产生大量腐败气体,使尸体液化失去原形。腐败最适宜的气温是30到40摄氏度[5]。温度越高,气温越湿润,空气越流通,腐败越快。若尝试重现现场,极可能的情况是:夏季的某个傍晚,荷默·伯隆来到艾米丽家,负责饮食的黑奴根据艾米丽的命令,把砒霜放进荷默的食物中将他毒死,随后两人将他搬上床。既然臭味如此明显,小说也从未提过使用任何药物器具进行防腐的痕迹,荷默的尸体极有可能一直暴露在外,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中快速腐败。
尸臭主要含有氨、胺、硫化氢和甲硫醇,味道极其刺激,且带有毒性。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尸体散发的腐臭味绝对比一条死蛇或一只死老鼠的臭味强烈得多。可以说,光是通过腐臭味的强度,经验丰富的居民也能断定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正如迪尔沃思(Dilworth)所说,死去的至少应当是大型动物[6]。其次,小说第三节已经讲到艾米丽买砒霜的事,大家都在盛传“她要自杀了”[4]126。第四节更是明确写到荷默·伯隆消失之前,曾有邻居“亲眼看见那个黑人在一天黄昏打开厨房门让他进去了”[4]127。婚礼并未进行,荷默消失,尸臭四溢,艾米丽有很大的嫌疑,但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她呢?居民采用的办法也十分含混蹊跷。他们选择在半夜时分潜入艾米丽家的花园,在地窖门和所有外屋都撒上了石灰。没有人会把大型动物埋在屋内,持续两周的恶臭已经让艾米丽的行为暴露无遗。与其说他们是在消除恶臭,不如说他们是在帮助艾米丽掩盖罪行。当臭味散去之后,叙述者说“自那以后,我们开始真正为她感到难过”[4]123,并提起了艾米丽的疯奶奶。假如叙述者真的相信恶臭只是因为黑仆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他们断然不会对艾米丽产生那么大的同情心,联想到疯癫的奶奶,暗示艾米丽拥有疯癫的血液。这一切证据都说明,叙述者并不可靠。正如刘玉宇在《艾米丽的“同谋”》中写的,叙述者“我们”显然对艾米丽的谋杀是知情的,却整整花了四十年保守秘密[7]。
二、嗅觉的时空象征
道格拉斯在《嗅觉地景》[8]89-106将风景研究注入嗅觉研究之中,认为正如视觉印象一样,味道在空间、地点和时间上也有分布的规律。味道并非随机分布,而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气味源头的强度、与源头的距离、气流强度和方向、接收气味的灵敏度等[8]91。一个空间、场所往往能够被气味作上标记,大到国家、城市,小到街道、房子、医院、图书馆、吸烟区等等。气味也能体现季节变化、城市发展等。
若说在《献给》之中,艾米丽所居住的房子究竟是怎样的味道,除了最为明显、刺鼻的腐臭味以外,还有贯穿小说的霉味和灰尘味。代表团拜访艾米丽时,走进阴暗的门厅,“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又沉闷”[4]120,她使用多年的枕头已经黄得发霉了。无论是腐臭味还是灰尘味,都暗示了空间的特征:狭小、封闭。房子的气味与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平行变化。
尸体开始腐烂时,气味极其强烈,刺鼻的腐臭味侵蚀周围的空间,空间是外扩的。随着石灰的倾洒和时光流逝,腐臭味侵蚀的空间缩小,随着锁紧的房门被封锁在房内。接着尸体白骨化,几十年过去,腐臭味被灰尘和霉味覆盖,最终随着艾米丽将楼上封闭,尸体仅剩的味道被锁在神秘的楼上,被封印在床上,最后遗留在那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上,“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4]130。最终消失殆尽。气味从浓到淡,空间从大变小。不仅如此,气味与艾米丽的身体活动范围基本一致。最初,艾米丽还会和荷默一同上街。荷默死后,她关了前门,把自己锁在房子里,极少出门,四十岁左右开了画室,短暂地开了前门,之后前门永久地关上了,并把楼上封了起来,俨然为自己建好了墓室,变成了“神龛之中的雕塑躯干”[4]128,失去了肉体的活力,成为了僵死的行尸走肉。作为南方仅剩的贵族女性,艾米丽携黑奴在恶臭的、满是灰尘的房子里走向衰亡。从刺鼻的恶臭到尘埃之味,象征着一位南方女性从反抗到死亡的过程,描绘出被男权社会侵蚀的女性身体和奄奄一息的南方旧贵族制度。
时间方面。小说在客观叙事上,从艾米丽三十岁叙述到她七十四岁,打破了叙述顺序。从艾米丽的葬礼说起,讲到她拒绝纳税、臭味事件、父亲去世、与荷默谈恋爱、买砒霜、荷默消失、艾米丽去世、发现荷默的尸体,再回到艾米丽的葬礼,叙述是圈状的。尘封的灰尘味贯穿始终,体现了时间编织的牢笼。心理上,艾米丽的时间是静止的。她明明可以让黑奴打扫房间,但她没有,厚厚的灰尘覆盖在房子中,画架失去光泽,她安静地躺在死尸身边,枕头黄得发霉。在她的世界里,时间是停滞的。她拒绝任何变化,因为变化对于她而言是失去,失去爱她的人,失去仅有的贵族尊严和特权[9]。她宁可停滞在最美好的幻象之中,被牢笼紧紧锁住。
除此以外,小说还隐藏着一种味道,那就是艾米丽住所周围汽车间和轧棉机的味道。通过隐隐约约的味道,福克纳实际上客观再现了20世纪初美国南方的客观现实: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贵族没落,北方工业兴起。根据科梅尔·范恩·伍德沃德(Comer Vann Woodward)的观点,1879年北方对南方的政策从传教到政治控制阶段,再转向经济剥削阶段,从而启动了南方的工业化,这种发展一直持续到20世纪[10]114。黄虚锋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在南方工业化的过程中,南方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商业和农业服务,城市多为单纯的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集散地[11]92。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棉花显示了它作为“王”的威力,棉花种在哪里,铁路就修在哪里,城市就建在哪里,汽车成为了经济地位的象征。艾米丽的一生正是内战后南方蓄奴制取消,美国全面工业化的时代。而她代表的正是拒绝流动的贵族,令人尊敬的南方尸骨,注定被时代抛弃。贯穿始终的灰尘气味是无声无息的牢笼,被困于传统观念的没落贵族女性只能癫狂,扭曲的爱化作恶臭,最后这一切气味都被工业化气息覆盖,旧的雕像倒塌,过去的南方消亡。
三、嗅觉背后的道德倾向
虽然福克纳并未直接在小说中评价人物,像传统小说那样说教,但他将气味纳入叙事之中,通过气味的描写做出道德批判。张世君提到,在西方嗅觉文化中,品质高尚的人往往被形容成芬芳的,而地狱、瘟疫、邪恶往往被形容成恶臭的[2]64。《献给》之中的气味无疑是臭的,那么福克纳对杀人凶手艾米丽、直接帮凶黑奴以及隐秘的间接帮凶群众的态度仅仅是批判吗?
首先,福克纳用腐臭味和尘封之味定义了艾米丽和黑奴的身份。道格拉斯说,气味接收者的适应度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当一个人暴露在一种气味之中一段时间后,对这种气味的敏感度会急剧下降[8]90。腐臭味再刺鼻,两人都已习惯;尘封的灰尘之味再明显,他们也难以察觉。这两种味道长年累月地萦绕在房间之中,沾染在他们身上。福克纳说“她看上去像是长久泡在死水之中的一具尸体,肿胀发白”[4]121,她俨然一具散发着臭味的尸体。待在艾米丽身边的他“似乎由于长期不用嗓子而变得嘶哑了”[4]129。他没有了自己的思维,如同一具无生命的机器。气味渲染了他们的身体,塑造他们的身份,将他们拉入将死之域。
而同处于臭味之中的艾米丽和黑奴,有着不同的结局。黑奴在女主人死去之后,打开了前门,迎接了第一批妇女,请她们进来。房间里尘封多年的空气终于得以流通。黑人穿过屋子,走出后门,随即消失不见。他为什么选择打开前门?是女主人的意思还是他个人的意思?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他之所以要在尸体被发现之前消失,也能理解,因为一旦被发现,他一定会面临审判。总之,如果说腐臭和尘封之味象征着南方故步自封的奴隶制度,黑奴最终得以摆脱臭味,得到解放。而身为南方最后一位贵族女性的艾米丽并未得到解脱,她死在臭气之中,最终也注定与臭气合为一体。那么,福克纳对艾米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事实上,他的态度隐藏在小说中“我们”对艾米丽的态度之中。
关于“我们”,小说中有一句蕴含深意的描述:“因此,那种气味越来越厉害之时,她们也不感到惊异。那是芸芸众生与高贵有势的格里尔生家之间的另一联系。”[4]122这里的联系指的是什么?仅仅是指芸芸众生能够嗅到艾米丽家的味道?仅仅是芸芸众生的惊叹:原来贵族家里也会散发恶臭?在第一章,我们分析到,叙述者事实上已经知道了艾米丽的罪行,却帮她隐瞒了四十年。那么这里的“联系”是否指的就是艾米丽和芸芸众生的同谋关系呢?叙述者为什么要帮助艾米丽隐瞒罪行?叙述者一开始就不愿南方贵族之女和北方佬荷默交往,不惜编造出荷默是同性恋的传言,可当艾米丽认真却被荷默拒绝时,他们更加憎恨荷默了:诱惑一位高贵的南方偶像,却拒绝娶她,这是对南方的侮辱。托马斯分析到,叙述者并不介意她杀掉一个北方佬。事实上,她的谋杀可以看作南北最后一场战役[6]257。这是一场安静的、绵长的战役,以恶臭和玫瑰为标志。艾米丽是这场战役的女战神,她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战斗。而当地居民表面上毫不知情,实际上他们是艾米丽的秘密支持者、合谋者。虽然他们在南北战争中失败了,虽然南方旧制度已然腐朽,可他们的偶像最终守护了自身的尊严。事实上,最为关键的语句在小说中的第二段就提出了:“现在艾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那些名字庄严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们沉睡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那里尽是一排排在南北战争时期杰弗生战役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无名军人墓。”[4]119
福克纳不仅不谴责这种合谋,他还是支持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不选择平铺直叙地写,而选择变换叙述顺序,用非线性手段将叙述者隐藏在案件之外。如此,他不仅隐瞒了群众的罪孽和动机,而且也隐藏了同样作为南方人的他心中的反叛。作为南方作家,福克纳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将南方没落贵族女性的房屋描绘为恶臭的,谴责旧贵族的冥顽不灵,对黑人的束缚。他知道旧南方在战败后逐渐瓦解,南北战争是正义战争。另一方面,在各种气味背后的隐藏叙事表明,战争、宗教、政治颠覆着南方民众的固有观念。在旧南方的种植园和奴隶制度解体中,民众,包括福克纳本人都极其不适应。他们仇恨北方人的侵略,怀念着旧制度,恐惧机器对生活的侵蚀。哪怕终将失败,也要联合艾米丽进行最后一战。
四、结语
福克纳是位嗅觉大师,除了《献给》,福克纳的其它作品也同样充斥着各种气味,如《喧嚣与骚动》中的树香味和忍冬味,《烧马棚》的乳酪味和罐头肉味,《我弥留之际》的尸臭味等。这些气味并非偶然出现的,而是福克纳刻意安排的。气味不仅能提供作品必要的时空信息,还是一种隐藏的叙事。对作品气味的挖掘可以增强对作品人物、情节、背景的理解,挖掘作者的真实意图、道德倾向、政治立场等。
文学研究中经历着漫长的视觉至上(ocularcentrism)的探索阶段,而如若人们进入嗅觉至上(olfactocentrism)③的领域,就会意识到不同的气味往往无形地缭绕在小说之中,正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说的那样:若凡事皆为尘烟,所有认知都将通过气味获取④。当读者沉浸在嗅觉的领域时,感知和思维的方式都将得到启发,得到改变。气味至上的文学世界还充斥着大片神秘领域,等待各位学者的探寻。
注释:
① 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恶臭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社会想象》首先以法文版本于1982年出版。文本选取了米莉安·L·柯婵(Miriam L. Kochan)于198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版本。
② 吉姆·杜布尼克编著的《嗅觉文化读本》于2006年出版,共分为七个部分,可译为气味恐惧(Odorphobia)、嗅觉空间(Toposmia)、气味与身份(Flaireurs)、论香水(Perfume)、气味与性(Scentsuality)、易挥发的艺术(Volatile Art)、崇高之精粹(Sublime Essences)。其中,道格拉斯的《嗅觉地景》收录在第二部分嗅觉空间。此书将读者带入以嗅觉至上的神秘领域。
③ Olfactocentrism为《嗅觉文化读本》介绍章的标题,为吉姆·杜布尼克根据术语ocularcentrism(视觉至上)造出来的新词。
④ 来自达文波特(Davenport)翻译的《赫拉克利特和第欧根尼(Herakleitos and Diogenes)》,199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