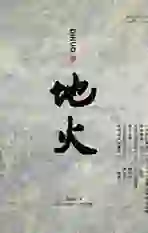你听到那种声音了
2019-12-19宋剑挺
刘一天躺在病床上,一醒来就问,样刊到了吗?我小心翼翼地说,没有。我猛然觉得这样说不妥,又改口道,编辑既然答应了,是不会变卦的。这篇小说绝对会发的……
严格来讲,刘一天是个生意人。他有十一个钻井队,资产超亿元。但他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一有空就拿着笔写呀写的。他老婆韩英只要见他写字,就会厌恶地走开,边走边嘟哝,字能当吃能当喝呀,闲得蛋疼!韩英怕刘一天,不敢当面发火,背后给我讲,他要是不整天写那没用的小说,俺的家业比现在要大得多。我想劝她两句,但想想又不知说啥为好。人家是富人,我是一个打工仔,怕讲不好人家烦,所以面对韩英的牢骚,我只有闭口不言。
家人都知道刘一天得了胃癌,但他们陪伴他的时间很少,韩英来的次数多一点,来了也只是简单问几句病情,然后就找个理由走了。由于家大业大,大家都很忙,没人闲着陪他。有时我想,假如他没恁大的产业,家人们恐怕也不会这样了。但刘一天好像没考虑这些,整天关心的都是小说的事。他躺在床上,身体变成了一具骨架,白色的被褥雪似的埋着他。我觉得他成了一根木棍,干干瘦瘦的,没一点生机。
我想让他轻松一点愉快一点,每天早上,就把鲜花搁在他的床前,再给鲜花洒上水。接着打开窗户,把窗扇弄正,好让第一缕秋阳落在这扇窗户上。刘一天醒来瞅见花瓣上静默的水珠,脸上便光艳了许多,这是一天中少有的气色。多年前,我曾见过他这种样子。
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就被刘一天的钻井公司聘用了。实际上我不愿来这个公司,它吸引我的是它给的3000元月薪。父亲看病需要钱,妹妹上学也需要钱,我已不考虑喜不喜欢了。
那天下午,我被告知到银海饭店去,说老板要请吃饭。那天阳光很强,我走进饭店,觉得光线像树叶一样哗啦哗啦地落了下来。我进了房间,他们早已到齐了。座位上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把我给大家作了介绍,当时我纳闷他咋认识我呢。他细瘦细瘦的,又戴着眼镜,像我中学时的一个老师。
他让我在他旁边坐下,他另一侧坐着的是一位微胖的女人,依次往下是四五个胖胖瘦瘦的男人,都是公司各部门的主管领导。我知道这是个家族企业,无心听他介绍,只顾哼哼哈哈地点头。戴眼镜的这个人当然就是刘一天了,不像我想象中的富人肚子挺着盛气凌人的样子。他甚至有点忧郁,话不多,只是时不时地给大家让菜。席间,微胖女人倒成了主角,这肯定是刘一天的老婆了。和我一起被录用的還有三位同学。他们学的都是钻井,刘一天的老婆和他们说说笑笑的,很是投机。我学的是中文,他聘我有啥用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们在省城参观了他的豪宅,这栋别墅是用1000多万元买下的,回来后大家不住地叹气。一人说,刘一天就是现代的皇上,他吃的住的用的,皇上也比不上。另一人说,1000万钞票有多重,几个人才能扛得动?于是他们摁着计算机,吭哧吭哧地算起来。我不想知道这些,我只想把每月的3000元尽快地挣回来。本来还能休息一周,在我的要求下,我提前上班了。
他的井队都在陕北地区,刘一天就住在陕北的一个县城里。我进了他住的院子。院里没人,风却吹得有劲,墙头上的茅草唰唰作响。院墙仅一人高,墙外是一片沙地,屋后立着几棵白杨,风从沙场上跳过去,又扑扑腾腾地窜到树上。我正在犹豫,旁边小屋里走出一个勒围裙的女人,我讲明来意,女人朝一个房门指了指。门虚掩着,推开房门,发现东西两面墙上各放着一个书架,有些书也许放不下了,都零乱地堆在地上。屋里较暗,我进了门,还没瞅清屋内的东西,陡地飘出一个声音:你过来了。我吓了一跳,仔细往里瞅,才从暗色里辨出一个人来。
刘一天坐在桌子旁,桌子上摞了许多书,桌子正中则放了一本稿子。见我来了,他放下笔,忧郁地瞅着我。我叫声刘总,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我朝稿纸瞥了一眼,稿纸上都是字,他正写着东西。他给我倒杯水,又重新坐到椅子上。他的头靠在椅背上,身子深深地凹了进去,整个人变成一件挂在椅子上的衣物了。我看出他有心事,且是重重的心事,不想打扰他,便和他寒暄两句准备出去。他却止住我说,我是专门挑你过来的。我有点惊奇,因为在招聘现场上,并没有看到他。他好像觉察到我的迷惑,便低声给我说,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文科学生,还发了很多文章。我好写小说,想让你帮帮我。他这一讲,我有点汗颜,在学校我是发了一些文章,但几乎都是些无聊之作。从内心讲,我真正喜欢的不是中文,而是历史。我怕他伤心,没有讲明,只是说些中听的话敷衍他。
外面阳光灿烂,屋里却暗得有点眼晕。我不明白他为啥不打开台灯。
他歪在椅子上,跟我谈了许多话,话题最多的当然是小说。他说他已写了多年了,但就是没多大长进,连他自己都看不中,更别提投稿了,所以一篇篇写好又一篇篇地压了起来,时间一长就积成一摞摞的废纸了。说完,他把我领到一个储藏室。里面有两捆东西,每捆有一米来高,上面压满了尘土。他指着两捆东西说,这都是写的稿件。
我心里震了一下,又感到像把刀子划过,有种隐隐的难过和疼痛。
我不敢再瞅下去,就故作随便地说,咱到外面坐坐吧。他又坐在椅子上,一点一点地瘪了下去。他的脸色灰暗,没一点生气,如一枚晒干的果子。我安慰他说,小说本来就难写,现在更难写,名家多大家多,他们都是专业作家,赶上他们可不是易事。他的身子动了动,半天才幽幽地说,我不赶他们,我只求能达到发表的水平,这一点就是做不到。我再想安慰几句,但脑里空空的,就是挤不出一句话。我斜眼往外瞅,外面晴晴朗朗的,风却一个劲地刮着,我奇怪,这个季节咋恁多风呢。
刘一天说,他喜欢这种风声。
窗外是片草地,也长着几棵白杨。我把窗户打开,风便孩子似的钻了进来。这时桌上的鲜花晃了一下,病床的单子也跟着晃了一下,风就有了形状。刘一天扬着苍白的脸问,你听到风声了?我迷瞪着答,啊、啊,听到了,听到了。实际上我什么声音都没听到。他见我点头,又补充道,应该不全是风声,而是那种风吹沙子的声音,刷刷地,带着轻微的铜音……他自言自语地讲着,然后扭着身子,极力瞅着窗外。这时,他脸上洇出一点红光来,额头变得明亮了,似乎渗出湿湿的汗液。
他写小说时往往是这种表情。我就住在他的隔壁,平时收发传真,处理公司的日常杂务。为了让他静心写作,我想把他房里的电话,挪到我房里。他怕耽误生意,说,这样习惯了,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电话断断续续地响着,他接了电话,安排好天南地北的工作,又吭吭哧哧地写起来。我惊奇得很,电话时不时响起,他咋能静心写作呢。
他的小说写了不到一半,公司要进一个井架,设备远在上海,为了把配套设备整好,刘一天不得不亲自赶往上海。我和他上了一个软卧车厢,他把稿纸一铺,就紧张地写起来。列车咣咣当当地响着,车内的广播还咿咿呀呀地唱着歌,这似乎对他没多少影响。
正是夏天,空调不太好,他的胸前背后渐渐地湿透了。我一直陪他熬着,直到子夜时分,他还伏案写着。我说刘总睡吧。他说你先睡吧我再写会儿,现在正写到一个关键情节,不敢停呀。
我不知睡了多久,被一泡尿憋醒,抬头一瞅,他还在写着,这时已是夜里两点了。
早上下了车,他依然精神很好。我们到了厂家谈了一上午,等签了合同,吃了晚饭,回到宾馆已是夜里十一点了。洗漱完毕,我以为他要睡觉,他却把稿子往桌上一铺,又呼呼啦啦地写了起来。由于喝了酒,他的脸红红的,一直红到了脖根。我说,刘总,你这样还能写吗?他说,我没喝高,我留着量咧,预备着晚上写作咧。
返程时,为了保持安静,他把一间软卧车厢都包了。天一黑,走廊里安静了,他拿起笔开始写了起来。列车咣当地响着,广播里仍然放着歌曲。我还是那样惊奇,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他怎么能写下去呢。
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过去了,我正准备睡觉时,他却坐着不写了。他先是朝窗外瞅瞅,愣了一阵,接着是一声接一声的叹气。我问他咋了,他说,刚才写得挺顺溜,一会儿就找不到感觉了。我说,你一天没有闲着,可能是累着了,脑子一累,就会变得空空的了。他拍拍额头说,我并没觉得累得慌,写着写着就感到前面有个坎,咋也跳不过去了。我说,你现在甭写了,干脆睡吧,明天到家再试试。
我们赶回前线那个县城,已是中午了。一进屋,电话就叮叮铃铃地响起来。他边接电话边吃饭,忙了一阵,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说,刘总休息一会儿吧。他揉揉眼说,再写会儿,写上一会儿就睡觉,我得把路上浪费的时间补过来。他不睡,我也不想睡,替他处理一些杂务。过没多久,门吱地开了,他從房里出来了。我猜测他又写不下去了,就给他端去一杯水。他喝了一口说,跟在火车上一样,没一点想写的意思,脑里好像有滩烂泥把里面堵得死死的。我说,你还是睡会儿吧,睡足了也许会好一点。
他没有睡,而是走出了院外。院外是片沙滩,滩的中间有几棵酸枣树,他就围着枣树走着。沙地上满是深深浅浅的脚印,风在枣树上晃了几下,就一头冲下来,扑到沙地上。这时他站住脚,歪着头,似乎倾听着什么。我仿佛瞅见风拉长身子,在他面前袅袅娜娜地舞动着。
他围着沙滩走走停停,一圈连着一圈,好像不愿停下了。风照样吹着,有的跑向树梢,有的跑向墙头,有的则懒懒散散的,自己也不知跑向哪里了。我感到,它们就在我耳边响着,嘤嘤嗡嗡的,像孩子的说话声。这难道是刘一天所说的那种声音吗?
回到房里,他又继续写起来。他的门关着,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声响,我想给他送杯水,但走到门口又站住了,我不能打扰他。我已发现多次,每次写作中卡住了,他就走到沙地上转上几圈,回来后就能继续写了。他多次说过,他能听到沙子蹭过树叶的声音,这种声音跑进脑里,像吹进一股风,到处都是凉凉爽爽的。
转眼到了雨季,公司生产更难组织了。有两个井队的道路被冲,需要找人抢修。刘一天带着我住到了井上。白天我们和工人一起干活儿,晚上就睡在井队的铁皮房里。经过一天的晒烤,铁皮房如蒸笼一般,刘一天脱掉上衣,铺开稿子就吭哧吭哧地写起来。我说,刘总,最好先放放,回家再写吧。他一抹脸,甩掉一溜汗水说,我心里不能放事,赶紧写完拉倒了。汗顺着他的胳膊下来了,洇湿了稿纸。我拿些卫生纸一点点把它沾干了。汗水流在椅子上,他的屁股下印出一个扇子大的湿痕。外面蚊虫飞舞,时不时钻进屋里在他身上乱咬。我不理解,他何必这样急冲冲地写作呢。
路修好后,又断续地下着雨,我们被困在井队。刘一天挥汗写到第三天,终于停了下来。他钻出铁皮房,脸白唧唧的,没一点血色,眼好像也瘪了,眯成一条线,怕见外面的光线。我问,刘总,写完了?他刮了刮脸上的汗说,卡住了,写不下去了。我说,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他说,也不全是。我多天没到院外的沙滩上转了,也多天没听到那种风声了。
雨仍下着,沥沥拉拉的,好像天漏了,再也补不上了。写不下去了,刘一天就抱着书看。我觉得他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读书人了。
多少年了,我没见过这样好的阳光了。也许阳光本来就这么好,只是没有好好地看过。我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阳光就轻轻飘飘地进来,羞涩地坐在床上了,坐在凳上了。
刘一天吃完药打完针,就直勾勾地瞅着窗外。窗外还是那片草地,那些白杨。也许他把它当成那片沙地了,也许他又听到了那种风声,那种风冲在叶子上的声音了,但他现在只能躺在病床上,再没力气写作了。
他总是长时间地瞅着窗外,阳光悄悄从叶子上滑下,静静地褪去了,地上有淡淡的雾气腾起,有时它们会胀着身子钻进房里。刘一天弓腰问我,这篇小说真能发吗?我说,既然编辑答应了,他们说的话不会假。他听后,身子结实地靠在床上,眼里闪过一道光亮,然后又重重地闭上了。
雨一停下,我们就从井队返回了。已是中午,我快捷地吃完饭,然后躺下休息了,醒来时已是天昏地暗。我翻开本子,挑出一两件重要的事,决定向刘一天汇报。推开门,他正伏在桌上写着。这时电话响了,他一边接着电话,一边还唰唰地写着。完后才放下笔说,我老婆从省城过来了,你替我去车站把她接来吧。我迟疑着说,嫂子轻易不来,我认为你亲自去接比较好。他摆摆手说,老夫老妻了,不讲那个。我尽量多写点,你还是替我去接吧。
夫人到了院里,他还没从房里出来,孩子进屋把他拉了出来。夫人的脸阴得流水。我赶快上前解释,她强装笑脸说,这辈子他就那样了,啥时候把生意丢完,啥时候他就甘心了。
夫人的到來,他显得并不高兴,好像有重重的心事。我认为还是那篇小说的缘故,如果小说写完了,心里没事了,他的情绪肯定不会这样的。
夜里我睡得很睌,每次出来解手,他房里的灯都亮着,我知道,他正伏案写小说,写不完觉是睡不好的。我想催他早睡,但猛地记起,他夫人就躺在他床上,我只好悄悄回屋了。
我们在饭店给夫人接风,他仍一脸忧郁,我知道他的心事,就安慰他说,文章就是要慢慢写的,不能急,更不能躁,要不就会影响作品质量的。他摇着头说,昨晚又给卡住了,笔几乎要捏碎了,只写了几个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给他倒杯酒说,先喝上几杯酒,然后好好睡一觉,缓缓劲也许就能写好了。他似乎听了我的话,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夫人可能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她转过脸去露出深深的不屑。
为不影响他的写作,我就前前后后照顾着夫人。他写得好像并不顺利,能听到他在房里高高低低的叹气声。临近中午,他走出房子,径直去了院外的那片沙滩上。他在沙滩上慢慢悠悠地转起来。这时听不到风响,看不到沙粒飘动的样子,但有小风从树间擦过,把墙上的茅草撞得歪歪斜斜的。他也许并没看到这些,但他可能听到风从沙地上唰唰飞过的声音,那种撞在叶子上的细响,会晃晃悠悠地跑进他的脑里,他的思路也许会渐渐地顺畅起来。
夫人见他冷冷的样子,就要走。我安慰她说,刘总虽说是个大款,但是个规矩人,他就这点爱好,咋就容不下呢。夫人说,他整天写呀写,写出啥名堂了?就是写出名堂又能怎样呀?他这样做,纯粹是耽误挣钱呀。我准备和她争辩,刘一天捧着稿子过来了。我见他兴奋的样子,就知道小说已经写好了。刘一天笑笑说,给我看看吧。从心里讲,我不喜欢小说,阅读小说的经验更是不多,怕误了他,决定找个编辑帮他改改。他听后感激不尽,说,我觉得这篇写得不错,无论如何得给我发了,写了恁多年发不了一篇,我快要崩溃了……
一轮井打完后,需要跟甲方再签新一轮合同,我们请甲方的有关人员吃饭。刘一天喝了不少酒,夜里胃疼起来了。我去送水,见他脸上挂满了汗。我担心地问他,他说这是老病了,喝点水就会好的。水喝下去并不见轻,反而显得更重了,我连夜把他送到医院。病一好转,他就问我稿子寄去几天了,我说才刚刚十天,十天时间太短了,起码得两个月编辑才给回话。他叹了口气说,两个月时间太长了,你既然跟他认识,能快点就快点,我有点等不及了。我再三安慰他,说这是个慢活儿,编辑要看的稿子多,光急也是没用的。
他总是闲不住,气色一好,在病床上又写了起来。
没想到的是,新一轮合同还没签下,又出现一家竞争者,他们开价更低。刘一天没法在医院住了,他连夜赶往几百公里外的省城,重新制定应对方案。经过一周的奋战,新的对策弄好了,刘一天的神情有些舒缓,当时已是中午,他吃过饭,又把稿纸铺好了。我问他今儿个回不回陕北,他晃晃脑袋说,今晚八点出发,连夜走,这样能节约时间呀。说完,就低头写了起来。
回到县城,刘一天得知工作量被另一家公司抢走后,急得不得了,为找到更好的关系,他连跑了四趟省城仍没有着落。刘一天万分沮丧,胃病又犯了,又不得不躺在病床上。墙是白的,被褥是白的,他的脸也是白的。他成天成天地瞅着窗外,窗外还是清一色的白杨,白杨树下仍是一堆堆的沙土。
编辑给我回话说,这篇小说需要修改,改好了,也许能刊发。我把编辑的话给刘一天讲了,他先是愣愣,然后眼慢慢睁大,说,这是真的么?我说,这还有假?于是他腾地抓住我的手说,小宋啊,我怎样感谢你呢。
他没法下床,就找张纸板往腿上一垫,算是临时桌子。我说,这篇小说得仔细改改,改不好,杂志社还是不会用的。他出口长气说,编辑让咱咋改,咱就咋改,我肯定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之后的整整一周,他都没有停下。腿压麻了,就掀开纸板轻微地活动一下。我劝他说,不能急躁,改稿是件辛苦的事,得静下心,慢慢磨呀。他说,我知我知,我肯定要慢慢磨啊!
稿子改完后,为让他好好休息,我帮他誊了一遍,交给编辑后,就开始等待了。凑这个空隙,他又跑了一趟省城托了很多人,终于要了几个井位。他苦着脸说,写这篇小说,我付出的精力不少,把生意都给耽误了。要不是搞了这几个井位,老婆又得跟我吵架了。
稿子又被编辑退了回来。
这一天,刘一天在野外组织井队搬家,我揣着稿子见他时,他正和工人一起装货。我把情况一讲,他伸开油手,就一下抓住了稿子。编辑写了一个修改提纲,他往地上一蹲,就仔仔细细地看起来。井队刚搬了一个新地方,没有通电。他改了一天,夜色慢慢降下,我就找了几根蜡烛让他照明,但蜡烛点上后,他却从铁皮房里出来了。他皱着眉说,脑子又被卡住了,一点也改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又连夜回到了县城。
满天都是星星。刘一天下了车,就径直去了墙外的沙地里。沙地中央的酸枣树人似的立着,白杨站在屋后,阴森森的。刘一天像往常一样,在沙地上磨磨叽叽地走着。树叶没有动,墙上的草也没动,听不到一点风响。刘一天也许什么都听不到了,因为他转了一会儿回到了房里,房里的灯亮了一夜。
改后的稿子寄去没多久,杂志社就下了用稿通知。刘一天在省城办事,我给他打了电话,他高兴得惊叫起来。我说,你最大的心愿总算了却了,就在省城好好养养吧。我搁下电话,冲了个澡,往床上一躺,觉得格外轻松。他的小说终于发表了,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再不必整日为他操心了,于是身子一歪,就踏踏实实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门被哗地推开了,睁眼一瞅,刘一天已站在面前了。我以为是在做梦,刘一天却说,用稿信在哪?快拿给我瞅瞅。这时我才迷瞪过来,便问道,你连夜回来了?他说,我肯定得连夜回来,我想看看用稿信,我还没见过用稿信咧。我把信递给他,他两只手捧着,借着灯光,几乎把脸贴到了信上。
天亮后,他又敲开我的门问,用稿信一来真的就定下了?我说,那当然,这就算定了,下面就等着样刊了。他还拿着那封用稿信,他的脸明显地光亮了许多。他连声说,小宋,今儿个咱到城里最好的饭店,我请你吃饭。
样刊寄来时是个下午,雨下得很大,已是秋天,按说是不该有恁大的雨了。我把秋裤穿上,又把夹克穿上,还是挡不住寒冷。刘一天的胃已疼了多日,并已查出胃癌了。我冒雨赶到医院,两只手捧着样刊恭恭敬敬地递给了他。这是个市级刊物,式样很不大方,但刘一天往怀里一揣,眼里已经湿乎乎的了。
过了一阵,他小心地打开刊物,翻到他那篇小说,一字一字地读着。
他中午没有吃饭,下午也没有吃饭。到了晚上,他悄悄地对我说,这应该算我的处女作吧。我说,你以前没有发过作品,这肯定是你的处女作。雨一阵紧似一阵,他的脸白白的,窗外也变得白白的,满屋都是雨声。这种雨声像蚊虫一样,嘤嘤嗡嗡乱响。他靠在床上,背后垫条厚厚的被子,就像张薄薄的纸,贴在雪白的被子上,他两只手牢牢地攥着那本杂志,好像怕被人偷去。
没过几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了,我怀疑他是不是等着这本杂志呢,要是杂志不到,他就鼓着劲,一直等下去?而这本杂志一来,所有的力气和耐心是不是都跑了呢。这样一想,我又后悔起来。我瞅着他虚弱的样子,心里盘算着,怎样让他重新鼓起勇气呢。
我一遍一遍地瞅着窗外,窗外还是那片绿地,那几棵白杨,我真想让这里变成那片沙地,变出几棵酸枣树。
阳光一点点强起来,我准备打开窗户,刚一伸手听到身后窸窣响动,转过身,见刘一天掏出了一本稿子。他说,我又写了一篇,你给我改改。我有点稀罕,心想,这是啥时写的呢,我咋没发现呢。他说,只发一篇不行,我想再发一篇凑个整数吧,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我把稿子拿回,转念一想,这篇小说不又是他的一个希望吗,我应该让他等着,让他耐心等着,拖延时间,说不定病会有好转呢。我把这篇小说仔细地改了三遍,才寄给了一家省刊。不久省刊退回,我又寄给一家熟悉的市刊。市刊编辑回话说,这篇稿子实在不行,再往别处投投吧。接着我又投了几家,还是不中,我灰心了,就把稿子藏了起来。刘一天时不时问我稿子的情况,为了拖延时间,我说还得等等,编辑还没回话呢。
可惜的是,这种希望没有留住他,病情却日复一日地恶化了。他疼得冒汗,汗水常常湿了胸,湿了后背。他常把发他小说的那本杂志搦在手里,想让他把杂志搁在桌上,他却瞥瞥我说,我搦着它,能减轻点疼痛。
疼痛稍缓,他就翻开杂志读他的那篇小说,蚊虫似的哼哼着。我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我又偷偷地翻出那篇被退回的小说,决定寄给一个熟悉的县级刊物编辑,想让他临终前看到这篇小说发表。
秋末,天气湿凉。
这时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并出现间断的昏迷。每次醒后,他都炯炯地瞅着我,我知道他想问啥,我总是委婉地说,那篇小说快发了。他不说话,而是使劲地抓着我的手。
我给这位编辑朋友说,不论那篇小说水平高低,一定得给发了,趁刘一天活着,尽量让他看到,好叫他安安心心地走了。这位朋友理解我的心情,说,最多半个月,还得校对印刷呀。可惜的是到了第八天,刘一天却永远闭上了眼。我跑到医院时,发现他手里还抓着那本雜志。
半个月后,朋友如期寄来了刊物,我把它交给刘一天的妻子,但她连看都不看地说,我要它干啥,我烦这些东西,不是它,我家的生意会做得更好更大,刘一天也不会死得恁快……
我叹着气出了门。
我认为得让刘一天知道,他的第二篇小说已印成铅字了。于是我坐了一天的车,来到他生前所在的陕北县城。
按刘一天的遗愿,他被埋在曾经住过的院子外面的沙滩上。
酸枣树还在,白杨树也在。我在他的坟前先鞠了三个躬,然后翻开他写的那篇小说,小说的题目是《你听到那种声音了》,然后沉重地朗读起来……
沙滩上的风很大。它们跳过沙地,跳过枣树,狠狠地打在我的身上。我看见大把大把的沙粒翻滚着,蹦跳着,然后蜂拥到我捧着的杂志上。我继续读着,这时,风夹杂着许多枯叶,绕着墓碑不停地盘旋着,沙沙作响。
我觉得是刘一天来了,站在我的身旁,激动地看着他的小说……
许多年后,我有了自己的企业。
傍晚,我站在阳台上,看到太阳一点点退去,总想起第一次见到刘一天的情景。我觉得阳光也像那天一样,树叶般地哗哗飘落,于是一种莫名的忧伤,风一样把我围住了。我的眼泪唰唰地掉了下来。
作者简介:宋剑挺,上世纪60年代生于河南省兰考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从事教育、党务工作等,现供职于中原油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在《当代》《山花》《飞天》等期刊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圈在院里的声音》、长篇小说《仓皇》《阴阳》等。部分作品入选年度最佳小说选。多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各类期刊、媒体转载。多篇小说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飞天”文学奖、“阳光”文学奖、中华铁人文学奖等20余项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