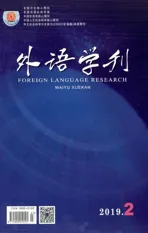《奥尔顿·洛克》中的绅士愿景与共同体理想*
2019-11-26陈彦旭
陈彦旭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提 要:本文从“绅士愿景”与“共同体理想”两个维度切入,通过对金斯利小说《奥尔顿·洛克》的阐释,论证维多利亚人对于绅士在教育、品位、审美以及身体规训方面的要求, 指出绅士观念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意义,并据此进一步阐释小说中通过想象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孕育出的“民族情感”与以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形成的“宗教信仰”作为两大重要维系关系对于实现当时英国共同体理想起到的重要作用。
1 引言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思想家、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于1849年创作了小说《奥尔顿·洛克》。封面上,相对于“奥尔顿·洛克”这个乍看上去充斥着陌生感的人名而言,更能吸引读者眼球的是下面一行副标题“裁缝与诗人”——两个看起来似乎丝毫不搭界,且之间存在着巨大阶级沟壑的不同职业。当它们被刻意并置在一处时,显得十分可疑。
小说中,这个兼诗人与裁缝于一身的人便是主人公奥尔顿·洛克。他在小说中运用诗性的语言描写“散发着臭气的工作车间”“弥漫着浓雾与毒烟的宿舍”,表明自己作为“人民诗人”(the poet of the people)的立场。 这实际上是延续了史蒂芬·杜克(Stephen Duck)开创的“劳动人民诗歌”的传统,但也使他自身沦为“次等诗人”的行列。奥尔顿本人也曾哀叹道,正是由于这个身份的缘故,他“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无法跻身于‘诗人’行列” (Kingsley 1893:2)。
作为“工人诗人”的奥尔顿为何被边缘化?一方面,受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维多利亚诗人们要么沉迷于奇幻莫测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与中世纪传奇,要么痛苦纠结地哀叹求而不得的爱情,要么关注宗教信仰危机与哲学终极问题之辩,这些散发着高雅气息的浪漫情怀与浸透着工业化气味的汗臭有着本质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期著名诗人们出身皆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譬如有桂冠诗人美誉的丁宁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过教育,阿诺德则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利厄尔学院,勃朗宁亦有在伦敦大学求学的经历,而出生在一个破产的杂货店老板家庭的奥尔顿·洛克自然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那么,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的穷小子为什么有着如此强烈地成为诗人的梦想。纵览全篇,不难发现“诗人”并不是奥尔顿梦想的终极所指,小说中他心心念念十余次的“绅士”身份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Ancient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中曾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绅士这一称谓,在英国每隔百年就会有所变化,且其边界有越发扩大的趋势。绅士从一种“生而俱来的权力地位”(gentleman by right)逐渐过渡为一种超越阶级的、具有道德评价功能的新词语。从这一点上来看,绅士内涵变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反映出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因而,穷裁缝奥尔顿是否能够最终成为“绅士”中的一员,象征意义重大。这种尝试通过获得文化资本以实现阶级身份跃迁的美好愿景,既带有个人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也反映出鲜明的“共同体”意识。
2 何为绅士——教育、品位、审美、身体规训
在小说中,奥尔顿是一个典型的“自学诗人”(self-educated poet),他希望通过自身持续不断的努力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从而完成其想要成为“绅士”的强烈愿望。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在白天做完漫长的苦工之后,夜晚还要瞒着母亲偷偷读那些在她眼中是邪教异端的书籍,即使身体状况由于睡眠不足愈发孱弱也在所不惜。
奥尔顿的行为实际上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内核——“自助理想”(self-help)的肯定与赞颂。正如米歇尔(Sally Mitchell)所说,“维多利亚人笃信‘进步’与‘自助’,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助’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Mitchell 1996:259)。而这一观念又在斯宾塞等人大力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中得到印证。
小说中有两个主要人物,奥尔顿·洛克和他的堂兄乔治·洛克。两人的命运走向从其父辈的时代便已敲定。两人的父亲最初在同一家杂货店打工,奥尔顿的父亲用多年辛苦积攒下来的积蓄开了一家店,娶妻生子,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结局却像“多数当时的小商人那样——债务缠身,心力憔悴”,死后未能给孤儿寡母留下丝毫积蓄。而乔治的父亲则头脑活络,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产业越做越大,很快就成为城市里最大的杂货店老板,并给他的儿子乔治铺好一条通往社会上层的金光大道:先去剑桥大学深造,然后顺理成章地在教堂谋一份牧师的工作。“在当时,这是把一个商人的儿子改造成一个绅士最合适的方式了”(Kingsley 1893:16)。而乔治也确实继承了其父亲狡黠的智慧以及令人有些不齿的行事手段,他精心设计,步步为营,极力讨好里奈戴尔爵士,并成功地赢得其女儿莉莉安的芳心,名利双收。纵观乔治父子这两代人,一个通过资本财富的积累从社会的“下层中产阶级”(lower-middle class)一跃至富裕的中产阶级,另一个则以高等教育为跳板,通过与贵族联姻,成功地摆脱商人家庭的市侩与土气,成为世人眼中真正意义上的“绅士”。 这实际上阐明绅士存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新社会群体提供一个通往社会尊贵的古老而又不太苛刻的路径” (黄梅 2003:47)。
乔治的成功范例并非独一无二,小说中数次提到的剑桥大学教员布朗博士(Dr. Brown)现在是“大学里最富有、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但是事实上,这个男人也曾干了好几年地毯工的活儿”(Kingsley 1893:140)。显然,布朗博士也是维多利亚时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众多佼佼者之一。
综上,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绅士”必不可少的经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所说的那样, 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迅速变化,人们对仅靠阶级出身划定绅士或身份等级的做法产生怀疑,因而尝试使用“精神”和“道德品质”来完善绅士观念,因而,而在谈到绅士的属性时,教育、教养、举止和品德等也成为重要因素(Clark 1962:253)。而上大学(尤其是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在多数人的眼中,就理所当然地为其品行与教养提供了担保。因此,对于奥尔顿而言,即便他天资聪颖,并通过后天的苦读已经使自己的才华初露锋芒,得到社会高等知识分子的认可,但他仍需要经历“大学教育”这种类似于“仪式”的必经之路。正如其赞助人里奈戴尔爵士所说的那样,“如果这个年轻人确实有一种适中的、努力将自己提升为更高层次人士的强烈愿望,而我也欣赏他这可圈可点的雄心壮志,觉得他是个合适的帮助对象,那么我觉得他应该上大学接受教育”(Kingsley 1893:139)。
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文化的学者们对当时“自助精神”的意义达成过两个共识:首先,它公开宣扬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向上流动性”的神话;其次,它成功地“诱惑”工人阶级自觉地向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靠拢(Perkin 1969:225)。奥尔顿言辞中对“自助”神话的深信不疑,确凿地印证了第一点。而对“价值观”的认同,无论是外显的装束与气质,还是内在的思想与观念,也均是如此。
譬如说,当奥尔顿与多年未见的堂兄乔治重逢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罗切斯特牌子的、裁剪精良的裤子以及他考究的法兰西靴子” (Kingsley 1893:161)。事实上,与奥尔顿记忆中的乔治相比,眼前的这位堂兄“所有的外在方面都大大地进步了”。而奥尔顿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有时候,即使对于一个穷裁缝来说,也会偶尔被人欣赏,至少外在可以做到吧”(同上:142)。正是受到这种观念的驱使,囊中羞涩的奥尔顿甚至向乔治借钱,在他的“御用裁缝”那里订做了几套“精致的礼服”(toilette refinements)。而这又印证了卡莱尔在《旧衣新裁》(SartorResartus)中宣扬的“衣服哲学”。除其 “人靠衣装”这一层浅显的字面意义外,卡莱尔更侧重其象征意义,即“更多有关于艺术、政治、宗教、天堂、人间、人的气质”(Deen 1963:447)。
诚然,一个穷裁缝可以借钱给自己添置一套新装,甚至购置手杖与马车。但是,“气质”这种更有关绅士品味与趣味的东西,借不到也买不到。在某次由社会上层人士所组织的宴会上,奥尔顿认真观察与模仿那些绅士们的一举一动,“仿佛他们的每一动作都富有深意……当我发现他们吃东西的样子和交谈的方式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时,我甚至有点失望”。奥尔顿的悲剧有二。(Kingsley 1893:220) 其一,他认为通过自学而获得的文学“品味”会完完整整地被社会上层人士接纳而欣赏;其二,他对于“绅士”一词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智力与道德层面,这两样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勉精神与自觉的自律精神来弥补的。然而,有关于绅士“品位”或“趣味”这类需要强大的金钱基础才能培育出来的生活习惯与气质,是囊中羞涩的奥尔顿永远无法企及的。
小说中,剑桥系主任高度赞扬奥尔顿对于“英语古典文学的熟稔”以及“音律与旋律方面规则的掌握”,并充分肯定他对弥尔顿的模仿,但是却不欣赏雪莱对他创作的影响。理由是,“雪莱在品味上是变化无常的,且在信仰上系异端之流”。而作为资助的条件,里奈戴尔爵士也要求他放弃诗歌中有些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观点。(同上:138) 奥尔顿若是想要公开发行自己的诗集,也必须经过一番“细心剪裁”的编辑。在某次投稿后,他的诗歌“四分之三被重写,所陈述的每一条事实都被扭转和曲解,以至于整首诗看起来都庸俗不堪,平淡无奇,抹杀了为人民而书写的动机”(同上:200)。
奥尔顿好比一株盆景,要随时接受人们对它的修剪。而怎样修剪才好看,当然取决于主人的审美与品味。于是,在奥尔顿决定接受资助的一刹那,他的脑中闪现出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灵魂,而是被放置在花盆里的一棵植株”(同上:139)。这一有趣的比喻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程巍在《隐匿的整体》中做出的一个有趣论断,即贵族身上体现的是“植物性”,与中产阶级体现出的“动物性”形成鲜明而深刻的对比。即是说,贵族不喜“动”,慵懒与闲散才是贵族的生活节奏。
奥尔顿在剑桥时每天都“呆在表兄的书房里苦读,从拂晓读到黄昏” (同上:143)。而乔治每天4点钟到8点钟都会准时神秘“消失”,后来奥尔顿才得知,原来这位堂兄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段雷打不动地学习品酒和打桌球,以提升自己的品位。这是一种以“闲暇”为基本特征的贵族生活方式,与奥尔顿忙忙碌碌的中产阶级苦干精神形成鲜明的、截然对立的价值观对比。
另外,这种品位上的差别,在“审美”这一维度上得以更加充分的展现。奥尔顿与埃莉诺曾经在教堂的建筑风格上有过很大的分歧。后者认为,教堂建筑风格雄伟壮观,笔直的立柱,拱状的屋顶,会引领人们的目光一路向上,直至天穹,因此可成为基督教的象征。而奥尔顿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如果站在教堂外面看,人们或许会形成以上埃莉诺所说的那种印象,一旦到了教堂内部,那些屋顶上交错复杂、层层交叠的木桩和石柱会把“自由的天空关在外面”(同上:160)。其表里不一,内部不过是一座昏暗的监狱罢了。显然,奥尔顿的审美观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正如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伊格尔顿 2001:27)。奥尔顿不喜欢教堂的风格的根本原因是其有碍自由的精神。而“争取自由”,正是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喊出的最为响亮的口号。
伊格尔顿在上述著作中还进一步提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审美话语,有着反抗资本主义内化之压抑的重要作用,从而达到人们心灵解放的目的(同上 2001:7)。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为文学的政治批评引进一个崭新的概念——“身体”,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身体、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马克思阐释的“劳动的身体”、尼采笔下的“权力的身体”以及弗洛伊德言说的“欲望的身体”为例,伊格尔顿精辟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美学视阈内,身体是审美意识形态的主要表达方式,亦被后者建构与规训,背后蕴含着强烈的政治冲动。
这一点或许能够解释小说中为何有多处对奥尔顿与乔治“身体”的描写。高大健壮的乔治在剑桥大学期间,“把一个伦敦人能够从事的体育项目全都练得尽善尽美……包括滑冰、划船、拳击,还有桌球” (Kingsley 1893:60)。相比之下,奥尔顿自小营养不良,孱弱多病,连亦父亦友的麦凯在小说中也常常揶揄他为“小姑娘”(Laddie),可见从外表上来看,他并不具备高大威猛的男子气质。奥尔顿自己曾沮丧地坦白过,“是的,我很孱弱……不仅仅是在我自己身上,事实上在所有的诗人身上,都有些阴柔的女性气质”(同上:212)。19世纪早期受纨绔子文化的影响,贵族阶级特有的苍白、瘦弱、阴柔的外表与气质曾经拥有美学上的合法性,但是到维多利亚中后期就已改弦易张。按照程巍的隐喻性说法,“伦敦蝴蝶”之地位已经被“帝国鹰”所取代。这一审美的变化在艺术上的表征最为敏感与明显。小说中的某次派对上,莉莉安一边抚琴,一边歌唱。对听惯“街头音乐与小教堂中的哀嚎之音”的奥尔顿而言,她演奏的音乐“既热烈又高雅”。但是,这种悦耳而感伤的意大利音乐,却遭到斯丹顿小姐的斥责,她命令莉莉安唱几首“带有男人气概的歌曲,日耳曼的还是英吉利的都可以,就是不要再哼唱那些令人感伤、无病呻吟的歌曲了”(同上:150)。
诚如奥尔顿本人所说,他视剑桥大学的学生为“傲慢的贵族”,并不羡慕他们所谓的知识与学问。但是,他也承认,“我羡慕他们有和学习一样多的玩耍的机会——如他们可以去划船,可以去玩板球,可以去玩足球 ,可以去骑马……这些健康与力量有关的运动”(同上:143)。两人在身体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表明19世纪英国流行的有关“绅士”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强健的基督徒”(Muscular Christianity)。 金斯利本人曾经讲过,“身体是灵魂的表达方式,且两者紧密相连。因此,身体越完美,它所表现的灵魂也更加丰盈”(同上 1899:119)。而“完美的身体”的典范,莫过于代表着古典艺术理想美的米开朗基罗之雕塑“大卫”,其高大、伟岸、健壮的身躯象征着古希腊人对于奔跑、跳跃和角力等城邦运动竞赛的热爱。虽然乔治缺乏心智培养,是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甚至认为牧师工作所要知道的那点东西,“任何人一个月就可以速成”(同上 1893:205)。他根本就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作为剑桥大学赛艇队员,他在比赛中“牙关紧咬,眼神炯炯,裸露的臂膀上大块的肌肉随着每一次快速的划桨而时隐时现”,使得对其人品颇为不齿的奥尔顿也不得不承认,乔治比他“更高、更帅、更有男人味”(同上:121,211)。事实上,奥尔顿被赛艇队员们的男子气概深深打动——“我热血沸腾,眼眶中满是泪水,只因为……我也是个英国人”(同上:121)。这一由观赛油然而生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印证了诺克斯(Robert Knox)在1850年出版的《人类之种族》(TheRacesofMen)中提出的一个非常激进但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将一个人的外表与体格与所处国度的“文明程度”(civilization)联系在一起。在书中他对撒克逊人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称赞他们是“高大、有力、人类中的运动健将;作为一个种族整体而言,他们是地球上最强壮的”(Knox 1862:50)。而金斯利本人对撒克逊人也倍加推崇,他曾在一篇题为“英格兰的工人们”(Workmen of England)的宣讲词中慷慨激昂地讲道,“英国人!撒克逊人……世界工厂,七百年来自由的领袖!”(Kingsley 1899:127)
3 共同体理想的两大维系关系——民族情感与宗教信仰
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以工人宪章运动为背景与主题,因此阶级矛盾通常是批评家在阐释这部小说时惯用的角度。本文提出,除“阶级矛盾”这条主线外,小说中还包含着一条若隐若现的民族主义的暗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值得读者的深入思考。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民族主义情感大于阶级利益,更容易唤起人们的共同体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当阶级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人们想象中的共同体将矛盾转移到非本族的“他者”,从而淡化甚至消解国内的阶级矛盾。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可以使社会的底层民众放下个人之间的恩怨,忘记阶级之间的仇恨,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同胞鼓掌喝彩——小说中观看剑桥大学赛艇比赛的几百人出身地位各有不同,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为这些参赛的社会精英疯狂地呐喊助威,因为他们的头脑中有着将他们团结起来的共同想象——“从古罗马时代起,英国人就是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主宰……这些勇敢的年轻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同上 1893:120)。
以上的说辞深刻地体现出以“英国性”(Englishness)为纽带与基础形成一个“共同体”。撒克逊人对于体魄、运动、尚武精神的追求以及对于自由的向往构成英国19世纪绅士内涵的重要部分,其蕴含的充沛原始生命力符合工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的美学追求,亦迎和维多利亚时期大英帝国向外扩展殖民的勃勃野心。而前文论及到的教育、品味与服饰文化则构成绅士精神的另外一个侧面。作为一种完美的理想人格的构成,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由此可见,绅士精神,正如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政体形式那样,体现出一种可妥协、可商榷、可互相吸收的状态。作为一座将社会各个阶层联系到一起的桥梁,绅士精神应该以贵族精神为核心,有效积极地吸收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价值观念,同时也鼓励后者向上看,为他们勾勒出一幅各阶层跃迁的美好愿景,从而最终通过这种文化的双向流动来实现社会整个价值的融合,从而最终实现一个“和谐”的太平盛世状态。
在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维多利亚时期绅士观念的价值内核体现出的共同体精神。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过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官方民族主义”,指统治阶级一方面想顺应民族主义潮流,另一方面又想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尽其所能地将所有臣民纳入一个范畴之中。而在维多利亚时期,通过历史上对共同的民族祖先撒克逊人寻根溯源的方式来激发每个英国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做法。在19世纪早期,英国作家司各特便很敏锐地捕捉到当时甚嚣尘上的“英国性”问题,并在小说《艾凡赫》的前言中对古代撒克逊人大加赞赏,称他们为“朴实平凡,直率坦诚……立法中渗透着自由的精神”(Scott 1840:2)。而19世纪晚期,狄更斯更是对撒克逊人不吝溢美之词。他曾经这样讲道,“(撒克逊人)具有地球上所有民族中最好的品质……无论他们的后代去了哪里……即便是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他们的后代都永远那么有耐性,那么坚忍不拔,那么永不气馁”(Dickens 2014:19)。
在19世纪中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各个人种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深化,人种学和解剖学等学科为这种差异提供了理论性依据,随后人文科学领域也涌现出大量的著作,论证撒克逊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历史的、天然的优势。这一观点背后有着显而易见的种族主义思想,其推动力则与维多利亚时期大力推行的殖民主义帝国思想休戚相关,这也是安德森所说的“官方民族主义”的重要目的。其背后的逻辑简单而清晰:作为优等族群的“我们”,有天然的、理所当然的权力去征服、统治和教化属于劣等族群的“他们”。而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意识到即便“我们”之间存在着阶级等级与财富分配上的种种差异,但归根结底“我们”还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应求同存异。
“撒克逊血统”蕴含的粗犷、强壮、血性的男子气质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精神契合,亦迎和了大英帝国对外殖民扩张的想象需求,从而谋得存在的合法性。在其影响下,“强健的基督徒”这一概念被绅士观念接受和吸收,成为构成后者气质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另一方面,在这部小说中,也多处流露出对于他族——如爱尔兰人的鄙夷之情。如小说中奥尔顿曾直白地称爱尔兰人都是“不可信赖的骗子”——“我瞧不起爱尔兰人,因为我不相信他们——他们之间相互也不信赖——他们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Kingsley 1893:286) 除对于爱尔兰人“不诚实”这一品行上的指责,奥尔顿还表达出对他们的恐惧,“伦敦有二百万爱尔兰人,攥着长矛与刺刀,脑子里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像野人一样,随时准备以流血的方式来报复我们的勇士”(同上:287)。于是,他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这些野蛮人离开英国的国土——“这些爱尔兰人每天都在大喊大叫,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尔兰。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为了英国,而离开我们的国土呢?”(同上:286)
由上述例子可见,“共同体”有其内在的矛盾性,即一旦根据某种“标准”划定出共同体的疆界,疆界之内形成的共同体对疆界之外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冷漠的、甚至敌对的“他者”的概念。正如雅典城邦内的公民所形成的共同体所宣扬的民主无法惠及到外邦人那样,一味宣称爱国主义与民族情感的做法只能建立一个范围有限的共同体,并为欺压、征服共同体之外的人群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
然而,在各民族国家休戚与共的现当代社会,我们趋于认同将全人类视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那么,消弭矛盾的出路,就在于对制定共同体的“标准”上。显然,这一标准的制定不易过于狭隘,应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以覆盖更多的人群,鼓励其求同存异,向“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迈进。
藉此,我们接着讨论后一种维系共同体的关系——“宗教信仰”,这显然是一种比民族情感更为宽泛的标准。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被当作人人得以平等的前提与基础——“我们都是兄弟,因为我们都从事工作,拥有同一个愿望,以及同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父亲”(同上:320)。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提及的“宗教信仰”与我们常识中的不尽相同,是一种经过工作理念“改造”或“改良”的宗教信仰,即“基督教社会主义”。小说中,艾莉诺秉承着“合作与团契”的精神,组织一个由五十多名缝衣女工组成的合作社。“她们每天一起工作,分享劳动所得的利润。这部分钱本来会被她们贪得无厌的主子们剥削去,但是现在却装在自己的钱袋里。艾莉诺为她们管账,帮她们销售产品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所有杂事,而且在她们工作的时候给她们念书,每天还给她们传授知识。”(同上:329) 殷企平认为,艾莉诺的作法成功地抵衡了自由竞争的狂潮,践行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想(殷企平 2007:47)。
由于意识形态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难相互包容。然而,它们在理论上的现实结合说明两点:第一,两者之间必有相通之处;第二,两者能够相互补益。其一,马歇尔(Peter Marshall)曾指出,“在基督教自由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共产主义理想……耶稣基督自愿清贫,与富人对立,以及他的分享精神(尤其是面包和鱼)……激励着众多的基督徒践行共产主义行为”(Marshall 2009:75)。而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同样提倡的是均贫富思想和大同理想。显然,两者的思想都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而基于“分享”与“平等”的价值观理想成为搭建在两者间的桥梁。其二,这两者结合后,在各自的身上均吸取到有益的成分。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其倡导的勤勉劳动由于被“神圣化”,从而获得在道德上与美学上的合法性。而对于基督教而言,它原本不提倡现世观念,亦不鼓励人们劳作,但吸收“劳动”观念后,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另外,从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基督教社会主义直接针对的对象是以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倡导的市场自由竞争学说。在斯密看来,所谓“利己心”是私人与国家财富得到增长的源泉,而满足这一私心的关键就在于经济的自由竞争与政府的自由放任。小说中对这一经济理念产生的恶果做出形象的例证阐释,一方面,奥尔顿那位“燃烧着19世纪伟大精神”的雇主,一心想着挣快钱,追求进步,扩大产业规模,要求工人把活儿带回自己家去做,并通过自由招标的方式,价格最低的工人可签到最多的活儿(Kingsley 1893:92)。这样貌似公平的竞争带来的后果是使得奥尔顿及其工友的工作量增加了三分之一,但实际报酬却少了一半。对此,奥尔顿愤怒地说道,那所谓的“自由工业”(freedom of industry),其本质是“资本暴政”(the despotism of capital)(同上:101)。这种理性以及在其指导下的作为不仅进一步拉大阶级间的贫富差距,使得两者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还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不作为怨声载道。小说多次表达出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失望,而当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时,有工人代表这样说道,“政府与议会中的议员都无法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只能依靠自己。自助者,天助之!”(同上:95)
“自助”与“天助”反映出当时工人两个重要的精神维度,是对维多利亚中产阶级追捧的“自助理想”的改造、丰富与革新。首先,“自助”不仅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实际的行动。这象征着工人阶级从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中的“自在”(class-in-itself)阶段过渡到“自为”(class-for-itself)阶段。其次,“天助”中体现的基督教思想隐含着劳动是获得神佑之途径的重要观念。这与卡莱尔倡导的“工作神圣化”密切相关,向上可追溯到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等有关新教的职业观念。小说的结尾将“自助”与“神助”这两个概念完美地镶嵌在奥尔顿·洛克留在世间的绝唱之中:
“哭泣,哭泣,哭泣,还是哭泣,
为了贫民,为了愚人,为了奴隶;
看啊!从那荒芜的沼泽地中看出去,
炎热的小巷,济贫院的小房间:
干活去!要么就去墓穴里!
下台,下台,下台,还是下台,
那些懒汉,流氓,暴君;
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应该劳动吗?
一个人,倘若他不愿辛苦劳作,
他就没有在大地上立足的权力;
这个道理,上帝为我们作保!”(同上:304)
卡莱尔在1840年曾做过题为《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业绩》的系列演讲。在他的心目中,除神明、教士、先知以外,还有一类可称为与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的“文人英雄”(the hero as man of letters)。其最为人称道的能力是“透过表面看到事物之本质”(Carlyle 2000:164)。而这“本质”即是费希特所言的“神圣理念”,亦等同于基督教的“圣言”。因而文人英雄的使命就是借印刷物说出所受的神启。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奥尔顿未能成为世俗标准中的“绅士”,但他所作的这首诗却道出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危机,并提出作为可能解决困境的两个关键——“人助”与“神助”的结合,带有启示录般的意义。因此,小说中卡莱尔的化身——麦凯对奥尔顿说的那句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为点睛之笔的祝愿实际上得以应验——“你是一个无冕英雄 (unaccredited hero)” (Kingsley 1893:59)。
4 结束语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英国在19世纪初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共同体危机。英国政府在1799年颁布的《结社法》与1818年颁布的“六项法律”,禁止一切包括工会、互助会在内的结社组织。然而,官方强硬的行政命令却只能助燃人民群众寻找新形式共同体的热情,小说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组建的“合作社”深刻地反映这一点。
在有关“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相关论述中,殷企平曾提出,优秀的文学家都有一种憧憬未来美好社会的共同体冲动,这冲动的背后既有社会转型产生的焦虑,亦蕴含着对理想的共同体愿景的期冀(殷企平 2016:78)。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亦是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们在纷繁复杂的思想、信念与价值观的碰撞中努力寻觅社会地位跃迁的机遇,小说中包括奥尔顿在内的多个人物对于绅士身份的追求亦清晰地表明这一点。
最后,社会转型期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与传统价值理想的断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共同体的衰落与瓦解。仅以欧洲为鉴,从公元伊始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之崛起到20世纪初奥匈帝国解体,又到近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不夸张地说,整个欧洲史就是一部由宏大的共同体不断分解为更加细碎的共同体的分裂史。在这一过程中,除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关系外,还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能维系这些共同体的关系?小说中隐含的 “民族情感”与“宗教信仰”这两大维系关系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今天笔者重新回顾金斯利的这部经典小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