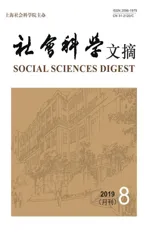20世纪20年代“劳动阶级”概念的纠葛与传播
2019-11-19蒋凌楠
文/蒋凌楠
对劳动价值的重视,是近代关键观念转变之一。18世纪洛克与亚当·斯密等提出,劳动不是贫穷专属,而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美国殖民地的经验,更使人们相信人类本被赐以丰饶之福,不会受咒匮乏之苦。这进一步赋予近代革命以社会解放的目的。由此,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上得到发展,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随着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传入,劳动问题在中国引发了“劳动阶级”相关概念的纠葛与传播、流行。
“劳工神圣”与泛劳动主义
1918年11月,为庆祝一战胜利,蔡元培发表演讲,使得“劳工神圣”口号响彻全国。“劳工神圣”因中国参战劳工而起,引发了五四时期知识界对劳动问题的关注热潮。同时“神圣劳工”带来了新的疑问与讨论:神圣的劳工包括谁?
蔡元培的“劳工”与早期中共党人理解不同,“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职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与劳工相对立的群体,是道德缺陷、生活奢侈的官吏、政客、军官、商人及继承遗产的有钱人,即所谓“寄生阶级”。
实质上,蔡元培所提出的“劳工神圣”,是融合了大同理想的泛劳动主义思想,以无政府主义者论述最多,对近代中国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著称的陈溥贤也曾表示:“我所说的劳动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1920年《申报》借此热潮谈“劳动的意义”,开篇就讲“‘劳动’两个字不是单指体力的工作,也是包括脑力的工作,所以凡用力耕田的就是‘劳动’的一种,用脑做文章的也未始不是‘劳动’。”沈玄庐也认为劳工的类别包括“筋肉劳工”和“精神劳工”,社会和个人生活上都是二者相互配合,反对“否认精神劳工的话”。
因为作者与读者同是读书人,无论从论述策略,还是“士”身份认同上,“我们劳动者”总归易于接受。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正是要求人人平等的劳动,不分体力、心力的区别。但凡不能做体力劳动的读书人,都应该去做工改造。于是工读计划、工学主义的高潮迭起。五四时期工学主义者已将社会结构看作“智识阶级”“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三种分类。但他们的目标正是打破这个现状,“要从这三种阶级里寻出有觉悟的人,使他们三个阶级的人,互相接近”。
可是,赴法勤工俭学、工读互助团等活动雨后春笋般兴起,又很快消散,谈不上社会改造的效果。如时人观察,“一般人对于‘劳工’的解释,仍不免有令人不十分满意的地方。他们把劳心也看做‘劳工’的一种,依旧是不彻底的办法:若果照这样解释,可以说对于世界永久和平的建设和现社会各种急待解决的问题的处置,仍然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这道出了心力平等观最重要的缺陷:由于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牢固,一个包括了劳心者的“劳工”概念,实际失去了改造世界的意义。工学主义尝试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智识与劳动两大群体不仅难以融合,接触之后发现隔阂愈深。劳心者自我改造未能完成,青年要寻找更具改造世界实践意义的出路。
反转:劳力至上与知识寄生
在一战胜利庆祝活动中,蔡元培演讲以外,还有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随着俄国革命实践传入,工农政治思想出现在知识青年面前。1922年北京学界“五一”纪念大会上,高一涵提出用“劳农”、“工人”的具体指称,代替泛称“劳动者”。劳动问题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对工农体力劳动者的关注。
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一脉的延续。儒家学说的基点,就是人的智力、能力与道德的差别。由此解释历史形成的社会分工,表现为“劳心”与“劳力”或“君子”与“小人”之分,更与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划分一致,成为社会秩序的象征。这种心力高下二分,在反对传统和社会等级的新文化精神下,必然会受到批评。
理性的批评者如李大钊,从社会经济变化角度认为它已不合时宜:“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
早期马克思主义倾向者,从动员策略考虑,提出打破根深蒂固的传统划分,作为启发底层劳动者的开端。陈独秀在1919年最初面向“劳动阶级”宣传时,所关注就是无财产而靠体力劳动的人:“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
陈独秀有意反转传统观念,不仅称赞劳力者的价值,而且将之凌驾于劳心者之上。“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陈独秀以体力做工释“劳工神圣”,理由是比儒家思想更久远的观念——勤惰与财富分配的反差对比,反对“不劳而获”与“劳而不获”。早在《诗经》里就出现反对不劳而获的“硕鼠”形象,这是古老的道德批判视角。
这一命题也是陈独秀常用的论据。如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揭示社会二分的意识,激发工人反抗意识,后因语言通俗易懂,被编进安源路矿工人学校的教科书里。1920年9月被当作《新青年》政治转向的文章《谈政治》也是这一思路。中共早期向工人、劳动者宣传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实行‘不做工不许吃饭’的法律”也是此意。
当时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可贵正在于将体力劳动者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揭示出来;提倡劳动运动,即人心道德所在,不为一味趋新,而是基于最简单、淳朴的同情心,做个“有良心的学者”。“劳动阶级”用语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意识中最质朴的道德情感。
同时,面对着体力劳动者,部分读书人的自我认同感发生变化。与“劳动阶级”二分对立的重点,不再是官僚老爷、资本家的“财产寄生”,而是读书人的“智识寄生”。《民国日报·觉悟》所刊短评感想,也呈现了小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理解的变化。最初舆论只是赞成劳动的价值,不久即有人提问“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有位知识青年即批评智识阶级的“寄生”,赞美庄稼人“更贵重些”。这样一来,除了体力劳动者以外,社会其他群体都是不劳动而获,即劳动的对立面,无论“智识阶级”还是军阀、官僚、纨绔子弟。无政府主义者最初对“劳动”的宽泛定义,包括的“心的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不如骡马”的体力劳动者比较之下,逐渐失去“神圣”的资格,成为“知识寄生者”。
从经济到政治:“生利”即“自给”
理论上,同情心与道德感的激发,必须建立在财富与剥削关系重合的基础上;但现实中二者未必重合。贫富与勤惰的判断则更易于观察,无论东西,都相当常见。英国诗人雪莱有著名劝诫诗《给英格兰人的歌》,以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雄蜂来比喻吸干工蜂劳动的领主与富人。从劳作的立场批判特权阶级的剥削,是18世纪革命的宣传论点之一。马克思结合经济学将之提练为“剩余价值”与剥削劳动的学说。在后世共产主义者的解释中,财富与剥削获利的增长循环成为共产革命时代的理论关键。陈独秀的论述模式也属于此。
但19世纪前半期,圣西门曾试图切断财富与剥削之间的联系。法国大革命已将贵族与非贵族的二分对立关系建立起来。圣西门则有意促成社会与产业进步,迎合当时掌权的新兴资本家,将革命初期“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二分对立的口号,改为“产业者”反对“闲惰者”的说法。其中“闲惰者”除了旧制度下贵族、教士等特权阶级,也包括其他没有生产贡献却占有收入的人;而工作者不止工资劳动者,还有一切对社会有贡献、有生产效能的人群,包括商人、经理人、科学家、银行家与手工业者等。圣西门依然使用“工蜂”与“雄蜂”的比喻,但“剥削”标准已经变化,产业家不必然是剥削者。圣西门的这一想法,在19、20世纪之交对日本社会主义也颇有影响。在中国,与之不谋而合的一方是研究系。
自19世纪末,梁启超受严复译《原富》影响,就对“生利”与“分利”的经济学概念颇感兴趣;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中更以专节论之,社会中生利者与分利者二种分别。1919年12月,《解放与改造》刊登了两篇文章诠释了“生利”“分利”、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与中国现实结合的两个方向。
其一篇《对待吾国“不劳而食”的阶级的办法》重申梁启超要“生利”而非“分利”的观点。在作者看来,“是要劳心力,或是劳体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但“谋个人的生活”,“而同时谋社会群体的生活。简单说一句,就是要做‘生利’的生活,不要做‘分利’的生活”。
“分利”与“生利”,即消费或创造社会经济的价值,更接近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社会经济理解。但是,除了无业游民、坐食利息者,连传统认可的读书人、奔波生计的商贩人、店家等正当获利者,都属于是“不劳而食”。这是比古来任何道德划分更彻底的“极爽快的方法”,当然,这意味着纸上谈兵。此矛盾的焦点回归人与物质的紧张,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上也无从解决。
同刊周佛海的文章是结合了现实的思考。当分析中国的阶级时,周佛海否认中国有“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或“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把中国人分做两阶级:一个是寄生阶级,一个是自给阶级。”周佛海的思路非常清楚,现实社会矛盾集中在“寄生在社会上的武人官僚和政客”,那么“要改造社会,必先除去障碍物。障碍物就是寄生阶级,所以不得不先除寄生阶级。要除寄生阶级,就要结合一个自给阶级,和他行阶级斗争”。明确提出二分的“寄生阶级”与“自给阶级”,给模糊的“非劳动阶级”以切实的批判指向,同时不再纠结于劳心或劳力的“劳动”。这种檄文思路适于论战,结合国情,结论接近无政府主义者,策略上却高出一筹。梁启超继续发展了这一思路,创制新名词将结合现实发挥到极致。
现实指归:产、业、枪的新名词
1920年9月,梁启超将《解放与改造》更名《改造》,更明确“稳健的社会主义”宗旨。此时,张东荪提“发展实业”,应暂缓发展社会主义,引起社会主义论战。梁启超加入论争,将社会阶级问题的分析推向高潮。
梁氏首先比较欧美“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认为中国有独特的社会形势与问题,产生了独特的社会结构分层,即“有业”与“无业”。“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辨析:“劳动阶级一语,本含广狭二义。广义的解释,自然凡农民及散工悉含在内。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恃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他极力反对将“游民阶级”与“劳动阶级”混淆,“此言虽近似,然细按之则大戾于名实也”,强调游民阶级的危害,而“农民与散工”也并非“劳动阶级”。
梁启超将这场辩论拉回到宣传社会主义劳动运动的意图,明确加以反对。因而李达视之为“最有力的论敌”。但李达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概念的混乱性,只从逻辑上反驳:有产业就一定有劳动者。“中国的游民,都可以说是失业的劳动者。”如李达所说,梁任公“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这种对无业群氓的负面评价,当时并不少见。“游民阶级”的提出,是将批评对象指向另一个政治问题,军阀与战乱。
另一个“有枪阶级”的新名词,是将政治上的军阀与社会上的“游民”“兵匪”结合起来创制的。梁氏认为,中国的现时症结是有枪的军阀武人,“我国目前生死关头,只有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一个问题”。有枪阶级,包括上到军阀,下到兵匪的一切持强凌弱者。
这样创制新名词,无疑是偷换概念,梁氏何尝不知。他实质反对运用此类概念,另一方面却利用时髦的阶级话语,来阐发现实舆论对军阀政治的不满。就这样,颇有戏谑意味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广为流传。
自此,“有业”与“无业”的对立二分,已不是纯粹反对“不劳而获”的固有道德,也不是近代社会经济学提倡生产效率与反对寄生食利,而是政治上的二分对立。一方面将政治上的军阀问题与社会上的“游民”“兵匪”结合起来批评,另一方面反对提倡劳动运动或布尔什维克主义。前者反映了舆论普遍心态,后者则是思想界在劳动运动大潮中的一点保留。
然而,“改造世界”的思考再多,革命终究是实践出来的。如果失业的穷人不是“雄峰”,那么谁来当“寄生阶级”?中共建党后便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引导劳动工人斗争,解决阶级矛盾的混乱理解。1922年,香港海员、安源路矿等几次大罢工事件之后,“工人阶级”“劳资矛盾”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即便国共合作期间两党的争论,也都集中在以劳资阶级二分为基础的阶级斗争之上。
国民革命时期“阶级”话语流行达到顶峰时,梁启超仍对革命时代有所保留,提出“无业阶级”概念,把党员、活动家都算为“无业阶级”,批评其无法代表劳动者。
针对此,郑超麟曾以正统理论派反驳,强调阶级的标准在社会生产上,对梁氏辨析字眼上的“产”“业”“枪”颇为不屑。但是,这样学究式的辩论夹杂着理论与外语词汇,反而不如望文生义的理解通俗易懂。20年代早期的“阶级”话语,反而借助“产”“业”“枪”这些贴近现实问题的新名词,赢得更广大受众。双方的论争客观上推广了此概念的泛化与流行。
从“劳工”到“劳动阶级”概念,与“劳动”价值的重现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劳动价值被赋予了道德的制高点,隐含情感动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劳动的经济学意义有着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撑,易于被知识界接受。
而在历史语境里,当“劳动阶级”的概念独立形成以后,它所表达的不再是人对土地、自然、或物质、社会经济的关系,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群体与分层的问题,寄生、特权、剥削、压迫、统治等不平等关系都可以纳入其中。劳动的价值结合社会阶级二分法,则进一步泛化为政治话语传播开来。围绕“劳动阶级”之纠葛,反映了外来理论与国情、实践之复杂,同时也是概念泛化的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