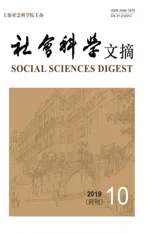逻辑能解法律论证之困吗?
2019-11-17王洪
文/王洪
舒国滢教授在《逻辑何以解法律论证之困?》中,基于约根森难题所揭示的经典逻辑在规范推理中遭遇的难题,提出了逻辑何以解法律论证之困的问题。他指出道义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手段和研究工具,并且指出法律规范适用的难题仍然需要建构出更为精致、实用的逻辑操作技术。接下来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道义逻辑能解法律论证之困吗;进一步的问题是“更为精致、实用的逻辑操作技术”能解法律论证之困吗;更为一般的问题是逻辑能解法律论证之困吗。
约根森难题对逻辑提出的挑战
丹麦逻辑学家约根森(Jørgensen)指出:“根据逻辑推理的一般定义,只有有真假的语句才能在一个推理中作假设或结论;然而事实是,一个祈使语态的结论可以由两个假设得出,这两个假设的其中一个是或两个都是祈使语态的。”在真值逻辑中,对推理有效性作以下定义:一个推理是逻辑有效的,当且仅当不可能其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即结论是前提的逻辑后承。而祈使句没有真假,因此包含祈使句的推理不能被视为逻辑推理,因而无逻辑有效性可言,但事实上存在包含祈使句为前提或结论的推理,在直觉上是被认为有效的。这两方面构成了冲突,这就是所谓的约根森难题。
约根森难题可推广到法律论证与推理之上。约根森难题有两个假设:一是有真假的语句才能作为逻辑推理中的前提与结论;二是祈使句没有真假。法律论证是包含规范命题为前提或结论的推理,许多法律论证与规范推理在直觉上被承认是有效的,应该有相应的逻辑评价它们的有效性。但对于该类论证与推理,约根森难题指出无法从逻辑上作出评价,无法从逻辑上判断其正确与否。约根森难题对规范推理构成了挑战,对法律可推导性与判决可论证性构成了挑战。
约根森与瓦尔特通过说明规范语句可以有真假而承认规范语句作为逻辑推理前提的合法性,以此消解约根森难题,此方案称为真值语义学解决方案。约根森区分祈使句的祈使因素与指示因素,指出前者描述说话者的意愿与愿望,因而没有逻辑后承,后者可以表达为指示性语句,因而有真假并能够被一般逻辑规则所支配。瓦尔特将规范与规范语句区别开来,指出规范语句对应于规范世界,规范语句描述规范世界中的各种规范、规则和道义。规范没有真假,但规范语句不是规范本身,规范语句可以为真,规范语句的真取决于与规范世界中的规范的符合。他指出:“如果将规范三段论的前提视作可以为真的句子,约根森关于逻辑应用的异议也就不再重要了。”
上述这种方案并没有完全解决约根森难题。首先,上述方案没有能够完全解决规范语句可以为真的问题。正如魏因贝格尔指出: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事实一致性,因而可以为事实语句确立真的标准。但规范世界中的规范并不具有如此一致性,因此,规范世界不能为规范语句确立真的标准,规范语句也就因此而不能被断定为可以为真。其次,按照上述方案,规范之间不存在逻辑推理,就不能解释法律规范基于推导的生成或衍生的现实。正如麦考密克所言:“在规范的领域内,有这样一些逻辑的关系和联系,借助于正式的规则可以使它们具有决定作用。如果规范被当作前提时是有效的话,那么规范的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后果也总是有效的。”再次,上述方案没有触及约根森难题的根本。尽管此方案强调规范语句与事实语句一样可以有真值,但这两种“真”其实是语词相同但意谓完全不同,因此,仅仅说规范语句与事实语句一样也可以有真值,并不能回答规范三段论为何是逻辑推理,不能解答“因现实世界中的事实而为真”的事实语句与“因规范世界中的规范而为真”的规范语句之间的推理为何是逻辑的。
因此,将司法三段论概括为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或一阶谓词逻辑推理就面临约根森难题。国内外学界认识到,经典逻辑不足以刻画法律论证与推理。一些学者建立了道义逻辑系统,冯·莱特和安德森的道义逻辑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应当指出,冯·莱特和安德森以及其后的道义逻辑系统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上述系统建立在广义模态逻辑理论之上,建立在基于真值的可能世界语义学之上,仍面临约根森难题;二是其逻辑语言是贫乏的,缺乏对规范三段论的表达与刻画;三是对规范算子的某些逻辑刻画并不适用于法律规范词,某些推理规则与法律规范推理相抵触。
阿尔乔隆和马尔蒂诺主张放弃真值语义学方案,甚至放弃语义学概念,寻求从逻辑的语法层面解答约根森难题。他们认为,规范没有真假但有逻辑,从假设后承而不从真值概念或语义概念出发可以说明规范推理的逻辑性或有效性。主张逻辑无需真概念,主张“没有真值的逻辑”(Logic without Truth),甚至主张逻辑推理不依赖语义。应当指出,这种放弃语义概念的方案扩大了逻辑的范围,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约根森难题。仅对推理系统进行构造并不能使逻辑后承完全摆脱语义学概念。构造与刻画逻辑推理不但要诉诸于语法层面的假设后承或逻辑后承概念,还需要其语义层面的解释。正如达米特所言,任何一个逻辑系统未必需要真值语义学,但一定需要语义学,即一个正确性或合理性的评价系统。
弗雷格指出逻辑本质是追求真。真值语义学刻画的是事实语句的推理有效性,而规范语句与事实语句有明显的区别,因此,用真值语义学来刻画规范推理的有效性,就必然面对约根森难题。问题并未就此终了,正如金岳霖所指出的:“事实上虽有不同的逻辑系统,理论上没有不同的逻辑。”约根森难题实际上在问逻辑之义是什么。约根森难题实际上也揭示了经典逻辑不能充分表达基于内涵推理与语用推理的复杂的法律论证与推理。逻辑是对有效推理规则的研究,如何回答好约根森难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逻辑的重要任务与使命。
逻辑难解涵摄与例推难题
基于制定法的法律论证存在涵摄难题。事实涵摄(subsumption)是对个案事实是否符合法律中的构成要件作出裁决。事实涵摄不是概念的分析与推演,而是对事实的法律评判。正如拉伦茨所指出的:“作为法律适用基础的涵摄推论,并不是将外延较窄的概念涵摄于较宽的概念之下,毋宁是将事实涵摄于法律描述的构成要件之下。”涵摄不是寻求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而是寻求事实与概念、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法律与事实间的目光流转”,是在事实和规范之间的“等置”。事实涵摄包含价值评价与利益权衡。尽管法律设定了评价标准与尺度,但法官有可能对当事人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有可能对事实的重要性程度及法律意义作出不同的评判,对案件作出不同的归类与裁决,且其孰是孰非有时难以判断与评价。因此,尽管有统一的制定法,但并不能确保事实涵摄的同一性或一致性。
基于判例法的法律论证存在例推难题。在司法中,有时面临多个先例,相互争夺对当前案件的支配力,需要法官进行区别性判断(distinguishing),判断本案与先例是否存在区别,以决定遵循先例还是区别先例。没有两个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当前案件是遵循先例还是区别先例,是由法官判断当前案件与先例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在法律上何者更为重要而决定的,法官有可能对当前案件与先例的相同点或不同点的重要性程度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从而作出完全不同的例推与裁决。因此,尽管确立了遵循先例原则,但并不能确保例推或类推的一致性,且其孰是孰非也难以判断与评价。
应当指出,涵摄难题与例推难题是法律论证的小前提证立难题。金岳霖指出:“积极地说,逻辑就是‘必然’;消极地说,它是取消矛盾。”但逻辑只解决名与名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的一致性问题。涵摄是名与实之间、概念与事实之间、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例推是个案与先例之间、个案事实与先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问题。逻辑不能解决“名与实”与“实与实”一致性问题,不能提供名与实、实与实之间的一致性判断标准,不能解决案件事实与法定构成要件之间的一致性争议问题,也不能解决个案与先例之间的一致性争议问题,因而不能解决涵摄难题与例推难题。
逻辑不能解德沃金唯一正解难题
在司法中,人们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法律问题有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指出,由于有“整全性的法”存在,即使是疑难案件,也有“唯一正确的答案”(single right answer)。这一答案或者从法律规则中获得或者从法律原则中获得。即使在疑难案件中,法官也不应诉诸自由裁量权而应在作为整全性的法律框架之中,通过建构性阐释(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以寻求唯一正解,这就是德沃金唯一正解问题。
在司法中,法官在解释法律与适用法律上会有意见分歧或争议。法官们有可能确立完全不同的权威性大前提作为裁决理由;有可能对法律概念作出不同的解释,对法律含义或意思及文字所蕴含的“事物本然之理”作不同的探寻;或者在法律未作规定或者可以这样决定也可以那样决定时,各自运用自由裁量来填补法律空白或漏洞;或者只考虑一般规则而不考虑其例外情形,以此为裁判理由作出不同的裁决。因此,即使有统一的制定法也不足以确保释法与裁决的一致性即法制的统一性。在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先例原则也不能完全确保裁决的一致性即法制的统一性。因为法官们有可能识别和适用完全不同的权威性先例,并以此作出不同的裁决。
法官承担依法裁判义务和公平与公正裁判义务,但实在法是开放的、非协调的、不完全的,不可能为每个具体案件都准备好现成答案。在审判案件中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但法官对制定法具有广泛的解释权与酌处权。法官承担着这样的职责:澄清法律疑义、平衡法律冲突与填补法律空白。法官有权确定法律是什么,他们是“活着的法律宣示者”。在英美法的判例制度中,尽管在审判案件中法官受先例的约束,但法官在决定是否遵循先例方面具有广泛的酌处权,有权决定何时遵循先例、区别先例、创制先例与推翻先例。法官有权从先例中抽象出基本的原则即判决理由,并且有权确定这些原则将要运行和发展的路径或方向。因此,尽管实在法与公平正义原则有助于构成司法评价主观自由游动的障碍,但最终也无法阻止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因为它们也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对象,存在着发生意见分歧与争议的可能。
有分歧与争议不等于不存在正确答案。但没有正确答案的标准,就谈不上有正确答案,更谈不上有唯一正确答案。因此,唯一正解的问题就是唯一正解的标准问题。唯一正解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是否存在唯一正确标准?应当指出,唯一正解的标准是可争议的,因此,唯一正解是可争议的。这些司法裁决可以放在正义的天秤上进行衡量,但这些衡量标准进一步面临着进一步的正义选择与争议。在通常情形下法律的正义之路是没有冲突的,但有时这些正义之路分岔了,有的正义之路通向这样一个正义,有的正义之路通向另一个正义,在这些正义追求之间就必须作出选择。但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不存在使结论具有必然性的无可辩驳的‘基本原则’,所以通常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通过提出似乎是有道理的、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论据去探索真理。”应当指出,德沃金唯一正解难题是法律论证的大前提证立难题。逻辑提出了法官释法与裁决的内在一致性要求,但未能提供解决其冲突的选择与平衡标准,因而不能消除法官意见分歧与争议,不能终结其唯一正解难题。
逻辑难解法律论证终极之困
在法律论证中,面临阿尔伯特所说的“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德国法学家阿尔伯特指出,任何命题都可能遇到“为什么”之无穷追问的挑战。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要求对一切命题都加以证明,就必然产生两种情况,其一陷入无穷后退,其二陷入循环论证,无穷后退和循环论证都不是证明。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某个主观选择的节点上终止论证。这三种情况被阿尔伯特称为“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
在司法中,对判决理由进行证立是必要和必需的,是法律论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法律论证的关键。司法裁决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对这些裁判前提或理由的确立与选择。法律获取或理由确立是可争议的,在疑难案件中涉及选择时更是如此,要避免公众合理的怀疑就必须对有争议的前提或理由进行证立。图尔敏认识到了对判决的争议不但来自对推论的争议而且来自对前提的争议。他在《论证的使用》中指出,不但结论需要证立而且前提受到质疑时也要予以证立。寻找正确答案是摆在每一个裁判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人们普遍地认为,不可能通过无穷后退或循环论证的方式来寻找正确的答案,也不能因为无法找到绝对正确的答案,而把裁决交给法官无根据的专断或无理由的武断。法官作出的裁判及其理由能够回溯到实在法规则与原则上,外部证立链条最后能终止于既有法律之内,这是司法判决追求的目标,也是判决证立的一个标准。应当指出,虽然制定法存在开放性结构,但制定法原则与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与指引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要尽力从法律上回答所有的法律问题。但制定法并没有为具体案件提供现成答案,如何证明判决理由是成立的,最终在何处结束裁决论证的链条,是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解决的。因此,法律论证本质上属于实践推理的范畴。佩雷尔曼强调证立或说服的标准是“普遍听众”的认同;德国学者阿列克西强调法律论证的正确性是因为它能够在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被证立是符合理性的;瑞典学者佩策尼克提出了法律论证的“深度证立”(deep justification)和“审慎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标准与要求。
如何走出明希豪森困境是法律论证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明希豪森困境是判决理由的可证立性难题,因而是判决的可证立性难题,也是法律论证的终极之困。在司法裁判中,判决证立最终是对判决理由或前提的证立。应当指出,逻辑难解法律论证的明希豪森困境。逻辑可以用于法律论证与推导,是论证与推导的工具,但它对其前提与理由却无法作出选择,不能提供前提或理由的选择与评价标准,因而不能消除关于前提或理由的分歧与争议,不能终结对前提证立的追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姆斯在《普通法》中开篇说道:“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时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见对人们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大于逻辑三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