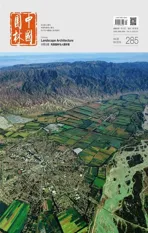科学、价值与判断在环境影响评估架构中之整合
2019-10-29赖世刚
赖世刚
1 科学、判断与公共政策制定
本文旨在申述环境问题的合理解决,尤其是环境影响评估作业,不仅是自然科学或技术上的问题,也是牵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或政治学的学科交叉问题。尝试提出一整合事实(facts)与价值(values)的合理架构,作为环境影响评估作业程序设计的依据。由于科学的日益进步,使得先进技术的研发触及了一些人类基本价值的调整。例如人类基因图谱的建构及基因复制工程的发现将对现有人权的定义与社会伦理制度有所冲击。过去的公共政策制定,以专业客观知识作为政策的实施评估绝对依据,如今此方法已受到挑战。因为许多有关科技的公共政策,随着知识的演进,其影响层面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已难以明确界定[1]。另一方面,完全依赖政治过程解决问题而忽略专业知识,则会导致难以弥补的错误决策。因此,科学与价值是重大公共政策制定时必须同时面临的政策输入。如何妥善并合理整合此2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以制定可靠的公共政策,实乃重要但却困难的工作。
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时便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例如,哈蒙德(Hammond)及阿德尔曼(Adelman)针对事实与价值在公共政策信息整合的过程设计,便对当时的一些作法颇为诟病。在认知科学对人类决策制定过程尚未有深度认识的当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科学家的专业地位受到质疑[2]。当从政者必须作重大决定时,往往诉诸具有特殊经验人士,而非客观而科学的方法。因此有所谓科学法庭(science court)的构想,即针对某一特定政策议题,由科学家就其所拥有证据以不同立场进行辩论,最终则由“法官”及“陪审团”裁定是非。此外尚盛行“以人为主”(person-oriented)的搜证方法,即由提供某政策议题科学证据的科学家主动说明其本人是否与该议题有利害关系,以供人判别其所提供之信息是否具有提供事实以外的动机。哈蒙德及阿德尔曼认为此2种方法皆不可取,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事实与价值仍然混搅在一起,使得科学家与从政者的角色混淆不清,甚至造成角色互换。哈蒙德及阿德尔曼认为科学家与从政者的角色可以厘清,应分别在政策拟订过程中扮演恰当的角色。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申述环境影响评估问题绝非仅仅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其同时必须依赖社会经济等价值判断。整合型架构可作为环境影响评估作业设计的依据。
2 环境问题的未充分定义性
假设环保部门欲在某水体设定最低水质标准,如溶氧量或DO值。该水平的设定乍看应属环境科学或环境工程专家的职责。传统的做法系以残余物管理的概念,建立该水体污染排放源与水体自清能力的系统模式,在决定水体生态溶氧量的最低标准下,制定各污水排放源的排放标准,据以立法限定该水体的生产行为[3]。如果该水体两岸有城市及其他活动,显然,水质标准的设定将会影响这些从事者的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过于严苛的标准将导致某些工厂关闭,较宽松的管制将使下游居民受害。因此,水质标准设置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成为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的政治问题[4-5]。
环境质量问题既牵涉到收入分配及社会选择议题,该问题便不同于纯技术问题而如此容易定义,并形成了未充分定义问题(ill-defined problems)。解决充分定义(well-defined)与未充分定义问题的逻辑有显著差异;前者主要依赖算法(algorithms)而后者主要根据经验法则(heuristics)。西蒙(Simon)所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其实便是解决未充分定义问题的权变方法之一[6]。此外,规划及设计面对的往往是未充分定义问题,使得霍普金(Hopkins)及哈里斯(Harris)认为我们只能用最适化(optimization)概念作为一种解决此类问题的类比(analogy),而非方法(method)[7-8]。换言之,最适化本身并不能直接作为解决规划问题的方法。至于何种逻辑是解决未充分定义问题的有效方法,至今似乎仍无定论。但至少有相关研究指出该逻辑应有的特性并应用恰当的实验设计来评估不同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7,9]。而在认知心理学及决策科学的研究中亦发展出实用的选择评估程序[10]。其他如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及MGA(Modeling to Generate Alternatives)等计算机系统的发展,亦尝试结合最适化模式、算法及人类判断以解决未充分定义问题[11-12]。
3 环境问题的政治性
环境质量为共同财产资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其管理为中国台湾有关当局的重要施政方向之一,且其涵盖之范围亦十分广泛。凡是空气、水、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甚至环境之规划与管理皆属共同财产资源管理的一部分。而共同财产资源管理与一般财产管理之主要差异在于前者无法进行财产权的设定且无市场存在以决定其价值,而后者恰好相反。共同财产资源在无适当机制(如市场及社会选择)的制衡之下,成为众人掠取的对象[13],因此有所谓的免费搭便车(freerider)及财产权掠夺情况产生[14-15]。共同财产资源的管理必须借由有关当局的干预以避免此现象的发生。
环境管理为共同财产资源管理的一环,因此具有前述资源的特性。当个人对环境质量的追求可通过市场机制获得时(例如高收入者可迁至环境质量较佳的地区),环境质量问题可视为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的问题。然而当社会中所有人皆遭遇环境质量恶化所带来的威胁时,便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质量的问题,而必须由有关当局实行必要的措施来减轻该威胁[5]。
一般而言,有关当局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多偏重技术层面,且以行政单位作为环境政策制定与监督的施政机关。例如,水源保护区的设定、污水及废气排放标准的制定与稽查,以及垃圾处理场(厂)区位的选择与兴建等,皆由有关当局及地方环保及相关部门负责。殊不知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何者受益而何者受害),且为有关当局行动的选择。这些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若未能反映民意,则以行政单位为主的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有违背民主政治原则之嫌。此外,有关当局行动无疑是社会选择方式之一,但社会选择理论在Arrow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的阴影下,凸显其在选择程序设计上的盲点[16]。亦即,在4个合理的基本前提下,包括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柏拉图原则(pareto principle)、无关方案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和非独裁性(nondictatorship),并不存在任一合理的社会选择机制同时满足前述4个前提。
中国台湾地区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已超越市场机制所能解决的范畴,且各种数据显示此种趋势有恶化的倾向。虽然有关当局已尝试采取各种适当的干预政策以减轻环境恶化的威胁,环境问题仍持续恶化。尤其精省条例之通过及有关当局再造工程的推动,势必整体影响有关当局甚至社会有关环境政策拟定与实施的选择机制。赖世刚认为环境政策之制定应隶属法律或民意机构的权责,而政策的执行则为行政机构的权属范围,法律或民意机构负责监督政策执行的绩效[4]。这个前提主要基于阿罗(Arrow)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以及黑费勒(Haeffle)针对美国环境管理社会机制所做的分析[5,16]。环境质量可视为一种财货,而个人可通过交易行为获取这项财货的财产权。例如:高收入户可以通过不动产交易行为迁移至环境质量较佳的地区。然而,环境质量作为一种财货有其特殊的市场性,即它属于一种公共财。公共财指的是在一群体中,任一个体对该财货的消费不能阻止其他成员对该财货的消费;换句话说任何成员即使不购买或支付这项财货,并不能阻止其共享该项财货[14]。因此,公共财的价值因缺乏类似一般财货之市场机制的存在,其价值难以衡量。尽管如此,有些公共财可以特殊方式来衡量其价值。例如:Sinden及Worrell列举并比较在没有市场价格下决策制定的方式,包括各种价值评估的技术[17]。由于环境质量具有公共财的特性,当环境质量优良时,个人可通过不动产交易行为获取这项财货的财产权。然而当环境质量恶化时,此项公共财必须通过集体行动由群体来提供。而群体或组织形成的最终目的之一,即在提供公共财使得群体成员共同获益[14]。因此,当环境质量恶化时,有关当局便有制定环境质量改善的政策与实施之诱因,以提供环境质量之公共财。此外,根据Arrow的说法,主要有2种方式进行社会选择:以“投票”方式进行政治决策及以市场机制从事经济决策[16]。由此观之,环境质量一方面因其具公共财的特性,势必由有关当局提供;另一方面因其市场之不存在,势必以“投票”方式之政治决策以决定在何时、何地,以及提供多少环境质量之公共财。
4 环境影响评估架构
环境影响评估作业绝非单一的技术(technical)问题,实质上它更涵盖政治(p o l i t i c a l)及法规(regulation)制订的概念。技术层面在一般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过程中最受到重视,且环评委员亦多具备合适的背景。至于政治及法规层面则鲜少被委员或专职机构所考虑,故本节将就环境影响评估有关政治及法规层面的意涵与课题作概略性说明,据以提出一整合型环境影响评估作业程序。
科学与价值如何在社会政策中作一平衡考虑,是颇具争议性的问题,而科学家与政治家对于科学事实与社会价值如何加以整合亦无适当的解决方式[2]。这方面问题的解决最为人知的莫过于社会心理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判断理论(Social Judgment Theory,SJT)。该理论所提出的线性权重模式,即科学家列举议题的科学事实作为自变量,而政治家以权重的方式赋予这些自变量以不同相对重要性的意义,最后以自变量加权加总的结果显示不同方案的可行性以彰显科学价值的整合评估。
虽然SJT理论企图平衡政策制订的科学与价值或政治判断,但对于政策制订实际的政治过程却缺少说明。例如,哪些政治家具有代表性参与SJT模式之建立?模式建立中权重的政治意涵为何?皆为SJT模式应用前应该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SJT理论指出许多公共政策(包括环境影响评估)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涉及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所需解决的便是如何将众人的意见反映在政策制订过程之中。环境影响评估之作业亦不例外,其看似为单纯之技术问题,其实若深究之,不难发现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意义。例如,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如何将民众意见纳入考虑?其影响范围如何划定?标准订定所造成之贫富分配的影响为何?这些问题绝非从单一技术层面便可解决。如何应对环境影响评估所带来之政治及法规层面的影响?为回答此问题,首先必须对环境影响评估的政治意涵加以说明。环境质量曾经一度被视为一种公共财,以现今环境恶化的情形来看,其已经转型为一收入分配的问题。环境质量被视为一种特殊财货,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而环境政策的拟定,亦将影响收入分配。此外,环境资源基准量化,如河川水污染质量的规定,亦将使某些民众获益而其他民众受损,因为水污染质量的规定一方面可能使业者的生产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得亲水游憩活动质量提高。环境政策之拟定便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其政治层面的意涵将使得环境决策必须有民意的参与。
民意参与拟定公共政策的精意在于如何设计合理的机制使得民众个别的偏好能反映在公共议题方案的选择上。此乃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研究的范畴。众所皆知,从Arrow的不可能理论所衍生的结论说明没有任一合理的社会选择机制可以同时满足民主社会的4个基本要求,即集体理性、柏拉图原则、无关方案的独立性及非独裁性[5]。简言之,集体理性说明给定一组个人偏好,社会偏好乃由个人偏好获得;柏拉图原则认为如果社会中每个人皆认为A方案较B方案更佳时,社会亦将视A方案较B方案更佳;无关方案的独立性指的是任何环境中,社会选择的决策端视个人偏好对该环境的方案而定;非独裁性则指社会中没有任何人其偏好自动形成社会偏好而无视于其他人的偏好。虽然Arrow的不可能定理否定了任何社会选择机制的合理性,但Haefele却能证明民主政体在允许换票(vote-trading)存在的情况下,理论上在此机制的运作下其结果与民众直接投票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个论点已被赖世刚及张慧英进行实验验证[18]。
中国台湾地区目前的环境政策皆由环保部门拟定与执行。前揭的简要辨证主要阐明在民主体制下,环境政策拟定应由民意机构负责,而行政部门负责执行[4-5]。例如,环评作业中环境资源基准项目量化的设定在理论上至少必须通过立法民意机构以民主议事决议过程拟定之,而非仅由环保部门邀集专家学者径自订立后报院实施。此外,法规的功能在于限制开发行为的种类及开发量。法规在开发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如同游戏规则的设定,而从业者、有关当局、民众及利益团体在此游戏规则的框架下进行协调沟通,以确保自身的利益[19]。本研究所拟议的开发行为规范便是以环境资源基准量化的整理为依归,以环境质量提升为要求,作为开发市场游戏规则确立的基础。
基于以上的认识,环境影响评估作业程序应平衡好技术层面、政治层面及法规层面,就下列原则而为之:
1)兼顾技术层面科学事实与政治层面价值判断的整合;
2)兼顾行政机构执行效率与民意机构代表层面的平衡;
3)兼顾从业者、有关当局、利益团体及民众利益的平衡;
4)兼顾环境资源基准量化适用范围以及民众收益分配的平衡;
5)兼顾地方特性、有关当局权责、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平衡。
根据多属性评估方法以及整合型公共政策评估方式[2],针对山坡地开发环境影响评估程序提出评估模式之建立,并将该程序以计算机程序撰写加以自动化,以辅助相关单位进行环评作业时达到公平有效的目的[20-21]。该评估模式之建立首先根据文献进行环评因子之筛选,包括物理(含坡度、坡向、土壤质地、土曾厚度、覆盖层N值、基岩性质及年平均降雨量)、生态(含植生分布状况、空气质量及河川水质)、景观及游憩(含自然人文游憩景观美质)及交通(含道路服务水平及交通可及性)等。利用Saaty所研发的层次分析法(AHP)及专家问卷调查[22],进行各因子权重分析并建立各因子价值函数,进而根据线型模建立环境影响评估模式如下:

其中,Xij为方案i因子j的水平;Wj为j因子的权重;而Zj为某开发案j因子的价值水平。各山坡地开发案便可根据此模式进行评估排序。仿效阿蒙德及阿德尔曼的精神,开发案的因子水平可由专家及行政部门以科学的方式决定,而权重则可通过民意代表及从政者的辩论决定之。必须注意的是权重的意义必须界定清楚,以免扭曲正确的判断。
5 结语
本文视环境影响评估为公共政策的一环,而公共政策的评估必须同时考虑科学的依据与可靠的价值判断。过去公共政策的决定往往依赖从政者的直觉与经验,使得该过程有黑箱作业之虞。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对决策过程的认知过程有深入了解。建立在这项知识的基础上,本文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目前所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估作业程序提出2点看法:1)目前环评作业权责偏重以行政部门为主体;2)环评作业内容偏重于技术层面。本文提出一综合科学事实与主观判断的整合型环境影响评估架构,冀望借由本架构的提出使得实际环境影响评估作业对技术层面以外的经济与政治有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