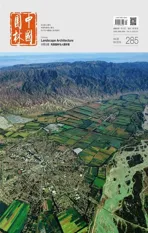体育公园模式演变与空间系统发展脉络研究
——基于竞技、风景和触媒的逻辑
2019-10-29叶郁
叶 郁
潘思融
体育公园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水平和人们对艺术与思想的意识追求密切相关,从20世纪中后期体育公园概念的提出到近几年在中国的兴起,体育公园充分发挥着改善大众生活质量、创建活动型生态绿地的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研究对象,从功能场所发展的角度对体育公园的概念和发展脉络进行研究,探求其发展动因和模式变化,以期对未来体育公园的建设发展提供参考。
1 体育精神与公园认识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和智力为基本手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1]。体育产业化之后,其组织与制度不断加强,已成为21世纪具有高渗透性、高活力性、高拉动性的绿色健康产业。体育场作为场所存在的雏形出现于公元前15世纪的古希腊,建设初衷是提供作为公共集会的场所,体育竞技、哲学座谈、辩论和聚会都会选择在这里进行。这一时期的体育场选址已经注意到与自然风景的结合,为体育公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体育公园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后期,是在生态型体育产业的大背景下,基于现代城市公园的本底,满足体育产业需求的发展模式。苏联在1985年出版的《世界公园》中定义体育公园为“设在风景如画的园林空间中,包含体育设施、运动场以及在这些场地上举办系统的体育训练、体育表演、竞技比赛和保健活动,并吸引居民来此休息的公园”[2]。我国在1982年的《城市园林绿地规划》中提出“体育公园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公园,既有符
合一定技术标准的体育运动设施,又有较充分的绿化布置,主要作为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和日常练习场地使用,同时可供运动员及群众休息游憩”[3]。1994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印发《全国城市公园情况表》,对体育公园的定义又做了更为精准的描述,明确说明“附属于专业体育运动馆的花园,以及设置简单健身器械的活动区,或公园中辟出的,仅供少部分人临时活动的小块场所,都不能称为体育公园”[4]。2006年,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园林设计分会在《风景园林设计资料集——园林绿地总体设计》一书中提出体育公园的功能包括体育竞技、体育休闲和体育医疗三部分[5]。2017年《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将体育健身公园划分为其他专类公园(G139)[6]。纵观体育公园定义的发展历程,可以确定体育公园首先应该涵盖体育产业所需的功能,并且具备城市公园的基本外貌特征。
2 基于竞技体育的体育中心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奥运会”)于1896年4月6日在希腊雅典举办,这是开启现代体育的标志性事件。区别于1500年以前的古代奥运会,现代奥运会是在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以体育运动为载体,旨在促进人类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运动与全球庆典[7]。体育中心是以体育场为中心,配套设置与竞技体育相关的功能场所。几乎从零开始的奥运会在筹建过程中受到时代发展的限制,以能够顺利举办全球级别的运动会为唯一目标来筹备所有空间场所。体育场是竞技体育发生的主要场地,首先应满足现代体育的竞技需求。其次,作为举办全球庆典的场所,体育场需要具备可容纳数万人的观众席位,体育建筑及外部空间也需要满足短时间聚积和疏散万人的功能。希腊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Panathinaiko Stadium)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典型竞技体育中心。帕纳辛奈科体育场又名大理石体育场,最初修建于2世纪,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部用大理石建造的体育场。体育场位于雅典市中心瓦西里·索菲亚大街,古代常用来举办纪念雅典娜女神的泛雅典运动会,后经战乱而废弃。1895年为举办首届现代奥运会,乔治·阿维罗夫捐赠100万德拉马克(Drachma)在废墟上重建了这座气势恢宏的体育场。体育场周长333.33m,长192m,整体为“U”形南北布局,东南西三面由看台围合,固定座位4万个。体育场的重建完全遵循竞技体育的需求,开闭幕式及竞技比赛中的田径、举重、射击、自行车、击剑、网球、古典式摔跤和体操8个大项和各项颁奖典礼均在这里完成。
第四届奥运会于1908年4月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次奥运会是竞技体育再次回归全球盛会的新起点,也是现代化体育中心的开端。伦敦奥运会的主场馆是白城体育场(White City Stadium),是一座可容纳7万人的多功能体育场,被誉为第一个现代化竞技综合体育场。体育场原址为荒芜的丛林,英国政府在当时简陋的技术条件下以惊人的工作效率完成了体育场的建设。设计者创新设计建造了一条534.45m长的煤渣内圈跑道为田径比赛所用;666m长的柏油外圈跑道为自行车比赛所用;中央场地内设有田赛场、足球场,还有一个100m长、15m宽的游泳池。白城体育场是一个集跑道、自行车赛道、田径场和游泳池4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场。

表1 竞技体育阶段发展脉络
从第一届到第十九届,从功能场所发展的角度分析,现代奥运会作为以体育运动为载体的全球盛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体育场到多场馆集群分布的体育中心这一发展过程,该过程可被称之为竞技体育阶段(表1)。体育中心的产生是竞技体育阶段的重要标志和成果。
3 风景化的体育公园

图1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区位(Behnisch & Partner事务所提供)
体育公园的产生是体育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变革,究其原因在于体育功能的延展。奥林匹克公园成为主办城市和其所在地区的大型活动中心,这些活动包括:职业体育赛事、大学生体育竞赛、国家级高水平运动训练中心和居民健身活动等[8]。顾拜旦提出“奥林匹克城应当是宏伟而高贵的,必须与周围的乡村环境吻合,能够有效利用周边环境,场地不应像古奥运会那样集中,但也不能过于分散”[9]。顾拜旦对自然田园的偏爱激发了在城市中建设奥林匹克公园的构想。随着19世纪城市公园系统理论与实践的日趋成熟,公园系统的规划设计有效解决了城市的诸多问题,并影响到城市空间的发展,这为体育从单一的竞技功能向竞技、健康、生态的多重功能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由此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风景化体育公园模式(表2)。
1972年的第二十届慕尼黑奥运会是当时历届规模最大的奥运会,所有数字均创造了历史纪录。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成为由体育中心转化为体育公园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是慕尼黑城市发展的一次飞跃。下文以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为例进行研究。
3.1 体育场馆布局和城市格局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选址于慕尼黑市以北(图1),场地内有一座由战后建筑垃圾堆积而成的舒特北格山(图2)。规划设计将整个奥林匹克建筑组群有组织地布置在公园之中。奥林匹克建筑组群主要包括一个8万人体育场、一个9千人游泳馆、一个1万4千人综合体育馆,同时还设置有自行车场、冰球场、拳击馆、大型水上运动人工湖等共33个体育场馆,此外,公园内还规划设计了奥林匹克村、新闻中心和290m高的电视塔等配套设施。无论是奥运会的竞技体育功能,还是由竞技体育所延展的住宿、媒体和绿色生态等功能,最后均以公园场所的方式进行布置和承载。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布局方式为现在“一场两馆”或“一场三馆”的体育公园规划设计提供了教科书式的参考(图2)。

表2 典型风景化体育公园发展对比
风景化的体育公园与体育中心的区别除了以公园的形式布局外,另一个重点是体育公园对城市格局的影响,甚至具备促使城市格局形成的作用。功能的复合不仅发生在体育建筑内部,建设具有多种功能和综合服务能力的体育建筑综合体,更应满足城市居民各个圈层的需求,实现区域性的城市功能和形态机理等各方面的综合整合[10]。慕尼黑体育公园的选址位于城市发展的第三个圈层,体育公园的兴建促使城市交通体系趋于完善,城市结构稳定发展,空间拓展目标基本实现,同时满足了城市人口和工作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3.2 创新的公园绿地系统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作为风景化体育公园的起点和典范,其杰出之处在于首次提出了“绿色奥运”的规划设计理念,将城市绿地系统与体育中心相结合,创建出风景化的体育公园。奥林匹克公园成为慕尼黑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园的建成实现了以阿尔卑斯山为背景、伊萨河为生态轴,内外双环的城市绿地系统结构体系。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借鉴了英国自然风景园的设计手法,突出山形水势的营建。主山奥林匹克山东西长900m,最高点约60m,可远眺慕尼黑市中心(图3-1);顺着主山北麓开凿人工湖,与城市水系贯通,该湖在奥运会期间是大型水上运动的比赛场地,赛后成为现代城市公园叠山理水的经典之作(图3-2)。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创新设计开放空间,有效解决赛时高峰人流与公园游憩道路之间的矛盾。大型体育建筑群是体育中心转变为体育公园的又一经典力作,把传统的功能型竞技体育建筑风景化,庞大的体量足以满足体育运动的所有功能需求,独特的形象又将其与公园环境融为一体,这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杰作,也成为慕尼黑现代建筑的代表。

图2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整体规划(引自https://www.olympiapark.de/de/der-olympiapark/veranstaltungsorte/)

图3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山形(3-1)及水系(3-2)(引自视觉中国)
风景化的体育公园将风景作为必要元素,以城市公园和绿地系统的形式承载体育中心的竞技型功能。风景解决了绿色和生态的实际问题,同时风景也成为体育从竞技迈向产业的重要推力。1992年第二十五届巴塞罗那奥运会,蒙锥克山上的露天跳水场又一次演绎了风景化体育公园的经典。蒙锥克山是一座高184m的小山丘,山顶足以俯瞰巴塞罗那全城和港口,蒙锥克跳水池正因为这个独特的风景化视角,成为当年拥有最美风景,为运动员、观众和媒体留下特别记忆的场馆而闻名于世。
4 触媒型体育公园
城市触媒理论产生的背景与美国联邦政府城市改造计划的失败和大型项目建设热潮的消退密切相关。“二战”后全球化背景下,人员、物品和信息的聚集与流动,使得城市形态变得愈加庞大、混杂和易变[11]。美国建筑师韦恩·奥图(Wayne Attoe)和唐·洛干(Don Logan)提出了“城市触媒”的概念,指出“孤立”的好设计是不够的,城市设计应能“回应现有的元素”并“指引那些接踵而来的元素”以实现可持续的过程[12]。奥运会发展到现阶段,其功能已经不单纯是竞技体育和风景公园,更是叠加了产业、资本、活动和人口等多重功能。混合用途开发是有目的性地对物质空间进行改造,需要容纳3种或3种以上相互配合的营利性功能,如文化、娱乐、办公和商业等[13]。奥运会成为一次性投资最大的城市事件之一。
4.1 体育公园的触媒机制
触媒的原理在于触媒点与城市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触媒型体育公园作为触媒点,已不再是单一的“体育”或是“公园”这类最终“产品”,而是诱导后续开发、驱动城市结构更新的城市元素。体育公园的触媒机制核心是短期(赛时)和长期(赛后)功能与空间的有机转化。体育公园天生具备“赛时”和“赛后”2个完全不同的功能需求,每个时段的特定功能都能够明确指向不同的城市发展目标和职能,这是体育公园能够成为触媒点的必然,也是体育公园由体育发展到公园又发展到触媒的根源。
4.2 体育公园的触媒模式
大型体育场馆植入城市结构是城市更新和城市再开发的催化剂[14]。体育公园初期的运营模式基本相同,都是以竞技为先决条件,风景为必要条件,因此在规划设计中也都具备相似的功能布局、流线组织和空间格局。随着城市建设者在城市更新与再发展中逐渐意识到“赛后利用”的重要性,触媒概念的引入成为体育公园现代价值再认识和再挖掘的切入点。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在规划设计之初就成为国内规划、建筑、风景园林等业界和学界的研究重点,奥运会对北京城的发展进入持续的“催化”时期,可以被认为是触媒型体育公园的初步尝试,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和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公园是触媒型体育公园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探索(表3)。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选址于北京城中轴线的末端,选址采取了“离散多属性决策分析法”,依据目标区域的现状用地、城市发展规划、国际奥委会的考核指标与经济测算等,促生混合用途开发[15]。体育设施在当前首都城市发展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对于首都现代化进程可以起到全方位的促进作用[16]。从体育公园的选址开始,相关的赛后利用研究也随之开展,通过近10年的规划建设,可以清晰地解读出当年所确认的未来发展模式,即“体育+旅游+文化”的多元触媒模式(图4)。总体赛后利用延续“鸟巢”“水立方”为核心的体育场馆功能区,充分利用奥运品牌的价值拓展多元的旅游功能和旅游产品,于2013年被国家旅游局正式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称号。作为城市主要的公共开放空间,不仅是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游憩活动场所,也是市民文化的传播场所[17]。体育公园的北侧用地在后期的城市更新中被置换成公共文化功能区,建设了“中国国学中心”“中国国家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与体育场馆功能区共同构建体育文化景观带;延续、拓展、置换的触媒策略促使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逐步转变为“体育+文化+旅游”的触媒模式。

图4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多元触媒模式简图(作者绘)

表3 触媒型体育公园对比
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因地制宜地探寻出与北京不同的触媒模式。体育公园选址在伦敦城郊的利亚山谷,曾经是一片废弃的工业生活区,是伦敦最贫穷的区域。因此,在伦敦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阶段,“社区生长”成为伦敦奥林匹克公园赛后利用的触媒模式,通过触媒催化新旧城市的迅速转型。基于伦敦绿色空间城市的发展理念,奥林匹克公园由风景型体育公园转化为一个功能齐全的新型社区公园,并以此为核心增值周边土地价值,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建设3.5万套住房,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配套建设教育、医疗等社区必备的功能设施,以及改善公共交通和基础运输设施等。伦敦奥林匹克公园新建5个低密度社区,50%的住宅将成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18]。“社区生长”的触媒模式为该地区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全新的社区生活、积极的商机和稳定的工作岗位。
2016年的里约奥林匹克公园地处生物资源丰富的“热带雨林”,规划以自然生态、城市空间、市民生活的平衡共生为基础,突出生态主题,整个公园成为流域系统生态廊道的一部分。里约奥林匹克公园的赛后利用提出了“生态保育+弹性架构”的环境引导模式。巴西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城市发展的巨大需求,因此赛后利用首先要保证资金,以环境为诱因利用几十亿美元的投入催化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奥运赛事结束后,近期先以公园作为开放空间的核心,置换主要建筑功能,补充建设艺术中心、商业服务设施等。远期借助体育公园的触媒作用,将公园及周边用地发展成为一个以街区为基本模式的高密度城市环境,体现里约的独特地方文化和多样生活方式。

表4 3代体育公园对比
5 结语
随着《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的实施,体育的核心精神、产业功能、经济价值和民生保障等诸多作用日益成熟和发展。现代奥运会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更推动了城市活动、文化交流和商业开发的战略性发展。自从古希腊将竞技体育与城市开放空间结合在一起,体育就成了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一代奥林匹克公园可以归结为竞技型的体育中心,让竞技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生活并成为庆典。多重功能复合的属性与生态可持续的自然观,又进一步推动体育中心与公园空间的结合,渐进为第二代风景化的体育公园,在城市生态化的背景下,成为生态城市的重要构成元素。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城市的更新愈加复杂,奥运会作为投资巨大的城市大事件必然成为城市更新与发展的触媒,对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都具有催化作用。因此,奥林匹克公园已不仅仅是为奥运会提供生态竞技的空间场所,更是成为一个城市“持续催化”发展的媒质,奥林匹克公园已发展成为第三代触媒型体育公园(表4)。
就发展时序而言,从体育中心到风景化体育公园,再到触媒型体育公园,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体育产业的发展特点和城市的进化特征。但单纯地从功能和空间的角度审视,这3种体育公园的模式并不存在时间顺序上的淘汰或落后,体育中心承载着单纯的竞技体育功能,风景化体育公园重在体育与公园的多重功能叠合,而触媒型体育公园重点强调区域的媒介作用,3代体育公园在投资规模、建设目标和后期运营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未来的体育公园建设中应根据现实需求有目标地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