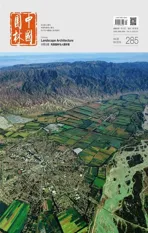澳大利亚水敏城市设计(WSUD)演进及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启示
2019-10-29孙秀锋
孙秀锋
秦 华
卢雯韬
21世纪初,全球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1-2],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突破50%[3]。过去30年,我国城市的快速增长对城市及周边的受纳水体及其生态价值产生了严重影响,世界各国的城市同样也面临这一问题的挑战[4-5],而气候变化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6]。作为应对,许多国家已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展了城市雨洪管理[7],我国也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4年工作要点》中明确要大力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加快研究建设海绵型城市的政策措施[8],并相继于2014年9月及2015年4月公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和确定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名单。
当前“海绵城市”已成为我国城市雨洪管理及风景园林领域的研究热点[8-9],如在海绵城市的内涵及建设途径[10]、跨学科协作[11]、绿地系统规划响应[12]、技术构建[13]、绿地优化设计[14]、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15-16]和风景园林教育[17]等方面都已得出大量研究成果。然而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是将海绵城市的功能和适用范畴或忽视,或扩大,即存在其“万能论”与“无用论”2种认识,另一方面是将海绵城市的建设内容局限于低影响开发分散式设施,忽视如多功能调蓄公园、污染控制等综合方案和设施的建设[18-19]。
澳大利亚淡水资源匮乏,但在气候变化及城市扩张的背景下,大多数城市也面临着雨洪威胁,作为应对,其水敏城市设计(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WSUD)研究与应用走在世界前列。国内已有学者对WSUD如何应用于我国的城市水管理领域进行研究[20-22],但仍缺少从历史演进视角对WSUD的解析及经验介绍。本文在几个相关概念对比的基础上,通过解析澳大利亚WSUD演进过程,分析其成功经验及前沿趋势,以期为我国当前海绵城市建设及低影响开发的景观规划设计以启示与借鉴。
1 “WSUD”与“海绵城市”内涵的一致性
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现代雨洪管理体系有美国的最佳管理措施(BMPs)、低影响开发(LID)、绿色基础设施(GI)、雨洪管理措施(SCMs),英国的可持续城市排水系统(SUDS),以及澳大利亚的水敏感性城市设计(WSUD)等[5,7]。在概念上或强调技术描述(如SCMs),或强调基本准则(如LID、WSUD),但都建立在2个原则之上,一是使流态尽可能地接近自然水平或符合环境目标,二是减少污染和改善水质[5]。正因如此,它们在适用特性和聚焦问题2个维度上具有显著的重叠性(图1)。
尽管以上概念的内涵具有动态性[5,23],但综合比较来看,“WSUD”与“海绵城市”的内涵重叠度最高。WSUD被表述为“旨在减少城市发展对周围环境水文影响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哲学方法”[24],强调在整个城市水循环的综合框架内考虑雨洪管理问题[25]。而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26]。通过对《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及相关学者对海绵城市内涵、应用尺度和技术途径等的解读[8,11,13,27],并和上述概念在适用特性和应用范围2个维度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海绵城市与WSUD在内涵及外延上有很高的重叠度,一些学者也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27]。因此,对WSUD成功经验的总结将会给海绵城市建设以借鉴。
2 澳大利亚城市水管理目标的转型
“水敏城市”表述的是城市水管理目标,“WSUD”描述的是目标的实现途径与过程[28]。“水敏城市”目标的形成必然涉及水管理认知上的变化[2],并最终导致和影响了WSUD的产生和实践[1]。因此为了能更加清晰地解析WSUD的演进,有必要进行澳大利亚城市水管理目标转型分析。
根据Brown等的研究[2,28],可以将澳大利亚水管理目标转型分为以下6个阶段(图2)。1)供水城市。19世纪初,澳大利亚城市水管理目标是保障城市人口的供水安全,表现为城市集中式供水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整个社会认同由政府向城市人口提供廉价和无限量使用的淡水。2)排污城市。19世纪中晚期,西方社会的疫情暴发催生了雨污分流,城市污水通过网状的污水排放系统被快速排放到受纳水体中,社会认同通过该系统保护公众健康。3)排水城市。20世纪中期,经济复苏后基础设施投入提高,排水管线被埋在地下,而地表河道则被渠化,其景观价值被忽视。4)水路城市。由于前期的“水社会共识”中没有为地表水的环境价值买单,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水资源被污染和过度利用,随着民众对环境舒适度需求的提高,地表水逐步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视觉和娱乐功能并被纳入城市规划。5)水循环城市。传统水资源对城市人口增长表现出的有限性,以及地表径流对污染物消解的有限性共同促使水循环城市目标的产生,目前这一概念基本上仍停留在学术层面,研究人员仍在不断通过积极对话和实践寻求实现综合水循环城市的方法。6)水敏城市。这一目标具有极大吸引力,但需要从认知、规范、管理等层面彻底改变,综合环境修复与保护、供水安全、防洪、公众健康、环境舒适、宜居和经济可持续等诸多方面。虽然目前没有关于水敏城市的实例,但为城市水管理明确了目标,促使WSUD的发生与发展。

图1 相关概念比较(根据参考文献[5]改绘)

图2 澳大利亚城市水管理目标转型[2]
这一过程可以为我国当下城市水管理目标设定以启示,同时有助于认清当前城市水管理所处阶段的属性、明确城市水管理变革所需,也能对不同城市的水管理目标转型进展进行横向比较。
3 WSUD内涵及其应用演进
3.1 WSUD的内涵解析
WSUD于1994年被首次提出[29],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寻求变革的探索,对待雨洪“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30],逐步转变为关注受纳水域的生态等多方面效益(图3)。如今WSUD被看作是城市设计范式的转变,积极主动地把水管理的多种目标纳入城市规划及工程实践的全过程,并承认城市设计、景观和雨洪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30]。
WSUD可以被定义为综合考虑供水、污水、雨水、地下水管理和城市设计与环境保护的城市水循环综合设计,总体目标包括[31]:应用高效水设备及装置,从供需两方面进行水管理以减少饮用水需求;尽量减少废水的产生,同时通过废水处理以回用或使其达到排放标准;处理雨水以再利用或使其达到排放水质目标;恢复或保持流域的自然水文特征;通过对前2个目标的管理提高水路健康;提升美学价值,建立与居民的联系;通过优化利用水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水资源自给率。在总体目标导向下,具体项目还需要明确设定可达的性能目标,这些性能目标需要从水供给、水量、水质、环境舒适和功能5个方面进行分解设定。图4为一个常规WSUD项目的目标集。

图3 城市排水管理的复杂性日益增长[5,29]

图4 WSUD具体目标集设定[31]
WSUD实施过程中将水循环管理纳入从战略规划、概念规划到详细设计的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并恰当地综合应用最佳规划实践(BPPs)和最佳管理措施(BMPs)(图5)。BPP是指WSUD中的场地评估和规划部分,而BMP是设计中用于实现WSUD目标的包括与雨洪有关的防范、收集、处理、转运、储存及再利用等要素,其中又包括非工程性措施和工程性措施[32]。
3.2 WSUD的发展演进
WSUD的演进可分为萌芽、产生、示范和应用4个阶段[33]。该过程符合一般社会技术转型路径规律,可以从社会技术情势、社会技术体制以及具体技术革新3个维度进行解析(图6)。总体来说,宏观情势的发展对社会技术体制产生变革压力,致使体制为技术革新提供机会窗口;研究人员在上述影响下进行技术革新,不同技术在主流设计领域逐步整合、稳定,随着内部动能的增加,逐步向上反馈并影响社会技术体制,最终导致社会技术体制变革重组,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具体如下。
1)萌芽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环境运动背景下,早在“排水城市”阶段就有了WSUD萌芽。在外部情势方面,发生了诸如“抵制排污口行动”等事件;在中观层面形成反馈,如1972年设立环保署等;具体技术领域也有所行动,如联邦科工组织(CSIRO)开展了如污水湿地等方面的研究。这些都为WSUD的产生奠定了基础。2)产生阶段:该阶段是WSUD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构建阶段,在外缘环境及具体技术革新的双重作用下,社会技术体制层面形成强烈反馈,如组建流域水文合作研究中心(CRCCH)等,并使城市水务部门重组,在技术领域形成如污染物捕获技术、湿地“软工程”处置技术等。该阶段WSUD主要是在联邦或州计划和项目的资助下,应用在展示性住宅及小规模社区当中[6],如菲格特里(Figtree Place)项目[34]。3)示范阶段:该阶段以应用示范为特征,上一阶段的技术革新逐步稳固,加之90年代的干旱事件及全球气候变化关注度的提升触发了社会技术体制的变革及重组[6],如形成跨机构的雨洪委员会等,完成了一系列雨洪管理规划,并出版了系列雨洪管理指南,同时也促进了微观层面的替代水源技术革新。示范项目主要应用在一些特定的开发项目上,由学术研究机构协同各州行政机构负责实施,一般由州和市级补贴并最终进入商业领域[33]。当然也有规模较大的地产项目,如维州的林布鲁克地产(Lynbrook Estate)示范项目[24]。4)应用阶段:2000年后在技术创新、集成及体制重构的背景下,WSUD进入应用阶段。该阶段技术的规范性得到提升,并依次出版了系列规划导则及规范;能力建设方面,CRCCH开发了WSUD分析评估模型工具(Model for Urban Stormwater Improvement Conceptualization,MUSIC)。该阶段一般应用在环境敏感地区新开发项目或州及地方当局指定区域的项目中,通常情况下由开发商联合专家顾问实施,项目进行商业化运作,如南澳州的莫森湖(Mawson Lakes)社区项目。
尽管澳大利亚的WSUD已经进入应用阶段,但它的推广依然被认为进展缓慢且实施较分散[35],澳大利亚的水管理也仅仅处在“水路城市”阶段,如何进一步实现向“水循环城市”甚至“水敏城市”目标的跨越,仍需要WSUD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图5 WSUD实施步骤[24,30-31]

图6 WSUD演进路径及阶段(根据参考文献[6,36-37]改绘)
4 WSUD演进及前沿领域对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的启示
我国海绵城市的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通过分析WSUD演进及前沿趋势,得出以下5点启示。
4.1 通过制度建设及行政措施,推进城市水管理及海绵城市建设
澳大利亚城市水管理目标及WSUD演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制度障碍的跨越。众多学者认识到管理破碎化、行政惰性和缺乏对WSUD的支持等是其推广实施的最大障碍[6,35],由此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建设研究[2]。此外,行政措施是另一个重要推手,如在某些州WSUD是特定规模和类型开发项目的必选项或规划方案的法定组成部分[31,35],布里斯班则指定WSUD是土地开发的首选项[38]。在我国,虽然也从行政的角度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出了指导意见[39],要求全国各城市新区、各类园区等要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但行政手段仍需要制度建设的保障,需要将城市尺度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纳入整体视野,建立符合国情和具备效果的管理体制,以突破管理上的破碎化,构建低影响开发建设的长效机制。
4.2 加强海绵城市设计的科学依据研究
澳大利亚有许多机构为WSUD提供技术支持[38],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如雨洪储存设计中水生植被养护及审美效应问题[40]、湿地和池塘的形状与水力效率关系等[41],再如应用CRCCH开发的“MUSIC”,即在规划图上应用雨洪处置策略并布置雨洪处置序列,系统将会模拟出因规划设计变化而产生的水质和水文变化,以便预测改善程度进而优化方案[38],为政策与雨水水质处理技术相结合提供了量化基础。而目前在我国海绵城市建设中还缺乏数量化分析,尤其是缺乏适用于不同场地及降雨条件下的海绵城市措施数量化分析工具。
4.3 通过项目实施后跟踪监测与效益评价改进海绵城市设计
通过项目实施后跟踪监测和效益评价加强设计研究,是澳大利亚WSUD不断演进的另一重要因素。如不同WSUD技术对雨洪净化效果的比较[42]、不同粒径砂滤装置对雨洪污染的去除效果[43]、WSUD能源消耗的影响评价[44]、设计目标与监测目标的比较[45],以及传统技术与WSUD成本的比较等[32],为WSUD改进与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34]。这种反馈与改进机制值得借鉴,特别是在我国不同自然地理区降雨模式及下垫面条件差别很大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项目跟踪监测与评价来构建有针对性的、适用于不同城市的海绵城市技术。
4.4 强化示范项目,推广应用海绵城市技术
通过示范项目来推广WSUD技术,最知名的莫过于墨尔本的林布鲁克地产(Lynbrook Estate)示范项目[24],该项目由工程(顾问公司)、风景园林(墨菲设计集团)和研究机构(CRCCH)三方联合实施,如今已经运行了近20年(图7、8),雨洪处置设施及景观效果依然良好,成为各方有效合作的典范,也为WSUD商业化应用带来了巨大的推动效应。反观我国海绵城市建设中,虽然也总结了一些经验[46],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示范项目,甚至项目周边的公众对其效益及功能也并不了解[47]。海绵城市建设应该是城市甚至超越城市尺度的百年工程、千年工程,需要通过示范工程全方位推广与认同,并向市场化应用阶段转化。
4.5 重视雨洪处置序列的合理组织
局限于分散式设施而忽视综合方案是我国当前海绵城市建设存在的一大问题[18-19]。研究表明排水链接性质对洪峰增加[48]和水质污染有重要影响[49],因此WSUD始终把每个雨洪处置措施当作处置序列(treatment train)整体的一部分看待[50],并将雨洪处置技术以序列的形式融入景观[45],这种方式已被证明在雨洪水质改善及消减洪水方面非常有效[51]。鉴于我国当前海绵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点尤其值得借鉴,需要从源头、过程、受纳水体整个序列中综合布局处置措施,真正提升海绵城市建设的效益。
5 结语
澳大利亚从国家层面制定水敏城市的相关法规和设计指导,在该框架下各个城市根据各自情况制定管理细则和设计导则并不断优化[52],经过6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水敏城市,如作为城市雨洪管理世界领军城市的墨尔本,基本建立了雨水、地下水、饮用水、污水及再生水的全水环节管理体系[53]。但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澳大利亚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高密度开发的中心区规模不大,其实现WSUD较我国城市更具有利条件[54]。同时由于其较低的居住密度,在家庭雨水回收利用方面也具有先天优势。
因此,借鉴澳大利亚水敏城市的建设经验,不能机械地应用其导则,即使在澳大利亚本土也需要因地制宜。同时必须看到,海绵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规条例、工程技术、管理体制、学科合作、观念转变和相关利益者平衡等诸多方面。从建设目标来讲,应该兼顾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四大目标的实现[53]。因此,在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及实践过程中,仍须鉴别发达国家城市雨洪管理中的可取之处,加强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研究,才能真正实现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

图7 林布鲁克地产WSUD示范项目2000年景观效果[24]

图8 林布鲁克地产WSUD示范项目2017年景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