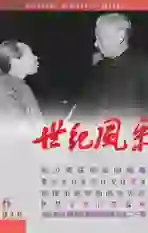父亲的画与儿子的路
2019-09-10姚江婴
姚江婴
“不合时宜”者的辉光
1923年,归国后的瞿秋白婉言谢绝了胡适介绍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做学问的好意,选择赴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等职,同时负责党的宣传與理论工作,任《新青年》主编等。由此,瞿秋白脱离了研究文学、当个教员的人生初设,踏上了职业革命家这条异常险峻的人生道路。
同年夏秋之交,瞿秋白抽空再次到济南探望父亲。
和这次会面差不多时候,父亲瞿世玮已从王璞生家搬出,带着儿子阿壵住进了历山街的道教团体悟善社的公房里,不久经由一位久别的老乡推荐,被聘为“私立山东美术学校”的山水画教师。
瞿世玮的山水画教学既严守传统,又富有逸情妙趣。他对待学生和蔼可亲,演示技法认真实在,论及幽玄深奥的画理哲思则侃侃而谈,故不时有学生到他的栖身处请教。此后近十年,瞿世玮一直与该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正逢军阀张宗昌督鲁时期,校无定所,学校生源也少,瞿世玮长期有职无薪,还得靠另外鬻画为生。尽管生活困窘清苦,瞿世玮仍然潜心画艺,心无旁骛。他对艺术的痴迷和执着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他曾教授过的学生,像王凤年、胡纯浦、韩少婴、李半残、吴炯等以后都成为知名画家。
据王凤年于1982年的回忆,瞿世玮在当时是很有名的画家。可以与之相印证的是,瞿世玮的丹青功力得到了当时上海画坛重要人物郑午昌(郑昶,时任上海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的认可,被收入其主编的《中国画学全史》。《中国画学全史》是中国人自行编著的第一部中国绘画通史,由中华书局1929年5月出版,吴昌硕为之题签,蔡元培赞誉该书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此书在论及画家时按逝者留传时贤留名的史书规矩,以收入瞿世玮的条目结束全书:“瞿圆初,武进,山水。”寥寥数字,见证了瞿世玮这位儿子眼中的“不合时宜”者于苍茫乱世亦曾绽放的辉光。
瞿世玮在历山街悟善社住了大约两三年时间,后来悟善社解散,他只得在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的正宗坛寻了一处房子住下。在瞿世玮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他被延请到学生王凤年家中做家教。王凤年幼时失聪,1927至1928年在学校读书时与瞿世玮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瞿世玮对他格外怜惜,每每不厌其烦地画给他看。王凤年家境比较殷实,除每月支付学费外,逢年过节倍之。如遇瞿世玮生病不能来上课,王父必让王凤年携礼品前往探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瞿世玮身体很差,50多岁的人像60岁开外: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蓄山羊胡,常戴一顶瓜皮小帽,着长袍,拄一根杖。在王凤年的记忆中,瞿世玮无论画画、做事都很有精行俭德的古风。瞿世玮痔疾甚重,常带病授课,但行笔落墨从不苟且;课堂画剩的色墨、裁下的纸边,瞿世玮都会妥善收好待用。人老了总会特别想孩子,但为了不给他人添麻烦,瞿世玮从不曾与人谈及长子,亦十几年不与人照相。仅有一次,瞿世玮应是苦闷至极,对王父透露了他与被通缉的共产党要犯瞿秋白的父子关系。王凤年曾珍藏瞿世玮28张一尺大小的画作,原是教学示范时画下的,但课后瞿世玮将每张都细心收拾完整并题款、钤印。1963年,王凤年将这28张画连同瞿世玮的另两幅作品一并交由常州市博物馆转交常州市瞿秋白纪念馆。
1932年6月19日,瞿世玮在正宗坛的一间平房病逝,终年仅57岁。他的学生吴炯和儿子阿壵在其同乡的帮助救济下,将其遗体安葬于济南南郊千佛山西麓与马鞍山东麓间的江苏第二公墓。
时空变换流转,转眼到了2015年。年初,著名学者王观泉老先生终于发现了一册瞿世玮的著作影印件——《山水入门秘诀问答》(以下简称《秘诀》)。《秘诀》的发现,为世人提供了从一个特别却重要的向度接近瞿世玮乃至瞿秋白的契机。《秘诀》是一册线装书,棉白纸、计38面(有内容的),封面封底皆为土灰色,素朴雅致。封面及全书文字系瞿世玮手书的小楷,文中尚有示范图例十多处,皆由瞿世玮亲绘。册尾版权页,印有“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初版,山水入门秘诀问答,每册定价大洋五角,编绘者武进瞿圆初,发行者爱美中学出版部,印刷者成章印刷公司,代售处济南东关爱美路口珊垣新书店”字样。
《秘诀》其实是瞿世玮在山东教画时出版的课徒教案。瞿世玮信奉道教,《秘诀》却透露出他道、儒、释、医兼收并蓄的哲理底盘之一隅。如卷首即言“画禅”,又如他强调虚则灵的道家思想:“画不过是一种最足表见人格上学养性灵之艺术。所谓物者,太虚之一点,原有之虚灵保护此灵,纯乎在学养,学然后知不足。心虚自然理明,明有能力建白于人类中,以维持人心者为德。克明峻德,皆自己从心根上发明出理路之原则来。其原则人人本来具足的,所以不克明白者,未能虚心耳。虚则未有不灵……”又说:“人,不过不与万物同其价值。若云躯壳,仅是一种倮虫,所不同者,灵耳。所克保持此灵,不与草木同朽者,惟心根耳……孟子日仁义礼智根于心,有诸内必行诸外,方可有取信于人之物。”
赴俄前意气风发的瞿秋白曾叹息父亲“不合时宜”,通过《秘诀》,世人却可一睹瞿世玮思想境界之新锐辽阔。试读:“天既与我以性灵,我又何必崇拜中外古人,呆呆的守旧时之派别而不自维新乎?胸中无一定成见束缚我性灵……乃知科学原可与哲理吻合,万事万物皆有个开始,何不由我改弦更张,一革旧日之习惯,专从真理上求根本解决耶?吾愿同志以后须知,华虽旧邦,其命令发现于今日之潮流者,莫不以维新为新民之主旨也。”
《秘诀》卷首注明“第一集”,卷末有“容后演来”,可叹从第一集出版(1931年10月)和瞿世玮病逝的时间上看,存在《秘诀》更多集的可能性不大。从《秘诀》还可知瞿世玮之前已出版过三集画册,宜与《秘诀》一起配合使用、欣赏。惜三集画册现已难觅踪迹,但《秘诀》中诸多平易透脱的妙语“真言”,以及山石、松柏桐椿等范图,用笔苍劲虚灵,气韵风神潇洒,已令识者一品再品、叹惋莫名!
未完成的追想和思忆
1923年父子相会别后,从此再未见面。据杨之华1962年给王凤年的复信可知:“秋白生前,开始还与其父保持联系,经常寄钱供养,后因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才被迫断绝联系,以致不知乃父之所终。”
据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回忆:1927年在武汉时,“我知道他学画于他的父亲,学金石于他的六伯父,殊不知他反感地说‘我父亲画是好的,但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价值”。而就在这一年,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的艰难时刻,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引领中国革命实现转折。这次会议后瞿秋白开始全面主持党的工作,成为党的领袖。
在浓重白色恐怖面前,党内普遍存在着急躁情绪。1927年11月起,“左”倾错误一度在全党占据支配地位,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负有直接责任。但在实际斗争进程中,瞿秋白很快认识并即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928年6月至7月,瞿秋白在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随后,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此后两年,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期间,在接手处理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一案时,因为秉公直接与米夫、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作斗争,招致他们的怨恨。
以后,随着米夫、王明等人逐渐得势,在极“左”的氛围中,瞿秋白的政治生涯发生恶性骤变。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瞿秋白再次遭受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从此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核心。
面对党内宗派集团的一连串压倒性迫害,瞿秋白选择顾全大局。会后,瞿秋白告假留在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养病,却并没有萎顿止步,而是试图在自己一直心仪却已离开了十年的文艺家园开辟出新的道路:撰写杂文和文艺理论、翻译苏俄作家的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依然是前所未有的艰辛劳作,且曲高和寡,周遭几乎找不到可以深层交流的人,直到他与鲁迅相遇相知。两位知己携手并肩,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世人皆知鲁迅曾将清人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赠与瞿秋白。殊不知在这之前的两三个月,即1932年12月7日,第一次在鲁迅家避难,感动于鲁迅的临危不避、雪中送炭的瞿秋白曾书录了自己的一首七绝旧作《雪意》赠予鲁迅先生:“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并加上了一段跋文:“此中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阡悔的贵族心情也。”
笺纸自古便是文房清玩,是文人雅士用于诗文唱和、书信往来的一种小幅纸张,一般以木刻水印技术将各色图案印于其上。《雪意》诗并跋并非书于一张素笺上,而是很别致地选用了一张印有陈师曾山水小品画作的笺纸。
画作绘有两株松树,一株略微粗壮,翠少枯浓,另一株稍清润丰茂一些。双松枝叶相接,有应答相携之意,却又各呈孤傲和清奇之态。画面下部近底端简笔绘有一人,着长袍,策杖,似在回首仰望高松。留白是中国山水画重要的技法,此幅双松山水小品虽并非特意表现雪景,因留有大片空白,与《雪意》诗境对照相映,也就给人以一派寒荒、清旷的雪境之感。画面右侧上部有题款。因被瞿秋白的浓墨书迹遮盖,经笔者辨识,确认题录诗句为出自唐杜甫《东屯北崦》的“步壑风吹面,看松露滴身”,落款“师曾”,钤“陈朽”朱文椭圆形印。
陈师曾,名衡恪,著名诗人陈三立(陈散原)之子,史学家陈寅恪之兄。在清末民初的画坛上,家学渊源深厚且学贯中西的陈师曾地位独特。周作人曾评: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1923年,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梁启超慨叹为中国文化界的大地震。
陈师曾还是鲁迅早年间最要好的画家朋友,关系极为亲密熟腻。陈师曾病逝后,故宫博物院编印《师曾遗墨》10辑,陆续出版时间长达两年,鲁迅逐期购买,直至购齐。
笔者将《雪意》诗笺上陈师曾的松树、人物与瞿世瑋《秘诀》中的松树、点景人物对比,发现诸多相通契合之处。陈师曾小品中的双松造型奇崛清峻,无烘染敷色,纯以松灵的逸笔草草写就,瞿世玮《秘诀》中松树的线条相对要收束、工整些,但细察松叶的画法,仍如出一辙;而二者中的人物,则都一样着长袍、策杖,形简神备。
据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介绍,瞿秋白的书法初学唐代书家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后来,受亲戚名书家庄蕴宽的影响,又临习了北魏的《龙门十二品》和南魏的《爨龙颜》等碑。所以“他的字一直保留着魏意”。笔者对比《秘诀》与《雪意》手迹中的书法,虽然父亲写的是正楷,儿子写的为行书,却都有着相似的端凝、内敛的气息。若再仔细揣摩,可以发现父子俩的书法都具有结体较紧密、线条凝厚、书卷气与金石味兼备等特点。
可以想见,当自小师承父亲,对松树、点景人物都很熟也画惯了的瞿秋白遭遇这张以双松为主体、配以策杖高士、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典型文人画笺纸时,怎会不念及经年音讯阻隔,也到了要拄杖年纪的老父亲?可叹瞿秋白其时并不知父亲已于半年前故去,但冥冥之中是否亦会有某种悲凉感应?当瞿秋白最终在此画笺上恭敬书写《雪意》诗并跋向鲁迅倾诉自己言语难及的意绪时,又何尝不是在笔墨深处经历一次与父亲的相会?
初次赴俄前瞿秋白曾觉得要追想父亲的种种缘故,“真太复杂”了。而此时的瞿秋白已过而立之年,对于父亲当初的失措、无告和踯躅、彷徨已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体谅:原来父亲亦有他难舍难离的旧时来路,亦有他的一份干净和担当,纵然“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总仿佛“不合时宜”。特别是在母亲撒手人寰后,父亲把情况最差的三弟阿垚一直带在自己身边,并且始终于山水画艺上执着精进,可怜风烛残年仍栖身寒坛道观……恰仿佛画笺中的策杖行吟者,于空无依傍的雪境中,在没有路的大地上,初心在怀,仰望高标,踽踽独行……原来自己和父亲都一样,都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地跋涉“在路上”。
1934年初,瞿秋白奉命前往苏区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等职。在继续遭受“左”倾错误打击的逆境中,仍对苏区教育和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用鲁迅的话鼓励大家:“路,是走出来的!”同年10月某天,已收拾好行装的瞿秋白得知自己未能获准随中央红军长征后,当晚喝了很多酒,对战友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之后,被留在苏区的瞿秋白不顾病重咳血,加班编发、出版《红色中华》,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发挥作用。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刚被俘时,因为从小跟着父亲一知半解学了点医道,加之久病成医,瞿秋白谎称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被红军俘虏后在总卫生部当医生、医助等。待到身份暴露,瞿秋白于长汀狱中写下了4000余字的“供词”,赞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驳斥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污蔑,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后,曾听过瞿秋白演讲、很仰慕他学问的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施展怀柔手段,来自军统、中统的各色智囊骨干、劝降专员也轮番上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瞿秋白始终不卑不亢地应对周旋,并凛然拒绝了所有违背自己人格高标、触及变节投降底线的变通之策。他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在狱中,瞿秋白要来唐诗宋词品读,又写了不少旧体诗词张贴在墙上欣赏,并应看守官兵的索请书录诗作、篆刻印章,活脱脱一副自己曾努力摒弃的“太没价值”的文人模样,更留下了一篇《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的《何必说?(代序)》中说,是因为“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于是“在绝灭的前夜”,瞿秋白又一次分析自己的一生,将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呈现给“识我者”。
在《多余的话》总体黯淡晦涩的语境中,瞿秋白异常清晰地表示:“我的思想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此时,虽然个人道路的终点已现,他回望这世界的眼眸依然如少年般清澈:“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
除了“供词”和近2万字的《多余的话》,瞿秋白还想再写两本书:《读者言》和《痕迹》。可惜未及撰写,只留下了一份《未成稿目录》,里面有一章的标题就拟为“父亲的画”。如此,一路跋涉,人生又一次行到山穷水尽之境的瞿秋白最后一次在灵魂深处回望自己最初的家园。在那里,有慈母的抚育怜爱,有江南风物、青山秀水……在那里,他终于可以和亲爱的父亲一起吟诗作画、踏月而归,也是时候好好欣赏一下父亲的山水近作了,至于父亲的画对于社会到底有没有价值,又或是个人的性灵自觉与时代担当以及中国社会新生路的问题,父子俩可以再好好同榻畅谈。
1935年6月18日,早晨8时,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伏案挥毫书写刚刚集唐人绝句凑成的一首山水诗《偶成》:“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瞿秋白镇静地把诗写完,并附跋語: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9时20分左右,瞿秋白走出囚室,向站在堂屋里的宋希濂及以下一干人等看了一下,步出师部大门。在中山公园凉亭前,他整理了一下衣履,然后背手昂然面对相机镜头,神情恬淡雍容。据一位临场记者的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日:‘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餐毕,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慢步走向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沿途用纯熟的俄语唱自己翻译歌词的《国际歌》,并唱《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
到达罗汉岭下,瞿秋白走到草坪中,对执行者说了一声:此地甚好。然后盘膝坐下,微笑饮弹。在这最后的时刻,36岁的他是“悲欣交集”的行吟者,亦是“我心光明”的猛士;他没有一丝的胆怯和犹疑,他不过是怀抱初心、逍遥归去,以一种不负平生美学修养的超迈气概。
白云低徊缱绻,青山起伏若泣。罗汉岭下,血染芳草,连天凝碧,《国际歌》雄浑的旋律久久回荡……
令人怦然再恸的是,一路艰苦跋涉,人生同样“未尽才”和“未完成”的父子俩离世竟也是同月。父亲6月19日,儿子6月18日,父子俩的忌日仅相差一天。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