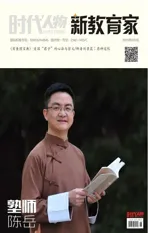数理与人文
2019-08-02丘成桐
文_丘成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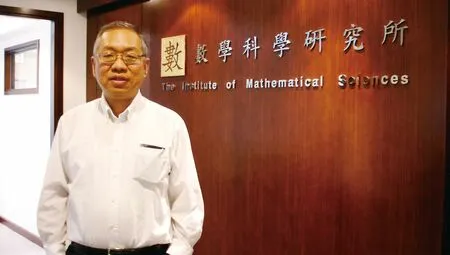
丘成桐:当代数学大师,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等,是几何分析学科的奠基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本概念,对微分几何和数学物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现在学科这么多又复杂,有人能做到吗?
学者在构造一门新学问或引导一门学问走向新方向时,他们的原创力从何而来?我认为除了踏实的基础,还源于丰富的感情。孟子説: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太史公说:意有所郁结也。能够影响古今传世文章的气必至柔至远,至大至刚。至于数理方面,也讲究相似的文气。
自希腊的科学家到现代的大科学家,文笔泰半优美雅洁。他们并没有刻意为文,然而文既载道,自然可观。数理之与人文,实有错综交流的共通点,互为学习。
科学的基础
古希腊人和战国名家,雅好辩论,寻根究底。在西方,产生公理的研究,影响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公理到牛顿的三大定律,到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莫不与公理的思维有关。
无论西方或是中国,科学的革命都以深刻的哲学思想为背景。希腊哲学崇尚自然,为近代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发展打好基础。中国人偏重人文,在科学主要的贡献在应用科学。但中国人提出五行学说,希腊人也企图用五种基本元素解释自然现象。中国人提出阴阳的观点,西方人也讲究对偶。希腊数学家研究的射影几何已有极点和极线观念。文艺复兴的画家则研究投影几何,对偶的观念,从那时已经开始。
文艺复兴的科学家理文并重,他们也将科学应用到绘画和音乐。从笛卡儿、伽利略、牛顿到莱布尼茨,这些大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都讲究哲学思想,以此探索大自然的基本原理。以后伟大的数学家高斯、黎曼、希尔伯特等都寻求数学和物理的哲学思想。黎曼创造黎曼几何,就从哲学和物理的观点探讨空间的基本结构。至于爱因斯坦在创造广义相对论时,除了用到黎曼几何的观念,更大量采用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想法。
每个国家、每个地方甚至每个大学的科学技术,虽然都由同样的科学基础推导而来,结果却往往迥异。除了制度和经费投入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地方的科学家对自然界有不同感受,而且受家庭社会背景和宗教习俗影响。他们学习的诗词歌赋、文学历史也与科技成就有密切关系。
比如,在中国成长的数学家,就受地域和导师的影响很大,不少中国数学家喜欢读几何,大概受到陈省身先生的影响,其次是读解析数论,则受到华罗庚先生的影响。印度的学者,则受Srinivasa Ramanujan和Harish Chandra的影响,喜欢数论和群表示论。日本近代数学的几位奠基者,家里都是精通兰学的学者,对荷兰文有很好的认识,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数学观念。
我遇见很多大科学家,尤其是有原创性的科学家,对文艺都有涉猎。他们文笔流畅,甚至可以媲美文学家的作品。文艺除了能陶冶性情,其创作与科学创作的方法也有共通的地方。
科学和人文的共同点
科学家与文学家有很多能产生共鸣的地方。除了共同感情,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比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作《洞仙歌》。七岁时,苏轼在眉山遇见一朱姓老尼。老尼说,一日,天气炎热,蜀主和妃子花蕊夫人深夜纳凉于摩诃池上,孟昶作了一首词。老尼还记得,并告诉了苏轼。四十年后,苏轼只记得词中头两句,有天得暇寻找词曲,猜测应为洞仙歌令。循着前两句的做意,猜测蜀主的想法,将这首词续完。
不同的文人对着残缺的词句,一定会有不同的反应。假如是清代乾嘉学者,可能花很多时间做考据,得出结论:这词不可考。因此不会续。有一些文人,可能没能力猜到词牌名,当然也不会续。另有一些文人,可能像苏轼一样,猜到词牌名,却没兴趣续。还有一些文人,虽然找到词牌名,但文艺功力太差,续的可能没趣味。苏轼却兴致勃勃地花了时间去推敲猜测,写了一篇传世杰作。
科研创作,有类似情形。上述四个不同的描述正好反映了清初到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深爱文学,才会在四十年后还记得七岁学过的词的前两句,纵然这是绝妙好句,有多少人过了一两年还记得?从这里也可看到学者的感情所在。
现在来看科学的发展。牛顿引力场论和狭义相对论,都与引力有关,同时都基本正确,却互相矛盾。爱因斯坦对此很感兴趣,在数学家闵科夫斯基、高斯、黎曼和希尔伯特的帮忙下,完成了广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创意和能力当然远胜苏轼补《洞仙词》,但却有点相似。我来做一个不大合适的比拟,苏轼记得蜀主的两句词,一句可比拟为牛顿力学,另一句可比拟为狭义相对论的洛伦兹转换。爱氏花了十年功夫来研究引力场,就是从这两件事出发,用他深入的物理洞察力和数学家提出的数学结构,完成了广义相对论。这有点像苏轼在续词时,对四川有深入了解,又能体会孟昶和花蕊夫人在摩诃池水晶殿的情形,心有所感,才能以高明的手法续完这首词。
但这有一个重要分别,假如爱丁顿在1919年没有用望远镜观察证明广义相对论,则无论爱因斯坦的理论多漂亮,仍然不是一个重要工作。物理学需要实验,数学需要证明,文学却不需要这么严格,但是离现象界太远的文学,终究不是上乘的文学。
曹雪芹并没有完成《红楼梦》,这可是千古憾事,我们如何续完呢? 除了出色的文学技巧,还需了解该书的内容和背景。
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借用自身经历描述封建大家族无可避免的腐败和堕落,也描述了当年家族的荣华富贵。他与评书人脂砚斋,一路著书,一路触目愁肠断。整本书可以说是以血书成,他也说:十年辛苦非寻常。书中的笔墨,充满澎湃的感情,但却是有条有理的创造和叙述。在差不多完成时,他却因伤感去世,“芹为泪尽而逝”。至今还没有人能完满续成,对曹雪芹当年的想法如何处理,还是争论不已的大问题。
曹雪芹和他家族的经历当然多姿多彩,但他不可能将真事尽数写下。毕竟事情有先后轻重之分,又为了将真事隐去,他不可能不创造一些情节、诗词和交谈内容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图画,他用了种种不同手法,将旧社会与大家庭的腐败和个人经历用富有感情的文笔表现出来。曹雪芹以后,很多学者想学他的写法,效果却相差甚远,除了文艺水平不如曹雪芹,他们写书时感情的浓郁和曹雪芹的内心世界也是无可比拟的。
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有如一个大型的数学或科学创作。数学家和科学家,也是企图构造一个架构,来描述见到的数学真理或大自然现象。在这个大型结构里,有很多已知的现象或定理。在这些表面没有明显联系的现象里,我们要企图找到它们的关系。当然还需证明这些关系的真实性,也需知道这些关系引起的效果。
但如何找到这些联系的方法,因作家而异。在小说的创作里,小说家的能力和经历,会表现在这些地方。一个好的科学家,都会创造自己的观点,来观察我们研究的大结构,例如韦伊要用代数几何的方法来研究数论的问题,而朗兰兹要用自守型表示理论来研究数论。他们在建立现代数论的大结构时,就用了不同的手法来联系数论中不同的重要部分,得到数论中很多重要的结论,值得惊讶的是:他们得到的结论往往一样,殊途同归。
科学发现的原动力
历史上无数有意义的现象抽象总结成定律时,中间的过程总是富有情感。在解决大问题的关键时刻,科学家的主观感情有重要作用,这是科学发现的原动力。面对震撼心弦的真理时,好的科学家会不顾一切,不惜冒生命的危险,挑战传统的理论,甚至得罪权贵。比如伽利略对教会的挑战。
当科学家发现他们推导出来的定律如此简洁普遍,如此有力地解释各种现象时,他们不能不赞叹自然结构的美妙,也为这个定律的完成而满意。这个过程值得一个科学家投入毕生的精力。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犹未悔。
文学艺术也一样,《红楼梦》《莎士比亚》《诗经》《楚辞》的感情,跨越时空,普罗大众都能感受到。好的艺术必须能够表现作者的感情。曹雪芹写《红楼梦》,笔尖带着他毕生的感情,后世学《红楼梦》的作者不知多少,但都缺乏深入的感情,所以都没学好。
由于艺术家的经验是在他们存身的社会吸取得来的,也是在观察普罗大众得到的,他们的著作反映的感情也往往代表着当时社会大众的感情,这一点和科学观察有类似地方。
用一个主要的思想来建造大型科学结构跟文艺创作也很相似,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以情悟道,以四大家族的衰败来拱托这个感情。
二十世纪代数几何和算术几何的发展就是一个宏伟的结构,比《红楼梦》的写作,更瑰丽结实,但这是由数十名大数学家共同完成的。在整个数学洪流中,我们见到大数学家各展所能,发展不同的技巧,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要左右整个大流方向的数学家,实在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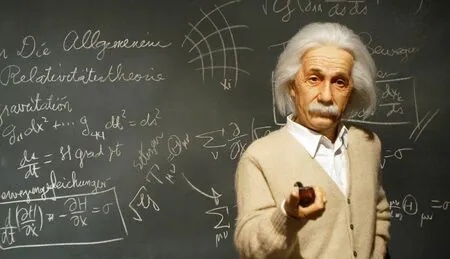
爱因斯坦花了十年功夫来研究引力场,用他深入的物理洞察力和数学家提出的数学结构,完成了广义相对论

曹雪芹写《红楼梦》,笔尖带着他毕生的感情,后世学《红楼梦》的作者不知多少,但都缺乏深入的感情,所以都没学好
我们需要培养一些能望尽天涯路,又能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学者,这需要浓郁的文化和感情的背景才能产生。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到中西数学的不同。直到如今,除了少数两三个大师外,中国数学家走的研究道路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在创新的路上,提不起勇气,不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我想这与中国近几十年来,文艺教育不充足,对数理感情的培养不够有关。
优良科学家需要人文训练
好的数学家最好有人文训练,从变化多姿的人生和大自然得到的灵感将我们的科学和数学完美化,而不是禁锢自己的脚步和眼光,只跟着前人的著作,作小量的改进,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大学者。
中国数学家,太注重应用,不在乎数学严格的推导,更不在乎数学的完美化,到了明清,中国数学家实在无法跟文艺复兴的数学家比拟。
有清一代,数学更是不行,没有原创性。可能是受到乾嘉考证的影响,大多好的数学家跑去考证《九章算术》和唐宋的数学著作。和同时代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英国、德法的学者不断尝试的态度迥异。找寻原创性的数学思想,影响了牛顿力学。因此产生了多次工业革命。
到今天,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还是比不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准,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人文修养还是不够,对自然界的真和美感情不够丰富。而这对科学家和文学家来说,其实是共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和深度的民族。文学家、诗人、小说家的作品,比诸全世界,都不遑多让。
但我们的科学家对人文的修养却不大注意,语文和历史用了一些浅显没深度的通识教育来代替,这是在舍本逐末。不熟习历史的国民,必定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一代。他们看不清现在发生事情的前因后果。史为明镜,不单指出古代伟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祖先留下来的感情传给我们,我们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创下的丰功伟绩骄傲,中国五千年丰富的文化使我们充满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祖先留下的遗产?
或许有人说,我不想做大科学家,所以不用走这条路。其实这事并没有矛盾。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学习任何学问都会轻而易举。至于数学和语文并重,先进国家也一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数理人文和博雅教育有莫大关系。中国的教育始终离不开科举的阴影,以考试取士,系统化的出题目,学生对学问的兴趣,集中在解题上,科研的精神仍是学徒制,很难看到寻找真理的乐趣。西方博雅教育的精神确实能增广我们的视野,激励我们的感情,更能培养大学问的成长。多读多看课本以外的书,对我们做学问,做人处世都会有大帮助。
好的文学诗词,发自作者内心,生生不息。将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感受表现出来。激情处,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而至于万古长存。伟大的科学家不也是同样的要找到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吗?(本文来自丘成桐教授2014年11月在中山大学的演讲,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