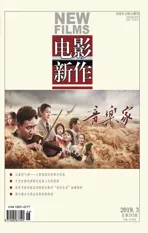徐峥喜剧电影与现实主义的碰撞、疏离与回归
2019-07-31陈乃嘉
陈乃嘉
作为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电影艺术词典》对喜剧片的定义为:“以产生结果是笑的效果为特征的故事片。在总体上有完整的喜剧性构思,创造出喜剧性的人物和背景。其主要艺术手段是发掘生活中的可笑现象,作夸张的处理,达到真实和夸张的统一。其目的是通过笑来颂扬美好、进步的事物或理想,讽刺或嘲笑落后现象,在笑声中娱乐和教育观众。”
由此可见,喜剧电影的主要特征是幽默、诙谐,艺术手段是对现实生活进行夸张处理,从而达到对真善美的歌颂、对假恶丑的批判。因此,从喜剧电影的定义中便可窥视出,喜剧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与现实主义产生了普遍联系,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彰扬现实主义精神。
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一波三折,风格多变。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喜剧电影从喜剧中脱胎而出,经过笑闹和滑稽手段的建构,完成了对中国电影的最原始形态的塑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体制进入全面改革,电影完全被推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喜剧电影在长期的压抑后得到了集体反弹,“性格喜剧+批判现实”“荒诞+无厘头”等风格多样的喜剧片成为市场的宠儿。时至今日,尽管受到好莱坞大片、印度电影的冲击,喜剧电影在国产商业电影市场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所取得的票房神话、获得的高度关注不得不让我们关注喜剧电影创作的手段,探讨其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内因。
徐峥进入喜剧片创作的时机,正值批判与讽刺类喜剧电影发展动力不足,同时好莱坞大片大量占据内地市场的时期。进入喜剧片创作伊始,徐峥的动机单纯—能和好莱坞大片对抗的只有喜剧片。“对抗”的意义首先是存活,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喜剧能够在好莱坞大片中突围。2010年,他主演的《人在囧途》在众多国外大片的夹击下,“囧”出了一片血路,刚上映的首周票房就破了千万。2012年,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刷新华语片首周票房纪录,最终票房为12.69亿。2015年,自导自演的电影《港囧》票房突破16亿。2018年,监制并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票房高达30亿。从商业角度看,徐峥的喜剧电影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商业电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它在被消费的同时产生一批接受这类电影的观众,观众的审美需求以及社会观念的不断变化又直接转化为创作者的原动力,因此,我们便会发现,《人在囧途》《泰囧》《港囧》《我不是药神》几部扛鼎之作在具备共同特征之余的差异性。四部作品看似从喜剧类型片走了一个轮回,然而,此“喜剧”已非彼“喜剧”,徐峥的喜剧电影创作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如《南方周末》在2018年7月19日登出的《专访徐峥:大众对中国故事是饥渴的》中所说:“暌违三年,徐峥变了”。笔者认为,所谓的差异,所谓的“变”,可归纳为现实主义与其作品的碰撞、疏离与回归。
一、喜剧电影与现实主义的碰撞
关于《人在囧途》的创作,徐峥曾多次表述过他的观点,他认为:“在所有喜剧片中,有一种是带有一定人文关照的,它不是闹剧,而是带有一定主题的”①。作为主创团队之一,“囧系列”第一部作品《人在囧途》便是带着这种思考和观众见面的。
《人在囧途》属于典型的公路喜剧类型,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人物类型,都未逃出《午夜狂奔》《飞机、火车和汽车》等好莱坞公路喜剧片类型范式的窠臼,其属性特征明显。从主人公现实困境的呈现,到归途过程的对立与和好,再到“奥德赛式”②的心灵回归,《人在囧途》继承了好莱坞三段式的经典叙事模式,李成功、牛耿这两个反差极大的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在相同的境遇下产生了错位式的喜感。值得注意的是,《人在囧途》所选取的“归途之路”以浩浩荡荡的春运为背景,承载着厚重的传统观念和中国情结,将事关无数个家庭、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热点问题搬上银幕,强烈的代入感直指观众心灵,必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共鸣。这样一个老套的故事能够赢得票房与口碑的双重成功,平民化、生活化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功不可没。
典型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从典型环境看,《人在囧途》将旅途建构在“人类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的春运上,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无论身在何处,外出的游子都要回家,与父母亲人团聚,春运大军也由此而来。这样一个全民性、普遍性又意义非常的时间节点,为片中人物的行动营造出了内、外两个典型环境,即回家过年的内部紧迫感及“春运”艰难的外部困境。作为外部环境,影片的提炼颇为经典:水泄不通的火车站候车大厅,大排长龙的机场安检口,人流如潮的长途汽车站,只有一张床的小旅馆“标准间”,从整体环境到细节展示,既有纪实感,又有典型性。内部环境则更为典型,农民工牛耿必须在除夕之前完成“讨薪”的任务,年根成为“年关”;而作为精英阶层的李成功,在回家团聚之余,面对的是情人逼迫与妻子离婚的任务。春运这一典型环境的设置,让每个人的归途都充满“必须”完成的紧迫感与现实性,将春节归途作为人物的情境依托,对人物的心理成长及性格塑造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典型环境的扎实建构是为公路喜剧的“旅途”做了本土化拓展,那么李成功与牛耿的人物设定则是基于典型形象思考下的喜剧性格塑造。《人在囧途》的人物设置遵循着类型技巧:美与丑、高与矮、精明与呆笨,精英与草根,人物的阶层及性格属性反差极大,这种对比设置并非简单的类型符号化,而是通过对比挖掘其生存现状的本质原因,揭示某一阶层普遍的生存困境。如果说徐峥在塑造李成功时,为了还原商界精英的沉稳内敛而在表演上有所收敛,那么王宝强饰演的牛耿则具备了新时期新农民的新特征,隐藏在憨厚朴实背后的,是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社会认同的渴望。在“想回家”的单纯动机下,两人总是不期而遇,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和动作,一系列囧事顺其自然地展开,成为偶然中的必然。两个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让喜剧人物的社会属性更加明确,也让其获得了更多的价值认同和普遍性意义,从而引发观者深刻的价值思考和道德评判。《人在囧途》的成功与其说是公路喜剧的成功,不如说是“类型片+现实主义”智慧的成功。
对此,徐峥坦言:“有一个小小的总结:《人在囧途》无疑是类型明确的喜剧片,加上公路片元素,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人物都是当下的”。③可以看出,徐峥当时认定的好作品成功的元素有三个:公路喜剧+当下人物+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喜剧元素的意外碰撞成功地使这部影片贴上了现实主义标签,成为一部思想深刻、关照现实、时代意义凸显的优秀作品。
二、艺术呈现中现实主义的疏离
从现实出发,从人物出发,一直是徐峥喜剧电影的创作思路。然而电影中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不仅在于题材的现实性,而且在于电影创作的艺术手段及表现形式如何实现了现实主义属性。无论是现实主义精神,还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段,任何一方面与电影的主题产生脱节,就不能称为一部成功的电影。艺术呈现中现实主义的疏离,直接导致《泰囧》《港囧》赢得了票房的成功,却在观众口碑上惨遭滑铁卢。
2015年,徐峥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道,“高票房并不是衡量一部电影成功的标志,其实《泰囧》在某些地方落入了一个俗套,因为喜剧的元素忽略了主题的深入。”④从《泰囧》开始,徐峥喜剧电影在高票房的背后形成了一个口碑缺口,观众在一场喜剧狂欢之后,内心的空虚感使他们不愿再为影片的口碑买单。在国内多家权威影评网站上,其评分和票房差距甚远。许多学者对《泰囧》和《港囧》高票房背后的“口碑囧态”作了分析,如马立新在《〈泰囧〉囧态批判》中指出:“最终的故事主题呈现出的碎裂与其叙事元素的选择安排有着密切关系。”⑤王赟姝在《喜剧的忧伤—评析〈港囧〉》中提到:“徐峥作为生长在内地、创作在内地、受众依然在内地的商业片导演,非常没有存在感地解读了《港囧》的‘港’。《港囧》的叙事、人物关系、人物形象、文化认同等方面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⑥
《泰囧》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充满异域风情的泰国,主要人物设置为在都市打拼的中年男人。不得不说,选择这样一个备受国人追捧的热门旅游国家作为典型环境,选择这样一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年危机男”作为典型人物,《泰囧》有望成为继《人在囧途》后又一部类型片与现实主义手段结合的佳作。然而,《泰囧》却出现了“叫座不叫好”的囧态。究其原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脱节恐怕要承担“主要责任”。马克思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非常明确,那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⑦,典型形象不能脱离典型环境而单独存在,典型形象与典型环境合而为一方能体现其典型性,人与环境也才能达到“影响和被影响”的有机统一关系,进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深入。在《泰囧》中,当徐朗与高博正欲为拿到商业授权书斗智斗勇,积极行动起来时,镜头一闪,场景却切换到旅游胜地泰国,泰拳、健康树这些浅层的人文环境与主人公的行为、心理格格不入,随之而来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在这种非必须的外部环境中显得刻意,不仅无法让观众感同身受,而且会产生疏远跳脱之感,很容易出戏。影片最后,尽管徐朗得以醒悟,选择“回归家庭”这一当下的幸福所在,但他为什么会退出,为什么会回归,影片并未进行明确的揭示,这就造成了主题呈现与过程展现之间的断裂,失衡的结构和仓促的情境架构使得观众对主人公的“回归”产生莫名的错愕,由此人物也变得不再真实可信,泰国这一典型环境的设定也只剩下商业价值,不再是为表现人物、塑造人物的独特的唯一的环境。
到了《港囧》,人物与环境、环境与情节、情节与主题的脱离更加明显,香港元素的硬性植入、大量无用桥段或镜头冲击甚至冲毁了主题的呈现。《港囧》所要表现的,是香港文化和主人公再也回不去的真挚情感之间的某种联系,可惜老式港片的情节与音乐堆砌不出来一个真实的香港情境,也无法代表真正的香港文化。首先,碎片化的影片场景和音乐与主人公完成的终极目标缺乏内部的必然联系,中年危机男置身于旧式香港的情境中,缺乏时代感。其次,人物所依托的情境构建单一,无法全方位地展示香港。在这部试图体现香港文化香港精神的《港囧》中,我们除了能看到模仿《古惑仔》《无间道》等港片场景的回字形楼、大哥追思堂、浴室等非典型性自然环境外,对香港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并没有具体真实的展示,缺失了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是非典型性,那么不要说香港文化香港精神,就连人物的行为逻辑、性格演变、心理流程都缺少了情景氛围的依托,种种情节、情感、情怀亦如无水之源,失去了呈现空间。

图1.电影《港囧》
回到最初《人在囧途》的成功,徐峥提出的“公路喜剧+当下人物+现实主义”的观点,不难发现,系列后两部疏离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喜剧仍然是喜剧,人物仍然是当下人物,但环境却不再是典型人物所生活的典型环境。缺少了对典型环境的精准营造与深刻挖掘,缺失对当下都市生活复杂性的探讨,也就失去了人物成长的土壤,影片的喜剧表达与主题呈现和观众审美之间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
令人欣慰的是,徐峥对自己的喜剧电影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深刻意识到现实主义运用和表达的重要性,从而在商业片中以现实主义手法再次获得成功。2018年7月,《南方周末》对徐峥进行专访,他表示,大众对中国故事是饥渴的,相对于《泰囧》和《港囧》,更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影片将是他接下来的方向。
徐峥看中的是故事本身的“蝴蝶效应”,在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同时,更多地能在观影过程中带给观众思想意识层面的启发。对于徐峥的创作来说,这不仅意味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更在于类型化模式的喜剧电影与现实主义题材及手段相融合的探索。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在对生活真实地表现之余,文艺作品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开拓和挖掘。马克思在评论雨果的《小拿破仑》时提出,他不应当把这场“事变”写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描绘成晴天霹雳;而应当说明法国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怎样的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能够扮演英雄的角色。”⑧
徐峥喜剧电影与现实主义的碰撞、疏离、回归,虽是个案,却让我们把目光又一次拉回到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上,“大众对中国故事是饥渴的”既是徐峥在暌违三年后喊出的口号,恐怕也是国产喜剧片需要直面的现实。徐峥喜剧电影从《人在囧途》开始与现实主义碰撞出火花,到《泰囧》《港囧》中现实主义精神与艺术表现手法的疏离,再到现阶段的现实主义的回归,充分说明现实主义之于喜剧电影乃至商业电影的重要性,只有直面现实,以镜头聚焦现实,借助现实主义手法体现现实主义精神,才能使影片在商业价值之余兼具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最大限度地得到观众认可,成为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片,为国产喜剧电影在商业语境下走出一条真正的突围发展之路。
【注释】
①徐峥.影视制作公开课:徐峥专访http://open.163.com/movie/2012/12/S/Q/M8IIIQJAD_M8IIMNFSQ.html.
②刘畑.奥德赛:精神进程的艺术[J].艺术评论2014(11):4.
③徐峥.影视制作公开课:徐峥专访http://open.163.com/movie/2012/12/S/Q/M8IIIQJAD_M8IIMNFSQ.html.
④杨澜.《杨澜访谈录 徐峥:人在囧途》https://www.iqiyi.com/w_19rtk7kiy1.html.
⑤马立新.泰囧囧态批判[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03):15.
⑥王赟姝.喜剧的忧伤—评析《港囧》[J].电影评介 2016(01):3.
⑦[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61.
⑧[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