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收入来源差异与旅游消费支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 015年数据的分析
2019-07-27张云亮冯珺
张云亮 冯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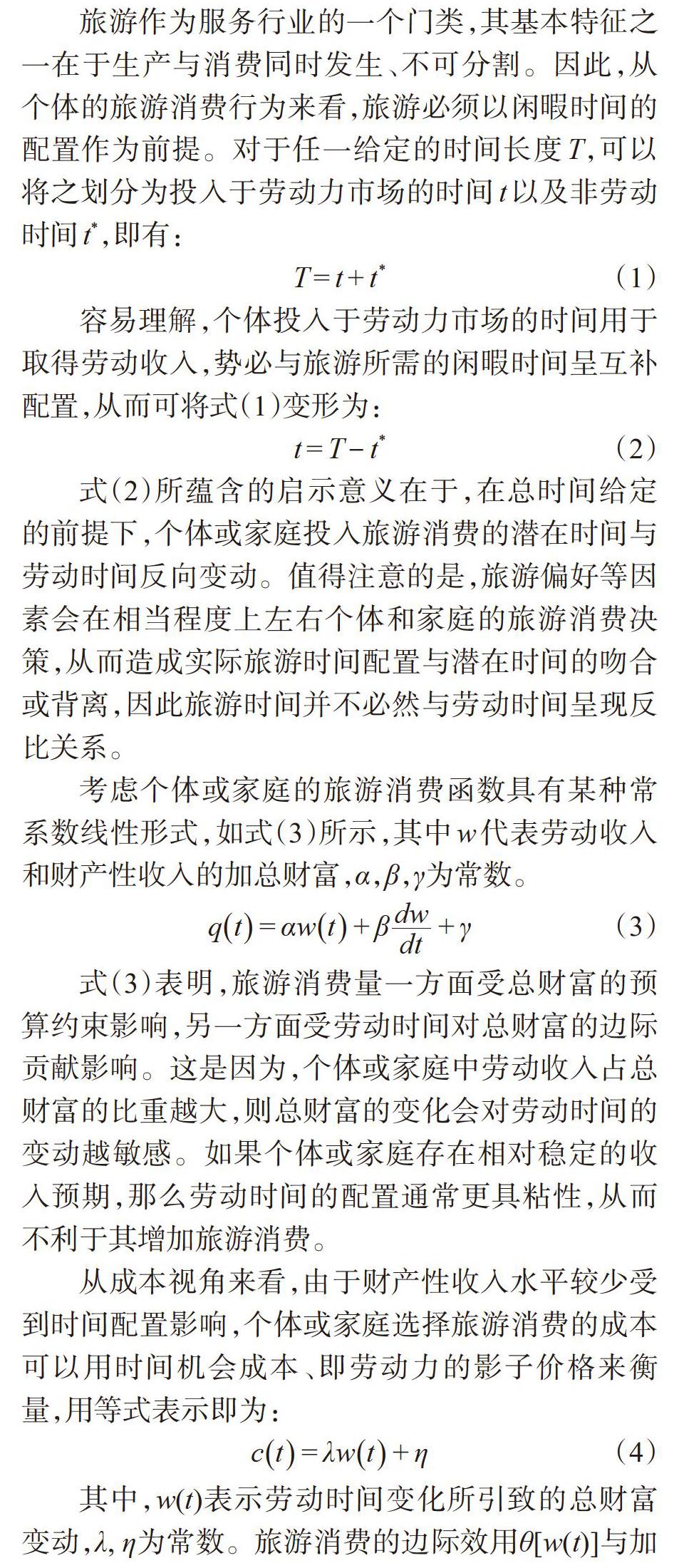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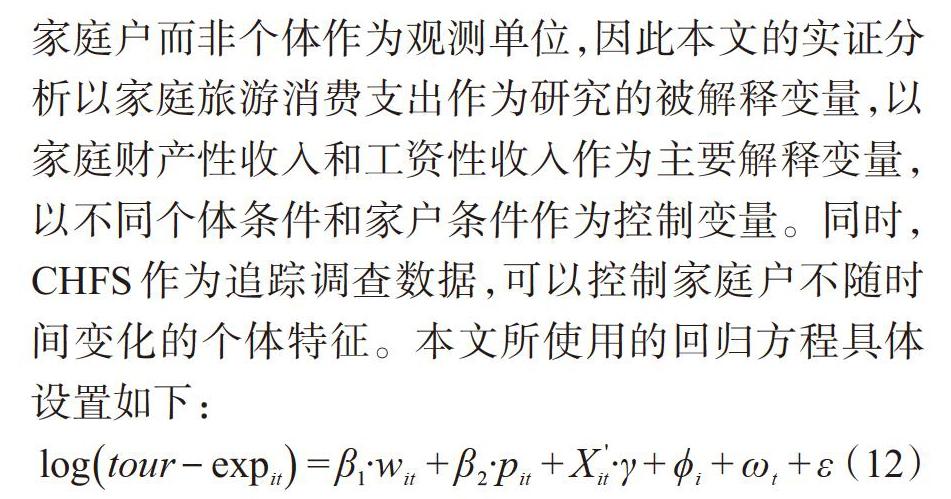
[摘要]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增加的背景下,旅游消费增长的趋势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引发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从居民家庭旅游消费的时间约束条件出发建立数理框架,并借助2011年、2013年、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3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收入结构因素。研究发现:首先,对全样本而言,不同类别的收入增长均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产生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其次,在利用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影响后,估计结果显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旅游消费的拉动效应大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最后,对非农户籍人口而言,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对农业户籍人口而言,税后补贴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兼职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影响显著,基本工资收入、金融类和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所引致的政策含义在于:一方面,就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侧而言,应创造条件让更多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或进一步提升其财产性收入比重,并着力增加农业户籍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以激发家庭潜在旅游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就旅游业发展的供给侧而言,着力建设更为友好的旅游休闲制度环境,有针对性地优化旅游产品及服务,以市场发育本身突破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性瓶颈。
[关键词]旅游消费;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5-0012-14
Doi: 10.19 765/j .cnki.1002-5006.2019.05.006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约9.5%,并于2010年跻身世界银行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标准下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①。经济飞速崛起所伴随的一个社会表征在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扩大。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和估算,21世纪初我国将近90%的成年人口均处于低收入群体或较低收入群体,而在2014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成年人口已经达到47.6%以上[1]。与这一变化趋势相伴,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正在成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2],使得居民收入结构趋于多元化。无需主动投入时间精力即可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引发社会关注,既部分地解释了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的原因,又是后者所引致的必然结果。从需求侧来看,收入总量增大和来源扩张导致我国家庭经济行为模式开始由生产型向生产和消费并行的模式转变,即食品等生存性消费占比开始下降,而教育等发展型消费和旅游等享受型消费占比不断上升[3]。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201 8年上半年旅游经济数据报告,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8.26亿人次,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为19.97亿人次和8.29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2.45万亿元,国际旅游收入达61 8亿美元①。数据表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旅游业消费结构、消费内容的升级已经成为培育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及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然而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繁荣,是否意味着旅游消费已经普惠地满足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仍须诉诸更加严肃和深入的讨论。
对于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引发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目前,旅游消费的研究对象大体可以作如下划分:(1)研究城市居民[4]或农村居民[5-6]的旅游消费;(2)研究特定身份群体(如大学生)的旅游消费[7];(3)研究特定地域的旅游消费[8]。纵观可知,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目前依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散化乃至碎片化的特征。尽管学者们通过使用来源相异的汇总数据或一手微观调查数据,尝试描绘影响旅游消费的不同侧面。但是,将具有收入来源异质性的研究对象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而更加细致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收入增长对于旅游消费的贡献尚属鲜见。
在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持续提升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本文尝试立足于家庭收入的结构视角,研究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于中国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不同影响,探索支撑我国居民旅游消费支出不断增长的切实原因所在。其研究意义不仅在有助于增强对旅游消费趋势和旅游经济整体发展形势的预判,而且能够更为准确地从收入贡献角度理解我国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从而为通过旅游产业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感、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对策参考。
1 文献回顾
研究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学视域内较为成熟的一类工作。在较早前的开创性研究中,学者即已注意到旅游和休闲服务的内容消费与实体产品的消费有所区别,前者受到收入和时间配置的双重约束,与消费主体的一系列个体和家庭因素密切相关,因而更为复杂[9]。此后,随着理论储备和研究工具的不断发展,学界从传统的收入因素出发,围绕此话题拓展出愈加丰富和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与维度。本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主要遵循两条文献脉络,针对收入和其他特征与旅游消费的关系所形成的理论解释,以及国内外影响旅游消费支出的经验证据。
收入是消费的唯一来源,人们的收入总是可以归结为当期消费和未来的消费,即储蓄。由于储蓄主要出于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动机,因此一般认为即期旅游消费受收入变动影響较大,而远期旅游消费对收入的变动不敏感[10]。仅仅通过短期和长期来理解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显得较为粗略,基于生命周期的储蓄一消费模型提供了更加完整和细致的分析框架。例如,在考虑了队列和进度效应的前提下,老年人的时间配置和社会成本显然更有利于旅游消费。但由于旅游消费支出对收入和流动资产的变化敏感,而对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其他类型资产价值的变化不敏感[11],因此老年人的旅游消费倾向反而较低,即年龄对旅游意愿有负面影响,而对旅游消费支出有积极影响[12]。在更加动态的视角下,代际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表明,进度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比队列效应更加有效地解释了旅游消费的群体差异,从长期来看,旅游消费主力群体的年龄中位数将是趋于上升的[13]。尽管生命周期假说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但也存在至少如下两个主要缺陷:一方面,永久收入增加引致终身旅游消费增加的推论在生命周期模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检验[14];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永久收入事实上比截面测量收入更加不平稳,因此旅游消费的相对平稳需要诉诸新的解释[15]。克服上述缺陷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考虑收入的内生变化,从而将相关讨论引向深入的过程。
在研究收入影响旅游消费的过程中,将收入按照来源做出适当区分有助于理解收入内生化的必要性。整体而言,人们的收入来源于向市场供给劳动而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和非劳动的财产性收入。但是,向市场供给劳动即意味着相同的时间不能够被配置于旅游等休闲活动,因此工资性收入影响旅游消费的机制无疑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给分析旅游消费造成的一个明显困难,在于研究者能否对工资性收入精确把握。例如,传统的工资方程估计有赖于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呈现的经验事实,但此类典型模型在用于分析已婚妇女、青少年和老年人等群体时可能会引致某些偏颇和不尽准确之处[16],而上述群体的闲暇时间配置同样具有不同于典型劳动力的特征,因此判断工资性收入对其旅游消费的影响应更加审慎。尤其是女性劳动力,其时间分配需同时考虑劳动力市场、家庭生产和闲暇等多重维度,旅游消费决策取决于一系列联合反馈和约束条件[17]。迁移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和闲暇时间配置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同时影响其工资性收入和旅游消费决策[18]。
此外,遗漏变量等技术性问题始终是估计工资方程所面临的典型困扰[19]。当针对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从个体层面延伸至个体间差异时,收入分配视角得以诉诸更加充分的讨论。中国收入分配的城乡差异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有学者指出,由于储蓄模式和耐用消费品的所有权不同,从静态意义上理解城市和农村的旅游消费差异是值得商榷的[20],城乡消费者对于旅游营销的态度也因而存在显著区别[21]。与此同时,与收入分配的组间差异相关的研究还涉及中国中产阶层的出境游消费偏好[22]以及消费升级背景下中短程观光旅游和短途周末游等供给侧变化[23]。
从收入影响旅游消费支出的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因其庞大的旅游消费群体而引起较多关注。美国经济同时具备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从而使得财产性收入对美国家庭消费的影响成为了学者讨论的重点。此前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美国高财富群体的收入消费弹性约为0.076至0.05[24],但该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囿于样本的选择性偏差。通过使用美国家庭的历史财务信息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住房财富比金融财富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更显著[25]。一项更加细致的研究区分了旅游消费的现有需求和潜在需求,使用针对澳门的区域性数据和Tobit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结构特征和劳动力市场收入对于旅游消费支出存在显著影响[26]。从欧洲旅游消费市场来看,意大利家庭房产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02至0.03 5[27];西班牙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市场收入下降会显著降低其旅游消费,无条件收入弹性值远高于1,而条件弹性值约为0.69[28]。对于政治、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其受到各种外生冲击的可能性和影响更大,因此常被用于观察特殊事件所引致的旅游消费变化。例如,有学者将1997年席卷印尼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作为自然实验,通过入境游实际抵达人数的变化探讨了旅游消费规模的预测问题[29],而2011年泰国洪灾和相应的减税政策也分别对旅游消费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30]。
经济体量扩张和旅游业迅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经验证据[31]。近年来,随着数据的可得性明显改善,探討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本土经验证据渐趋丰富。此类研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一消费异质性是学者的重点关切。既有研究显示,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工资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32],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33],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小[34]。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消费习惯差异、家庭转移支付和代际支持等因素使得其消费对工资性收入的反应相较于城镇居民更不敏感[35],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36]。此外,随着刘易斯转折区间①的推进和完成,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特征趋于瓦解,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改善的消费含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静态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更多地诉诸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37]。如果在更加动态的意义上考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阶段性,经验证据表明,经营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阶段前后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工资性收入增长对消费的推动作用在收入快速增长后反而逐渐降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随收入快速增长而日趋关键[38]。
当研究视野聚焦于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时,早期的研究框架通常将旅游休闲消费视作和食品、住房、通勤相类比的消费渠道,通过国民收入的分解技术被学者加以识别[39]。随着经验证据的不断积累,在较前沿的视野下研究者更加聚焦旅游消费本身,并且尤其关注因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所谓旅游消费的异质性问题[40]。从宏观层面来看,通过使用汇总数据的需求侧模型加以测算,我国城市地区国内旅游收入弹性约为0.3[41],但旅游消费明显受到资源配置的优先性和热点溢出效应的影响[42]。从微观层面来看,有学者利用2002-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了消费者收入的可自由支配周期,结果表明,非跟团游的消费支出按年龄呈S型分布[43]。此外,如果在估计模型中同时引入收入变量和时间配置变量,则研究结论认为收入提升对于增加旅游消费的贡献比传统估计结果更为保守[44]。研究者尝试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加以结合,通过衡量省份或城市的个人收入与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形成基于相对收入关系的联合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绝对收入水平的改善,个人或家庭在地区层面的相对收入收敛会对旅游消费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45]。除上述立足于中国本土数据的实证研究外,近年来跨国别的出境游研究亦不断涌现。例如,有研究指出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的旅游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和逗留时间,以及澳方的旅游营销管理[46]。
通过对研究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既有成果加以同溯可知,首先,与国际研究通常把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加以分离、并更加重视财产性收入的作用不同,来白中国的实证证据受限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在笼统地探讨“收入”这一变量时往往依赖各种间接估计,从而难以细致反映理性人做出不同旅游消费决策的因果机制[47]。其次,在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和经济转型过程[48],并伴随有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迅速增加,但目前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不足以捕捉旅游业消费升级的进程全貌,尤其是新时代背景下地区发展差距所造成的旅游消费异质性还有待于深入讨论。再次,相较于成熟和视角多元化的国际成果,试图反映中国旅游消费特征的既有研究工作还缺乏针对特定旅游形式[40]或旅游业某些特定供给侧要素[49]的更为细致的探讨。最后,探讨中国居民收入结构与旅游消费关系的既有研究,多使用不同统计层次的汇总数据作为实证证据,其结论能够反映不同收入来源影响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但通常缺乏对于个人、家庭等微观主体理性消费抉择的深入刻画。
通过对国内外探讨收入与旅游消费关系的相关研究加以同溯可知,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归纳为一类,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归纳为一类,通过引入时间配置的内生维度,在细分意义上探讨不同来源的收入对于旅游消费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该议题的研究视角;第二,着眼于个体和家庭户数据,能够充分反映理性行为主体的收入约束变化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使得相关实证分析建立于一个更为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第三,使用时间序列延续至2015年的3期面板数据,在充分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削弱内生性影响的同时,又能够通过较新的经验证据捕捉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以来的旅游消费变化特征。
2 理论演绎
2.1数理分析
旅游作为服务行业的一个门类,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不可分割。因此,从个体的旅游消费行为来看,旅游必须以闲暇时间的配置作为前提。对于任一给定的时间长度T,可以将之划分为投入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t以及非劳动时间t*,即有:
T=t+t*(1)
容易理解,个体投入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用于取得劳动收入,势必与旅游所需的闲暇时间呈互补配置,从而可将式(1)变形为:
t= T-t*
(2)
式(2)所蕴含的启示意义在于,在总时间给定的前提下,个体或家庭投入旅游消费的潜在时间与劳动时间反向变动。值得注意的是,旅游偏好等因素会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个体和家庭的旅游消费决策,从而造成实际旅游时间配置与潜在时间的吻合或背離,因此旅游时间并不必然与劳动时间呈现反比关系。
考虑个体或家庭的旅游消费函数具有某种常系数线性形式,如式(3)所示,其中w代表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加总财富,α,β,γ为常数。
q(t)=aw(t)+βdw/dt +y
(3)
式(3)表明,旅游消费量一方面受总财富的预算约束影响,另一方面受劳动时间对总财富的际贡献影响。这是因为,个体或家庭中劳动收入占总财富的比重越大,则总财富的变化会对劳动时间的变动越敏感。如果个体或家庭存在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那么劳动时间的配置通常更具粘性,从而不利于其增加旅游消费。
从成本视角来看,由于财产性收入水平较少受到时间配置影响,个体或家庭选择旅游消费的成本可以用时间机会成本、即劳动力的影子价格来衡量,用等式表示即为:
c(t)= λw(t)+η
(4)
其中,w(t)表示劳动时间变化所引致的总财富变动,λ,η为常数。旅游消费的边际效用θ[w(t]与加总财富相关,综合式(3)和式(4),可得到个体或家庭的旅游效用函数如下:
代人整理可得:甜
(6)
欲使得既定约束下的旅游消费效用最大化,相当于求解如下目标泛函:
(7)
根据泛函取极值的必要条件,可列得:
因此,与式(7)相对应的欧拉方程为:
(9)
极端情况下,对于总财富为零的个体或家庭而言,即使无成本地获取旅游产品或服务,其边际效用至少为零。由此确定初始条件θ(0)=0,解式(9)这一微分方程可得:
将式(10)代入式(7),计算可得最大化的旅游消费效用为:
从式(11)的结果来看,由于
恒为正,因此I*的大小主要取决于
的相对比值。根据式(3)可知,
反映了个体或家庭总财富的变化对于劳动时间变动做出反应的敏感程度。因此,在旅游消费支出一定时,旅游消费会对劳动时间占比高的个体或家庭带来更加明显的边际效用改善,因为此类个体或家庭已经将更多的时间配置于可以带来负效用的劳动力市场。该命题一个对偶形式的推论是,如果个体和家庭对于旅游消费的效用目标一定,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相对提升则会导致更高额度的旅游消费。
2.2研究假设
通过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前述分析将个体或家庭的旅游消费与其收入结构联系起来。结果表明,旅游消费与收入对时间投入变化作出反应的敏感程度有关。在诉诸于实证分析的过程中,相应的经验观察可以来自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差异,以及财产性收入内部的金融性收入与非金融性收入的差异。因此,综合理论分析结果和既有的相关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
假设2:在财产性收入结构内部,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1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的3期面板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 China Household FinanceSurvey, CHFS),包含2011年、2013年、2015年3个调查年度。CHFS数据在全国范围内采集个体层次和家庭层次的金融信息,包括家庭户成员的职业收入、资产与负债、社会保险与信贷约束、家庭消费结构等[50]。201 1年是CHFS首轮调查,样本量为8438户,覆盖全国25个省80个县(县级市)320个村(社区);2013年的调查在2011年的基础上进行了样本量扩充,覆盖全国29个省262个县(县级市)1048个村(社区),共计28 143户家庭;2015年第3轮调查再次进行了样本量扩充,覆盖全国29个省353个县(县级市)1373个村(社区),共计37 348户家庭。总体而言,CHFS的调查样本具有全国、省级、副省级城市等不同层次的代表性[51]。在经过必要的数据清理过程后,匹配合成的3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共包含符合研究需求的样本量为71715户,其中有7037个相同家庭户的观测记录。
3.2模型说明
在CHFS的调查问卷中,旅游支出相关问题以家庭户而非个体作为观测单位,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以家庭旅游消费支出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以家庭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以不同个体条件和家户条件作为控制变量。同时,CHFS作为追踪调查数据,可以控制家庭户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本文所使用的同归方程具体设置如下:
式(12)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面板数据中的不同家庭户和调查年度;tour-exp代表家庭旅游消费支出;w和p分别代表家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模型同时纳入了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户主的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家庭户规模等控制变量;φ和ω分别为调查地区固定效应和调查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3.3变量说明
依据CHFS的数据结构和相关研究的通行口径,本文首先界定收入变量的讨论范围。本文所指的收入由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包括个体和家庭内其他劳动力过去一年获得的税后工资收入、税后奖金收入、税后补贴收入以及兼职收入。财产性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指调查年过去一年内家庭依靠不同财产获得的增殖税后收入[52],包括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债券收入、股票差价及分红、基金差价及分红、金融衍生品收入、黄金收入、非人民币资产收入、商业保险分红等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和依靠房产、土地、汽车等获得的租金构成的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是指通过经常性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收益。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对个人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产生的收入,以及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为克服模型的异方差问题并更好地反映变量间的弹性关系,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均以对数形式进入同归方程。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本人的受教育状况、婚娴状况、政治面貌、户籍性质、户籍流动以及家庭人口规模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4 实证分析与讨论
4.1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1~模型5为本文所使用的基准同归模型。其中,模型1估计收入结构解释变量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未纳入任何其他控制变量,也未控制年份和地区的固定效应;模型2和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户主本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婚娴状况、政治面貌以及家庭户的人口规模等控制变量,但并未控制年份和地区的固定效应;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调查年份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5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划分的地区固定效应。模型1~模型5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基准方程的同归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收入增加均对家庭旅游消费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小于财产性收入。当模型纳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并分别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时,可以更加清晰地识别到财产性收入对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收入。这一结果与本文的研究假设1初步吻合。此外,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旅游消费支出越高;户主年龄越高,家庭旅游支出则越少;与2011年相比,家庭在2013年和2015年旅游支出在降低;与东北地区相比,中西部的家庭在旅游消费方面支出更高,东部地区家庭并不显著。
4.2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文进一步考虑模型所面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从收入与旅游消费的理论关系来看,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消费增加,但消费增长本身仅有可能作为收入变动的结果而非原因存在。因此,模型的估计结果较少受到反向因果的威胁。另一方面,如果模型遗漏了某一个或某几个既有数据结构无从测量的变量,且该变量能够同时影响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因素,那么就会开启后门路径,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相关的所谓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得估计结果不再可信。为克服这一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可以考虑提升解释变量的数据统筹层次作为工具变量。在非对称的数据统筹层次下,个体的收入变动必然影响汇总意义上的区域收入水平,但区域收入变动却难以影响个体和家庭的旅游消费,因此可以起到阻断后门路径的作用。
本文分别使用由样本数据计算得到的各类收入的省级平均值作为各自收入类别的工具变量。为增强可比性,表3的模型5为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模型6~模型9为面板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其中,模型6仅控制个体和家庭的控制变量,模型7在模型6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调查地区的固定效应,模型8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模型9与前述模型的区别在于,其采用了面板广义矩估计( Panel GMM),而前述模型6~模型8均采取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PaneIIV-2SLS)。工具变量同归所纳入的控制变量与基准同归均相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影响后,同归结果依然表明不同类型的收入增加均对家庭旅游消费增长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意义,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带来的正向效应低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具体而言,在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后,财产性收入增长1个相对单位能够引起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增加约0.362个相对单位,T资性收入增长1个相对单位仅能够引起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增加约0.064个相对单位,本文的研究假设1得以验证。此外,模型的LM(p值)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处理模型不存在IV识别不足问题;Hansen J统计量显著,表明模型选取的IV变量是恰当有效的;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显著大于Stock-yogo弱T具变量临界值,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3模型9的估计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1。
4.3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部分控制变量、选择子样本以及变换模型设定形式等方式,针对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穩健性检验。其中,模型10用被访者的“总体幸福感”替换原模型的控制变量“家庭人口规模”;模型11选择使用“宗教信仰”变量替换原模型的控制变量“政治面貌”,由于“宗教信仰”变量仅在2013年调查中存在,故模型11仅使用2013年调查样本;模型12选取户籍不在本地的流动人口子样本进行同归;模型13为了克服样本中大量无旅游消费的家庭所形成的0截断现象对于分析结果的影响,转而采用Tobit模型对非农户籍人口进行同归。上述模型均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无论是替换部分控制变量、变换模型设定形式还是选择使用部分子样本进行同归,工资性收入对数和财产性收入对数的同归系数均未改变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即家庭财产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工资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
4.4异质性分析
事实上,如果从财产性收入的内部结构加以考量,则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与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时间配置的敏感性不同。于是,在进一步考虑财产性收入对于时间配置需求的异质性时,一个自然而然的追问在于,具有不同时间投入敏感性的财产性收入是否也意味着不同的旅游消费影响。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户籍二元制度,导致居民在收入来源、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即户籍差异形成的收入来源机构的分割现象。于是,在对全样本人群进行收入内部结构的异质性分析时,还应该进一步估计由于户籍差异导致的收入结构分割是否影响家庭的消费支出。
表5呈现了这一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模型14使用全样本数据,模型15使用农业户籍的子样本数据,模型16使用非农户籍的子样本数据。结果表明,从家庭旅游消费影响来看,在全样本和非农户籍的子样本中,金融类财产性收入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均领先于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户主为农业户籍的家庭中,财产性收入和基本工资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补贴收入、兼职收入、奖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化影响因素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从前文的表1可以发现,农村户籍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对数、财产性收入对数的均值分别为0.707和0.052,而非农户籍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对数和财产性收入对数的均值分别为1.035和0.169,后者远高于前者,正是因为这种收入结构的分割导致农业户籍家庭和非农户籍家庭在旅游消费支出影响因素上的巨大差异。至此,本文的研究假设2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验证,即在户主为非农户籍的家庭中,从财产性收入结构内部来看,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
4.5进一步探讨
本文的实证分析通过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此前的研究假设,即家庭财产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工资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且对于户主为非农户籍的家庭而言,在财产性收入结构内部,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旅游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家庭而言依然属于富于弹性的消费品。这一基于全样本的发现能够与此前关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研究相印证。尽管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该作用会受到其他优先级更高的“强制性”消费因素影响而被大为削弱[53]。另有基于省级汇总数据的研究表明,工资性收人对我国农村居民出游率的贡献最大[5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的统计口径下,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所形成的所谓工资性收入,其统计精度通常难以支撑省级层面的宏观分析,因此本文更加强调通过微观家户数据观察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影响旅游消费的方法论意义。从城市家庭旅游消费的既有研究来看,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均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旅游消费[55],与本文观察结果基本一致。
正如本文在理论演绎部分所指出的,时间的内生分配是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本文已经注意到时间变量对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内部结构的影响,但受限于数据结构而并未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加以更为细致地探讨。可以预见,在未来涉及旅游消费的学术研究中,量化分析个体和家庭成员配置于劳动力市场和旅游休闲活动中的时间要素将成为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方向。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作为“幸福产业”的典型代表,旅游能够愉悦身心、增长见闻、陶冶情操,在综合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给予消费者健康快乐的人生体验,是人民群众提升生活品质、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和向往的重要渠道。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旅游经济主要数据报告,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居民总体旅游意愿分别为83.0%、84.8%,分别同比增加1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①,显示出我国居民的旅游意愿继续保持上行势头。在旅游消费与国民收入近乎同步增长的趋势现象背后,本文捕捉到不同收入来源影响旅游消费的潜在差异并加以分析,研究结论可简要归纳如下:
第一,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而言,不同来源的家庭收入增加对旅游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发现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解释,即收入增加会扩大家庭消费支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增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体,引领包括旅游消费在内的服务业发展,无疑是从需求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对于旅游消费的拉动,其作用要大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效应,本文的理论演绎表明,当旅游消费支出或旅游消费效用目标二者之一保持不变时,个人或家庭的劳动时间配置与前两者中发生变化的另一者呈反向变动关系。由于旅游消费的服务业属性,旅游体验的供给与消费同时发生、不可分离,因此一定的时间投入是旅游消费的必要条件。对于将更多时间配置于劳动力市场的个人或家庭而言,一方面,其能够投入旅游消费的时间面临更加严格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劳动供给的负效用又提升了其增加旅游消费的潜在边际效用。正确认识这对矛盾是理解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贡献的关键所在。即中国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单纯依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扩大旅游消费有其局限性。
第三,收入结构对不同户籍状况的家庭旅游消费支出产生差异化影响。首先,对于户主为非农户籍的家庭而言,在财产性收入结构内部,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其次,对于农业户籍的家庭而言,财产性收入和基本工资对家庭旅游消费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影响,家庭税后补贴收入、兼职收入、税后奖金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有积极效应。整体而言,金融类财产性收入与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主要体现于两点:二者的流动性不同,以及二者对收入主体时间约束的粘性不同。在财产性收入引致旅游消费扩大的过程中,一方面,流动性更强的收入可以实现更为灵活的消费转化,而较少受到投资周期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依附于房产、土地、汽车等物质要素存在的非金融类财产性收入显然与必要的时间投入相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收入增加所引起的旅游消费转化。
基于前述研究結论,本文拟提出如下对策建议:首先,应从制度建设与劳动力市场发育双向着力,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着力增强农业户籍人群的创收能力,提高其工资性收入水平,加强转移支付力度,拓宽劳动者除基本工资外的其他收入渠道,促进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优化。其次,应创造条件让更多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或进一步提升其财产性收入比重,切实减少相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高强度的职场环境对劳动者的时间和经济束缚,充分保障个人和家庭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最后,应积极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为友好的旅游休闲环境,为人民群众更好满足白身旅游需求提供便利,以提升性价比和灵活性为抓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旅游产品及服务,从而进一步激发潜在需求、缓解供需错配,以市场发育本身突破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性瓶颈。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1 Chunling. Growth trend and composition change of middleincome group[J]. Journal of Bez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8,(2):1-7.[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趋势与构成变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7]
[2] ZHANG Juwei, ZHAO Wen. How to realize the growth ofresidents' income?[J]. Studies in Labor Economics,2014,(6):3—25[张车伟,赵文如何实现居民收入增长?[J]劳动经济研究,2014,(6):3—25]
[3]
ZHANG Yi. The consumption tendency of all sectors of thecurrent Chinese society: From subsistence to developmentconsumption[J].Soc/o/og/ca/ Studies,2016,(4):74-97.[张翼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J]社会学研究,2016,(4):74-97.]
[4] LIU Jingjing, HUANG Xuanxuan, LIN Derong. Impact ofhouse prices on the urban residents' tourism consumption: Ananalysis based on dynamic panel data[J]. Tourism Tribune,2016,31(5):26-35。[刘晶晶,黄璇璇,林德荣,房地产价格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而板数据的分析[J]旅游学刊,2016,31(5):26-35.]
[5]
YANG Yong. Sources ofincome,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tourismdemand of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on panel data from 2000 t0 2010[J]. Tourism Tribune,2015,30(11):19-30.[杨勇.收入来源、结构演变与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基于2000-2010年省际而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J]旅游学刊,2015,30(11):19-30.]
[6]
YU Fenglong, HUANG Zhenfang. Research progress on Chineserural residents' tourism consumption[J]. Economic Geography,2017,37(1):205-211.[余凤龙,黄震方.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研究进展[J]经济地理,2017,37(1):205-211.]
[7] ZHAO Peng. Research on Inj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Students3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D]. Changsha: CentralSouth University, 2012.[赵鹏.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8]
WANG Qiyan, WEI Jiaji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Beijing residents' tourism consumption[J].Social Science ofBeijing, 2018, (8):120-128.[土琪延, 韦佳佳.北京市旅游民费
消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 2018, (8):120-128.]
[9]
VEBLEN T B. The I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Study of Institutions[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1899:116.
[10] ROOIJ M, LUSARDI A, ALESSIE R J M. Financial literacy,retirement planning and household weahh[J]. EconomicJournal, 2012, 122(4):449-478.
[11] LEVIN L. Are assets fungible? : Testing the behavioral theoryof life- cycle saving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1998, 36(1):5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