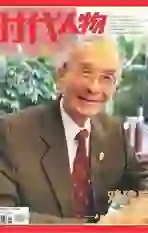人口“少子化”问题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2019-06-14郑亚楠
郑亚楠

东亚地区进入21世纪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中国港澳台地区、新加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均降至不足1.1,为世界最低水平,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愿生育的地区。日本是东亚最早步入少子化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应对少子化的国家,生育率出现回升迹象。韩国和中国台湾(以下简称台湾)的超低生育率持续时间更长,也更难摆脱困境。关于人口少子化和低生育率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试从文化决定论的角度来分析日韩台出现低生育率差异的原因。
一、超低生育率在全世界蔓延
所谓超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是指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现象,远远低于保证人口更替水平2.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北欧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生育率率先迅速下降,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语国家,其次是其他西北欧国家。80年代,北欧的生育率并没有如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停留在更替水平附近,而是出现了新一轮的下降。荷兰学者Van de Kaa提出“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从价值观的世俗化、个人主义化角度来进行解释。根据这一理论,20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的第一次人口转变体现的是“孩子为王”的利他主义和家庭主义价值观,20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反映了“以伴侣(父母)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同居、非婚生育、离婚的增加等一连串的家庭变化都是个人主义的影响,生育率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也是其影响之一。
进入90年代,南欧、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3甚至更低,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在这些国家,家庭主义价值观占社会主流,传统的性别分工仍然存在,女性劳动力的社会参与度低,婚姻制度健全,婚内生育占主导。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无法用价值观的变化来解释这些国家出现的极低生育率。
21世紀初生育率下降的前沿转移到东亚。首先是韩国在2001年达到1.30的极低生育水平。接下来是2003年的台湾(1.24)和日本(1.29)。日本的生育率波动比韩台略慢,2005年达到最低点1.26后,2006年回升到1.32,摆脱了超低生育水平。相比之下,韩国和台湾在2010年仍然是超低生育率。韩国2005年降至1.08,台湾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0.895。
欧洲各国中,意大利(1993- 2003)、西班牙(1993- 2003)、捷克共和国(1995- 2005)和斯洛文尼亚(1993- 2003)在11年间一直保持超低生育率。相比之下,韩国在2001~2015年、台湾于2003~2014年生育率一直处于超低水平,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长。2016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7,台湾仅为1.12,日本则回升到了1.44。
二、文化决定论
发达国家超低生育率的出现要归因于后现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全球化导致就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强,经济缓慢增长背景下年轻人就业市场恶化,收入下降造成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养育子女费用特别是教育费用高涨,经济服务化使女性劳动力大量增加。这种变化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是由此引发的生育率下降的程度因文化圈而异。
Peter McDonald将英语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西欧(不包括德语国家)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以上的国家列为第一组,生育率远低于这些国家的列为第二组,包括德语国家、南欧、东欧、前苏联各国和东亚发达国家。日本的最低值(1.26)与德语国家和南欧的平均水平相当。东欧和前苏联一些国家,如捷克(1.13)、拉脱维亚(1.10)、保加利亚(1.09)生育率非常低,不到1.15,但也没有降低到韩国和台湾的水平。
东欧和前苏联各国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经济变化之外,还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剧烈变化。因此,即使生育率比德语国家、南欧、日本下降得更快,也不是不可理解。然而,韩国和台湾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两国社会也没有发生比东欧和前苏联更动荡的变化,其生育率下降到更低水平很难从这些方面找原因。因此,韩国和台湾的极端生育率下降应被视为反应的特异性,而不是“压缩现代性”等特异性因素。
铃木透从文化决定论的角度将生育率极端下降地区分为西北欧国家、德语国家和东南欧国家、日本以及儒家文化圈等四类,韩台属于儒家文化圈。在西北欧国家,妇女地位从古时候开始就很高,传统性别分工的退化、男性参与家务和育儿也最先发生在该地区,男女平等程度与生育率呈正相关的态势。然而,台湾社会男女平等程度比日韩高得多,生育率反而很低,德语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三、日本的家庭模式和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模式
日本的生育率在2005年下降至最低点1.26,相当于南欧、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韩台则更低。日本和韩台虽同属东亚,深受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其文化却显示出不同于儒家文化圈的特点。在家庭利益优先、尊重父权、孝顺父母等价值观方面明显弱于韩台。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日本排在中华文明之外,自成一体。日本的传统社会构造与其说是东方式,不如说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类似。双方不约而同地具备相近的社会—文化结构:氏族制的强劲遗存与相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构筑起军事贵族统治下的采邑群体,出现官方权力与领主地产的融合物,而附庸对领主的效忠提供了这种制度的伦理基础。”而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以孝为根本,孝移之于国家,才产生了忠。
中国的孝道发展到后期强调绝对支配和服从的片面性,绝对化的“孝”变成盲目的服从和愚昧的举动,片面的“孝”道被极端化,立身处世无不以“孝”为标准,甚至由道德修养演变为法律制度。反观日本,作为伦理道德观念的“孝”于日本社会并非原发性概念,而是由大陆文化输入的,“孝”更多表现为子女对长辈单方面承担的一种义务。日本的“孝”道中掺入了大量佛教色彩,更多地宣扬“恩”的作用。认为子女对父母尽“孝”就是回报父母的“恩”,“恩”是“孝”的前提。传统中国人最担心的事情是无后,人们视生育后代为一个人对祖先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男人没有尽到这种义务与责任,便自觉有愧于祖宗,无地自容。女人在家中的地位也因其生育能力而定,未生儿子是被丈夫抛弃的合法理由。中国人在生育观上始终有两个偏好:一是偏好男性,一是偏好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