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画的交响
——同四位前辈画家的合作
2019-05-23陈四益
☉陈四益
在我的文字写作生涯中,曾有幸得以同丁聪、华君武、方成、黄永厚等四位前辈画家长期合作。这种机缘有一已属难得,同时得四,岂非异数。
近代报业大兴,尤其是中国报纸副刊的发展,使“新闻纸”多了一块文艺天地,于是杂文、短论、漫画、散文、诗歌、随笔,均得在报纸上占一席之地。其中漫画,虽可数幅连缀,毕竟以单幅为多;虽可引人联想,画境仍多局限。于是,漫画家同作家,或作家同漫画家,开始联手。这种联手,方式颇多。
我少时知道名头最响的,要算《马凡陀的山歌》了。马凡陀是袁水拍的笔名,作图者有丁聪和华君武。“山歌”本就好玩儿,如:“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怨见脑袋打木棍,木棍打伤十几根。抓住脑袋上法庭,气得木棍发了昏。”一连串的“反话”,是对当时世道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讥嘲,就像我小时学会的《古怪歌》,“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清早走进城啊,看见狗咬人哪。只许它们汪汪叫,不许人们用嘴来讲话”一样,朗朗上口,好玩儿得紧。《马凡陀的山歌》每首都有图,更是有趣。这些讥讽社会怪现象的《山歌》,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东安市场还能于旧书摊上买到,后来就难于寻觅了。
那时,漫画在报刊上依旧活跃,漫画与讽刺诗相配的作品也时有所见,但像“马凡陀”那样持续地、抨击性的讽刺作品不见了。因为持续的批评,可能会被认为是“立场与方向的错误”。可是缺少了持续,也就不容易形成作画者与为文者的长久合作。
“文革”结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工作的变动,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机遇。那时,我从新华社湖南分社调到总社,参加《瞭望月刊》的创办工作。
后来,月刊改成周刊,虽然是新闻性的周刊,但社长穆青希望新闻周刊也要有一个副刊,并为定名“珍珠滩”,尽管只有寥寥四页,却也要求品种多样,丰富多彩。这个副刊的稿件安排,落到了我的头上。
一周要有四页稿件并不难,但要活泼多样,却难。要长短相间,图文并茂,必得费一番功夫。于是想到,倘能集聚一些短稿,岂不便于版面安排。可是做编辑的都知道,稿件是按字数计酬的。写三二百字的短稿,气力不少费,所得却无多,因此约稿甚难。于是,只得一面约稿,一面自己动手准备一些短稿。想法是,稿虽短,但不能弄成可有可无的“补白”,文虽短,也独立成章,蕴藉有趣,且能“抗压”,方有存在的可能:一可留着备用,二不致因时间延宕失去刊登的价值。这样就想到佛家有《百喻经》,每篇一个故事,暗含一番佛理。若能仿此,岂不妙哉。可在白话时代,要用文言,能否成功,全无把握。写了十几则,自觉尚可,便先请大学同窗林东海、林冠夫二君帮助推敲。“二林”是20世纪60年代初复旦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后,最早一批攻读古代文学的行家。我连续几周,每到周末,便去他们在和平里的家中,推敲文字。等到他们都觉得可以,便将十几则改定稿打印后复印了几份,一份送给《瞭望》主管文化稿件的副总编辑审阅;另几份则分呈严文井、王朝闻、华君武等前辈,征求意见。未几,严、王、华三老都有回音,觉得用这种浅近的文言写寓言,可行、有趣,且预想会受欢迎。华君武先生对我提出是否可以伴以漫画的设想,更约我当面一谈。他的意思是,如有漫画,更加有趣。但又坦言,由他来画不妥。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我借古人衣冠,用文言来写,而他一直是画现代题材。但他说可以帮我介绍一位画得又好,对古时衣冠器物又非常在行的漫画家——丁聪,若我同意,就帮我介绍。丁先生我所素知,少时读“马凡陀”就知道,只可惜无缘识荆。闻此一言,大喜过望。待到华先生征得丁先生同意,便告知我丁先生的地址和电话,叫我同他相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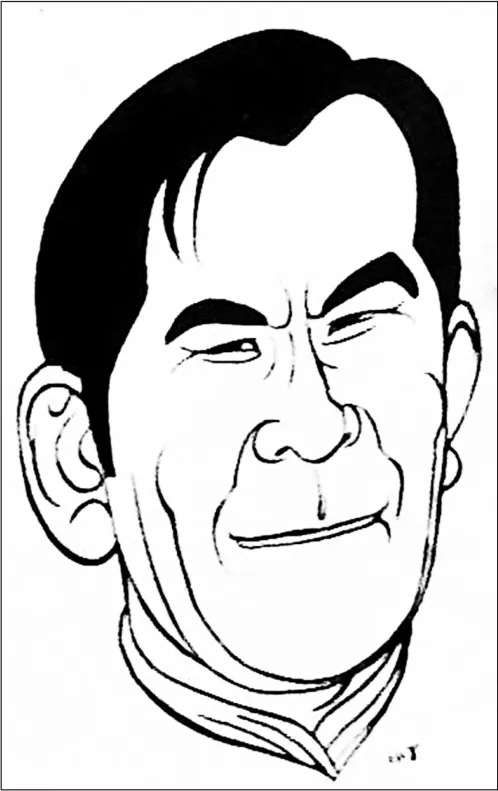
丁聪画陈四益

丁聪自画像
丁先生甚是和气,电话中道“先看看稿子再说”,并立即约我到家相见。我敲门入室,丁先生略无客套,便把我引进他的“画室”。说“画室”,实在是夸张。那时,他同夫人、岳母住在一套有一个门厅的小两居中。他的工作室在小间屋里。小屋地上堆满了一摞摞的书,我随着他蛱蝶穿花似地在书堆中行走,生怕一不小心碰翻了书堆。书堆中有一张书桌,桌面三边也堆着书,只一面中央有一方空处,一盏曲臂台灯伸到上面。那一方“盆地”,便是他作画的地方。墙角倚着一张折叠床,像是晚间睡觉所用。那房子,好像还是丁夫人从单位分到的。这也难怪后来熟稔之后,丁夫人要开玩笑说:“我是看他可怜,才把他捡回来的。”丁聪先生分到较为宽敞的住房,已是几年之后。
丁先生把我写的十几则文言体短文看毕,只说了五个字:“有意思,我画。”有丁先生这句话,我那一直悬着的心就落地了。
兴致勃勃回到单位,告诉了主管副总编辑,但他未置可否,沉默半晌,才说“再看看吧”。看得出他在犹豫,但他既然没有否定,我也只好等待。又过了些时候,仍无回复,丁先生却已有图寄来。我只好再试探道:要是不合适,就把稿子还我,另投别处吧。这一说,他立即从抽屉里取出还我。这样倒也两蒙其休:他免了作难,我则脱去了“种自留地”之嫌,可以自由处理稿子。版面安排的麻烦,只好另想办法。
试着将文、图向北京一些报刊投寄,竟都很快刊载——包括一些党报、党刊——并希望我继续“赐稿”。还有些报刊见到后,也来索稿,似乎很有“销路”。我也略略安心,没有令前辈先生白忙。丁先生的图,版面大都给得宽松。
同丁先生的合作,断断续续延续到1990年初,《读书》杂志的赵丽雅(扬之水)君突然来函,问我能否同丁聪先生在《读书》开一图文相生的专栏。并说,你们这样文图配合的方式,最适合《读书》刊载。
我本是《读书》的热心读者,《读书》的版面安排又一直是丁先生在负责,当然一拍即合。从1990年开始,先是写了几首玩具杂咏,经丁先生作图,在《读书》上刊载,似乎颇得好评。于是,《读书》把封二空出来,专登我同丁聪先生文图配合的“新百喻”。“新百喻”写到一百则,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为《绘图新百喻》,本拟收煞,不想读者编者都意犹未尽,于是又续写至“双百”,还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为《绘图双百喻》。
《绘图新百喻》出版后,趣事不少。因为用了浅近的文言,有人询问作者是哪里冒出来的老头儿。有人诉苦:在当地新华书店遍觅无得,结果在少儿读物架上找到——笑问:这是少儿读物吗?最有趣的是,在福建一座名寺的法物流通处,《绘图新百喻》居然赫然陈列。想是顾名思义,将此书当作《百喻经》一类佛门“典籍”了。
看来,这种有文有图,各尽其长的方式,颇得读者编者认可。后来《读书》准备把封三也拿出来刊登。于是就有了“诗画话”。诗画话,用白话,直击现实,文尾缀打油四句,仍是丁先生作图。读者似也喜欢。待到《双百喻》结集,“诗画话”就移到封二刊登了。
在《读书》杂志上,同丁聪先生合作的专栏,从1990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丁聪先生病重不能握笔才告结束。十数年间,《读书》的不离不弃,令我衷心感之。一家刊物能给作者这样的关照,不知是否有过先例。其实,那时一家刊物,长期刊登这样以批评为主的文与画,是要承担不少风险的。据说,有不相识的朋友问:为什么这样的社会批评可以长期存在?同样是不相识的朋友想当然地回答道:他是特许的。也许是知道我在新华社工作,所以有此一想吧。

丁聪画方成

丁聪画华君武
其实,哪里有什么“特许”,那个时期,正是中国锐意改革进取的时代,而《读书》杂志又是一家博取兼收、传播新知的有担当的刊物。
同丁先生的合作,除湖南文艺出版社不离不弃地跟踪结集,最后又有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总印行为《百喻图》《世相图》《唐诗图》《竹枝图》四种五册,几乎囊括了我同丁聪先生合作的全部作品。这套书出版时,丁先生已不能握管作画。我把样书拿给他看,他赞赏道:“这个人画得真好。”丁太太在旁打趣道:“他画得这么好,你要向他学习啊!”丁先生摇摇头道:“不行了,我学不了了。”闻此言,我鼻子一酸,掉下泪来。十数年的合作,最后竟是这样一个辛酸的定格。
为我介绍与丁聪先生相识、促成丁陈合作的华君武先生,同我也有一次小小的合作。这次合作,其实是一次互动。那起因是一张照片。由于原先设想用寓言与漫画来活跃版面的计划未能实现,我便同《瞭望》摄影记者王辉兄商量,能否用一些有趣的摄影作品来活跃版面?王辉兄很快便送来一张他的作品,拍摄的是华君武先生“抽冷烟”。20世纪50年代华君武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漫画《决心》,脍炙人口。记得那是一幅四方连的漫画:第一幅决心戒烟;第二幅将烟斗从楼上扔下;第三幅快速奔下楼梯;第四幅赶在烟斗落地前双手接住。“决心”改变之快,远超自由落体。这幅漫画让我这个当年的初中生开心了好几天。他嘲笑的决心下得快、也变得快的现象,当然不止于戒烟。王辉兄的这幅作品,大概摄于20世纪80年代,照片上华君武先生凝神端坐,含着一支无烟的烟斗“过干瘾”,着实有趣。为了增加谐趣,我填了一支《挂枝儿》略作调侃:“难禁你,难管你,又难舍你。待舍你,斩不断一缕情丝系;不舍你,怕污了一室清新气。舍你添烦恼,不舍伤身体。你是我的冤家也,只索假惺惺、冷丁丁、口儿里衔着你。”华先生看到这幅“摄趣”后,很快寄来了一张图:一只玻璃盆中,横七竖八堆着一盆烟斗。画上有一首诗:“曾作《决心》自嘲,无奈气管坏了。从此见烟就怕,受到妇女称道。烟斗堆满一盆,闲置橱内逍遥。四益诗词绝妙,早写八年更好。”

《衡文》丁聪 画
收到华先生的图和诗,高兴极了,立即在下一期上刊登,版面一下就生动活泼起来。可惜如华君武先生这样的互动,可遇而不可求。后来虽然还有过几帧“摄趣”,总觉得不如这幅有趣了。
再稍后些时,一些朋友在北海后门的文采阁聚会。华先生、丁先生都来了。席间,华先生忽然指着丁先生和我道:“你们两个还没谢媒呢。”大家一愣,然后才悟到:当初丁陈合作是华先生介绍,岂非“做媒”?这时已合作几年,故华先生调侃道“还没谢媒”。于是哄堂大笑,举杯尽欢。
我曾经合作过的老一辈漫画家还有方成先生。一家刊物希望写一点关于“时尚”的文章,便陆续写了六篇“时尚闲谈”。大意说,流行是一种时尚,时尚是一种商机,商机便有时限,所以追风时尚,常常尚未追上,已是明日黄花;时尚往往需要大把花钱,随风而舞,难免落入消费的泥淖;时尚是有人带领的,不懂得自己“这一个”,就不会找到自己的“时尚”,多少随风而起的时髦,到头来不过是幻梦一场。这一组关于时尚的闲谈,承方成先生不弃,都为作了妙图。一生能与一位漫画大家合作,已是大幸,而我竟能得三,可说是“殆天数,非人力”了。
在同丁聪先生合作的同时,我又有机缘认识了一位国画家——黄永厚先生。永厚先生是黄永玉先生的胞弟,排行老二。原先在合肥,是安徽画院的画家,这时来到北京暂住。
永厚先生好读书,且兴趣广泛,几乎无书不读。交往渐多,熟络起来,有时他读书读到会心处,会忽然打个电话来,把他觉得有趣、有味的精彩段落或他读后在书边写下的心得念给我听。只是他那湘西不是湘西、合肥不是合肥的读音,常常使我不知所云。而他读毕,便是一句“怎么样?精彩吧!”或者“好,就这样吧”。于是电话挂断。直到我去他家看到那段话的文字,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画了什么。他大哥黄永玉有言:“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吾家老二有此风骨神韵。”这是实情。
那时,他已有不少仰慕者登门求画,但他最大的兴趣仍是读书,读得兴起,便铺纸作画。许多画题就是读书的心得。
有段时间,他忽然对“竹林七贤”有了兴趣。从山涛、嵇康、阮籍、刘伶,到王戎、向秀、阮咸,画了个遍,还饶上一个“搭头”吕安。一个人物一张图,图上跋文满纸,发表着他对人物的评论,而那龙飞凤舞的书写,竟与图画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他的特点,也是我初次看他图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阮籍》黄永厚 作
有一天,他忽然把他画的《竹林七贤图》寄给我。同他的其他画一样,题跋满纸,都是他对“七贤”的评论。譬如,《嵇康图》画的是嵇康被杀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情景。跋语是:汤武统一脑袋,周礼规定等级秩序。“非汤武”是独立思考(这一条大家同意顾准一人够份);“薄周孔”则争的是人格了。而他的越名教、任自然,绝非我们脑子里装着汤武,行为上不出周礼,口里嚷嚷回归自然那么闹着玩儿,却是搭着性命的。
这些评论是他对这八位为人处事的思考。只是画面有限的题跋,读者很难看懂。若要读者读出味道,必得要做解说。于是征得黄先生同意,便从山涛做起。“七贤”,再加上同他们(至少同嵇康、向秀)大有关系的吕安,一共写了八篇。之后,我意犹未尽,觉得中国的文言小说,《世说新语》当推第一,何不继为之“说”?那时京沪等地的几家报刊索稿,于是同黄先生相约,依旧是我说我的,他画他的。“说”不必同于“画”,“画”不必同于
“说”。这样就开始了“《世说》闲评”。周实兄是我和永厚先生共同的朋友。这时,他正为新创办的《书屋》杂志索稿。湖南是永厚先生桑梓之地,我虽不是湘人,但也在湖南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八九年时间,结识了许多朋友。于是,同永厚先生商定,就《儒林外史》作“错读儒林”,依旧是一文一图,交由《书屋》审发,最后结集成两部书稿——《魏晋风度》与《错读儒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丁聪先生停笔后,《读书》编辑部仍想把图文并茂的形式继续下去。这事又落在了永厚先生和我头上。永厚先生调侃道:“什么事儿啊,先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跑第一棒,现在又找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跑第二棒。真有你的!”这个有趣的接力,便是我同永厚先生在《读书》上的专栏《画说·说画》:先有文字的是画说,先有图的是说画。这个“接力”,是我的幸运,更是我们对丁聪先生的共同怀念。
前不久,黄永厚先生也去世了,方成先生也去世了,我也行年八十。回想此生能同这样四位前辈画家合作,真是难得的际遇,也是难得的幸运。
少时读欧阳修《祭石曼卿文》,有“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又有“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最为动人的是“感念畴昔……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怀想华、丁、黄、方四位先生,这些感人语句,倏然又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