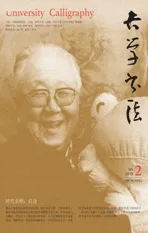书画创作
2019-02-12启功自述本文选自启功全集第9卷
启功自述(本文选自《启功全集》第9卷)
很多人认识我是从书法开始的,在回顾学术及艺术历程时,我就从这里说起吧。
如前所述,我小时是立志做一个画家的,因此从小我用功最勤的是绘画事业。在受到祖父的启蒙后,我从十几岁开始,正式走上学画的路程,先后正式拜贾羲民先生、吴镜汀先生学画,并得到溥心畲先生、张大千先生、溥雪斋先生、齐白石先生的指点与熏陶,可以说得到当时最出名画家的真传。到二十岁前后,我的画在当时已小有名气了,在家庭困难时,可以卖几幅小作品赚点钱,贴补一下。到辅仁期间,我又做过一段美术系助教,绘画更成为我的专业。虽然后来我转到大学国文的教学工作上,但一直没放弃绘画创作和绘画研究。那时也没有所谓的专业思想一说,谁也不会说我画画是不务正业。抗日战争后几年,我还受韩寿宣先生之约到北京大学兼任过美术史教员,当时他在北大开设了博物馆学系。当陈老校长鼓励我多写论文时,问我对什么题目最感兴趣。我说,我虽然在文学上下过很多功夫,而真正的兴趣还在艺术。陈校长对此大加鼓励,所以我的前几篇论文都是对书画问题的考证。到了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最高峰,在几次画展中都有作品参展,而且博得好评。如解放前参展的临沈士充的《桃源图》,曾被认为比吴镜汀老师亲自指导的师兄所临的还要好,为此还引起小小的风波。又如解放后,在由文化部主办的北海公园漪澜堂画展上,我一次有四张作品参展,都受到好评,后来这些作品经过劫波都辗转海外。有的又被人陆续购回。后来我又协助叶恭绰先生筹办中国画院,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为此陈校长特批我可以一半在师大,一半在画院工作。如果画院真的筹建起来,也许我会成为那里的专职人员,那就会有我的另一生。可惜的是画院还没成立起来,我和叶先生都成了右派。这无异于当头一棒,对我想成为一个更知名的画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我的绘画事业停滞了很长时间。一来因在画院为搞我最喜爱的绘画事业而被打成右派,这不能不使我一提到绘画就心灰意冷,甚至害怕,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二来在以后的工作中,特别强调专业思想,我既已彻底离开画院,那一半也就回到师大,彻底地成为一名古典文学的教师,再画画就属于专业思想不巩固,不务正业了。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文革”后期,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我有时又耐不得寂寞,手痒地忍不住捡起来画几笔,但那严格地说还不是正式的创作,只是兴之所到,随意挥洒而已。“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后,思想的禁锢彻底解除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时我的书名远远超过了我的画名,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我原来是学画出身。那时大量的“书债”已压得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我找不出时间静下心来画画。即使有时间,我心里也有负担,不敢画:这“书债”都还不过来,再去欠“画债”,我还活不活了?我的很多老朋友都能理解我的苦衷,挚友黄苗子先生曾在一篇“杂说”鄙人的文章中写道:“启先生工画,山水兰竹,清逸绝伦,但极少露这一手,因为单是书法一途,已经使他尝尽了世间酸甜苦辣;如果他又是个画家,那还了得?”此知我者也。所以“文革”后我真正用心画的作品并不多,有十余幅是为筹办“励耘奖学金”而画的,还有一张是为第一个教师节而画的,算是用心之作。
看过我近期作品的人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您为什么喜欢画朱竹?”我就这样回答他:“省得别人说我是画‘黑画’啊!”“黑画”一词,从广义上说可以泛指一切能供上纲批判的画,如反右时的“一枝红杏出墙来”之类的画;狭义的是说“文革”后不久,有些人画了一批画,如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被正式冠名为“黑画”。听我这样解释的人无不大笑。其实这里面也牵扯到画理问题。难道画墨竹就真实了吗?谁见过黑得像墨一样的竹子?墨竹也好,朱竹也好,都是画家心中之竹,都是画家借以宣泄胸中之气的艺术形象,都不是严格的写实。这又牵扯到画风。我的画属于传统意义上典型的文人画,意并不在写实,而是表现一种情趣、境界。中国的文人画传统渊源悠久,它主要是要和注重写实的“画匠画”相区别。后来在文人画内又形成客观的“内行画”和“外行画”之分:“内行画”更注重画理和艺术效果;“外行画”不注重画理,更偏重表现感受。如我学画时,贾羲民先生就是“外行画”画派的,而吴镜汀先生是“内行画”画派的,但他们都属于传统的文人画。而文人画都强调要从临摹古人入手,和解放后大力提倡的从写生入手有很大的区别。我是喜欢“文人画”中的“内行画”,所以才特意从贾先生门下又转投吴先生门下。我也是从临摹入手,然后再加入自己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追求的是一种理想境界,而不是一丘一壑的真实。我在《谈诗书画的关系》一文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
(元人)无论所画是山林丘壑还是枯木竹石,他们最先的前提,不是物象是否得真,而是点画是否舒适,换句话说,即是志在笔墨,而不是志在物象。物象几乎要成为舒适笔墨的载体,而这种舒适笔墨下的物象,又与他们的诗情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的东西。倪瓒那段有名的题语说他画竹只是写胸中逸气,任凭观者看成是麻是芦,他全不管,这并非信口胡说,而确实代表了当时不仅只倪氏自己的一种创作思想。
就我个人的绘画风格来说,是属于文人画中比较规矩的那一类,这一点和我的字有相通之处,很多人讥为“馆阁体”。但我既然把绘画当成一种抒情的载体,那么我就对那种充满感情色彩的绘画和画家都非常喜欢,比如我在《谈诗书画的关系》一文中又说:
到了八大山人又进了一步,画的物象,不但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几乎可以说他简直是要以不似为主了。鹿啊,猫啊,翻着白眼,以至鱼鸟也翻白眼。哪里是所画的动物翻白眼,可以说那些动物都是画家自己的化身,在那里向世界翻白眼。
我又在《仿郑板桥兰竹自题》中写道:
当年乳臭志弥骄,眼角何曾挂板桥。头白心降初解画,兰飘竹撇写离骚。
这首诗不但写出了我对绘画情感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我的绘画生涯:我从小受过良好全面的绘画技法的训练,掌握了很不错的绘画技巧,但对绘画的艺术内涵和情感世界直到晚年才有了深刻的理解,可惜我又没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我所喜欢的这项事业,只能偶尔画些朱竹以写胸中的“离骚”了。
我从小想当个画家,并没想当书法家,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书名远远超过画名,这可谓历史的误会和阴差阳错的机运造成的。
了解我的人常津津乐道我学习书法的机缘: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表舅让我给他画一张画,并说要把它裱好挂在屋中,这让我挺自豪,但他临了嘱咐道:“你光画就行了,不要题款,请你老师题。”这话背后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看中了我的画,但嫌我的字不好。这大大刺激了我学习书法的念头,从此决心刻苦练字。这事确实有,但它只是我日后成为书法家的机缘之一,我的书法缘还有很多。
我从小就受过良好的书法训练。我的祖父写得一手好欧体字,他把所临的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作我描模子的字样,并认真地为我圈改,所以打下了很好的书法基础。只不过那时还处于启蒙状态,稚嫩得很,更没有明确地想当一个书法家的念头。但我对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也像一般的书香门第的孩子一样,把它当成一门功课,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阅帖和临帖。所幸家中有不少碑帖,可用来观摩。记得在我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一个人蹲在屋里翻看祖父从琉璃厂买来的各种石印碑帖,当看到颜真卿《多宝塔》时好像突然从它的点画波磔中领悟到他用笔时的起止使转,不由地叫道:“原来如此!”当时我祖父正坐在院子乘凉,听到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地自言自语,不由地大笑,回应了一句:“这孩子居然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屋里屋外的人忽然心灵相感应了一样,其实,我当时突然领悟的原来如此的“如此”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这“如此”是否就是颜真卿用笔时真的“如此”,我更难以断言。而我祖父在院子里高兴地大笑,赞赏我居然知道了究竟,他的大笑、他的赞赏究竟又是为什么,究竟是否就是我当时的所想,我也不知道,这纯粹属于“我观鱼,人观我”的问题。但那时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就好像修禅的人突然“顿悟”,又得到师傅的认可一般,自己悟到了什么,师傅的认可又是什么,都是“难以言传,唯有心证”一样。到那年的七月初七,我的祖父就病故了,所以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通过这次“开悟”,我在临帖时仿佛找到了感觉,临帖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出现了上一段所说的事,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再是简单地好好练字了,而是促使我决心成为书法的名家。到了二十岁时,我的草书也有了一些功底,有人在观摩切磋时说:“启功的草书到底好在哪里?”这时冯公度先生的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这是认识草书的人写的草书。”这句话看起来好似一般,但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鼓励和重要的指正,我不见得能把所有的草书认全,但从此我明白要规规矩矩地写草书才行,决不能假借草书就随便胡来。这也成为指导我一生书法创作的原则。二十多岁后,我又得到了一部赵孟頫的《胆巴碑》,非常喜爱,花了很长的时间临摹它、学习它,书法水平又有了一些进步。别人看来都说我写得有点像专门学赵孟頫的英和(煦斋)的味道,有时也敢于在画上题字了,但不用说我的那位表舅了,就是自己看起来仍觉得有些板滞。后来我看董其昌书画俱佳,尤其是画上的题款写得生动流走,潇洒飘逸,又专心学过一段董其昌的字。但我发现我的题跋虽得了些“行气”,但缺乏骨力,于是我又从友人那里借来一部宋拓本的《九成宫》,并把他们用蜡纸勾拓下来,然后根据它来临摹影写,虽然难免有些拘滞,但使我的字在结构的谨严方正上有不少的进步。又临柳公权《玄秘塔》若干通,适当地吸取其体势上劲媚相结合的特点。以上各家的互补,便构成了我初期作品的基础。后来我又杂临过历代各种名家的墨迹碑帖,其中以学习智永的《千字文》最为用力,不知道临摹过多少遍,每遍都有新的体会和进步。
随着出土文物、古代字画的不断发现和传世,我们有幸能更多地见到古人的真品墨迹,这对我学习书法有很大的帮助。我不否认碑拓的作用,它终究能保留原作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好的碑刻也能达到传神的水平,但看古人的真品墨迹更能使我们看清它结字的来龙去脉和运笔的点画使转,而现代化的技术使只有个别人才能见到的秘品,都公之于众,这对学习者是莫大的方便,应该说我们现在学习书法比古人有更多的便利条件,有更宽的眼界。就拿智永的《千字文》来说,原来号称智永石刻本共有四种,但有的摹刻不精,累拓更加失真,有的虽与墨迹本体态笔意都相吻合,但残失缺损严重,且终究是摹刻而不是真迹;而自从在日本发现智永的真迹后,这些遗憾都可以弥补了。这本墨迹见于日本《东大寺献物账》,原账记载附会为王羲之所书,后内滕虎次郎定为智永所书,但又不敢说是真迹,而说是唐摹,但又承认其点画并非廓填,只能说:“摹法已兼临写。”但据我与上述所说的四种版本相考证,再看它的笔锋墨彩,纤毫可见,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是智永手迹,当是他为浙东诸寺所书写的八百本(千字文)之一,后被日本使者带到日本的。现在这本真迹已用高科技影印成书,人人可以得到,我就是按照这个来临摹的。在临习各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融会贯通和独自创造,我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风,我不在乎别人称我什么“馆阁体”,也不惜自谑为“大字报体”,反正这就是启功的书法。当然我的书法在初期、中期和晚期也有一定的变化,但这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发展的。
和我学画时正式拜过很多名师不同,我在学书法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能称得上以老师的名义向他请教的并不多,近现代书法大师沈尹默(字秋明)算一个。他也是老辅仁的人,所以有很多交往的机会。他曾为我手书“执笔五字法”,并当面为我讲解、示范,还对我奖掖有加,夸奖过我的书法,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多少年后,新加坡友人曾得到沈尹默先生所书的一卷欧阳永叔(修)文,请我题跋,我还不由地以满腔的深情回忆道:
八法一瓣香,
首向秋明翁。
昔日承面命,
每至烛跋空。
忆初叩函丈,
健毫出箧中。
指画提按法,
谆如课童蒙。
信手拾片纸,
追蹑山阴踪。
戏题令元白,
纠我所未工。
至今秘衣带,
不使萧翼逢。
……
还有张伯英先生,我曾多次登门求教,看他写字,听他讲授碑帖知识,获益匪浅。老先生对书法事业的热情以及对后辈诲人不倦的关切令我感动。其他的前辈对我也有所指点,像前边所说的冯公度对我草书的评价。还有一位寿玺先生,号石公,书画篆刻都很好。此人非常有意思,他管人都叫“兔”,他从来不说“这个人”“那个人”,而说“这个兔”“那个兔”。比如他夸奖某人的扇面画得好就说:“这兔画得还不错。”日久天长大家都反过来叫他“寿兔”。我曾恭敬地向他请教,称他为“寿先生”,他生气地对我说你不该对我这么谦恭,把我臭骂一顿,骂得我还挺舒服。通过我的经历,我觉得练习书法最重要的还要靠自己长期刻苦的努力。
有人总喜欢问我学习书法有什么经验或窍门。我首先可以奉告的是要破除迷信。自古以来书法已成为“显学”,产生了很多“理论”,再被一些所谓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一炒,好些谬论也都成了唬人的金科玉律,学习者千万不能被他们唬住。比如握笔,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虽然有一定的方法,但绝没有那么多神秘的讲究,有人现在还提倡“三指握管法”,称这是古法。不错,这确实是古法,而且古到当初席地而坐的时代,那时没有高桌,书写时,左手执卷,右手执笔,三指握管(犹如今日握钢笔)的姿势,正好和有一定倾斜的左手之卷呈九十度,非常便于书写。而有了高桌之后,人们把纸铺在水平的桌上,这时再用三指握管法就不能和纸面呈垂直状态,不便于软笔笔锋的运用。那些人不明白这基本的道理,还在提倡“三指握管法”为“高古”,并想当然地说“三指握管法”是拇指在内,食指、中指在外的握笔姿势。更有甚者,还有提倡所谓“龙睛法”“凤眼法”的,说三指握笔后虎口呈圆形的为“龙睛法”,呈扁形的为“凤眼法”。还有人在如此执笔的同时,尽力地回腕,把手往怀里收,可惜不知这叫什么方法,权且叫它“猪蹄法”吧。最可笑的是包世臣《艺舟双楫》记载的刘墉写字的情况:他为了在外人面前表示自己有古法,故意耍起“龙睛法”,还要不断地转动笔管,以致把笔头都转掉了,这不是唬人是什么?难怪刘墉的字看上去那么拘谨。人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王羲之在看儿子写字的时候,在后面突然抽他的笔,但没抽下来,不禁大加称赞。于是有人又借此编织神话,提出所谓要“握碎此管”和“指实掌虚”之说——指要握得实,而且要握得有力,有力到恨不得把笔管握碎才好,而手掌要虚,虚到能放下一个鸡蛋才好。这不是唬人吗?对此苏东坡有一段精彩的评论: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王羲之)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幼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苏轼不愧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聪明人,我们要向他学习这种勇于破除迷信的精神。一个握笔有什么可神秘的,在我看来就像握筷子一样,怎么方便,怎么舒服,怎么便于使用,就怎么来好了。
至于悬腕、运笔、选帖、择笔等也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如有人说不但要“悬腕”,还要“平腕”,练习的时候要在手腕上放一碗水,让它不洒才行,请问这是写字还是耍杂技?运笔讲究提顿回转,这本不错,但有人硬说写一横要按八卦的位置走,“始艮终乾”(艮和乾都指八卦的位置),请问这是写字还是排八卦阵?还有人说只有练好篆书才能练隶书,练好隶书才能练楷书,练好楷书才能练行书、草书,这貌似有理,但怎么才叫练好?难道学画蝴蝶必须先从画蛹开始吗?这是写字还是子孙传代?有的人字还没练得怎么样呢,就先讲究笔的好坏,有些人还把不同质地的笔的功能差异说得神乎其神,还以用稀奇古怪的质地为尚。其实善书者不择笔,我80、90年代最喜欢用的是衡水地区产的七分钱一支的笔,一下就买了二百支。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先破除迷信才行。
至于具体的方法我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如碑帖并重,尤其要重视临帖。碑拓须经过书丹(把字形描到石头上)、雕刻、毡拓等几道工序才能完成,每道工序都要有一次失真,再加上碑石不断风化磨损,所以笔画还会有一些变形,拓出后有的出现断笔,有的出现麻刺。可笑的是有人在临帖时还故意模仿,美其名曰“金石气”。我小时看到兄弟二人面对面地临帖,每写到碑上出现拓残的断笔时,哥儿俩就互相提醒,嘴里还念念有词:“断,断!”那时还觉得挺神秘,现在想起来真可笑,不妨称它们为“断骨体”。还有人故意学那麻刺,我戏称它们为“海参体”。有些魏碑的笔画呈外方内圆的形状,临摹者刻意模仿,写出的字都像过去常使用的一种烟灰缸,我戏称它为“烟灰缸体”,殊不知这种笔道是无奈的刀刻的结果。当然碑的功劳不可灭,好的碑拓基本能保留原作的风貌,虽然笔墨的干湿、枯润、浓淡以及细微的连缀难以传真地再现,但结字的间架还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多临摹还是有好处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通过刀锋看笔锋”,想象其墨迹的神态。而临帖则不同了,帖保留了原作墨迹的实际状况,更何况现在高科技十分发达,可以毫不失真地把它们复制下来,供我们随意使用,为我们“师笔不师刀”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
再如用笔与结字并重。赵孟頫曾有名言:“书法以运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这似乎已成为书法界的共识。但我以为不然:书法当以结字为先,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而运笔与结字的关系又可以通过临摹碑帖得到统一,即运笔要看墨迹,结字可观碑志。再如“不师今人师古人”。效法今人也许便于立竿见影,但也容易拾人牙慧,从人乞讨,误入“邯郸学步”的歧途。而古人的作品,特别是那些经过时代考验的作品,却是今人学习的永恒基础,可以保证我们有正确的审美观念而不至于走火入魔。当然师古人的时候也要有所选择,别以断骨体、海参体、烟灰缸体为尚就是了。
《启功全集》(第9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