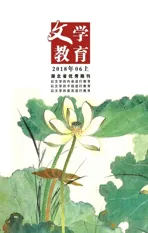论池莉小说《霍乱之乱》的内聚焦叙事
2018-11-29陈明锦徐礼诚
陈明锦 徐礼诚
《霍乱之乱》是作家池莉1997年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讲述了某地防疫站应对一次突发霍乱疫情的故事。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各具特色,作品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性。而这种魅力的产生,与作家采取了第一人称固定内聚焦叙事模式具有极大关联。
在内聚焦叙事中,叙述者仅仅讲述作品中某个人物所知道的情况,而无法叙述人物自己不知道的内容,其叙述严格地限制在人物所感受的范围之内。这种叙事模式的全部内容都是以故事中某个人物的角度来观察和叙述的,《霍乱之乱》的视角自始至终都来自“我”这个防疫站青年医生,属于第一人称固定内聚焦叙事。
一.叙事中的曲折情节:中心矛盾牵连着各种问题的沉浮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防疫站消灭霍乱疫情,矛盾冲突的双方是防疫医护人员和烈性传染致命病毒。但在“我”的固定内聚焦叙事中,推动着矛盾发展的连带问题显得更加有趣。在中心矛盾从发生发展到解决的叙事脉络中,一个个小矛盾曲折摆动着整体情节,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读完了全文。
1.站院矛盾。首先浮现的矛盾冲突是防疫站和挂靠医院各处室之间的紧张关系,防疫站工作得不到医院最起码的支持。“我”和秦静值班时要去医院供应室换储槽,但是洗衣房和供应室根本看不起防疫站,百般刁难。“我”对该事的叙述充满了无奈和愤怒。视去供应室换储槽碰上小谢为“不幸”,“非常倒霉的事情”。然而去供应室还是碰上了小谢,她“用她漂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傲慢地耸着肩膀”,拒绝换储槽。我受了一肚子气后回到防疫站,把空储槽盒推给主任让他处理。“凉凉的金属储槽盒在闻达的怀里仿佛变得滚烫,他的手哆嗦着,惊慌地四处寻找放下它的地方。”储槽心结成了叙述者展现站院矛盾的最佳意象。霍乱突发,防疫站成了全院乃至全市上下的救星,赵武装打电话要医院食堂准备夜餐无果,闻达当即找到医院院长亲自下命令。防疫站的设备设施一夜间也都“旧貌换新颜”,“简直比神话还不可想象”。后来要去封锁疫点,储槽不够,“我”和秦静“既客气又优雅,装出有几分怕她的样子”,找供应室的小谢拿来了五只大储槽。即便最后消灭了疫情,叙述者也没忘交代站院之间的财产归属纠纷,防疫站没用完的储槽也被医院供应室要求还回,“一切都恢复了从前的平静和单调”。
2.秦赵关系。疫情中心矛盾带出的另一个较为完整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秦静和赵武装展开的。随着疫情的发生、发展、消灭,秦赵关系也经历了一次接近、亲近、冷淡的过程。疫情发生那晚,赵武装一开始是来向值夜班的秦静献殷勤的,而秦静始终没怎么搭理赵武装。等到疫情警报召回防疫站所有人员连夜赶回站里时,秦赵距离逐渐接近,他们会在一起商量该准备哪些东西,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这个阶段,叙述者一直都是深度介入的,认为这是“特殊的时候可以催生爱情”。再后来,流行病室需要连夜出发追踪病人和确定疫点,秦赵二人又在车上因为寻路找人发生争执,反而拉近了距离。这时,叙述者坦白道:“大家都有一点头脑发热了。”
在疫点消杀排查病毒时,秦静的专业性责任感和赵武装对待疫情的随意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秦静关注的是疫情,而赵武装在乎的是人情。秦静脑子里盘算着该如何更高效地开展工作,排查病患,赵武装却因为闻达表扬了秦静而到处找“我”道歉,连叙述者也忍不住表态:“赵武装懂事也太懂过分了一些。我讨厌这样的男人。”性格和人生选择的差异终于成为秦赵关系的鸿沟,两人关系的最后结果便是不了了之。
叙述者没有兴趣注意却有意注意的矛盾冲突还包括医患间和官民间的紧张感,这些瞬时出现却潜藏已久的社会矛盾冲突在“我”的短时间活跃参与下得以浮现,叙述者拨弄着这些问题起起伏伏,沉稳地控制着小说节奏,不断推动着情节发展。
二.叙事中的正面人物:可信的叙述者塑造了伟大的灵魂
聚焦可用来表达感知或认识的立场,小说用内聚焦叙事表现出闻达、秦静这对老少医生爱岗敬业的美好品质,信息的传递从另一位青年医生的视点进行,显得十分可信。
1.闻达。闻达是防疫站流行病室主任,新中国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流行病学专家,有着丰富的流行病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所有的流行病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防疫专家,工作条件却如此恶劣,妻子埋怨他,领导漠视他,连作为下属的“我”和秦静也不无好笑地作弄他。看到闻达下班后仍在办公室撰写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叙述者暗自窃喜道:“闻达的推迟下班对我们是有利的。我时常利用他替我们坐科室,而我们去尽快地做完例行的工作。”这种作弄老好人的心理恰好是两种对待防疫工作的不同态度:闻达当工作为事业,两个小姑娘眼下还只当它是职业。
也正是闻达的糟糕处境,让青年防疫工作者更加没有事业热情。叙述者“多么希望从前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现在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和我们生活的美好。现在这个样子的闻达,应该说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未来对理想的信心和我们对现实的态度”,可信的叙述者表现为叙述者的信念、规范和隐含作者一致,这番可信叙述更加真实地反映了闻达正长期身处困境,也就更能反映出后来闻达功成名不就反而受指责时淡泊宁静的可贵。
然而闻达毕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现实中也不会有那么完美无缺的人物。当“我”奉命赶到闻达家里汇报疫情时,闻达立即开始“用命令的口气”跟妻子说话,到了防疫站后也敢对领导大呼小叫了。在叙述者眼中,这已经不是往日那个埋头书桌钻研病情的老学究了,他长期以来的研究心血终于有了施展的空间,在这场防疫攻坚战中掌握了绝对权威,也一点没有谦让客气的态度。等到去疫点进行封锁时,闻达那种急躁专断的性格缺点再次暴露出来,他既无法统筹各职能部门派出的人员,也无法平复疫点居民惶恐的内心。叙述者距离闻达不远不近地观察,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虽然情商有限但事业热情无穷的流行病防治专家。
2.秦静。秦静是小说中距离叙述者最近的一个人物。作者采用的固定内聚焦模式,单一地从“我”这个秦静的同学兼同事的人物角度,非常完好地再现出防疫事业新生代工作者的成长、成熟。
秦静和“我”是医学院同学,学习期间便对流行病有着较执着地探寻。分配到防疫站后,枯燥又不受待见的工作并没能销蚀她的积极性,她不甘平庸,准备改行投靠一位著名病毒学家的研究生。接到疫情电话后,“我”不知所措,她却能拿来随身的教材找寻信息,并冷静坚定地向门诊医生布置任务。秦静的专业表现让“我”刮目相看,叙述者细腻的心理流动起来,佩服她“关键时刻居然说得这么流畅这么冷静”。
秦静形象最集中升华的地方是在封锁区,她尖锐地当面指责疫点居民的过失,清醒地提出分组检测的建议。叙述者承认“秦静率领的小分队工作效率最高”,“嗓音里透出的是那种高学历高年资医生的威严和魄力”,“相比之下,我只能服气”。而这个时候的秦静,思想上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她激动地感慨道:“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工作太有意义了,我觉得我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得心应手的工作”。透过叙述者的眼和主人公的嘴,读者感受到了防疫事业接班人终于在实际工作中成熟了,她不再思考着改行的问题,也不会因为事后没受到表彰而感到失落。小说结尾交代了秦静还有闻达一直留在防疫站,他俩合作的论文最终在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上宣读,得到了广大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如叙述者之前惊讶的,秦静“在哪一点上有一点儿像闻达”。虽然两人都有那么一点不通人情,但他们的事业信念都是执着的,至此,两代防疫工作者的光辉形象便印刻了下来。
小说同时也塑造了另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力图摆脱窘迫现状的赵武装、有行政威权没业务实力的各级领导等,当读者通过小说的内聚焦透视这些人物时,其实看到的正是“我”这个内在性的外在世界,对他们的认识实际上也就体验化了。
三.叙事中的严肃主题:审视人生道路的抉择和崇高人性
故事在一个闷热潮湿的雨夜拉开帷幕,而在人际互动中产生的是另一种背景——浮躁的社会风气。霍乱之乱不仅是应急管理时的场面混乱,同时也反映了物欲横流中人心的纷乱。因为是内聚焦叙事,小说的真实感大大得以加强,不过这种真实感伴随着严肃的陌生化和荒诞性,故而能产生很大的思考空间。
作家池莉曾经从事医务工作,不止一次地遇到过霍乱,这种“经历过的东西隔了时间的距离”让她感到格外亲切,可对于读者来说却极具陌生化效果。小说在叙述者亲切的回忆中缓缓展开,医学院的学习片段、防疫站的工作环境、封锁区的紧张气氛,这一幕幕场景走马灯般旋转,每一处都不是普通读者能现实触摸的,每一处也都充满与常识不符的情形,给读者一种荒诞感受。
比如说,本该作为防疫战线最前沿阵地的防疫站不仅设备缺乏,人员的工作状态也令人担忧,勤奋者如秦静想着转行,麻木者如“我”得过且过,钻营者如赵武装试图跳出怪圈,这一张张面孔无不反映着防疫事业的惨淡现状和前景。内聚焦叙事控制了叙述者的活动范围和权限,从形式上消除了叙述者和读者的不平等关系,让他们有了相同的所见所闻,可读者的期待视野毕竟不同于叙述者,所以当后者用一种淡漠的语调叙述防疫站的荒诞气氛时,读者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新奇,进而是紧张和无奈,最终会是忧虑和思索。
叙述者在小说结尾严肃地反思道:“我实在是没有勇气为了消灭什么而遭遇什么,为了不可知的结果而长久地等待,为了保存内心而放弃外壳。”这种自我审视,能发挥第一人称固定内聚焦叙事常有的效果,将“我”放在一个陪衬的角色突出中心人物,这样读者更会因闻达的坚守和秦静的进步而真心高兴。物欲泛滥中人生该如何抉择?是像闻达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事业,还是像赵武装那样汲汲于富贵?叙述者满是温情的回忆已经说出了答案,表现出对坚守信念者的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