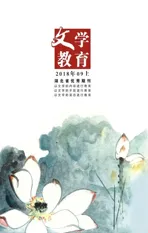浅论《呼兰河传》中的审美意象描写
2018-11-28张淑杰
张淑杰
萧红的《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个人立传,也不是为呼兰河这条河流立传,而是为在松花江和呼兰河北岸一座名为“呼兰河”的小城立传i。她用散文化的笔触,从儿童、成人及自身三重视角ii,展现出二十世纪十年代前后“北中国”乡民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寄托了对家乡的独特情感,书写着对千千万万苦难愚民的哀婉与关怀。
杨迎平评价《呼兰河传》说:“作者通过戏剧艺术的讽刺批判、散文艺术的怀念倾诉、诗歌艺术的吟唱咏叹、电影艺术的影像书写这些陌生化的叙述,使读者对呼兰河小城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国民惰性产生惊讶和好奇心。”iii关注到《呼兰河传》对各种文体艺术融会贯通的一面。萧红自己也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iv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价更是广为人知:“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水画,一串凄婉的歌谣。”v的确,萧红不仅以散文化的笔调展开叙述,同时在意象的选取组合与描写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本文关注的正是萧红在审美意象选取组合与描摹上的特色。作者描绘着看似杂乱实则构成有机联系的“白色审美意象组合”,并借鉴色彩艺术中“白与黑”的对比技巧,呈现出文本张力及背后的现实张力,将自身情感与理念蕴含其中。同时,本文将结合色彩心理学的知识,论述这种“白立于黑”的状态给读者带来更强心理冲击的可能性。
“白色审美意象组合”,指小说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白色事物——“豆腐”、“白兔”、“小白牙”三个相互独立又内含联系的审美意象所构成的有机组合。
“白立于黑”,指作者将这些有代表性的白色审美意象凸显于呼兰河这片黑土地之上进行描写,所形成的色彩状态。
下文将在对“白色审美意象组合”进行阐释后,具体论述白与黑的色彩对立状态所具有的文本张力与现实张力,并进一步分析这种色彩状态蕴含的作者生命体验,以及其给读者带来更强心理冲击的可能性。
一.“白色审美意象组合”的具体阐释
审美意象是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在某些理念和抽象思维制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与多义性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vi
“白色审美意象组合”中的“豆腐”、“白兔”、“小白牙”三个审美意象各有其丰富的内涵及特征。
“豆腐”被小城百姓视为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使他们在物质上得到了卑微的满足。它也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用来计量财富的单位。不以鸡鸭鱼肉为美味,反而钟爱豆腐,体现出呼兰河老百姓的敝帚自珍,同时凸显出当地人民生活姿态之低。那一块块白净的豆腐,便在这片黑土地上更加耀眼,更不可或缺了。
“白兔”这一审美意象,是作者将其抽象思维参与到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揭示而构造出来的。小团圆媳妇哭喊着要回家,却至死都未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她幻化成了一只隔三差五就要到东大桥下哭泣的大白兔。它是温顺、弱小的象征,是小团圆媳妇悲惨命运的昭示,似乎也是作者寂寞、思乡的隐喻vii。“我”家的长工有二伯,苟活求生而备受嘲讽后,天天把“兔羔子”挂在嘴边。在梦中,“我”十分荒诞地将他变成了长着毛驴那么大耳朵的白兔。那一声声“兔羔子”,是他作为受难者的象征,也是他悲戚的呐喊。
“小白牙”这一审美意象和这片严寒的黑色土地进行抗争,有力地象征着在自然暴虐面前人的顽强生命力,似乎使人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冯歪嘴子的小儿子渐渐长出了小白牙,小家伙在与寒冷和饥饿的抗争中,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伸展着他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二.“白立于黑”的文本张力与现实张力
来自于自然宝库的色彩,很早就被我们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
中国很早就有了“五色”——黑赤青白黄。水墨画作品中的黑与白是不可分离的色彩组合。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色彩变成文人骚客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诗鬼”李贺是一位对色彩表达极为敏感的诗人,他尤其钟爱白色。陆游评:“如百家锦衲,无色炫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赵宦光《弹雅引》)viii
在西方,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黑白画十分流行。随后,雕版印刷画的传播,使人们将黑色、白色视为两种与众不同的色彩。17世纪下半叶,牛顿从光学的角度阐释了黑与白的重要性后(牛顿《光学》),更多人开始用黑与白表现色彩的魅力。ix
可见,白色与黑色对比组合的色彩艺术由来已久,它不仅在画作中得到应用,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接下来将要分析的,正是这种“白立于黑”的状态在小说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并提出本文对“此种色彩状态有何意义”的些许思考。
“白立于黑”的色彩状态,在《呼兰河传》中有何体现?又好在哪里呢?
首先来看必须谈及的第一个层面——文本张力。
“白色审美意象组合”中的“豆腐”、“白兔”、“小白牙”三个意象,与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及命运息息相关,彰显在这片黑色的土地上。作者通过展示这白与黑的对立,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促进对小说主旨的揭示。
小团圆媳妇的悲惨故事中,她的婆婆在“抽帖”时将豆腐作为了自己计算费用的单位:
十吊钱一张可不是玩的,一吊钱拣豆腐可以拣二十块。三天捡一块豆腐,二十块,二三得六,六十天都有豆腐吃。若是隔十天捡一块,一个月拣三块,那就半年都不缺豆腐吃了。她又想,三天一块豆腐,那有那么浪费的人家。x
随后,“云游真人”恐吓她说小团圆媳妇脚上被她弄的烙印若不消除,她也会被阎王爷带走。这时她便什么帐也不算,急急忙忙询问可以避祸的法子。最后硬生生被那“真人”忽悠走了五十吊钱。
小团圆媳妇的死亡似乎还不是最惨的结局,她的鬼魂来到了小城里的东大桥下面,变成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地就到桥下来哭。
有人问她哭什么?
她说她要回家。
那人若说:
“明天我送你回去……”
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
若没有人理她,她就一直哭,哭到鸡叫天明。xi
对小团圆媳妇来说,死亡并没有让她逃离地上的苦难,反而陷入一个无边的黑洞。那阴暗的世界里,是无边的恐怖与荒凉。作者借白兔这一温顺的动物来安排小团圆媳妇的结局,加大了文本所表现出的悲剧力量,增强了这一故事的情感穿透力,使女孩的可怜处境呈现得更掷地有声。那“回家”的声音直抵人们灵魂深处,可悲,可叹!小说的情感也在此达到了顶峰,将悲剧效果呈现得淋漓尽致。
“小白牙”这一意象在最后一章出现,直接与小说前两章描写的小城的荒凉与黑暗相对撞。开篇裸露在天空下的东北大地,与结尾咧露出来的“小白牙”,是两种相反因素的并置。正是这相反的对撞,构成了一种相互撕扯、对抗,而又相互交流的稳定文本结构。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xii。
看了冯歪嘴子的孩子,绝不会给人以时间上的观感。……
但是冯歪嘴子却不这样的看法,他看他的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大的。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给他东西吃,他会伸手来拿。而且小白牙也长出来了。
微微地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xiii
在色彩直观上,前者灰暗,后者洁白;在性质上,前者是毁灭并吞噬着一切的大自然的淫威,后者是反抗着大自然淫威而生长出来的人的刚强。小城中的光明与黑暗交替并存,共同构造出真实的人类生存境界。
其次,来看第二个层面——现实张力。
从整部作品来看,“白色审美意象组合”与黑色的大地相对立,在形成张力增强文本表现力的同时,服务于作者对呼兰河城里多彩而又刻板单调生活的描绘。展现出了呼兰河人民麻木、愚昧的内心,恪守传统不求改变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描写出他们的善良本质、顽强的抗争。小城百姓的生活代表着当时千千万万劳苦愚民挣扎而又甘愿堕落的矛盾生存状态,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
豆腐这一审美意象在第一章便已出现。“卖豆腐的人来了,男女老幼,全都欢迎。打开门来,笑盈盈的,虽然不说什么,但是彼此有一种融洽的感情,……”xiv买不起豆腐的人家,五岁的孩子说自己长大了要开豆腐房。甚至竟有想要倾家荡产买豆腐的:“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xv
作者通过豆腐这一与人温饱相关的味觉意象,展现出呼兰河人的实际生活状况xvi。于是,他们天天惦记着吃瘟猪肉,宁愿在路上留个大泥坑,凡事都依照礼教迷信来评判……这一系列行为都有了根源上的经济基础原因。
“我”家的长工——有二伯,看似知天命,仿佛看破了人生,说“活着是个不相干”,却极其渴望被别人看得起。老厨子说他头上的“有”字去掉后就剩“二爷”时,他便喜笑颜开。而当他最后发现自己的存在成了别人的笑料时,他的内心便彻底异化了。
“狼心狗肺,介个年头的人狼心狗肺的,吃香的喝辣的。好人在介个年头, 是个王八蛋,兔羔子……”xvii
小团圆媳妇的年华早逝,有二伯的苟延残喘,都是悲剧。从小说内容中可以发现,他们的悲剧是因抗争而产生的。在当时,对传统的反抗者大都以悲剧告终,要么心灵备受打击,如行尸走肉般苟活;要么直接因此丧命。小说通过对白兔这一意象的不同安排与表达,也反映出作者对这样一些反传统的先觉者们最后落得悲剧下场的愤懑。
可以说,小白牙这一意象形成的张力,构造起了呼兰河城乃至当时千千万万乡镇中劳苦愚民光明而又黑暗的生存世界。
呼兰河人对路上的大泥坑熟视无睹;邻里的“善良”断送了小团圆媳妇的性命,在她洗澡时大喊着加热水,又在她被烫晕后,一盆盆地泼冷水去“抢救”。……这些情节使人在发笑之后,随即感到一阵心酸甚至悲痛。
小说最后,作者虽然只用了匆匆几笔来描写小白牙这一意象,却让人看到了那微弱的曙光。整部小说似乎已营造出这势所必至的运笔方向,也正是这微弱的曙光,蕴含着作者在当时中国的苦难环境下对未来所怀有的光明希冀。
在论述第三个层面——读者心理冲击前,有必要先谈一谈“为何会产生‘白立于黑’的状态”这一问题,以便更好地论述其给读者带来更强心理冲击的可能性。
下文将从作者生命体验、创作理念与小说篇幅、人物塑造角度提出本文对“白立于黑”状态产生原因的解答。
三.“白立于黑”蕴含的作者生命体验与创作理念
1927年秋,萧红在祖父的支持下,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女子第一中学(原从德女子中学)。刚读初中一年级的她,便对美术与文学产生浓厚兴趣xviii。1933年3月,她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随后,在萧军的影响下,她开始了文学创作。xix
从萧红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她对美术兴趣浓厚,并且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刘恒在《文艺创造心理学》中提到:“文学作品中的色彩世界是作家创造的,这和自然界的色彩不一样,除了形态上和色彩丰富性存在着差异之外,主要是文学作品中的色彩具有作家审美的情感上的意义。”色彩变成了寄寓作家理性思考与情感内容的一种符号。
同时,从篇幅角度直观来看,作者对“白色审美意象组合”中豆腐、白兔、小白牙意象的描写,占据了篇幅的较大比例。“白立于黑”的色彩状态,不仅更好地描写了 “白色审美意象组合”,也与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命运揭示息息相关。
“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虽然目前尚未找到萧红本人直接谈及《呼兰河传》中色彩运用的资料,但至少可以据此提出:“白立于黑”的色彩状态有作者主观上掌控的可能性。
《呼兰河传》的创作,1938年开始于武汉,1940年12月在香港完成。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三号xx。在寂寞、苦闷又怀旧的心情中,她完成了《呼兰河传》的创作。感情之路再三波折的苦闷,对亲人的思念,孤身一人身处异地的寂寞,身体不适的烦闷……这些复杂的情感都被她融入了小说之中。
“豆腐”这一食物,让人嗅到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想回家却永远无法回家的“白兔”,或许象征着她的归乡呼喊,最终削弱成了微小的鼻息。结尾处的“小白牙”作为光明的象征,受时代呼声的影响,更是作者刻意为之,来暗示自己要有与死亡抗争的勇气。
最后,来看第三个层面——读者心理冲击。
四.“白立于黑”可能带来的读者心理冲击
作家在创作时,可以将色彩变成寄寓作家理性思考与情感内容的一种符号。
阅读文学作品时,富有色彩的审美意象会在我们脑中形成鲜活的画面,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加强我们的情感体验。下文将试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论述《呼兰河传》中“白立于黑”的色彩状态为何存在有增强读者心理冲击的可能性。
色彩心理学强调不同的色彩能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效应。俄国画家康定斯基专门谈到过不同色彩的不同心理效应:“白色对于我们的心理作用是一片毫无声息的静谧,如同音乐中倏然打断旋律的停顿。但白色并不是死亡的沉寂,而是一种孕育着希望的平静。”“相比之下,黑色的基调是毫无希望的沉寂。”xxi
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也体现出色彩的心理效应。读者阅读文本时,通过将书面语转化为自己理解的语言来进行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有颜色的、具体的审美意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读者将“干巴巴”的文字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的彩色图画。从而增强对作品的感性了解,进一步加深对作品主旨、对人生的理性思考。
白色与黑色一般与人们的情感有这样的联系:白色——洁净、单纯、明快、朴实、纯真、清淡;黑色——严肃、稳健、庄重、沉默、静寂、悲哀xxii。黑色的土地、灰暗的房屋、阴暗的天空,黑色是呼兰河城冬天里的基调。小城里杂多的事物中,白白净净的豆腐块备受钟爱,让读者看到他们生活窘迫的同时,也感受到平淡与朴实;小团圆媳妇变成了一只在冰冷的桥下整日哭泣的大白兔,这洁白而又温顺的白兔让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小团圆媳妇的同情,加强了对那些始作俑者的愤懑,情感达到了顶峰;那一颗颗小白牙,是生命力的象征,让读者看到了一缕曙光,获得一丝明快之感。
小说呈现出呼兰河城的千姿百态,让读者看到了小城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作者将“白色审美意象组合”凸显于黑土地之上,形成“白立于黑”的色彩张力,强化了读者在情感层面上“洁净、单纯、明快、朴实”与“静寂、严肃、沉默、悲哀”的抗衡,进而增强对读者的心理冲击。
“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xxiii色彩的象征意义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基于经济、历史、文化等条件的不同,存在着差异。但人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色彩形象作为心理基础又使人们对色彩的感受有着共同性。xxiv可以进一步提出,“白立于黑”的色彩状态,不仅有加强读者心理冲击的可能,而且有共同性与共通性,能够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
“白立于黑”的状态,体现出《呼兰河传》在意象描摹与组合上对色彩艺术的独特运用。从那些有色彩的文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小说的文本张力与现实张力,进一步感受其中蕴含的作者体验与理念,带来更强烈的心理冲击。
注 释
i 李重华.《呼兰河传》导读新论.[J].大庆社会科学.2011(1)
ii 杨迎平.论《呼兰河传》的三重视角——纪念萧红诞辰一百周年.[J].名作欣赏. 2011(35)
iii 杨迎平.《呼兰河传》:融汇各种文体艺术的奇文.[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1)
iv 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v 茅盾.《〈呼兰河传〉序》,《茅盾全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350 页
vi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29-230页
vii 董晓霞.《论<呼兰河传>中的白兔意象》.[J] 名作欣赏.2011(17)
viii 张明玲.《色彩文化》[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1. 第136页
ix [法]帕斯图罗著.张文敬译.《色彩列传:黑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
x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2版.哈尔滨出版社.2016.4.第260页
xi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 哈尔滨出版社.2016.4.第281页
xii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哈尔滨出版社. 2016.4.第167页
xiii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哈尔滨出版社. 2016.4.第323页
xiv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哈尔滨出版社.2016.4.第188页
xv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哈尔滨出版社.2016.4.第189页
xvi 张凤燕.《呼兰河传》中的意象分析[J].名作欣赏,2015(17)
xvii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哈尔滨出版社.2016.4.第300页
xviii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哈尔滨出版社.2016.4.第378页
xix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哈尔滨出版社.2016.4.第379页
xx 《萧红经典全集》萧红著.第2版.哈尔滨出版社.2016.4.第382页
xxi [俄]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5页
xxii 《美学原理》.编写组编《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1,.第121-122页
xxi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549页
xxiv 《美学原理》.编写组编《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1,第121-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