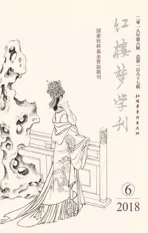章回小说与重复叙事
——以《红楼梦》为中心
2018-11-12
内容提要: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红楼梦》等经典名作的成功,恰与对章回体之文学可能的发现分不开。本文讨论了《红楼梦》中重复叙事的类型、功能与意义生成。小说内部的重复叙事有着不同的文体特征与文化属性,却又被小说家艺术性地组织为一个整体,互相对话又互相竞争。《红楼梦》和章回小说的文体学意义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由于与说话艺术的历史联系,章回小说形成了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具、韵散兼容的文体风貌。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与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章回体逐步被目为小说发展的桎梏。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曾这样批评:“章回的格式,本来颇嫌束缚呆板,使作者不能自由纵横发展,《石头记》《水浒》的作者靠着一副天才,总算克胜了难关,此外天才以下的人受死板的章回体的束缚,把好材料好思想白白糟蹋了的,从古以来,不知有多少!”实际上,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成功,恰与对章回体之文学可能的发现分不开。本文拟以《红楼梦》为中心,讨论章回小说中重复叙事的类型、功能与意义生成,从而重审章回体的价值和小说史意义。
一、重复叙事
重复叙事是热奈特在论述叙述频率时提出的概念。所谓叙述频率,“即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简言之重复关系)”。热奈特将叙述频率分为四种类型:(一)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二)讲述n次发生过n次的事;(三)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四)讲述一次发生过n次的事。热奈特认为,类型一和类型二属单一叙事,类型三属重复叙事,类型四属反复叙事(或称集叙)。
类型二的归属存在可商榷之处。热奈特将单一性定义为讲述次数和事件发生次数的相等。也就是说,类型二(讲述n次发生过n次的事)可以看成是n个类型一(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的集合。按照这个逻辑,“三顾茅庐”只是三次单一叙事,而非一组重复叙事。可见,热奈特所谓的重复仅指叙述也即话语层面的重复(类型三,如《罗生门》),而非事件层面的重复。原因在于,在热奈特看来,事件层面的重复是“思想的构筑”:一件事“多次出现的同一性严格说来是不可靠的”,是“去除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的结果。显然,热奈特对单一叙事和重复叙事的区分过于机械:类型二虽然从理论上可以被分解为n个类型一,但是n个类型一的集合却不能变成类型二,除非所讲述的事件之间存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正是重复的基础。
本文讨论的重复叙事包括事件重复和话语重复两类,也即热奈特所论的类型二和类型三。重复叙事大量存在于章回小说之中,原因不外乎文化与文体两个方面。从文化角度说,受循环时间观影响,章回小说常以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为基本框架,三生故事之间互相指涉、互相诠释,构成事件重复;另外,按照特殊数字衍生出来的情节系列内部,也构成事件重复,如“三顾茅庐”“七擒孟获”“八十一难”等。从文体角度说,源于说书艺术的楔子、头回以相对独立的故事揭示出正话(故事主体)的主题和情节概要,构成事件重复;而作为章回体基本特征的回目、“有分教”和部分韵文,承担预叙功能,构成话语重复。
本文讨论的中心是《红楼梦》中的重复叙事。可归入事件重复的包括:第一回中的补天神话、还泪神话和甄府故事等。可归入话语重复的包括:各回回目、第五回判词和套曲等。在一组重复叙事内部,一定有“同”有“异”。研究重复叙事,不能仅仅着眼于“同”,更要关注“同”中之“异”。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讨论了两种对于重复的态度:一为“柏拉图式的重复”,认为各类相似的事物背后存在一个纯粹的原型(idea),所有的实例仅仅是这一原型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完美的摹本;一为“尼采式的重复”,认为相似性只是“幻象”,“每样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与所有其他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无疑,以上两种态度均过于极端:前者将现象与本质对立起来,否定现象层面的千姿百态,热衷于追寻唯一的本原;后者则彻底否定相似性,实际上消解了重复本身。
当前学界并不缺乏对重复叙事的关注,不过,往往倾向于“柏拉图式的重复”。部分学者只关心那个丢失的本原(情节原貌/曹家历史/明清史事……),将诸多重复叙事的文本差异视为必须被穿越的迷阵;任何与其预设不符之处,均被斥为后人妄改或创作失误。这不但不符合《红楼梦》成书的历史过程,而且与文学接受的一般规律相抵牾。下面,本文将从文体角度入手,分析诸种重复叙事的“异”,进而探讨在相异的重复叙事之间,意义是如何生成的。需要说明的是,从“异”处着眼,并不意味着滑向“尼采式的重复”。对于重复叙事来说,“同”是文本的存在基础,“异”是文本的存在方式——二者相反相成,不可偏废。
二、事件重复
事件重复即“讲述n次发生了n次的事”,前提是事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红楼梦》第一回中的补天神话、还泪神话和甄府故事,均与正话之间构成事件重复,只是关联方式有所不同:两个神话与正话之间主要通过三世因果观念相关联;而将甄府故事与正话关联在一起的则是源自说话艺术的文体规约。虽然关联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体的差异同样客观存在,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双方互证互释。意义并非源自双方的叠加,而是生成于双方的差异之中。
(一)神话
神话与正话之间的重复关系无需多论:补天余石化身通灵宝玉,同时又因谐音而与贾(假)宝玉系联,因此,补天神话被视为贾宝玉的人生寓言/重复事件;神瑛和绛珠转世为宝黛,因此,还泪神话被视为宝黛的爱情寓言/重复事件。很少有人在解读贾宝玉思想或宝黛爱情时不对以上神话加以利用。不过,神话与正话之间存在鲜明的文体差异,在意义阐释时,不能将二者无条件等同。
无论补天神话还是还泪神话,都不是真正的神话,而是小说家利用神话元素而进行的艺术创作。学者们一般称之为拟神话或亚神话:“它只具有神话的外观或形式,已失去神话的‘根基’——即万物有灵的神话观念和主客体浑然不分的神话思维方式。”反过来说,虽然拟神话已失去神话的“根基”,但依然具有神话的“外观”——也即神话的文体形式。神话文体具有三个特征:宏大性、道德性和清晰性。与之相应,构成正话的世情小说文体同样具有三个特征:日常性、历史性和多义性。
神话文体的宏大性首先来自与时空相关的大词,时间词如“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空间词如“大荒山无稽崖”“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离恨天”“灌愁海”等;其次来自具有形而上学含义的数字,如“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在渲染宏大性之外,以上词语同时为神话的道德性奠定了基础。所谓道德性,指的是对是非善恶的明确判断。造人补天的圣王女娲氏必然不会出错,那么顽石无法入选补天,只能是由于自己无材。“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暗示出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那么绛珠草必须回报神瑛的灌溉之恩,哪怕是用一生的眼泪。在一个是非明确的寥廓空间之中,人物与故事具有清晰性:容易理解,不存争议。
与神话文体的宏大性相应,世情小说文体首先呈现出“琐碎细腻”的日常性,“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均需述记。生活细节的充盈使人物在小说中的存在获得了历史性,一言一行均可置于这一世的现实语境中加以理解——这不但使是非善恶的明确判断变得不再容易,更使正话中的故事脱离了前世因果的束缚,获得了独立性。宝玉不等于顽石,他的“似傻如狂”不是因为“无材”。黛玉不等于绛珠,她的眼泪不是为了报恩。是非明确的寥廓空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繁复多变的生活世界——在这里,多义性才是常态,对人物和故事的理解存在丰富可能。
神话与正话之间的重复关系,只有在明确了二者的文体差异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毫无疑问,含义清晰的神话与多义的小说无法简单等同。那么,是牺牲小说的多义性,以神话的道德性和清晰性来规训小说?还是颠覆神话的清晰性,以小说的历史性和多义性来反思神话?对于这个问题,清人已有疑问。姚燮说:“还泪之说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处,即还泪亦不足以极其缠绵固结之情也。”显然,还泪神话中的因果观念无法解释宝黛爱情的缘起,更无法把握天下之情的幽微之处。实际上,小说家并非借还泪神话来宣扬因果观念,而是借神话和正话的对比来质疑此种观念。同样,“无才补天”也不足以解释作为新人的贾宝玉和传统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正话的映衬下,神话的道德性和清晰性均被否定,更进一步获得了反讽意味。换句话说,神话的意义不在于为正话提供明确的阐释方向,而在于以被消解的方式呈现出对自身表层含义的反思。
(二)头回
头回,也称得胜头回或笑耍头回,是宋元话本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正话之前,先简略叙述一个与正话主题相同或相反的故事,构成正话的铺垫。甄府故事相当于《红楼梦》的头回。甲戌本第一回脂批已有此意:“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从小至大”,同时也是“以小见大”:正话的人物、情节均具体而微地浓缩于此。
从脂批开始,学者们对甄府故事与正话之间的重复关系多有发明,如甄士隐与贾宝玉最后均“悬崖撒手”、英莲的遭际象征全书女性的普遍命运、甄府贾府均在元宵节前后“烟消火灭”、《好了歌》揭示全书主题等。不过,大部分学者都是从互证互释的角度来理解二者之间的重复关系,并未关注到文体差异的存在。头回和正话虽然均属白话小说文体,但是由于说书艺术的历史影响,二者存在重要的区别。
与正话相比,头回文体具有三个特征:简明性、清晰性和合法性。回溯历史,头回产生于说书人的静场需要。观众刚刚坐定,说书人先以一个小故事来吸引其注意力,为正话的表演创造良好的剧场氛围。因此,故事必须篇幅短小,简明扼要,否则便会喧宾夺主;故事必须主题清晰,易于理解,否则不但无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且会妨碍正话的接受;同时,故事隐含的价值观不能与社会主流有太大出入——即使有标新立异的思想,也需留待正话来表达。
甄府故事符合头回文体的全部特征。如果不与正话相对照,那么它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化故事:情节简明扼要,人物缺乏个性,借世事无常以宣扬“一切皆空”的宗教思想。在通俗小说中,源自佛教的“一切皆空”早已获得与“忠孝节义”同等的合法性,融入了社会价值观的主流。既然甄士隐和贾宝玉的结局都是出家,那么头回的主题是否就等同于全书的主题?实际上,头回的主题渲染是建立在弱化情节与人物的基础上的,是头回文体特征的产物。甄士隐是典型的头回人物:有工具性,无主体性。他所能做的只是承受接踵而来的苦难,直至“悬崖撒手”。他的经历是典型的头回情节:命定性是情节发展的唯一动力。在他这里,出家是水到渠成和理所当然。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一切皆空”提供例证。
贾宝玉则不同。在正话中,他被小说家赋予了历史性和主体性:他存在于大量繁复的生活细节所搭建的文化逻辑和权力关系网络中,他的性格由来与发展均可在此现实语境中加以理解;在承受之外,他还在观察、在思考、在追求、在选择。这样一个人的出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发问:首先,如果“一切皆空”,那么他所经历的青春与美有何意义?其次,甄士隐的出家是因为看破世情,而根据庚辰本第二十一回脂批,宝玉的出家恰是因为有情:“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宝玉看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那么,情和空之间,到底是何关系?
由此可见,在头回中无可辩驳的“一切皆空”,一旦置入正话的丰富细节,立刻不那么理所当然了。本文不是要彻底否定“一切皆空”与《红楼梦》主题的相关性,而是想指出,细节和语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理解路径和阐释空间,从而也使任何进入小说的观念只能以反思性面貌被呈现。从头回到正话,并非简单的扩容,而是文体风格的根本转变:繁复性、多义性和反思性取代了简明性、清晰性和合法性。与正话并置,头回的单调与苍白立刻显现出来:其过于弱化的情节和人物无法支撑一个本就略显陈腐的主题,反而使后者陷入反讽之中——这正是小说家的意图所在。
三、话语重复
话语重复即“讲述n次发生了一次的事”。章回小说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其叙述的多元性:回目、韵文均可承担叙述功能,与正话构成话语重复。学界对此虽有较多关注,不过一般的做法是将不同叙述当成是本事的摹本,通过对众多摹本的研究,去伪存真,以还原文本表象背后的“真故事”。此种思路的缺陷有三:仅注重叙述的内容层面,忽视其话语层面或者说文体层面;仅注重不同叙述之间的互证互释,否定客观存在的差异;强调阐释的唯一性,窄化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实际上,与正话相比,回目、韵文源流不同,文体各异,即使叙述相同的内容,也可能产生意义的分歧。作品的意义,正是不同文体的不同叙述互相竞争、互相颠覆、互相补充的结果。
(一)回目
分回标目是章回小说最明显的文体特征。成熟期的回目多为双目,前后对仗,概括本回主要内容。回目是最完整的话语重复:由全书回目构成的小说目录,可以被视为对语形态的全书概要。如何处理回目与正文的关系,是小说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回目的主要作用“就是概括和揭示本回正文所写的内容的,因此,回目和正文所叙必须统一和谐,不能有不符或矛盾的现象出现”。这种观点完全将回目当成工具性要素,忽略了回目的文体特征和文学功能。
回目文体具有三个特点:叙述性、诗性与二元性。回目的叙述性源自其基本功能:对正文内容的概括。绝大部分回目从语法角度,都是一个叙述句。但是,回目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古典诗歌的影响:句法、炼字、用典、对仗……不能否认,“信”与“雅”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回目的诗化所带来的简洁、委婉与隐微有时会引起表意的分歧——这不是小说家的失误,而是诗化文体的共同属性。回目的二元性源自双目的对偶特征,并对正文产生一种反制的可能:仿佛每回正文也应由两个篇幅均匀的情节单元组成。同时,双目的形式也成为一种解读的提示:处于对偶地位的人物、事件之间或许存在一定的关联。
据《红楼梦》第一回,本书的创作过程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也就是说,《红楼梦》是先文后目,而非先目后文。小说文体的连续性和回目文体的二元性并不能完全兼容,因此,将一个连续的叙述流转写为若干二元性的回目,必须有一方做出妥协。于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了很多文目不符的例子:有的回目所说并非本回所写,有的回目所说和正文所写比例轻重失调,有的回目所标的内容同正文所写顺序恰好颠倒,等等。对于《红楼梦》回目,后人多有“拟改”,但是,无论如何修改都无法跨越文体间的鸿沟。
不过,如果承认文目差异的自然性,并加以有意运用,那么未尝不能从中挖掘出丰富的文学内涵。俞平伯在《谈〈红楼梦〉的回目》中说:“即以回目言之,笔墨寥寥每含深意,其暗示读者正如画龙点睛破壁飞去也,岂仅综括事实已耶。”此文对《红楼梦》文目不符背后的“微言大义”多有发明,如“与本文相违,明示作意之例”“句似未工,意义却深之例”“与本文错综互明之例”“主文在宾位不见回目之例”等,虽然不一定是对小说家本意的还原,但是却从阐释学角度提供了一种颇具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
与正文的冷静和克制不同,章回小说回目通常不回避对人物和事件表明态度。李小龙在《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中讨论了回目的“叙述者的画外音”功能:虽然章回小说一般禁止作者直接出现在作品的叙事世界里,但是回目却流露出作者的判断。孙逊在《〈红楼梦〉人物与回目关系之探究》中专门论述了回目中的“一字评”:“可以说每个字都下得非常准稳:袭人是‘贤’字,平儿是‘俏’字,晴雯是‘勇’字,探春是‘敏’字,宝钗是‘时’字,紫鹃是‘慧’字,湘云是‘憨’字,香菱是‘呆’字,凤姐是‘酸’字,不仅很好概括了每个人的品性和个性,而且都非常形象生动,真所谓换一字不可,颇让人拍案叫绝。”
两位学者均认为,回目中的人物评价是作者态度的正面表达。但是从清代以来,关于袭人、宝钗、薛姨妈等争议人物的“一字评”,读者一直争议不断。一种意见是,作者对袭人等的态度是负面的,所以回目错了,代表为陈其泰。他说:“以袭人为贤,欺人太甚。”因此将回目中的“贤”改成了“刁”。即使是今天,依然有学者从文目相符观念出发,认为“陈氏所批、所改也不能说就没有道理”。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虽然作者对袭人等的态度是负面的,但是回目没错:作者是明褒暗贬。从修辞层面看,这同样说得通。
“一字评”的确可能是作者态度的正面表达,但是却被《红楼梦》的接受史证明缺乏对读者的普遍说服力。原因在于,读者不会抛开正文来理解回目:正文的繁复多义为回目的理解提供了意指丰富的修辞语境,从而使释义的唯一性变得不可能。李小龙说:“由于作者写出了生活的原生态和人物的立体感,故对许多人物的许多行为,读者意见纷纭。……因此,回目中透露出的作者‘表态’值得我们注意。”实际上,回目中的作者“表态”无法解决读者的分歧,因为“生活的原生态和人物的立体感”也使读者对回目的理解变得“意见纷纭”。
因回目文体而引发的解释争议还有一例,即回目中的用典。用典的功能有二:一为美化词句,一为暗表心声。一处用典,往往可以兼有两种功能。由于用典本身的隐微性和功能的多重性,导致读者在解读回目时必须从繁复多义的正文中寻找支撑,从而导致了理解的分歧。第二十七回回目为“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在中立派的读者看来,这不过是化用“燕瘦环肥”的成语,以美化词句,如蔡义江所释:“我国古代美人中汉代的赵飞燕体态轻盈,唐代的杨贵妃(玉环)长得丰满,有‘燕瘦环肥’之称。故回目中借‘杨妃’比薛宝钗,‘飞燕’比林黛玉。”但对拥黛抑钗的读者来说,很难相信这不是作者在暗表心声。他们既舍不得放弃这个以杨妃暗讽宝钗的机会,又不愿因此而连累黛玉(因为杨妃和飞燕必须成对出现)。周汝昌说:“‘藤花榭本’‘飞燕’二字空白,必非无故,此等文笔,恐非出芹手。”此派读者内心的纠结可见一斑。
回目受诗歌影响,以用典的方式刻画人物本无可厚非。但是,回目的表意受正文制衡,一旦典故的歧义与正文发生冲突,便会引发读者的反弹。更重要的是,《红楼梦》正文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女性书写方式,使此回回目中的传统修辞相形见绌。换句话说,读者的反感并非来自以飞燕比黛玉这一事实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已被重塑的审美趣味无法再接受陈旧的表现方式。
(二)判词与套曲
如果说回目是《红楼梦》最完整的话语重复,那么第五回的判词和套曲便是最重要的话语重复:前者是章回小说文体的客观要求,后两者则是小说家的有意创造。根据小说描写,判词是记录在册的,置于题着“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大橱中;套曲则有所谓的“《红楼梦》原稿”,宝玉在“耳聆其歌”的同时也“目视其文”。《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均为本书题名之一,小说家分别用以指称判词和套语,证明了后两者和全书之重复关系的自觉性。正由于此,判词和套曲成为研究者理解人物、索隐探佚的重要依据。不过,此种思路仅注重事实重建,忽略了二者在作品中的存在语境。从上下文看,判词和套曲均为警幻受宁荣二公所托用以警醒宝玉、促其觉悟的手段,虽然其本事与小说相同,但其文体、命意、口吻、立场,均不能与小说等量齐观。
针对判词,甲戌本脂批云:“世之好事者争传《推背图》之说。……此回悉借其法,为儿女子数运之机。”《推背图》传为唐人袁天罡、李淳风所作,以图配诗,对历史发展加以预测。判词显然模仿了《推背图》的形式。从文体上看,判词属于谶诗,因而兼有谶语和诗歌的文体特征。首先是行文隐微:由于“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对未来的预测只能以谜语的形式委婉地表达出来,如“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自从两地生孤木”“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虎兕相逢大梦归”“一从二令三人木”等。阅读判词时,读者对智力的运用要优先于审美与同情。其次是意存褒贬:谶语不只是陈述事实,更需引导人趋吉避凶,因而有时会在叙述中隐含人物判断,如“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枉与他人作笑谈”“情既相逢必主淫”等。最后是感情节制: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传统影响,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方式通常比较含蓄;相应的,判词对人物命运的慨叹也比较收敛,通常仅以“堪伤”“可叹”“堪怜”“可怜”一类词语进行笼统的表达。
既然判词是小说的重复叙事,那么便有必要追索其背后的叙述者,而从判词文体中拼贴出的叙述者与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并不一致:他与人物的距离太远,姿态太高,抒情过于程式化——更重要的是,受文体所限,他对人物的评价过于空泛,甚至有些陈腐。例如,“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是形容宝钗和黛玉的名句,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塑造相比,虽然不能说南辕北辙,至少是单调而苍白的:我们需要牺牲多少细节,才能将二人纳入孟母和谢道韫所定义的德/才范式中去?“情既相逢必主淫”一句是典型的从社会主流价值出发的人物评判,看不到任何对秦可卿所处之复杂境遇的指涉。实际上,叙述者的立场反映出警幻此时的用意:应宁荣二公之托,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揭示和评判,传达对宝玉的警醒。
与谶诗相比,曲体更加通俗,句法接近口语,篇幅灵活,擅于铺排,抒情更加直白充分。在套曲中,有四首出现了第一人称:《终身误》《恨无常》《分骨肉》与《留余庆》。此外,《虚花悟》也采纳了主人公视角,近似于第一人称。因此,研究者多以套曲为依据来理解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不过,套曲中的第一人称不一定是对人物内心的直接呈现。警幻说:“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必有生旦净末之则,又有南北九宫之限。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谱入管弦。”可见,套曲并非剧曲,其主旨是咏叹和感怀,并无人物扮演。
那么,如何理解套曲中的代言体呢?中国古代戏曲中有以代言的方式进行人物评论的惯例。如关汉卿《望江亭》中,杨衙内上场诗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普天无处不闻名,则我是权豪势宦杨衙内。”杨衙内当然不会称自己“浪子丧门”或“权豪势宦”。可见,此处是以代言体的方式表达剧作家对人物的看法。换句话说,这是化装成第一人称的第三人称。套曲中的代言体均加入大量说教内容,如“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终身误》)、“须要退步抽身早”(《恨无常》)、“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分骨肉》)、“乘除加减,上有苍穹”(《留余庆》)等。这些内容在思想倾向上是一致的,最终归结为《收尾·飞鸟各投林》。这恰恰证明,套曲并没有真正模拟人物的口吻和思想,而是借人物经历中的若干场景,表达前后一贯的咏叹和感怀。套曲中的人物拥有各自的躯壳,却未被赋予各自的灵魂。是谁藏在他们的躯壳里面?其实还是判词背后的那个叙述者。不要忘记,套曲是用来警醒宝玉的第二重手段。正因为此,作为套曲主题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警幻希望灌输给宝玉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的主题。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判词还是套曲,都没有让宝玉觉悟。宝玉的沉迷代表着一种拒绝,也将判词和套曲中的一切置于反讽语境之中:它们并无对人物进行盖棺论定的权威性——要理解人物,必须转向纷繁复杂、意蕴丰富的小说正文。几篇韵文怎能把故事说尽?这不过是第五回,还有一整部书等待展开。
小结
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将长篇小说定义为“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杂语(heteroglossia),又译“众声喧哗”,指的是统一语言内部发生的社会性分化,如各种社会方言、各类集团的表达习惯、职业行话、各种文体的语言、各代人各种年龄的语言、各种流派的语言等。巴赫金认为:“杂语中一切语言,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的,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的视点,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在长篇小说中,杂语之间总是构成对话关系。意义生成于对话之中。
巴赫金的长篇小说理论是以西方小说为参照提出来的,但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同样具备指导意义:文备众体的中国古代小说天然具有杂语性。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发展的最高阶段。本文以《红楼梦》为中心,探讨了章回小说内部众多的重复叙事。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文体特征与文化属性,却又被小说家艺术性地组织为一个整体。它们用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话语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凭借文体差异,它们互相对话,互相竞争,互相颠覆,互相生成。它们就是章回小说内部的众声喧哗。正如一加一可能大于二一样,一减一也可能大于二:杂语之间的对话与竞争使双方的自明性同时消失,从而揭开一个待定的全新世界。
《红楼梦》的美学、思想和文化意义已经得到充分关注,而其文体学意义仍然有待深入挖掘。《儒林外史》中同样存在杂语性的重复叙事,如楔子、回目和“有分教”等,值得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清代的小说家已经开始自觉地从文体层面探索章回小说的更多可能性。遗憾的是,这种探索随着晚清中国的文化剧变而告中断。从此,中国小说走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再无回声。
注释
① 《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②③④[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0年版,第73、74—75、73页。
⑤ 本文对重复叙事的概念分析参考了李卫华《叙述的频率与时间的三维》,《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⑥ [美]J.希利斯·米勒著,王宏图译《小说与重复》,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⑦ 李庆信《〈红楼梦〉前五回中的亚神话建构及其艺术表现功能》,《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3辑。
⑧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⑪⑫㉕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668、87、342—343、158 页。
⑩ 前辈学者对此已有阐发,如蔡义江曾指出:“甄家的遭遇是后来贾府、特别是主角贾宝玉遭遇的缩影。这有点像宋元话本的‘入话’或称‘得胜头回’的形式,在讲主要故事前先说一个情理相似的小故事。但它又是与前面的‘楔子’及后面的贾府为故事中心的叙述彼此勾连着的。这也是在继承传统形式上的发展和创造。”(《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2010年版,第16页)
⑬⑭⑳ 刘永良《〈红楼梦〉回目指瑕》,《红楼梦学刊》1995 年第4辑。
⑮ 如清人陈其泰在《桐花凤阁评〈红楼梦〉》中的回目修改,参见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1页)。
⑯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27页。
⑰㉒ 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43—351、348 页。
⑱ 孙逊《〈红楼梦〉人物与回目关系之探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
⑲ 刘操南《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㉑ 如韩洪举在《陈其泰‘红楼梦回目拟改’的得与失》中说:“陈其泰很明白作者的意思,但没弄明白作者的艺术手法。‘贤’字显然是‘明褒暗贬’手法,因为曹雪芹讨厌袭人的为人,通过这一手法对她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㉓ 《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2010年版,第301页。
㉔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漓江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页。
㉖ 《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㉗㉘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3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