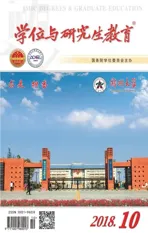艰难的衔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的权利之争
2018-10-16王世岳
王世岳 秦 琳
艰难的衔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的权利之争
王世岳 秦 琳
在德国,是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最为显著的差异之一。为了探索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新路径,衔接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培养,德国联邦与联邦州近年来推行多项政策,让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博洛尼亚进程也为德国高等教育一体化创造了契机。但德国大学对此态度极为谨慎,招收博士研究生要求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须专业对口,拥有优异的学习成绩,并完成预备学习,这让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学术进修之路漫长而艰难。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学术进修的权利之争,反映了研究生教育改革过程中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培养衔接的艰难。
博士生招生;应用科学大学;德国;研究生教育
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发展特色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应用型高等教育领域,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简称FH)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典范。近年来,衔接不同的培养类别,支持学生的二次选择成为德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保障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能够激发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活力,有效促进社会流动和人才竞争,推进教育机会的公平配置。因此,德国联邦和各联邦州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规定,保障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大学对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设置了相应的选拔标准。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制度障碍和隐形歧视,折射出了应用型与学术型人才培养衔接的艰难所在。
一、法律基础与政策语境
20世纪60年代末,为应对产业升级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德国对原有的一批工程技术学院进行合并或改革,建立了应用科学大学,作为大学(Universität)之外的一种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1]。2017年,德国共有应用科学大学245所,在校生86.5万人,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6%[2],是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于综合性大学偏重理论学习和学术训练,应用科学大学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在知识领域注重于实务知识和应用技术的传授。最初,德国综合性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颁发不同的学位,综合性大学颁发的第一级学位为文凭学位(Diplom)和文科硕士(Magister)学位,而应用科学大学颁发应用科学大学文凭学位(Diploma FH)。1999年,促进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博洛尼亚进程启动之后,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一样,全面引入“学士—硕士”两级学位体系,两类机构之间的差异相对弱化。但应用科学大学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这被视为是区分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最鲜明的标志”[3]98。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最初是为回应德国社会对高等教育扩张和多元化发展的需求而建立,体现了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分化,以不同的机构承担不同的培养目标和科研任务[4]。随着知识生产方式转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之间明确的培养目标差异趋向模糊,很多大学生并不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目标,而很多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却有志于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HRK)曾于2007年组织了“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博士培养和资格确认调查”,对130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的839个学院和学科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5]。统计结果表明,从1996~2006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数量呈现出了较大幅度地增长。另据统计,2009~2011年,有836名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参与了博士生入学考试,相较于2006~2009增长了近一倍[6]。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学术深造是在联邦和各州相关法律框架下,由一系列政策改革建议文件推动实现的;各州对于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有各自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地区间的政策差异。而旨在促进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博洛尼亚进程则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为德国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轨道之间的衔接创造了条件。
1.联邦
德国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人人有自由从事艺术、科学、教育和研究的权利”,第12条第1款规定“所有德国人均有权自由选择职业、工作单位和培训单位”。这就意味着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具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法定权利。早在1987年,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的前身西德校长联席会议(Westdeutsche Rektorenkonferenz)就提出应该给那些不在普通大学学习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7]。两德统一后,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继续扮演着改革推手的角色。作为学校的代言人,联席会议不断以决议或报告的形式,提出要为特别优秀的应用科学大学学生提供学术领域的上升之路,以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对学生的吸引力。
1990年6月25日,具有教育规划智库性质的德国联邦—州教育规划和研究促进会议(Bundes-Länder-Kommission für Bildungsplanung und Forschungsförderung,BLK)提交了《改善特别优秀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机会》的报告。1992年,联邦州文化部长常务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通过这一报告,成为德国高校招收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政策基础[8]。同时,作为调和政府与大学教师间关系的科技政策建议机构科学审议会(Wissenschaftsrat)也提出建议[9],要让那些特别优秀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有机会进入到高校攻读博士学位[10]。
自此,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开始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其后二十多年中,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进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相关政策不断得到完善。2000年,联邦州文化部长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明确各个大学有权决定采取何种考核方式,录取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11]。
2.联邦州
联邦层面的法律法规为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依照德国高等教育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第18条第2款第1项“联邦州决定可以授予哪些学位”的规定,具体的学位政策要由各联邦州依照自身情况确定。
“德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由16种潜在不同的政策组成,这16种政策是根据对高等教育有责任的16个州制定的。”[9]193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的教育事务是由各联邦州负责的。因而各个联邦州扮演着政策执行推手的角色,法律法规就成为极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各州高等教育法都对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做出了具体规定,但是细节各不相同。其内容主要围绕着几个问题:①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是否可以攻读博士学位;②攻读博士学位是否需要获得过综合性大学的学位;③攻读博士学位是否需要附加的学习或考试;④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师是否参与博士生的选拔和培养过程(见表1)。
通过对十六个联邦州高等教育法的比较,我们可以总结以下几个特点:
(1)所有的联邦州都明文规定,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有权利攻读博士。
(2)柏林、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上波莫瑞、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尔特明确博士研究生申请者不需要获得综合性大学学位。

表1 联邦州高等教育法关于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要求
注:联邦州名后的括号内为高等教育法条款,如柏林高等教育法第35条,石勒施威格—荷尔施坦因高等教育法第87条第a款。
(3)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八个联邦州要求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必须在博士研究生申请前参与资格确认(Eignungsfeststellungsverfahren),资格确认的方式一般是在所要就读的专业学习,并获得相应的成绩。成绩的有效期各不相同,在巴伐利亚限定为一年,在萨尔和萨克森限定为三个学期。
(4)有十一个联邦州的法规规定,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可以参与学生指导。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师可以用两种方式参与培养,一是参与指导博士论文的写作,二是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除柏林外,凡是确定不需要普通高校学位的联邦州,都没有规定申请者需要参加学习或考试。
对于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条件的限定,反映了各联邦州在支持学术性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衔接上的不同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明确攻读博士学位不需要大学学位的柏林、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上波莫瑞、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尔特五个州是德国经济发展相对较为滞后的地区。除柏林外,其余四个联邦州与图林根长期位列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倒数五位。这些联邦州全部都是原东德地区的“新联邦州”[12]。与之形成比较的是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它们是德国经济和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三个联邦州。2014年,三州分别录取了29200、37000和41400名博士研究生,占全德国博士研究生数量的14.9%、18.9%和21.1%[13]44。
3.博洛尼亚进程
1998年启动的博洛尼亚进程进一步加速了德国研究生教育的结构化改革进程,为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权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三级学位制度、学分制度、模块化学习以及相应的质量保障机制更加强调大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功能,研究生教育走向结构化,也开始承担更多的教学功能,而不仅仅是专注于科研。另一方面,“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应用科学大学在一定意义上向综合性大学趋同,在某些方面原本分工明确的两种高校类型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3]98。德国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在授予文凭方面的差别缩小,变相提高了应用科学大学毕业文凭的含金量,而大学定位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特色不再突出[4]。
博洛尼亚进程要求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相同程度的毕业证书具有共同的效力,不仅不同欧盟国家间的学历要相互承认,不同教育体系间的学历也应相互承认。为了使得不同学制之间能够相互联通,博洛尼亚进程设置了资格框架(Qualifikationsrahmen)。传统的成绩单上,人们能够看到谁(who)在什么课上(what)获得了多少分。而在新的框架之下,成绩单上可以看到人们已经掌握的能力,以及知识水平[15]。这就使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可能。新的学历认证体系的建立,使得不同培养类别和不同培养机构类型之间的学历至少在理论上有了更多可比性,应用型教育经历也可以作为学术型教育学习的基础,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也就有了更多的合理性和政策支持。
二、质量保障,还是地位保证?
为了保障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基本权利,德国联邦和联邦州制定多项政策,为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提供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但是在德国,博士学位的颁发在本质上属于学术事务,不受政府的影响。德国高校的博士招生一般是依据学院或系科层面依照博士生培养章程(Promotionsordnung)进行。依据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的统计,2006年840个学院的博士生培养章程中,637个学校(占总数的76%)的培养章程对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如何申请博士学位做出了规定。其中,比例最高的专业是工程科学,在113个工程系科中,有103个招收来自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占总数的90%。其次是数学和自然科学(88%,216个中的191个),法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80%,148个中的117个),语言和文化科学(70%,251个中的177个)。而较为传统的学科,如神学、医学和动物医学以及哲学专业很少招收来自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5]37。
通过学校的严格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相关政策的悖论所在。从政策角度出发,衔接应用型和学术型的人才培养,可以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吸引力,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深化研究生培养改革,因而联邦与联邦州不断推进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保障政策。但是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招收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并不能给学校带来更多利益,却可能影响其研究生培养质量。故而在招收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问题上,大学普遍缺乏动力。
1.专业对口
在招收博士生时,大学教授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来自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是否具备科研能力并能够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因此,在招收博士生的过程中,各个学院和系科都会特别要求学生在应用科学大学中所学专业与其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关,以保障其博士学习的顺利进行。
攻读博士学位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中,工程科学类学生的比例最大。在2005~2006学年攻读博士学位的1043位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中,有322人为工程科学;其次是数学和自然科学,为263人,占总数的28%;再次为法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人数为156[5]39(见表2)。工程科学人数较多除了应用科学大学本身工程专业占比较高之外,工程类的知识更为偏向于应用,因而应用科学大学和大学工程科学类课程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也是重要原因。

表2 2005~2006学年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专业分布[5]39
大学对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专业的要求也为许多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增添了困难,一些新兴的应用型专业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而在这些领域具有科研潜力的年轻人,一样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诉求”[3]102。例如社会工作(Soziale Arbeit)专业就没有直接相关的专业能够攻读博士学位,其毕业生只能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寻求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并与这些专业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进行竞争,无疑要面对较多的困难。
2.学习成绩
大学招收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基本条件是,学生要在应用科学大学中表现特别优秀。因此,在各个高校招收学生的过程中,都对学生在应用科学大学的学习成绩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柏林洪堡大学要求学生在应用科学大学中的成绩为“非常好”(sehr gut,95分以上),哈勒—维腾堡大学要求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在应用科学大学以“好”(gut,85分以上)的成绩获得学位。依据乌尔姆大学的统计,该校约62%的院系在招收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时有分数要求。其中有60%的院系要求学生能够获得“非常好”,其余40%的院系要求学生获得“好”。就专业而言,要求最为严格的专业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70%)、工程科学(65%)以及法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62%)[16]。
通常情况下,德国大学中只有5%~10%的毕业生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在一些传统专业,如法学、医学等专业,其优秀率更低。因而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要求就显得更为严格。
3.资格确认
除了在应用科学大学表现出色,想要攻读博士学生的申请者还需要证明自己能够适应博士阶段的学习。因而,许多高校提出了“资格确认”的要求,以测试申请者是否有能力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资格确认”一般由学校确定课程内容,通常是在指定大学或研究所中学习两到六个学期。还有一些机构要求学生参加考试或者参加指定的科研活动。考试的内容一般由学校征求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意见,有时职业院校的教师也会对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内容提出建议[8]11,从而让考试的内容能够更加符合应用科学大学学习的特点。
以埃尔富特大学为例,其下所设的国家科学学院[17]和马克斯·韦伯学院[18]均规定,为了证明申请者具有博士进修专业所需要理论基础,需要在与博士进修专业相关的机构参与两门习明纳讨论课,并获得“非常好”或相等的成绩;同时,申请者不能有参与其他高校博士考试失败的经历。教育科学学院则规定申请者应该至少参与12个周学时(SWS)的课程,其中有至少两门讨论课,并通过笔试获得成绩;其中至少一门得到“非常好”的成绩,另一门获得“好”[19]。
资格确认实质上凸显了博士生导师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原则上说博士生的录取并不以实现确定导师为前提条件,但是事实上博士生通常都事先获得了导师的同意才进入具体的申请程序……因此事实上教授是最重要的”[20]。如果教授不同意学生报考,那么学生实际上就失去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从各学校的要求中,我们可以总结以下几点共性:①想要攻读博士学位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只能攻读相关专业,一般不存在转专业攻读的情况;②申请者在应用科学大学的学习期间的成绩应该达到“非常好”或“好”;③申请者需要参与大学的资格确认,并获得“好”以及更高的成绩;④在一些热门专业里,如法学、医学,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很少有机会能够攻读博士学位。
堪称严苛的入学条件保障的不仅是生源质量,更是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传统观念认为,学位可以证明获得者具有某种特殊的技能或资格,如学士学位意味着申请者在大学阶段接受了通识教育;硕士学位意味着申请者已经具有在特殊领域实践的资格;博士学位意味着学位拥有者有在大学中教授课程的能力[21]。正是由于文凭所具有的符号效应,使得高等教育学位和文凭的增长并不源自于人们对高等知识和技能的需求,而是地位竞争和社会排斥的结果[22]。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博士学位授予是一种传统,意味着那些已经为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人判断申请者是否具有进入共同体的资格[23]。大学对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把控,不仅是对大学权利的维护,也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肯定。因此,德国高校教师联盟主席穆勒—布罗姆雷(Nicolai Müller-Bromley)就曾坚决反对应用科学大学获得博士生培养的权利,他认为这样可以保护大学,更进一步保护大学已经获得的竞争优势[24]。
三、困境与超越
2007年,德国共有23850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学位,其中,有约100名学生毕业于应用科学大学,占总人数的0.4%[8]9。即使在招收比例最高的工科类学校,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规模也极小(见表3)。

表3 柏林工业大学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的博士所占比例[25]
博士生培养的主体是综合性大学的学院和系科,对于它们来说,最为重要的责任在于使得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业。显然,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教育背景并没有成为这些学生的加分项,反而影响了博士指导教师对于应用科学大学毕业学生的印象。2009年,德国的教育职员工会直接提出:“应用科学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或者应用科学大学的硕士生攻读博士学位,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有资质,而是在于是否有这样的能力”[26]。在德国博士入学申请过程中,导师是否同意接受申请者是最为关键的步骤。因此许多申请者即使能够达到申请标准,但很多博士生导师对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存在偏见,所以这些学生也难于获得在大学中攻读博士的机会。
除了严苛的选拔之外,学习时间也成为制约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因素。2016年,德国在读博士生中有40%以上的学生是应届毕业生,另有约38%的学生已经毕业一到两年的时间[13]25。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博士研究生实际上在两年之内就开始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对于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而言,漫长的学习时间就成了他们攻读博士学位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业和生活压力使得许多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学开始承担科研功能,一些学校开始设置具有理论导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项目,特别是在一些大学之中并不设置博士点的学科,如社会工作和健康科学(Gesundheitswissenschaft)。2014年修订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高等教育法中也规定:“应用科学大学承担着研究和发展的功能”[27]。因而一些具有研究能力的应用科学大学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以便更好地完成研究任务,建立科学研究系统,使得毕业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攻读博士并为他们打开在科学系统中就业的机会[28]。
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中国而言,毕业难以继续深造都是限制应用型人才培养发展的重要阻碍。教育政策的意义恰恰在于突破现有状态的限制。学术型与应用型高等教育相衔接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两者间的交流。但是在衔接过程中,两者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学术型人才培养往往具有先发优势。如果普通高校不能保持开放的态度,那么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相衔接最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1] 秦琳.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经验[J]. 大学(学术版), 2013(9): 60-66.
[2] 德国教育与科研部在线数据库[EB/OL]. [2017-11-22]. http://www.datenportal.bmbf.de/portal/de/Tabelle-2.5.1.html.
[3] 周海霞.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获博士学位授予权之争议[J]. 外国教育研究, 2014(10): 96-108.
[4] TEICHLER U. Fachhochschulen in Deutschland: Geht die Erfolgsstory zu Ende?[M]//Hochschulstrukturen im Umbruch. Frankfurt und New York: Campus, 2005: 191.
[5]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Ungewöhnliche Wege zur Promotion? Rahmenbedingungen und Praxis der Promotion von Fachhochschul- und Bachelorabsolventen[R]. Beiträge zur Hochschulpolitik, 2007(3): 37.
[6] HOFER S. Streit um Doktortitel: Schleswig-Holstein will Fachhochschulen Promotionsrecht verleihen[N/OL]. [2017-04-20]. http://www.spiegel.de/lebenundlernen/uni/ schleswig-holstein-will-fachhochschulen-promotionsrecht-geben-a-934133.html#ref=rss.
[7]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Zum Verhältnis von Universitäten und Hochschulen und zur Gemeinschaft der verschiedennen Hochschularten in der Westdeutschen Rektorenkonferenz, Entschließung des 151. WRK- Plenums[R]. Bonn, 1987.
[8] KWLLER A. Promotionsführer für Fachhochschulabsolventen. Möglichkeiten und Zulassungsverfahren für eine Promotion an mehr als 70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mit hinweisen für Absolventen und Masterstudiengängen sowie Berufsakademien und zur Promotion im Ausland[R]. Berlin, 2011: 9.
[9] 弗拉克曼, 德维尔特. 德国的高等教育政策[M]//范富格特. 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93.
[10]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r Entwicklung der Fachhochschulen in den 90er Jahren[R]. Köln, 1991.
[11]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Zugang zur Promotion für Master-/Magister- und Bachelor-/Bakkalaureusabsolventen, Beschluss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vom 14.4.2000[R]. Bonn, 2000.
[12] SIMEANER H, DIPPELHOFER S, BARGEL H, et al. Datenalmanach Studierendensurvey 1983-2007: Studiensituation und Studierende an Universitäten und Fachhochschulen[R]. 2007.
[13]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Promovierende in Deutschland 2016[R]. Wiesbaden, Wintersemester 2014/2015.
[14] WÜRMSEER G. Auf dem Weg zu neuen Hochschultypen[M].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0: 73.
[15] BARTOSCH U. Promovieren, aber wie? Eine Perspektive aus den Fachhochschulen[J]. Erziehungswissenschaft, 2010, 20(39):91-103.
[16] BRUNNER S. Informationssystem Promotion für FH- Absolventen. Fachhochschule Neu- Ulm, 2002.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Ungewöhnliche Wege zur Promotion? Rahmenbedingungen und Praxis der Promotion von Fachhochschul-und Bachelorabsolventen[J]. Beiträge zur hochschulpolitik, 2007(3): 29.
[17]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Erfurt. Promotionsordnung für die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Erfurt[Z]. Erfurt, 2011: 3-4.
[18] Max-Weber-Kolleg fü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der Universität Erfurt. Promotionsordnung für das Max-Weber-Kolleg fü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Z]. Erfrut, 2012: 7.
[19] Erziehung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Erfurt. Promotionsordnung für die Erziehung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Erfurt[Z]. Erfurt, 2015: 5.
[20] 袁治杰. 德国博士学位法律制度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比较法研究, 2009, 23(6): 149-158.
[21] GREEN H, POWELL S. Doctoral study in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M]. McGraw-Hill Education (UK), 2005: 48.
[22] 柯林斯. 文凭社会: 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M].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8: 3.
[23] 王世岳. 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合法性工具——论布迪厄“再生产”理论中的考试功能[J].现代大学教育, 2015(2): 14-19.
[24] CZORNOHUS S, DOBERSALSKE K, HEUEL F, et al. Auf dem Weg zur Promotion: Zur Benachteiligung von Fachhochschul-Absolventinnen und-Absolventen[J]. Das hochschulwesen, 2012(5): 110-117.
[25] STEINBACH J. Rechenschaftsberichte des Präsidenten[R]. Berlin, 2013: 5.
[26] KELLER A. Wege zur Promotion für Fachhochschul- AbsolventInnen- Vorschläge der DoktorandInnen in der GEW[R]. Frankfurt am Main, 2011: 1.
[27] Gesetz über die Hochschulen des Landes Nordrhein- Westfalen(Hochschulgesetz–HG) [A]. 2014-09-16.
[28] IHNE H, CLEMENT R, HERPERS R. Graduierteninstitut an Fachhochschulen als Nukleus wissenschaftlicher Nachwuchsförderung[J]. Neue hochschule, 2011(2): 84-87.
(责任编辑 黄欢)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博士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编号:17JZD057)
10.16750/j.adge.2018.10.012
王世岳,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93;秦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