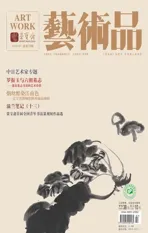清风如可托 终共白云飞—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国书画文物收藏
2018-08-20冯朝辉
文/冯朝辉
文人情愫,往事悠悠,从青春懵懂到不惑半百,人生十六载的黄金岁月,曾频繁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近文从艺,道不尽的故事,说不完的感慨,时常涤荡着我的胸怀,每每回首北宋政治家、诗人寇准一首描写《纸鸢》的小诗总是不期而至:
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
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纸鸢也即风筝,我时常感到那时的自己好像就是一只纸鸢,骨子里那份对中日两国间类同传统文化的不尽热爱,牢牢地将我栓系,从中国到日本,又从日本到中国,一路托“传统文化”之风,寻迹飞行。
20世纪90年代我自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本科毕业后,欲走出国门,开阔视野,攻读硕士学位,进一步谋求笔墨艺术上的造诣,日本成了我留学之地的不二选择。当我熟练掌握了日本语,顺利完成了学业目标,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专注,鉴于日本民间保有中国文物,尤其是书画类文物量较大的缘故,我的脚步便一时难以离开。
十六年里中日两国间的文化深深地滋养着我,读过的书可谓汗牛充栋,过手的中国名家字画不胜枚举;十六年里的收藏故事太多太多,打眼刻骨铭心,“捡漏”更像传奇;十六年里艺术市场的跌宕起伏早已装在心底……当郑板桥的《峭壁芝兰》、吴昌硕的《竹石图》、齐白石的《酒熟蟹肥》、傅抱石的《高山仰止》、徐悲鸿的《柳鹊》等件件记载、著录清晰,流传有序的华夏艺术瑰宝,经我之手回流祖国,带着历史的尘风,洗去贫穷的耻辱,让我不经然地也带上了一份自豪,毕竟“中国的文化属于世界,但中国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国”。

吴昌硕 瓜实图 57cm×103.3cm
一、中日绘画艺术的互渗
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地理位置相邻,尽管近代以来,包括近些年间两国政治立场相异,地缘争端不断,但于民间文化交流而言却渊远流长,这种长久交流的直接结果便导致了两国文化的深度互融,于绘画上表现得颇具代表性。
中国画与日本画两个分别以国家之名命名的画种先皆以笔墨等东方文化为基,合而后分,先后各自分别经历了西方思潮的冲击,形成了今天这两个画种“你中有我,我中融你”,然而又朝向追崇“意象”与“自然之象”两个完全不同方面发展的局面。
1.日本画家对中国画艺术的学习
日本是一个“有着承认更为优越文化心理态度” 的民族,曾经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大陆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于是日本便全面学习之。随着清政府的没落,相反日本的崛起,日本人发现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的西方文化更具吸引力,于是他们就义无反顾地“脱亚入欧”,转向了新的学习目标,与中国文化开始分道扬镳。
这个转折点便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即19世纪60年代日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国内由上而下进行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国家,后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的开端,也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日本的绘画艺术也不例外,自此开始转向,抛弃中国,转向西方学习。
(1)明治维新前日本绘画界对中国艺术的师法
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7世纪(中国唐朝时期)日本就曾向中国派“遣唐使”学习大唐文化,达19次之多;13—16世纪中国宋元水墨画成为日本室町时代画家们的追求目标,出现了以日本画家雪舟为代表的一批水墨画家,中国南宋画家梁楷、牧溪影响了日本的禅宗画派,如当时日本派遣来中国学习佛法,归国后被尊为国师的圣一,曾同牧溪一同拜在中国无准禅师门下学法,其归国前牧溪以所画观音、猿、鹤三幅作品相赠,后这三幅作品被日本人视为国宝,现珍藏在日本大德寺中,南宋画院马远的“一角”与夏圭的“半边”式构图亦深受当时日本画界追捧;18世纪(中国清中期)日本出现了以中国文人画为楷模的南画运动,并涌现出以日本池大雅、与谢芜村为代表的南画领袖,1748年日本翻刻出版中国《芥子园画传》;19世纪以后(中国清晚期)随着中国的没落,日本的南画运动随之衰落,但其遗风尚存,富冈铁斋成为日本绘画步入近代后的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

八大山人 古松图 182.5cm×49cm

齐白石 酒熟蟹肥68cm×34cm

冯朝辉 松鼠 30cm×50cm 2017年
(2)明治维新后日本绘画界对中国艺术的师法
近代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调整,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直接作用于艺术,洋画为日本画提供了新的美学参照标准,日本画家们从洋画中汲取营养,与本民族先前自中国学习、沉积、化合后的绘画技法、观念相融合,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进而发展、确立了新的美学认识,并相应地创造出了新的绘画材料与技法,如选用岩彩、胶等,他们弱化甚至放弃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线”与“水墨”两个基本构成要素,转以强调对色彩的应用取而代之,为日本画的变革送来一股新风,完成了日本画从古典向现代、从旧传统向新时代的转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清朝末期至民国初年)虽然日本主流思想转向学习西方文化,但一种文化的转型并非一代人能完成的,有时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老辈日本学者、文人骨子里遗留下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仍然在持续,故而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1864年日本人安田老山到中国上海师从中国画家胡公寿习画,归国后成为日本画界泰斗;1893年、1906年、1912年日本画家冈仓天心奉日本官方之命三次赴华,调查中国古代美术,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寺庙等古代建筑;1895年日本近代油画大家中村不折作为随军记者来到中国,收集并运走了大批中国文物,归国后于日本东京成立了“书道博物馆”,馆内藏有大量中国文物,据推测其规模与质量不逊于中国很多的省级博物馆;1900—1914年间日本学者河井荃庐以及长尾甲频繁往返或久居中国,拜中国海派艺术巨匠吴昌硕为师,习画制印,并加入中国杭州西泠印社,成为其首界社员,归国后前者成为日本印学宗师,后者成为日本一代文人领袖,同时他们又致力于吴昌硕、王震书画艺术在日本的推广,这一时期来华拜会吴昌硕的还有日本书法家日下部鸣鹤;1910年在获知中国官府已将敦煌藏经洞所剩文书全部运抵北京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日本称法,即中国史)的日本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内藤湖南,奉命到北京调查敦煌文书,翌年写出《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并将所获资料在日本展出;1913年日本人有贺长雄以中华民国法律顾问的身份居北京7年,在此期间虽无其美术活动记载,但归国后有贺长雄即撰写了《东亚美术史纲》;1913—1928年日本南画名家桥本关雪数次来华,与中国画家吴昌硕、王震、刘海粟、潘天寿等深度交往,并邀钱瘦铁赴日本讲授中国篆刻;继桥本关雪来华之后,日本美术史论家长广敏雄于20世纪30、40年代多次来华,开展对云冈石窟的相关调查,后期值中日两国战争之际,但长广敏雄的谦卑却并不让中国艺术家们排斥,1944年他在北京访问了很多中国画家,回国后即写成了《北京的画家们》,书中记录了当时他对北京最有名的大画家蒋兆和、黄宾虹、陈半丁、齐白石等人的访问。

赵之谦 逍遥堂 27.5cm×124cm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两国民间的画界交流遂中断。
2.中国画家同日本绘画的交流与学习
如前文所言两国政治经济状况的逆转,造成日本画家向中国艺术家学习,从积极摄取到惯性前行的前后两个分阶段状况,反过来也造成了中国画家学习日本文化、开展文化交流的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中国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应当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划界,这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了30年。如果说明治维新让日本画家们发现了西方艺术的魅力,转而弃中学西,那么中日甲午战争则让中国画家,以至中国人认识到了日本的先进与强大,进而由授业转为向其学习。
(1)以传教与布道为主的中国学者东渡
古代因为中国的强大,中国学者到日本多以传教、布道为目的,如唐朝鉴真和尚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弘传佛法,成为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明末清初隐元禅师应邀率30位知名僧俗赴日本,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隐元禅师知识广博,诗文书法均佳,他为日本带去了中国书法、印刻、建筑、雕塑、雕版印刷、医药学和音乐等作品和书典,日本称之为“黄檗文化”;1731年中国清代画家沈铨应日本天皇之聘,偕弟子郑培、高钧等东渡日本传艺,深受日本人推崇,从习画者颇多,日本江户时代长崎画派即在其影响下形成。
清末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金石文字家、书法家杨守敬曾出使日本,期间与日本汉学书法家论碑,被称为“杨守敬旋风”;中国画家蒲华、陈曼寿、戴以恒、顾沄、胡铁梅、罗雪谷、王冶梅、叶松石皆曾旅日鬻画,这一时期中日双方画界间的交流是分散的,且仍以中国画家的艺术“输出”为主。
(2)以交流、学习为主的中国画家东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一向自以为老大的中华泱泱大国却败在邻家区区弹丸岛国手上,并接受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自省,于是康有为等人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维新”主张,同时奏请皇帝变法,但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可它让国人警醒,中国并不强大,必须通过走出国门去学习,以求变法图强。在大批中国外派留学生当中,东渡赴日本的人数丝毫不逊于赴西方国家的人数,这其中既包括诸多政治家,也包括了许多文人、学者和画家。
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中国画家到日本双方间的交流已由先前的以中方文化输出为主,渐渐转变为相互间的学习和借鉴。上海地区先是王震(画家,同时是日清汽船会社中方经理),继而是钱瘦铁(旅日画家、篆刻家),北京地区以陈师曾(画家,曾在日本留学8年)为主,频繁往返于中日间,从事书画交流活动,积极参与推动成立画会(社),有规模、有组织地推介中国艺术家以及其作品到日本,与日本艺术家作品一同展出,从而也令吴昌硕、齐白石虽未出国门,其作品却风靡东瀛。这期间陈师曾翻译了日本大村西崖《文人画之复兴》,且合并自撰成《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同时潘天寿参照日本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绘画史》译著了《中国绘画史》,代表着中日两国间的艺术交流由实践走向了理论,并由相互间的对等交流开始向以日本方的文化输出为主转变。

冯朝辉 烟林清旷 65cm×33.5cm 2017 年
1906年高剑父赴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校学画,第二年又带其弟高奇峰再赴日本学画,吸收日本画风后在中国形成了“岭南画派”;1907年陈树人赴日本,1909年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绘画科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考古学家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1919年回国,在日期间汉学著述颇丰,并成为当时旅居日本的汉文化、文物专家;1908年何香凝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学习;1917年徐悲鸿得友人赞助赴日本学习;1917年张大千赴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与绘画;1916年汪亚尘赴日本,1917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1918年朱屺瞻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绘画;1919年陈之佛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图案设计;1921年丰子恺赴日本游学,晚年翻译出日本古典文化巨著《源氏物语》;1929年方人定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绘画;1932年黎雄才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绘画;1932年傅抱石赴日学习,专攻美术史论,归国后翻译了日本梅泽和轩的《王摩诘》、金原省吾的《唐宋之绘画》,并参考日本人著作,编著了《中国绘画理论》《中国美术年表》等。

吴昌硕 宜龄多子 116.5cm×54cm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画家们到日本留学交流中断。
日本近代百年艺术史实质上是对西方文化消化与吸收的历史,自上而下意识形态的全面转变,已经让曾经取法中国画的日本画与西画完美地融合,与中国画面貌渐行渐远,但其骨子里最初建立起来的中国审美观在画面中依然存在,比如日本画的画面构图审美还是中国式的,对雅致、柔和色彩的崇尚仍印有深刻的中国烙印。同时近代中国画家通过对日本画的学习与吸收,也在中国画的发展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岭南画派自不必说,学术界一直有声音言其照抄日本画风;王震的人物画风受到日本禅宗画的影响;丰子恺的漫画、汪亚尘的花鸟画、陈树人、傅抱石的山水画中均明显带有日本画的影子,即作品中大多弱化了对“线”和“笔墨”的运用,强化了色彩效果,画面视觉感受趋于干净、柔和。
展望未来,传统中国画与日本画势必沿着各自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二者的趋同性会越来越少,传统中国画将以“神”“意”作为其追求目标,从而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而日本画仿效西画,早已贴近了自然。二者不必再趋同,但依然可以相互借鉴。
二、日本的中国书画艺术品收藏
正是因为有着在这种包含大量汉民族传统元素的文化,老辈日本人普遍对中国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与喜爱,对中国艺术品收藏十分热衷,很多中国知名画家在日本同样家喻户晓,如宋代牧溪、明代的王铎、张瑞图,清代的朱耷、沈铨,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当代的范曾,等等,对其作品日本民众也是趋之若鹜,珍视有佳的,只不过在20世纪之前,日本藏的中国画还是相当空缺的,仅是一些民间包括宗教界人士交往携带过去而已,一些充满禅意如南宋马远、夏圭、牧溪等的作品,受到喜爱,并被日本寺庙和幕府等权贵阶层收藏。

冯朝辉 阿坝所见 30cm×50cm 2017年
到20世纪初,随着两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日本藏中国画空缺的状况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帝国主义入侵,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清朝封建统治土崩瓦解,国内各路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间相对于日本国内则是大正时期(1912—1926),在经历明治维新后,国家、国民正逐步走向富强、富裕,一些深研,或是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业家、银行家、政治家、文物经营商以及收藏爱好者,其中比较有名气的收藏家有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原田悟朗、住友宽一、黑川幸七、藤井善助、桥本末吉、小川为次郎、菊池惺堂、须磨弥吉郎、林宗毅、矢代幸雄、冈村商石、池部政次等,面对中国文物大量外流的现状,私机借助天时、地利和频繁两国民间往来,凭借其对中国文化全面了解与掌握的优势,又请当时的汉学研究专家,如内藤湖南、长尾雨山以及旅居日本的罗振玉等充当顾问与中介,站在中国人对中国美术史评价的角度上,大肆收购不仅止于满含禅意画作的大范围中国文物,一时间兴起了中国书画搜集、研究的热潮,这在日本输入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现在我们回顾那段令无数中国人为之心痛的历史,我们说日本人当时是图谋不轨,乘人之危,以至后来发展成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文物肆意的偷盗与掠夺,日本人则说是抢救亚洲文物,面对中国文物流向海外求售的状况不能坐视不管,比如内藤湖南就曾说“中国在那样的状态下,贵重文物接二连三流出海外,我们得设法将它们保存在同属东亚的文化圈,并且是很久以前就有着深厚关系的日本才是”。这种状况在侵华战争爆发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是存在的,如20世纪初日本纺织业巨头阿部房次郎在当时中国举办的“天津赈灾展”上就收购了不少,后来其在所著《爽籁馆欣赏》(第一辑)序言中写到“东亚古美术中又以中国美术的成就最高。这样的中国美术品在兵乱中散佚毁坏,着实令人难以忍受”。山本修之助撰写的收藏家《山本悌二郎先生》一书中记战前“其在上海书画商店打听到数包货物都是打算运往美国的古画时,便在未查看内容的情况下将之全数买下”。日本收藏家矢代幸雄在伦敦演讲中国美术史时说到“美术是全人类的现象,其本质具有普世性”。收藏家林宗毅在其编辑出版的《定静堂藏中国明清书画图录》跋文中说到收藏的目的“防止书画之散佚损毁,固守传统念愿之发露也”等,中日双方评价不一,各自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讲话也是必然的,但如果说是日本人是以投资增值为目的,笔者首先不完全赞成,因为这些流往日本的中国书画文物,尤其是一些古代重量级的,如今绝大多数都保存在日本公、私博物馆里,被日本国列为“重要文化财”,予以保护,日本的公、私博物馆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现今去日本旅游、考察、参观的重要到访地。而一些我国近代名家,如吴昌硕、王震、张大千、齐白石、王雪涛等人的作品,自然都是通过购买的形式流通到日本的,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中国书画的喜爱,因为这些画作在当时看来尚属当代作品,还算不上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曾将其作为销售创汇的来源之一,于国有文物商店或中国的“广交会”上公开销售,张大千在其年谱中曾记载其观日本藏家原田观峰收藏,多有中国海关封蜡、火漆、钤印,时间推算应为中国“广交会”所购, 1967年5月(“文革”期间)中国公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一部分囤于国内各地,一部分则以换取外汇为目的,通过广交会出售”。在此,我们说文化暂不评政治与历史,透过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感受的是两国人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汉民族文化、文物的无限喜爱与珍视。
由此亦可见,日本文物收藏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广泛的民间性,文物收藏公、私并存,私人藏家、博物馆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大数百家之多,这在世界范围内应当也是一大特色,藏品存量之巨、质量之高(有的即便拿回中国也是孤品)、跨越年代之久,绝对可以与国有博物馆一争高下。国民对文化的喜爱,对文物的欣赏和保护意识是普遍的,如在日式的住宅里一般都设有专门挂画的区域,下边摆放文玩,一年四季定期更换。公、私博物馆间相互也并不封闭,彼此交流得比较多,私人藏家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常常会被借展或寄藏于国有博物馆中,短期地参加一次展览活动,为期一两个月,长期的也可以几年。借展或寄藏结束后,仍归其原主人,原主人有权决定这件文物的去留,包括予以买卖等商业行为。日本公、私博物馆文物收藏间的这种互补性,不仅丰富了藏品内容,传播了文化,也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收藏热情,推动了民间文物收藏业的繁荣。

冯朝辉 仁者乐山 30cm×50cm 2017年
日本书画收藏的另一大特点是荣誉、责任与保护意识,当藏家的藏品质量和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有时需要一代人,有时是几代人),他们大都愿将其捐赠或象征性地收取一定资金出售给国有博物馆,或是由家族企业出资兴建私人博物馆收藏,做进一步的出书、展览、整理、研究、保护与文化传播,如上野理一、须磨弥吉郎的收藏后捐赠给了京都博物馆,阿部房次郎的收藏后捐赠给了大阪市立美术馆,成为该馆的核心收藏,池部政次的收藏后捐赠给了早稻田大学的会津八一纪念博物馆;国有博物馆优先出资购买的,如冈村商石的大部分收藏由大阪市立美术馆购得;收藏在家族企业或个人出资兴建的私有博物馆的更多,如山本悌二郎的收藏如今保存在澄怀堂美术馆,并出版有《澄怀堂书画目录》,黑川幸七的收藏如今保存在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矢代幸雄的收藏如今保存在奈良大和文华馆,原田观峰的收藏如今保存在东近江市的信乐观峰馆,桥本末吉的收藏如今寄存在东京的松涛美术馆,林宗毅的收藏则分为几处保存,一部分捐赠给了京都博物馆,一部分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部分则保存在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这种文物管理机制,对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研究与交流,包括日本本国的,也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可以说是一个贡献。为此日本也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繁荣、艺术品市场一定程度放开后,回流中国书画类文物最多、也是最为集中的货源地之一。
文化演进至今,现在日本的新生代已经彻底西化,当下日本人对中国文物收藏显然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中国人去“掏”日本人就“卖”,他们宁可去花上亿美元购买西方油画大师凡高的《向日葵》,也不会再为购买一件中国文物不择手段,或是在海外的拍卖行上用钱与中国人拼争得“你死我活”,除非其以拿到中国拍卖,投资增值赚取利润为前提,即便如此也是寥寥无几,只有那些早年不管通过什么手段流传到日本的,如今已静静地存放在日本公、私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还在向这个民族昭示着他们民族的文化渊源,诉说着他们祖辈的文化审美,也传播着中华文化。
三、中国书画艺术学习感悟
清代画家范玑有言:“学画须得鉴古之法。鉴古不明,犹如行远而不识道路之东西,鲜有不错者。”当年从国内艺术高校中国画专业本科毕业的我,若说对此艺术认识有着多么深刻的理解,确实不敢言,但无心插柳,16年的海外中国书画文物鉴定历程,让我的经历恰好贴合了这一艺术成长规律,走上了一条和大多数艺术工作者成长所不同的道路,中国画收藏、鉴定与中国画创作同时成为了我当下所从事和研究的专业领域,两个专业相辅相承,相互滋养,相得益彰。

黄宾虹 山静日长 150cm×46cm

冯朝辉 仙草 30cm×50cm 2017年
首先书画鉴定滋养了我的艺术创作,其所带给我的“师古营养”是巨大的,它不是十几幅、几十幅名画临摹所能比拟的,常年累月的真、假、优、劣辨识,日日的知识浸润、冲击、洗礼,每一位名家的不同画风、笔性、设色特点,甚至同一位画家不同时期的风格演变都要了然于心,试于笔端,这对画者认知上的锤炼作用是巨大的,对作品格调的提升作用也是显著的。
作品是一个人十几年、几十年的文化沉积、精神素养和艺术品性的集中体现,书画鉴定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更为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画的传统笔墨精神、个性风格和师承关系,从艺术的本源上将绘画、鉴赏、诠次、批评有机地联系起来,在继承中求发展,一路沿传统文脉走行,反映在我的绘画作品中,由金石画风而生发,讲法画面整体布局,骨法用笔,意蕴淡远,笔墨简练,但不想简单,面对浮躁、功利、迅捷、多变的当下社会,力图于作品中展现出宁静、空灵,参以禅意的精神气质与追求,努力为自己也为观者搭建一座可以休憩与深呼吸的心灵家园。
其次中国画创作加深了我对中国书画鉴定领域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书画鉴定不是纯理论的学科,它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甚至偏向于实践更多一些的学科,一方面是鉴定者自身的笔墨实践,即要能书善画,它可以让我们对笔墨的理解入木三分;另一方面是艺术品市场实践,它不但可以让我们知其真,知其假,更可以知其何以真,知其何以假。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兴起与繁荣,人们越发地认识到中国书画鉴定市场实践环节于书画鉴定专业成长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市场也呼唤着更多鉴定专业知识人才的出现,然而客观成长条件的限制,一是大家接触真迹的机会太少,二是鉴定真伪难以形成责任意识,如博物馆里的东西大都不需要鉴定,需要的是研究;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的鉴定又需要个人较大的财力支持,并非人人具备条件,所以无压力、无责任之下的学习,人才是难以成长的,从而造成了我国目前鉴定理论与实践兼而能之的人才缺乏的局面,同时这也是当下国内高校这一专业的教育现状。
我的书画鉴定专业即沿着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发生发展过程走来,国内的本科学习为中国画专业,多年旅居日本的岁月,客观上优厚的条件(中国艺术品市场崛起,中国名家书画在日本民间的保有量大),攻取硕士学位的同时,对中国书画鉴定进行了尤为深入且广泛的实践,回流了大量的中国名家书画作品。
对利益的追求无止境,只有对知识文化的传播才可以放大人生。2013年应国家的召唤我自日本归国,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讲授传统中国画和中国书画鉴定两门课程,并招收传统中国画研究与实践方向研究生。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开展积极的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始终是我的职业梦想,校内外教学和高校、艺术研究机构间学术交流的需要,结合自身特殊的成长经历,近几年我将自己于海外中国画鉴定、艺术创作领域的认知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梳理,撰写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5年来已有近五十余万字发表,其中十余万字发表于全国核心期刊、专业学术文集上,并受聘担任辽宁省可移动文物普查书画类专家,多次受邀参加国内专业研究机构学术会议,参与国家重点艺术项目等研究工作,参编史上名家画集出版,开展学术讲座、交流等。
喜爱民族传统文化,回报社会各界,通过教学、著述无偿地将我这十几年于海外学习研究、书画鉴定回流、中国画创作中的所知、所思、所悟、所得传播出去,让更多的继学者能够站在我的肩上实现人生理想,是我回国任教的唯一目的。
几年来,从行业到专业,从行家到专家,从教学到教研,从实践到理论,我深感话语权多了、重了,但肩负的责任也更大了,时不我待,未来要学、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问所得,但求有益”是我人生一以贯之的基调,因为奉献与传播总是使我充实并给予我快乐。
谨以此文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本文作者为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鉴藏家)

八大山人 兰蕙图 32cm×3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