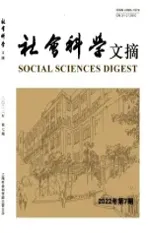数字经济的经济哲学之维
2018-08-15
数字经济在当代社会的时代定位
数字经济在当代社会的时代定位是什么?要想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两个前提性问题。第一,何为数字经济?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一个通识性界定:“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第二,科学界定数字经济时代地位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必须以“技术社会形态”概念为参照。我们知道,“技术社会形态”是用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作为划分社会发展形态的一种基本方法,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劳动资料与经济时代关系的如下论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据此,人们提出了技术社会形态的概念,并划分出了渔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等历史形式。
根据上面两个前提性问题,我们当下所说的数字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形式?理性告诉我们,数字经济无疑应该属于信息经济的一种主体发展形式。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把当代社会称之为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在世界各个国家和企业制定的发展纲要和规划中,似乎无形中依然认同数字经济只是工业经济的一种高级发展形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阶段的一种更为高级的经济发展形式。
在这里,一个极其典型的悖论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宣告了信息革命正在到来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数字经济》《网络社会的崛起》和《数字化生存》告诉我们数字经济已经到来的时候,近几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却依然从工业革命意义上界定我们的经济时代。
由此,当我们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甚至“新经济”这些与“数字经济”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切换中思考数字经济的发展意义时,既不能严重低估,也不能简单拔高。从原则的高度说,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发展观和社会历史观问题: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之后的人类社会是否能够借助于数字经济迎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和社会形态?
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及其哲学意义
无论如何定位,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都充分表明,数字经济在当代社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说,这种作用表现有三:
首先,数字经济为人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创造了条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在信息社会,数字形式的“比特经济”将取代工业社会里物质形式的“原子经济”而重建现代世界的经济体系。事实证明,作为物理世界、网络世界和人类社会“人机物”的三元融合,数字经济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跨地域性和高关联性等特征,使得它实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真正征服,使经济变得轻盈、灵活、飞速发展。这不仅大大地减少了人们的交易时间和交易费用,而且从根本上使人们日渐摆脱了传统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时空限制,获得了人身在时间、空间、居留地点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从而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自愿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如果说“时间”就是“人的积极存在”和“人的发展的空间”,而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拥有“自由时间”基础上实现“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的“一致”,那么数字经济正在为人们拥有更多自由时间从事个性化生产和服务奠定着充分的经济社会前提。
其次,数字经济带来了劳动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变化。从根本上讲,数字经济是一种融合创新经济,其本质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劳动的呈现。就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规模来说,无论是作为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信息产业本身,还是作为数字经济融合部分的信息通信技术对其他产业的融合渗透,数字劳动都呈现出其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数字劳动所具有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特征带来的一个根本社会变革就是,不仅推动了传统机械性劳动向现代智能性劳动的转变,而且模糊了传统经济活动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生产者与消费者、内行人与外行人之间的明确界限,使工业经济所依据的两个劳动基础(“占有他人劳动时间”和“直接的联合劳动”)也日渐消失了。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托夫勒将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这两个词合成了产消者(prosumer)一个词,认为产消合一这一微妙而意义重大的变化,带来了市场在社会上作用的急剧改变和人们劳动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托夫勒的预言已为世界各国正在强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公共服务和金融业等实体经济和产业经济力求借助于“互联网+”实现数字化转型等事实所证实。
最后,数字经济为现代社会走向共享经济提供了一条探索性方案。在上海“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和2017年贵阳“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马云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就大数据时代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发展问题展开了两次论战。两次论战背后隐含的其实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前途这个大问题:数字经济能否建构起智能型大数据的计划经济?数字经济能否弥合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对立?以此来看,当马化腾针对数字经济首次出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事实而提出“‘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网络强国是目的”这样的解释时,他显然忽略了“数字经济”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分享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数字经济只是手段,分享经济才是目的。唯有数字经济才能借助于“互联网+”体现出的开放精神、平等精神、普惠精神和共享精神,推动人类“从产权观念向共享观念的转变,从交换价值到共享价值的转变”,通过改变和重构传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关于占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产权革命,建构起里夫金所说的真正超越“市场资本主义”的“协同共享”的新经济形态。
必须正确处理数字经济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几个关系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正确面对。
首先,经济手段与经济目的的关系。数字经济与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该是手段与目的或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的关系。然而,“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当人们日益消融在数字经济公然承诺的必须每日每时去从事和完成的生产生活的繁琐细节时,数字拜物教就会像其他拜物教那样如期而至。对数字经济的过分迷信与过度崇拜,不仅会产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谁更重要的社会大讨论,而且极可能出现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人作为人”和“人作为工作者/消费者”之间的“断裂”。发展所及,正如西美尔所说,人们忘记了手段“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以至于“陷身于这些手段的迷宫中”而“遗忘了最终目标”。所以,无论是互联网+、数字经济还是网络强国,都是人和社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只具有外在的、相对的、阶段性的意义,不应该对之过分迷信和过度崇拜。
其次,数字素养与数字鸿沟的关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成了最大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于是,以获取、理解与整合数字信息为根本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就成了数字人才的必备素质。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仅全世界仍有40多亿人不能上网,我们国家亦有半数人口不能上网或不会上网。显然,在“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的基本人权”的条件下,随着数字技术向各领域的渗透,数字素养与数字能力越来越成为不仅对消费者而且对生产者的新要求和硬约束,对于那些无法上网、无力上网、不会上网的人来说,数字鸿沟的存在不仅无法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与素养能力,反而有可能形成新的社会隔离与社会忽视。所以,如何通过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的提升消除数字鸿沟进而弥合经济与社会鸿沟,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最后,经济共享与社会支配的关系。数字经济既实现了信息共享又实现了经济共享,然而,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和工具,它的作用是技术中性的、二重性的,既可能弥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差异,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数字经济所蕴含的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拓展和辐射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必然带来传统的技术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在当代社会的“再结构”与“再组织”过程,创制出一种“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比如,在一个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与高端设备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是否会产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短板和软肋效应?在一个依然受资本逻辑控制的经济社会中,如何才能产生出协同、共享和互利的共享经济,从而弥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对立?在一个维系于再生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取决于生产者的社会,是否会因为技术专家的傲慢和统治而产生如鲍曼所说从“穷人”向“新穷人”转化的新的社会排斥、社会歧视和社会怨恨?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决,通过数字经济实现重建信用和信任的共享经济、实现以网络强国为后盾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