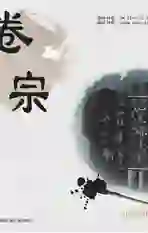节庆民俗保护与创新中的困境
2018-06-06曾红梅
摘 要:节庆民俗包含诸多活动及符号意义,节庆中鲜活的人物正是传统文化的生机所在。本文以兴文苗族“花山节”被当地文化促进会搬上舞台为例,通过对其起源、现状的探究,思考节庆民俗在保护与创新中是否可能因“民”的消失而丧失其文化生命力。
关键词:花山节 文化展演 文化主体
当代社会,无论哪一个民族,其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都绕不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与冲击。作为文化大观园的节庆民俗,其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习惯、活动空间可否会因搬上舞台而影响其民族信仰、情感、精神的表达呢?
一、“花山节”的前世今生
花山节的起源,主要有三:一是人类繁衍说。“传说在远古时代,有两位神仙叫蒙博、蒙耶,他们下凡后创立了农耕,解决了衣食问题,但无子女,蒙博、蒙耶就去问叟, 叟就说‘要想生儿育女就得设花坛、立花杆、祭祀许愿。蒙博、蒙耶按照叟的要求办后便如愿以偿。从此,族人便效仿举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花山节。”
二是神树信仰说。“传说初到兴文县境内的苗民,见仙峰山附近天上星星洒落到地上,有很多红、黄、蓝、白、紫五色艳丽的花朵。此期间一个土著长老对新来的苗民说:‘树上的花会结果,果是制造油的原料,可供食用。还是晚上照明用油的生活必需品,要新来的苗民们传承下来,把花树发展起来。这个花树叫‘山茶树,要苗民们把这山花树当为神树信仰起来。苗民们便用红布条把山茶树栓起来,并燃香烧烛,敬酒拜树,祈求开花结果。后来果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大家纷纷效仿,山茶树后演变为杉树。”
三是祖先信仰说。“花山节”过去是在老人去世、举办过篝火晚会后的第三年所举办的,用以召唤老人的魂灵。现在则被定在了每年的3月3或者是正月15前几天。其主要意思就是子女、儿孙来迎接老人,老人保佑儿女平安。
兴文县举办花山节的确切时间无法考证,据说在明朝时期苗族人就开始举办,清朝时达到顶盛。花山节举办的地点全县大概有24处。其始建时一般都是由婚后多年无子女的苗族人选定一个山坪,并选择黄道吉日,请苗族长老在山坪上立花杆,举行祭祀祈祷活动,同时,要备酒肉,请亲朋好友参与同欢共饮,并连续举办三年。这样就形成了固定的花山坪,以后就由民间自由组织活动。这也印证了其起源的第一种传说。
从前的24个花山坪,解放前每年正月间都有人活动。解放后,民间花山节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玉屏山的 “踩山亭”至今仍在。新世纪以来,花山节随兴文世界地质公园旅游业的发展而发展。近年来,针对苗族古歌濒临失传以及表演技藝如“上刀山”、“下火海”等人员年龄偏大等状况,苗族文化促进会应运而生。苗族文化促进会一方面依托中共兴文县委、县政府斥资主办花山节大型活动,另一方面依托县文化馆、县民族中学等进行苗族民间文化的培训和保护等工作,同时还引导建立石海苗族艺术团,进一步挖掘和打造特色节目,以石海苗寨、县城温水溪度假村等地为基地,加强苗族传统文化与旅游文化的结合,使兴文苗族花山节大放异彩。
二、“花山节”在保护与创新中的困境
在田野调查及文献查阅中,我们发现,花山节各地节期不一,通常在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间,也有在三月三,五月或六、七月过节的。在兴文县毓秀苗乡,苗族村民对花山节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春节期间的“打秋”活动,以及过去用“土电话”来对苗歌。但是,“山上”的花山节搬到“街上”后,首先在形式包装上就有了一些不同,如电子设备的完善使得歌舞的表演渐趋舞台化、标准化;打秋活动也渐被其他现代娱乐所取代,如斗牛,爬杆(从打秋改造过来)等竞赛性活动。此外,苗族是一个巫文化传统十分浓厚的民族,从蚩尤时代的“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到“三苗”时代的“相尚听于鬼神”,再到汉代的“其俗信巫而好祠”,以及近现代的多神灵信仰,如毓秀胜利村的“河南教”,巫文化因子在苗族传统节日文化中积淀深久,许多节日活动无不是由祭祀仪式演化而来。但这些巫文化因子不可能为外来的旅游者轻松解码,于是苗族文化促进会挖掘出“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技艺。另外,随着兴文石海侗乡旅游业的发展,花山节定在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一个月里,以迎合市场。这就引出了第二个不同,即参与主体的不同。现在广为流传的花山节多是经过媒体包装、知识精英打造后出现在旅游胜地的花山节,因此,这个节日的参与人群多为职业表演者以及旅游观光客。
花山节已经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在其起源传说上,文献资料和山野苗民的记忆存在显著差别。大山里的花山节渐趋没落,而舞台上展演的花山节却大放光彩,那么究竟谁才是该节日文化的主要受众呢?是知识精英,是表演者,还是游客?山里的苗民当然不可能花上一笔不菲的费用跑到石海侗乡参与花山节的庆典,但是文化的展演如果没有真实生活在里面的人的参与,它很可能变成一个空壳。继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花山节”在其传承和发展中已然具有了两种内涵,一个在山上,一个在街上;一个代表的是普通苗族人民,一个代表了创新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这种“上下”的分离也许正是其传承、保护与创新的困境。
三、节庆民俗发展困境中的困惑
田野调研中,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文化展演中“人”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民族的青年、少年将要去哪,谁也没有办法。所以兴文县苗族文化促进会的重心就很自然落在了具体某一类表演形式的传承人接档上,特别是“上刀山下火海”这类的表演人。这在杨永华老师的《兴文在挖掘和使用苗族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一文中也有所表述。但是,节庆民俗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某几个、几十个传承人的事,它还涉及到一个群体认知的问题,也就是“谁的传统?”“谁来传承?”这类的问题。正如苗族文化促进会理事马仕俊所言:“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过节,祭花竿,打枪,耍狮,唱苗歌,吹芦笙,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过这个节,这一点很多青年人是不知道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不知道”,花山节这个形式才显得尤为重要。据说,苗族古歌的渐趋消亡也是因为这个“没氛围。”如果那个围炉夜话、谈天说地的语境消失了,那么节庆便有可能是它回魂的最后场域。所以说,开展民族传统节日活动,不仅是一种生活的调节,它更是人们认知本民族文化的窗口,“花山词”及其仪式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敬祖追远、崇尚英雄”情结,也是民族自豪感的自然生发。
故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节庆活动中的人。节庆展演无可厚非,因为没有旅游者不行,但是,只有旅游者更不行。就如花山节上的“芦笙四部曲”一样,族群的认同是有情境性的,苗族人在婚丧嫁娶的生活过程中体验并习惯着芦笙的声音,所以在族群聚集以及意识到族群差异时,容易在芦笙中产生归属感和亲切感,它是民族情感的一种天然符号。但是,按照五线谱演奏的芦笙歌舞,会不会因为规范了统一的动作而失去其内在的生命力呢?那些对世界对土地对族群甚至是对个人差异的认识,在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后,情感从何而来?我们又如何来认同一个只拥有技巧而没有艺术精神的表演?可见,花山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政府和民间组织正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抢救,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承主体人群或者正在融入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中,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到“上面”的保护中来(像毓秀苗乡的山民)。正如苗族文化促进会的成员的焦虑:“青年一代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是有些东西快要消失了,我们有责任留下一些它存在过的证据。先就这样吧。”
参考文献
[1]杨永华《兴文苗族》,中国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2]龙海清《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当代意义》,《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10月第10期。
[3]袁定基 张原 《苗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承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4月第4期。
作者简介
曾红梅(1987-),女。绵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