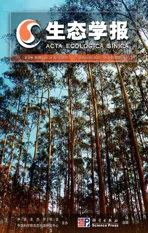破碎化生境中粗柄独尾草种群大小对繁殖特性的影响
2018-04-19王海娟王丹丹
安 静,刘 鸯,王海娟,王丹丹,张 霞,吴 玲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石河子 832000
生境破碎化是一种景观动态变化[1],即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干扰,使景观由单一、均质和连续的整体趋向于复杂、异质和不连续的斑块镶嵌体发展的过程[2- 5]。生境破碎化造成生物种群生存生境总面积减小,彼此孤立的小斑块越来越多[6],产生隔离的异质种群[7- 8],而生物种群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群的大小[9],很多植物表现出对生境破碎的敏感性,就是由于生境破碎导致种群变小以及种群间隔离的加剧[3]。当前,生境破碎化是许多物种生存的主要威胁[10- 14],从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寻找保护地方特有种的规律和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
粗柄独尾草(Eremurusinderiensis)是生长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部固定、半固定沙丘上的多年生类短命植物,早春时节固定沙丘重要的植物之一[15]。在自然生境中,该物种地下芽能形成新的个体,利用早春(3月底至4月初)地面积雪融化、春雨开始、土壤湿润的有利条件,在60d内迅速完成从萌芽到开花结果并形成种子的整个生活史过程[16- 17]。虽然生活周期短暂,该物种却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早春防风固沙、稳定沙面的主要贡献者以及维持荒漠生态系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学意义[15,18- 19]。然而,随着绿洲沙漠过渡带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导致粗柄独尾草所在生境斑块化现象明显,斑块数目、斑块隔离程度增加。以往有关粗柄独尾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核型分析、光合特性、化学成分、生物量分配等方面[20- 23],有关生境斑块化对其繁殖特性的影响尚未见报道。
本文基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不同破碎斑块生境下粗柄独尾草种群的野外调查,分析研究生境破碎化程度与其种群大小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生境破碎化对其种群幼苗比例、自然座果率、结籽率、萌发率等的影响,了解现有粗柄独尾草种群生存现状,分析种群大小与受干扰情况及其种群动态与内在的生活史特征和外在的干扰状况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揭示生境破碎化后粗柄独尾草种群大小动态变化规律对其繁殖成功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沙漠绿洲过渡带,地理坐标为44°45′00″—44°55′49″N,85°31′30″—85°58′13″E,海拔在304.7—343.4m。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最大的固定与半固定沙漠,该沙漠年积温3000—3500℃,降水相对较多,约70—150mm,冬季稳定积雪深度多在20cm,荒漠植物长势良好,春季气温回升积雪融化也为早春短命、类短命植物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24- 25]。研究区主要植物有:白梭梭(Haloxyionpersicum)、柽柳(Tamarixchinensis)、琵琶柴(Reaumuriasoongorica)、白茎绢蒿(Seriphidiumterraealbae)、角果藜(Ceratocarpusarenarius)、羽毛针禾(Stipagrostispennata)等,短命植物有粗柄独尾草、异翅独尾草(Eremurusanisopterus)、早熟猪毛菜(Salsolapraecox)、沙大戟(Chrozophorasabulosa)、东方旱麦草(Eremopyrumorientale)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人工绿洲面积扩大,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人类干扰活动不断增强,使得粗柄独尾草原有连续成片的自然生境被分割,景观破碎化问题日益突出,自然植物种群生存受到威胁。
1.2 种群的选取
本研究通过对沙漠绿洲过渡带粗柄独尾草自然种群的充分踏查,考虑人为干扰强度及生境破碎化程度等因素,于2015年4月—6月、2016年4月—6月在石河子垦区炮台镇、西古城镇和十户滩镇(简写为PTZ、XGCZ、SHTZ)三地共选择9个斑块分别设为样地。野外观察发现各斑块间的距离远在100m之上,因此可将不同斑块划分为不同种群[26],其中PTZ1与PTZ2相距4.4km;XGCZ1、XGCZ2相距1.5km,与XGCZ3相距2.3km;SHTZ1、SHTZ2相距4.6km、与SHTZ3相距1.7km、与SHTZ4相距4.3km以上(图1)。调查记录各斑块样地干扰因素、干扰年限、地理坐标、海拔高度、斑块面积、斑块周长等信息,并根据这些基本信息将斑块的破碎程度由高到低划分为3个等级,即破碎程度强、中、弱。
其中,将面积小、形状复杂,且干扰因素多、干扰年限长的斑块划分为破碎化程度强的斑块;将面积中等,且干扰因素一般、干扰年限较长的斑块划分为破碎化程度中等的斑块;将面积较大、形状较规则,且干扰因素较少或没有的斑块划分为破碎化程度弱的斑块(表1)。

图1 研究区及样地示意图Fig.1 Study area and sampled plots炮台镇种群1记作PTZ1,以下类同
1.3 种群大小及幼苗比例的统计
于2015年、2016年4月15—19日,粗柄独尾草生长旺盛期(即当年实生苗大部分已萌发且前一年休眠的植株也打破休眠转入营养生长阶段)采用样方法对不同斑块中粗柄独尾草种群大小进行统计。每个斑块设置3个10m×10m样方,调查各样方内粗柄独尾草的植株数,并对样方内粗柄独尾草进行每株调查,调查指标为轮叶数。轮叶数为1的为当年实生苗,幼苗比例=(斑块种群粗柄独尾草总数/实生苗数)×100%。
1.4 自然座果率统计
2016年6月4—8日,粗柄独尾草果实成熟后,随机选取各斑块种群样方内各10株植物,统计其果实数目及花柄数,自然座果率=果实数/花柄数×100%;在果实成熟后种子散布前,收集各斑块种群样方内所有植株的种子,每株分开采集,装入种子袋带回实验室备用,结籽率=种子数/(花柄数×12)×100%(粗柄独尾草每花平均胚珠数为12)。

表1 各样地基本信息
炮台镇种群1记作PTZ1,以下类同;一级道路是指由石、 土铺设的道路, 可走小型机动车;二级道路是指连接于一级道路、 由行人行走而形成的狭窄土路, 一般不走车辆[27]
1.5 种子形态特征
(1)种子大小:随机选取每个种群的30个植株,每株采集10粒种子,用电子游标卡尺(LINKS哈量电子游标卡尺,量程为20.00mm,最小刻度尺为0.01mm)测量种子长度、宽度及种翅宽;(2)种子千粒重: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龙腾ESJ110- 4B)测量,以100粒30组的平均值为其平均重量。
1.6 种子萌发特性
由于粗柄独尾草种子具有休眠特性,采集的种子在自然风干后将供试种子置于冰箱冷冻层(-18 ℃)保存,采用低温层积的方法打破种子休眠。种子萌发试验采用沙培法,沙土采集于粗柄独尾草原生境,过筛去除杂物和植物残枝后,用蒸馏水冲洗三遍,烘干灭菌后备用。
萌发实验始于2016年10月14日(低温层积4个月后),选取籽粒饱满、无破损、无虫害、大小一致的成熟种子,用0.1%氯化汞消毒5—10min,蒸馏水冲洗3遍后将种子放在装有细沙的培养皿(直径90mm)中,每皿50粒,每个处理4个重复,置于12h光照/12h黑暗(光照强度为4000lx)、培养温度为4—10℃的培养箱(GXZ智能型)中进行培养。在种子萌发过程中为了保持湿度一致,依据实际情况,每天添加蒸馏水。种子的萌发以胚芽突破培养基质2mm视为萌发,每24h统计一次发芽种子数,直到萌发结束。实验结束后计算分别萌发率,公式如下:
种子萌发率(%)=n/50×100%(n:萌发种子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群大小、幼苗比例及其关系
破碎度轻的斑块种群规模大,如XGCZ3种群2015年个体总数为1381.48株,2016年种群更是增长到1829.63株;重度破碎的斑块种群大小为229.63—425.93株,2016年种群稍有增长(图2)。相关分析表明,粗柄独尾草种群大小与种群中1龄级幼苗的比例呈极显著相关,2015年与2016年r值分别为0.955、0.968,P值均小于0.001(表2),说明种群大小影响到种群中幼苗所占的比例,即种群越小,年龄结构中幼苗所占比例越小;而种群越大,幼苗数量也越庞大,更有利于种群的更新与发展。

图2 粗柄独尾草各种群大小与1龄级幼苗数Fig.2 Population size and seedling number of E. inderiensis

种群Populations2015年2016年个体总数Individualnumber一龄级幼苗数Seedling幼苗占比Seedlingpercentage个体总数Individualnumber一龄级幼苗数Seedling幼苗占比SeedlingpercentagePTZ1325.9325.9310.23496.3011.112.24PTZ2229.6333.3311.29374.0755.5614.85XGCZ1970.37359.2637.021333.33522.2239.17XGCZ2555.5677.7814.00637.04114.8118.02XGCZ31381.48448.1532.441829.63585.1931.98SHTZ1303.7062.9620.73307.4129.639.64SHTZ2425.93118.5227.83522.22137.0426.24SHTZ3696.3096.3013.83622.2292.5914.88SHTZ41155.56351.8530.451425.93577.7840.52r0.9550.968P0.0000.000
2.2 9个种群自然座果率、结籽率与景观破碎化的关系
由表3可知,粗柄独尾草单株花数、果数、种子数以及自然座果率与结籽率在9个斑块中均表现为XGCZ3种群最大,PTZ1种群结籽率最低,PTZ2种群除结籽率外其他各项指标均最小;从破碎化程度来看,随着破碎化程度的加强,花数、果数、种子数、自然座果率与结籽率均下降,且在斑块种群之间差异显著。
2.3 种子形态特征及千粒重与景观破碎化的关系
景观破碎化条件下条件下粗柄独尾草种子的种子千粒重表现为:随着破碎化程度的加强,种子千粒重减小;形态特征中的长度和宽度也符合这一趋势(表4),说明随着生境破碎化程度的逐渐加强,斑块种群种子体积变小、种子变轻;种子翅宽虽然也有减小的趋势,但是比较种翅宽/种子长和种翅宽/种子宽会发现存在干扰、有一定破碎程度种群的种子两个比值大于无破碎或轻度干扰破碎的种群。种群种子体积变小、种子变轻利于种子的扩散;同理,种翅占比更大则更有利于种子随风散播的更远。
2.4 种子萌发特性
粗柄独尾草种子在培养第20—30天开始萌发(图3),从萌发曲线来看,景观破碎化程度弱的XGCZ1、XGCZ3、SHTZ4,以及破碎化程度中等的XGCZ2的4个斑块种群种子萌发趋势较为一致,第25天开始萌发,继而快速萌发,培养第45天左右就能达到最大萌发率,最大萌发率在90%以上;景观重度破碎化的PTZ1与PTZ2斑块种群的种子萌发曲线则表现为初萌后有一个缓慢增长阶段,萌发速率较为缓慢,在第50天左右萌发率开始加快,最终在培养70d后能达最大萌发率。粗柄独尾草果实成熟期(6月中旬)正值荒漠干热季节来临之际,因此,在这种对异质环境和荒漠环境的适应过程中粗柄独尾草可能演化出了一种风险分摊策略,即加大对土壤种子库的投入。

表3 粗柄独尾草9个种群自然座果率与结籽率(平均值±标准误差)(n=30)
表中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用LSD多重比较变量间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4 9个种群粗柄独尾草种子千粒重及形态特征(n=300)
表中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用LSD多重比较变量间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图3 9个种群粗柄独尾草种子萌发曲线Fig.3 Seed germination of E. inderiens in 9 populations
3 讨论
生境破碎常伴随着种群变小及隔离程度的增加,进而影响到传粉者访花频率、花粉沉降、座果率、植株适合度以及植物种群的生存力[28- 29]。粗柄独尾草为长寿命、多年生、类短命植物,它们的长寿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对生境破碎化负面影响的抵抗力,但不管是长寿命的还是短寿命的植物,当种群减小时,传粉过程中花粉数量及质量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它们的繁殖很快就会受到冲击[30- 31],表现为种群自然座果率、结籽率的下降等方面。自然生境中每一个斑块资源都有限,生境破碎化造成物种的部分生境丧失,种群原有生境面积减少,即生境容纳量减少,所能维持的平均物种个体数量随之降低。同时,种群扩散受到限制,导致种群分布范围缩小,进而影响种群的未来发展动态。在过去20多年的植物种群生境破碎方面的研究中,尤其重视研究破碎化对植物繁殖的影响[32],但不同植物对生境破碎的响应不同,植物种群大小并不总是决定种群生殖成功的主要因素[33]。胡世俊等人[13]通过对破碎化生境中缙云卫矛(EuonymuschloranthoidesYang) 6个种群的生殖特性研究也发现,小种群的自然座果率低,种群大小与座果率、幼苗比例之间呈显著相关,表明生境破碎不利于该物种的生殖成功,导致小种群的座果率与幼苗比例降低;王海娟等[34]分析了荒漠斑块生境中异翅独尾草(E.anisopterus)种子形态特征,发现在被干扰的生境中,种子有尺寸小、质量轻、种翅长且小种子比率较高的特点,说明干扰条件已经对异翅独尾草种子的形态特征产生了影响;郭丽等人[35]通过野外多位点同时段取样,对比研究了不同斑块种群伊犁郁金香(TulipailiensisRegel.)种子的形态学特征和萌发特性,发现随着生境破碎化加剧,种子体积变小、种子变轻,相比破碎化程度较弱、生境破碎化程度中等和较强的斑块,种群种子的萌发优势更明显。种子的形态和萌发特性既反映了亲代的繁殖特性,又反映了子代幼苗建群的能力。种子大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性状,是植物生活史的重要特征[36],一个植物物种的种子重量一般被看作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和性状[37- 38],影响种子萌发、幼苗定居、存活、个体适合度以及植物生活史特征的表达[39],最终影响整个群落的物种组成、结构和功能[40]。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表明,生境破碎化限制了种群分布,降低了种群大小,甚至还可能改变种群结构。生境破碎化对物种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显著负面作用。因此,对于人类活动和放牧干扰较重生境中的粗柄独尾草种群,应积极进行限制或禁牧及围封育林措施,减少人类干扰,发挥其有性生殖与无性繁殖(通过地下部分)实现自然恢复的潜力。
4 结论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绿洲沙漠过渡带粗柄独尾草分布的自然生境正遭受着景观破碎化的威胁。本研究发现,随着生境破碎化程度的加强,粗柄独尾草种群规模不断减小,而更小的种群对应更小的幼苗比例、座果率、结籽率与萌发率,不同种群的萌发曲线因种群大小及生境破碎化差异,呈现为不同的萌发趋势及变化特征。上述4个方面的分析结果都反映了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强以及破碎化程度较高的斑块生境不利于粗柄独尾草种群的生存与发展,种群在未来有趋于衰退的风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Vos C C, Opdam P. Landscape Ecology of a Stressed Environmen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td., 1993.
[2]Harris L D. The Fragmented Forest: Island Biogeography Theor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Biotic Divers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3]Fahrig L. Effects of habitat fragmentation on biodiversity.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2003, 34: 487- 515.
[4]Saunders D A, Hobbs R J, Margules C R.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cosystem fragmentation: a review. Conservation Biology, 1991, 5(1): 18- 32.
[5]武晶, 刘志民. 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综述. 生态学杂志, 2014, 33(7): 1946- 1952.
[6]Rodríguez A, Delibes M. Population fragmentation and extinction in the Iberian lynx.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3, 109(3): 321- 331.
[7]张育新, 马克明, 牛树奎. 异质种群动态模型: 破碎化景观动态模拟的新途径. 生态学报, 2003, 23(9): 1877- 1890.
[8]Santos K D, Kinoshita L S, Santos F A M D. Tre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similarity in semideciduous forest fragments of southeastern Brazil.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7, 135(2): 268- 277.
[9]García M B. Life history and population size variability in a relict plant. Different routes towards long-term persistence.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2008, 14(1): 106- 113.
[10]Keinath D A, Doak D F, Hodges K E, Prugh L R, Fagan W, Sekercioglu C H, Buchart S H M, Kauffman M. A global analysis of traits predicting species sensitivity to habitat fragmentation.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017, 26(1): 115- 127.
[11]瞿娇, 武碧先, 苏黎明, 操国兴. 生境破碎化对星叶草繁殖成功的影响.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2016, 22(1): 151- 155.
[12]智颖飙, 杨持, 王中生, 安树青, 王再岚, 李红丽, 宿志安, 王强. 孑遗植物四合木(Tetraenamongolica)的濒危肇因与机制. 生态学报, 2008, 28(2): 767- 776.
[13]胡世俊, 何平, 张春平, 张益锋. 破碎生境中种群大小对缙云卫矛生殖成功的影响. 生态学杂志, 2013, 32(4): 821- 824.
[14]林永慧, 何兴兵, 田启建, 胡文勇, 陈玲, 何平. 生境破碎化后濒危植物缙云卫矛种群的数量动态. 植物研究, 2011, 31(4): 443- 450.
[15]钱亦兵, 吴兆宁, 张立运, 赵锐锋, 王小燕, 李有民.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短命植物的空间分布特征. 科学通报, 2007, 52(19): 2299- 2306.
[16]刘媖心. 中国沙漠植物志-第一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223- 225.
[17]崔乃然. 新疆植物志(6). 乌鲁木齐: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1996: 480- 482.
[18]王雪芹, 蒋进, 雷加强, 张伟民, 钱亦兵.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短命植物分布及其沙面稳定意义. 地理学报, 2003, 58(4): 598- 605.
[19]张立运, 陈昌笃. 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植物多样性的一般特点. 生态学报, 2002, 22(11): 1923- 1932.
[20]吴玲, 张霞, 马淼, 王绍明. 新疆独尾草属植物的核型分析. 武汉植物学研究, 2005, 23(6): 541- 544.
[21]陈蓓雷. 新疆三种独尾草属植物光合特性的研究[D]. 石河子: 石河子大学, 2008.
[22]王恒, 张丽, 朱瑞罡, 田丽萍, 谭勇. 新疆3种独尾草总蒽醌和芦荟大黄素含量的比较.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16, 36(6): 437- 440.
[23]陶冶, 张元明, 周晓兵, 程军回. 类短命植物粗柄独尾草器官生物量分配与估测. 干旱区研究, 2012, 29(1): 93- 100.
[24]季方, 叶玮, 魏文寿.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固定与半固定沙丘成因初探. 干旱区地理, 2000, 23(1): 32- 36.
[25]周宏飞, 李彦, 汤英, 周宝佳, 徐宏伟.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积雪及雪融水储存特征. 干旱区研究, 2009, 26(3): 312- 317.
[26]Mavraganis K, Eckert C G. Effects of population size and isolation on reproductive output inAquilegiacanadensis(Ranunculaceae). Oikos, 2001, 95(2): 300- 310.
[27]毛志宏, 朱教君, 谭辉. 干扰对辽东山区次生林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2006, 17(8): 1357- 1364.
[28]Winter C, Lehmann S, Diekmann M. Determinants of reproductive succ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endangered river corridor plants in fragmented habitat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8, 141(4): 1095- 1104.
[29]Dauber J, Biesmeijer J C, Gabriel D, Kunin W E, Lamborn E, Meyer B, Nielsen A, Potts S G, Roberts S P M, Sõber V, Settele J, Steffan-Dewenter I, Stout J C, Teder T, Tscheulin T, Vivarelli D, Petanidou T. Effects of patch size and density on flower visitation and seed set of wild plants: a pan-European approach. Journal of Ecology, 2010, 98(1): 188- 196.
[30]Steffan-Dewenter I, Tscharntke T. Effects of habitat isolation on pollinator communities and seed set. Oecologia, 1999, 121(3): 432- 440.
[31]Kéry M, Matthies D, Spillmann H H. Reduced fecundity and offspring performance in small populations of the declining grassland plantsPrimulaverisandGentianalutea. Journal of Ecology, 2000, 88(1): 17- 30.
[32]Aguilar R, Ashworth L, Galetto L, Aizen M A. Plant reproductive susceptibility to habitat fragmentation: review and synthesis through a meta-analysis. Ecology Letters, 2006, 9(8): 968- 980.
[33]Klank C, Pluess A R, Ghazoul J. Effects of population size on plant reproduction and pollinator abundance in a specialized pollination system. Journal of Ecology, 2010, 98(6): 1389- 1397.
[34]王海娟, 段呈, 安静, 吴玲, 张霞, 王绍明. 荒漠斑块生境中异翅独尾草种子形态特征研究. 种子, 2015, 34(5): 17- 21.
[35]郭丽, 吴玲, 王绍明, 段呈, 赵维奇. 破碎化生境中伊犁郁金香种群种子形态特征和萌发特性的适应性演化. 种子, 2015, 34(9): 1- 5, 10- 10.
[36]张丽坤, 王朔, 冯玉龙. 紫茎泽兰种子形态特征和萌发特性与其入侵性的关系. 生态学报, 2014, 34(13): 3584- 3591.
[37]Harper J L, Lovell P H, Moore K G. The shapes and sizes of seed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0, 1: 327- 356.
[38]于顺利, 陈宏伟, 李晖. 种子重量的生态学研究进展. 植物生态学报, 2007, 31(6): 989- 997.
[39]王桔红, 杜国祯, 崔现亮, 郑秀芳, 齐威. 青藏高原东缘61种常见木本植物种子萌发特性及其与生活史的关联. 植物生态学报, 2009, 33(1): 171- 179.
[40]Silvertown J W. Seed size, life span, and germination date as coadapted features of plant life history.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81, 118(6): 860- 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