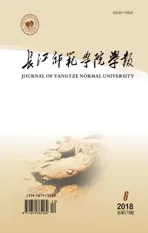苗疆开辟前后黔东南农业生产模式变迁
——基于清代至民国初期的考察
2018-03-29李凌霞
吕 炎,李凌霞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清代雍正年间开辟苗疆后,为了提高农业发展效果,地方官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开辟的黔东南“新疆六厅”的农业生产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图以一手奏折档案为依托,从农作物种类、农业生产工具、农田管理等方面呈现黔东南苗疆农业生产模式的变迁,以揭示出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相关因素。
一、黔东南苗疆开辟前的农业生产
黔东南苗疆位于由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山地过渡的山区地带。都柳江自西南奔流入各县境,于丘陵山地形成一些地势较低的平坝,自古以来是苗、侗、水、布依族、土家族、壮、瑶等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居住区域。这里“崇山密箐,鸟道羊肠,瘴疠繁兴,天时人事迥与世殊”[1]1,一直是帝国边陲“不通声教”的“化外之地”,国家力量鞭长莫及。清雍正“开辟苗疆”前,当地的农业生产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地农业生产模式基本上处于“刀耕火种”的游耕状态。如史料所载,其地“焚烈山林,久荒之土,一亩数倍,古州、丹江禾长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粟”[2]164,“苗人聚种而居……依山傍涧,刀耕火种,其生性之野蛮,洵非政教所可及”[3]20。刀耕火种式的迁移农业需要大量的土地,以进行轮替休耕,因此对土地的利用效率较为低下。
其次,农业生产工具相对缺乏,当地少数民族的农具仅有犁和耙。古歌唱道:“香崔来造犁,都克来造耙,造成咱才犁,造好咱才耙。”[4]664水利设施相对简单,主要通过简单的“连筒”在短距离内引水灌溉。“苗有取水具名曰连筒,以大竹为之,按笋门合,随山势为上下吸取涧水,可逆流至数十丈。”[3]23农业生产工具的匮乏限制了土地的开垦面积。整个贵州地区自然耕作条件亦非常恶劣。康熙年间,贵州布政使孟世泰会同粮驿贵东道高恒豫在给康熙的奏折中称:“黔省重峦叠箐,田亩均在万山之中,土性寒冷,瘠薄不堪,秋成籽粒,难抵内地膏腴田产三分之一,开垦山田,人工牛种又倍于他省,迨四五年后始有些少收获,不偿人工牛种之费。”[5]2148雍正七年(1729),贵州巡抚张广泗则奏称:“黔省山多田少,最为瘠薄。若雨水稍多,则高阜者得济,而低洼者浸损;若晴霁稍久则低洼者尚资灌溉,而高阜者已觉干旱。是以历年收成不过六七分至七八分而止。”[6]57耕地面积不足成为粮食低产的原因之一,生产工具的简单粗陋则限制了单位面积内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再次,农作物种类单一。当时仅有水稻、玉米、粟米(小米)等几种。“(雍正七年)新开苗疆今年皆风雨应时……稻谷有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长至二尺有奇”[6]56,因此,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庆云七现”事件溢美歌颂雍正“文治武功”,但他能奏报的农作物品种只有稻谷和粟米[6]58。另外,苗族古歌唱道:“冬天吃我田里鲫鱼,夏天啃我地中玉米。”[7]21其中只描述了稻米和玉米两种作物。这一点在地方官的奏报中也得到了印证。乾隆三年(1737),古州镇总兵韩勋奏称:“小麦、高粱……黄豆、芝麻、菽麦等种……向来新疆地方……素不出产。”[8]75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古州地区粮食的获取渠道单一,依赖于水稻、玉米、粟米(小米)等少数作物,以及在水田内养殖的鲫鱼。一旦某种作物因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原因歉收、绝收,则当地少数民族就面临严峻的生存威胁。
迁移性的农业、低效的生产经营模式、简陋的农业工具、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黔东南苗疆土地的开垦数量极为有限,相对单一的种植作物种类使得当地粮食产量处于较低水平。另外,粮食过分依赖于个别作物,导致当地人对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引起的饥荒的抵抗能力低下,生活极为困苦,“娶妻只有一子,多即淹之,以为无产业给养也”[9]160,“深居林箐,掘野笋、薇蕨食之,饥寒交迫,时出为匪,其势然也”[10]158。饥饿,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出掠地方”的原因之一,也是清政府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前的社会常态。
二、黔东南苗疆开辟后的农业生产
雍正二年(1724),鄂尔泰和张广泗经略西南,中央王朝开始对黔东南苗疆进行大规模剿抚并举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招抚;至乾隆元年(1736)镇压“古州苗民起义”后,中央王朝实现了对古州及周边地区的直接统治。在“开辟苗疆”以后,随着中央王朝的治理深入,内地大量人口迁入苗疆进行军屯,汉人移民不断与当地少数民族交流和融合,古州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获得较大程度的发展。
首先,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工具得以引进和改良。在“开辟苗疆”之初,古州地区西北部的平越州便已有会制作水车和龙骨车的工匠,“龙骨车地方黔省工匠多能制造不必远求,即使工匠缺少之处亦可就近于平越等府雇觅,无庸远赴江楚雇募致滋劳费”①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这一类水利灌溉工具在古州的周边地区已开始使用。而到了光绪年间,当地已经广泛使用了水车和龙骨车,少数民族根据当地的地势特点进行了改良,通过增加水车的轮辐使水车的取水效率更加高效,又可以在“溪大岸高之地”引取地势较低处之水,“水轮使舀以灌一轮之水,长轮五十”[11]卷三《田赋志》一。在灌溉工具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当地少数民族开始创新,使用“开堰蓄水”的方法解决山地种植水稻的水源问题,“开堰为上,堰高下平坝皆宜择地当诸水之上……储三尺之水足灌十五石田,倍深之其灌亦倍……值大旱无不收者”,“开堰蓄水”使得当地水田的抗灾害能力也得到提升。而在堰中“蓄蒲鱼,上周植柳树”,将水利灌溉设施变为鱼塘,增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计来源。“竹船”“小锄”“风簸”“捷耙”“浪耙”等内地的农业生产工具亦开始见诸当时的地方文献[5]1334,农业生产中病虫害的防治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其次,得益于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善,当地耕地开垦面积大幅度提高。由于古州“苗人田土历来并未清丈,无亩可计,其水田系以坵计,山土系以块计”①道光七年(1827)八月二十四日,嵩溥上《奏为遵旨编查附居苗寨客民保甲完竣并户口田产数目及酌拟随时稽核章程事》,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01-0684-079。、“苗田无亩可稽奉”[11]卷三《采运》十三,无法直观地通过面积计量来衡量“开辟苗疆”以后古州地区的土地开垦状况,但从文献中的描述来看,由于水利灌溉设施的进步,在当地开垦的土地中山区水田的耕作面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苗疆自乾隆嘉庆之间生齿日繁,人力极足,开控山坡田土几无隙地”“一溪若流百里则百里近岸地皆上田”[11]卷四《食货志》六,水田的耕作区域由两山之间的平坝区域沿着水源向山区延伸,“自山麓以至山腰,层层叠累而上,成为细长之阶级,田塍之高度,几与城垣相若,蜿蜒屈曲,依山萦绕如线……汉人以其形似楼梯,故以梯田名之”[12]122。“境内有可开垦水田者,一丘一壑纤悉无余,无水之地种植荞麦、大麦、燕麦、包谷等以裕旨蓄”[1]5,由此可见,水源较少的旱地也得到了开垦,可种植杂粮。
再次,农作物品种变得多样化。内地的杂粮作物随着屯军和汉人的迁入开始在古州地区得到种植,除前述荞麦、大麦、燕麦外,当地少数民族根据气候和土性在不同的地块耕作不同的杂粮,种类繁多,“干田宜胡豆,山地肥者宜诸豆,高山宜包谷,山地之新垦者宜小谷(俗作粟),冷湿地宜稗子,干松地宜薯、荞、香麦、老麦、包谷、高粱”[11]卷四《食货志》一。旱地作物的引进和种植,不但解决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口粮问题,甚至改变了他们的饮食结构和习惯。由“苗人具食糯米”[1]5演变为“种植杂粮以自食,所产粳米,则上采买之外,尽数变价”[11]卷三《采运》十三,稻米从基本口粮发展为换取货币的商品,被纳入市场流通领域,流向市场的中心——城市,“合城百姓俱俟苗民负米入城郭,计升合贸易,有不足者出重息以称贷于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则饥,称贷不得嗷嗷待哺而已,平岁如此”[11]卷十下《艺文志》十五,甚至开始融入全国市场的商品流通,“(苗人)其收获稻米除纳赋之外,皆运售楚省也”[9]148。
新的农业技术为当地少数民族摆脱“刀耕火种”的游耕方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了土地的复耕,农作物一年一收甚至一年几收,其中肥料的制作技术尤为重要。至光绪年间,古州地区少数民族已经掌握了肥料制作技术并广泛应用,“农惟储粪为至计,来年之粪必于本年先积之,以一屋掘大深坑,甃以砖石勿令渗漏,凡牛马等粪,悉盛之……春二月出之”[11]卷四《食货志》四,“治秧田刈戎菽等,密布田内,用秧马践入泥,候烂播种,其力倍于粪……名——踩青”[5]1335。肥料的使用,使有限面积内的粮食作物产量得到提高,并为再次种植提供了基础。
新技术的引入催生了养殖业,“每日饲以嫩草,鲭鱼啮食,故名草鱼,鲢鱼则食其屎,鲤鱼继食之。谚语云:一草养三鲢,三鲢养九鲤……畜鱼获息,多有致富者”[5]1412。此时出现了以养殖为生的专业养殖户,这说明当地的传统农业生产发生了更为专业、更为细化的分工,农业不再仅仅用于提供基本口粮,也开始生产和提供能满足更高品质需求的农副产品。
在“开辟苗疆”以后,古州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在当地人的生计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古州的农业产品开始进入全国的商品流通市场,成为全国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究其原因,可以从“开辟苗疆”后西南地区与内地联系加深、官府治理强化和族群互动频繁等层面进行分析。
三、农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原因
“开辟苗疆”后中央王朝开始在古州及周边地区设置统治机构,并派驻流官进行管辖,“古州、都江、清江、台拱、八寨、丹江各处于雍正七年设有同知、通判等员”。军事上驻防军队,“增营设汛,凡腹内郡县防兵大半移戍新疆”[11]卷七《武备志》三十八;民事上清查统计人口,(古州)“雍正六年招抚苗民五百七十一寨计三万一千五百二十六户”[9]152;经济上建立征赋税制度,“(古州等处)自雍正七年起至十二年止共认纳银八千二百六十八两五钱一厘零……已于雍正七年五月内详请题明于十一年追入地丁册内,历年奏销在案”①乾隆四年(1739)八月十八日,讷亲上《题为古州等处化诲苗民认纳钱粮一案依议题》,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2-169-13130-011。;教育上引入科举考试制度,“(雍正)十二年,学政晏斯盛题请赴黎平府学考试,凭文进取,向无定额”[11]卷五《学校志》二;等等。一系列的治理措施确保了苗疆的社会稳定,乾隆初年(1735)以来,黔东南苗疆经过了整体安定的发展期,屯军和汉人移民开始迁入黔东南苗疆,当地农业生产得以顺利发展。
(一)交通条件的改善
黔东南苗疆偏居于山区一隅,交通不便限制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史载:“云贵远居天末……今水路不通,陆路其险,往来贸易者,非肩负即马载,费本既多,获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诸物艰贵。”[13]卷八十六《兵政蛮防上》《云贵事宜疏》黔东南苗疆处于云贵连接两广、两湖地区的战略交通要道之上,开辟苗疆之后,这一地区马上成为西南地区连接内地的交通要地,“都江一水,在古州诸葛营之南,由诸葛营而西为上江,来自黔之都匀;由诸葛营而东为下江,直达广西之柳庆”[5]898,“雍正七年,总督鄂、巡抚张奉命清厘,夷人归诚,黔粤舟行无阻”[5]268,都柳江得以疏浚,与内地的交通往来开始密切起来。
随着都柳江沿岸与内地航道的畅通,贸易活跃起来,内地对于粮食和木材的需求刺激了苗疆的农业发展。黔东南苗疆商品被贩运至内地,肥沃的林地培育出的香菇成为当地特产而远销外省,“味极香,尝贩他省售卖”[5]1422,“每年浮柳江以至粤省,黔杉十居之九”[12]124,杉木成为重要商品沿着都柳江而下,“(苗人)其收获稻米除纳赋之外,皆运售楚省也”[9]148。云南所产的铜等物产亦经永从县被远运至福州,仅一次的运输量就达到了二万一千六百九十斤②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二十八日,图思德上《参奏贵州委员永从县丞刘集禧逼死脚户事》,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3-1227-034。,可见当时都柳江航道通行规模之庞大。古州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内地通往西南腹地的重要通道之一,黔东南苗疆逐步被纳入全国市场,与内地的联系和往来加深,从而为其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官府鼓励垦荒
为了维护黔东南苗疆的稳定,地方官员意识到必须解决当地民众的温饱问题,提升粮食产量。早在乾隆六年(1740)时任云南巡抚张允随便会同贵州布政使陈德荣、署古州道徐永祐等官员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
首先,兴修水利。乾隆初年(1735),贵州巡抚张广泗便要求地方官员勘察地形,兴修水利设施,并根据水利设施的多寡进行奖励,“督臣张广泗请开渠筑堰,以资地利之处,应请仍照部议,饬行各属,按实查勘,多方劝课,如果率先修筑,分别灌田多寡量加奖励,以重农功”③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
其次,奖励开垦。对开荒出来的土地“给照管业”,承认民众因开垦荒地而获得的土地,甚至允许在“官山”开荒,并且对开垦者予以奖励,“是劝民广垦山土之议,亦应循照部议,通饬地方官,悉心劝导,其有业之主地,即三年内不能自垦,应听其从容开垦,不必勉强抑勒,如系官山,即为立界给照管业以杜争端,如开垦多者,量为奖励,再有弥望,官山似可开垦,而遍山皆石者,不必强民徒劳”④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考虑到贵州恶劣的自然条件,官府鼓励垦荒,强调了“从容开垦,不必勉强抑勒”。
再次,引进外来作物。内地的作物被有计划地引入黔东南苗疆地区,特别是引入了杂粮类作物,“旱地既专种杂粮,则二麦登场之后,黔民原种秋荞、毛稗、黄豆、高粱之属……题令地方官审其地之所宜种之,所缺酌量借给,秋成照数缴还,不愿借者,听至,令农民于秋收后随时种植之处”⑤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为了鼓励农民种植杂粮,官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各级官府购备种子借给农民种植。至嘉庆年间,杂粮的推广种植已见成效,“无水之地种植荞麦、大麦、燕麦、苞谷等以裕旨蓄,薏苡产植甚多……小麦亦间有种者……仅见绿豆”[1]5。而对于气候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如养蚕、种棉、采葛诸条,于黔省天时地利不甚相宜”①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则采取了“只宜听民各从所便,不必加以劝惩”的灵活态度。
最后,改进农业技术。官府主张“劝力上农”,通过肥料的使用改变“刀耕火种”的耕作模式,“又有停种一二年,将荒草焚灰肥土,然后种者,此固因土性之薄,亦由民俗之惰。如果劝力上农,山中庶草繁膴,取之不竭,不难烧灰肥土,何致停种抛荒?”②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效法内地的作物轮种,“贵阳、遵义、思南、镇远、安化、施秉等处,禀报所种荞麦杂粮,多系一岁两收,他处自可效法”,通过农业技术的改进实现农作物的交替轮种,达到“一岁两收”,并且通过杂粮的产量多寡对农民进行“劝惩”,“劝谕农民尽力播种,以裕民食,并稽查劝惰,酌量劝惩”③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
(三)汉人移民的大规模进入
汉人移民的大规模迁入,使得黔东南苗疆人口开始高速增长。以古州为例,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实在古州所管苗民四百五十四寨,共两万七千二百九十八户”[5]1282,发展到“嘉庆十九年……所有合境汉民共五千一百一十二户,男妇大小二万四千四百零六口”[5]1282-1283和“苗民四百五十四寨,计户二万七千有奇”[1]1,合计三万两千余户。四十三年间古州地区人口数量增长了18%,其间汉人数量不断增长。随着军屯和汉人移民进入黔东南,汉苗族群开始不断交流融合,“(军屯)厥后渐立家室,族姓浸繁,率成土著”[9]160;“(熟苗)与汉民井里相连,室庐错处,抑且日中为市,彼此交易,实与汉人无殊”[6]97,也因此使得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技术、工具逐渐为当地少数民族接受和采用。
首先,黔东南苗疆少数民族逐渐习得水车和龙骨车的制造技术,“龙骨车地方黔省工匠多能制造,不必远求,即使工匠缺少之处,亦可就近于平越等府雇觅,无庸远赴江楚雇募,致滋劳费”④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民间率用自然车于溪边,拥水急流,架车水上,冲击旋转,昼夜灌输不歇,然至地势平衍溪流缓散之处,自然车不能旋转,则用龙骨车以济自然车之不及。”⑤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水车、龙骨车一类的水利灌溉设施的引入,使得开垦梯田和山地水田成为可能。
其次,外来作物由汉人移民带来并迅速传播开来。从现今榕江(即清代之古州)地区的苗语发音,可以看出很多农业品种是由汉人带入的。当地苗语发音称汉人为“丢”,地瓜苗语发音为“西丢”,南瓜苗语发音为“则都丢”,洋鸡苗语发音为“北丢”,洋鸭苗语发音为“奥丢”。从文献记载来看,“杂谷亦曰高粱,一名蜀麦……木稷一名荻梁,此种来至蜀”[11]卷四《食货志》三。这些称谓从侧面印证了汉人移民在引进农业品种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最后,新的种植技术,比如农林混种模式以及林业专门化,也逐渐为当地少数民族所接纳。“牛皮箐……客民结伙入内开垦,掘不及地而止,惟砍伐大树种植香菇往往有之”[1]4,汉人带入了新的物种并传播了技术,使得林业混种模式开始在林业种植区域得到应用。当地少数民族也开始通过杉树、麦、玉米的混种提高生产效益,“种杉之地,必须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5]1386。传统依赖自然林木砍伐“知伐而不知种”⑥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三日,张允随上《奏为遵议署布政使陈德荣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种棉栽植树木一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4-01-22-0009-001。的林业生产模式发生了转变,专门的林业种植开始出现,“杉阅十五六年始有子,择其枝叶而上者,撷其子乃为良……春至前则先粪土覆以乱草,既干而后焚之……既出而后移之,分行列界……稍壮,有拳曲者则去之……树三五年即成材,二十年便供斧柯矣”[5]1386。在汉苗族群的互动和交流中,林业生产力得到了提高。
综上所述,随着黔东南苗疆交通条件的改善,在官府鼓励垦荒的政策驱动下,汉人移民大规模进入,当地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苗疆社会的农业生产水平逐步向内地看齐,农产品产量随之提高,这不但解决了当地的口粮问题,并且黔东南苗疆在市场的作用下开始向全国农产品市场输出高品质的农产品,在经济上与内地的联系更为紧密。
四、结语
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等因素的限制,在开辟苗疆之前,“新疆六厅”农业生产效率处于较低水平。自“新疆六厅”开辟后,黔东南苗疆刀耕火种式的游耕逐渐转变为灌溉农业,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善,耕地开垦面积大规模扩大,农作物品种也变得多样化,部分农产品甚至输入内地。黔东南苗疆开辟以来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官府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政策以及汉人移民所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随着都柳江的航道疏浚,古州及周边地区成为内地通往西南腹地的重要通道之一,贸易活动的繁荣使得黔东南苗疆与内地的联系与交往日益密切。军屯和汉人移民的进入以及官府鼓励垦荒的政策,使得“新疆六厅”汉人与少数民族的互动越来越频繁,汉人带来了内地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新的农作物品种。总之,黔东南苗疆农业生产模式的变迁,不仅是黔东南少数民族与汉人移民交融的结果,更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内地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