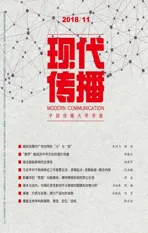从表征到拟像:纪实影像中的“现场”建构
2018-02-10■孟婧
■ 孟 婧
一直以来,人们对“观看”都抱有一种迷思。眼见为实,影像似乎就代表了现实与真实,或者是最能接近现实的一种记录方式。如何“再现真实”贯穿了整个影像的发展史,而“影像”与“真实”之间的勾联正是通过记录和还原“现场”来实现的。近年来,视觉技术进一步发展,虚拟现实(VR)所带来的沉浸式视觉体验更是颠覆了以往的视觉逻辑。如果说影像致力于对“现场”的记录,那么VR则实现了对“现场”的重构,正如其名所指“虚拟现实”,VR通过重构“现场”重新定义了现实,提供了一个虚拟和现实结合的“新现实”。本文将追溯纪实影像中的“现场”,并结合VR新闻和纪录片案例,探讨VR纪实影像作品如何重构“现场”,以及VR纪实影像中的“真实”。
一、观看的迷思
从古至今,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各种视觉媒介都在试图“记录和复制瞬间的现实”①。19世纪,摄影和留声机等一系列技术的发明使得人们能够进一步实现这种可能。然而,人们对影像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认知。
1.“完整电影”的迷思:复制现实
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巴赞认为“复制现实原貌”是人类一直渴望和追求的神话,电影就是从这样一个迷思中诞生,即一个关于“完整电影”的迷思(the myth of total cinema):电影是对现实瞬间完整而全面的再现(a total and complet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一切使电影臻于完美的做法都不过是让电影更加接近这一起源。②巴赞之所以称“完整电影”是一个迷思,因为它尚未实现,电影只能无限地接近现实(Approaching reality)③,而不能完全复制甚至取代现实。
2.“真实电影”:介入现实
关于“完整电影”的概念也有不少人提出批判,认为这一观点将现实视为外在既定的客观存在,忽略了电影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法国纪录片导演让·鲁什提出了“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概念,与“完整电影”的迷思相似,“真实电影”也认为影像是为了记录现实。但是“真实电影”并不是排斥创作者的主观性介入,相反,让·鲁什认为只有通过展现拍摄者和被拍摄对象之间的互动,甚至是有意的挑衅,才能让隐藏在平静表面之下的“真实”显现出来。④“真实电影”这一概念最早源于苏联纪录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维尔托夫于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电影眼睛”(Kino-Eye)理论,认为:摄影机这个“机器眼”可以记录和揭示平时不被肉眼所观察到的现实。也就是说“电影眼睛”不仅仅是再现,更是一种创造,它“能够感受到更多、更美好的东西”⑤。
无论是“完整电影”,还是“电影眼睛”都把“再现现实”作为电影的重要使命,虽然两者对于现实的定义不尽相同。“再现现实”的迷思始终贯穿于影像,或者说视觉媒介的发展史。在纪实影像中,“再现现实”主要是通过记录“现场”来实现的。
二、影像:记录“现场”
“现场”是构建纪实影像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元素。20世纪60年代,以罗伯特·德鲁和理查德·利科克为首的一批纪录片人就提出“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这一概念,认为纪录片就要走出摄影棚,不做解说,直接记录生活的原本状态。20世纪90年代前后,“直接电影”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中国纪录片创作者。记录“现场”,拥抱那些不确定。未被设计的当下,成为了当时很多纪录片的风格,以此来区别于一些主题先行的专题纪录片和中国第五代导演寓言式的表达。⑥因此,记录“现场”不仅仅是一种拍摄方式,还是一种艺术手法,体现了创作者对“真实”的认知。
1.广播直播:耳朵的在场
直播被认为是记录“现场”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也是构建“在场感”的一个重要手段。最早的现场直播诞生于广播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默罗站在伦敦一间民居的屋顶上播报:“你好,这里是伦敦”,向美国听众广播战争,实现了广播史上第一次“现场直播”,默罗也因此被誉为“现场报道鼻祖”。广播直播实现了“耳朵的在场”。
2.纪实影像:眼睛的在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新闻和纪录片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电视媒体对民权运动、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海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将“世界的现场”搬进了客厅。电视直播实现了“眼睛的在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直播让人们在更短的时间内去到更多的“现场”,并且与“现场”互动。如今,移动直播的“现场”越来越多元,被直播的“现场”不仅局限于大事件或大场面,越来越多的突发新闻及日常生活的“现场”被实时记录和传播,让更多的人实现了“眼睛的在场”。
纪实影像记录“现场”的一个前提就是摄像机的在场,而那些没有被及时记录的“现场”,就成为了消逝的“现场”,例如历史的“现场”。对于这类“现场”,一般来说,纪实作品主要通过拍摄历史物料和人物口述,来进行还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很多“现场”的细节却无法复现,例如当时“现场”的气氛,当事人的情绪等无法用言语或静态图片来完全体现。因此,很多时候,需要通过一些其他艺术创作的方式来还原消逝的“现场”。
3.动画纪录片:记忆中的“现场”
对于那些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现场”和仅存在于记忆中的“现场”,除了口述和历史物料,还可以通过表演和动画的方式去演绎和还原“现场”中生动的细节。例如纪录片《与巴什尔跳华尔兹》正是通过动画的形式,还原了以色列国防军老兵阿里·福尔曼(导演本人)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的经历。在华尔兹的伴奏下,枪林弹雨,光影的变化,影片营造了一个记忆中的战争场景。动画还原的“现场”与现实的访谈录音穿插在一块,实现了时空的重构。《与巴什尔跳华尔兹》展现了一种新的记录“现场”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表面的“真实”,而致力于再现那些不可言说,不可用文字表达,也曾未被影像记录的情感、环境和氛围。如何用影像去还原“消逝的现场”也触发了一系列关于“真实”的探讨。“真实”不仅仅局限于记录,还需要通过介入、对话和创造才能抵达。如果说记录“现场”可以实现耳朵和眼睛的在场,那么虚拟技术和艺术表达则更加侧重于对 “现场”情感和感受的还原,而这一点在VR影像中被进一步彰显。
三、VR:重构“现场”
在数字化之前,影像,无论是摄影还是摄像,主要是通过光学成像原理使胶片上的感光化学物质发生反应,进而记录影像。在曝光的一瞬间,底片上就记录了“现场”的光影。因此,当“现场”的光与胶片产生化学反应的那一刻,影像和“现场”之间直接产生了连接。影像是对“现场”的一个“完整”记录,每一帧画面都是一个完整的“现场”。在进入数字媒体时代后,记录的方式开始转变。不同于胶片所记录的模拟信号,数码影像被分割成无数个细小的像素进行存储和读取。于是,“现场”也被分割成一个个像素,同时,每一个“现场”都可以被分布式地存储和读取。数码影像不再是对光影的“完整”复制,而是将“现场”变成了一个个碎片,进行存储,读取和重构。数字影像让人们开始拥有重构“现场”的可能,而VR则将其推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影像艺术对现实还停留在再现(Represent)的阶段,那么VR技术则实现了对现实的取代(Replace)。
1.模拟“现场”:再造真实
VR影像传承了一直以来人们对于 “再现现实”的一种迷思,通过模拟现实中的视觉体验,进一步提升“在场感”。目前来看,VR影像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还原现场:360度全景摄影和计算机图形技术(CG)。前者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VR影像制作技术,利用计算机软件将专业相机捕捉的二维场景图片进行拼合,形成一个三维的空间,有360度环视效果,是一种基于静态图像的VR技术,目前在移动端的VR设备中应用较多。现在大部分的VR纪录片都采用了360全景视频,例如《纽约时报》VR栏目的作品,《财新》VR纪录片《山村里的幼儿园》等。360度全景视频的优势在于其环绕的视角可以带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有“在场感”,同时,影像逼真。但是360度全景视频只能用于记录和再现尚未消失的“现场”,而那些已经逝去的“现场”,只能通过CG技术重新构建。
CG技术制作的影像并非是对“现场”的记录,而是一种模拟。由有VR“教母”之称的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研究员Nonny de la Pea 成立的专门致力于VR纪实作品创作的Emblematic Group公司与全球各大媒体合作拍摄了多部VR作品,这其中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利用CG技术或者是结合了360度全景摄影和CG技术制作而成。在公司网站上展示的13部VR作品中,其中有6部是用CG技术来还原新闻事件。例如影片《基亚》(Kiya,2015年)讲述了一场真实的家庭暴力杀人事件。影片根据对幸存者的采访、911报警电话录音和法院的记录,还原了事件的经过。同时,影片还通过演员扮演,用计算机抓取演员表情,生成模拟人像,重现了事件发生的“现场”。观众能够在这个模拟的“现场”观看事件的全过程外,并且还可以在第三人称和受害者间切换视角。Emblematic制作的另外两部影片《使用武力》(Use of Force,2014年)和《黑暗的一夜》(One Dark Night,2015年)基本上也是使用了相似的手法,还原了犯罪现场。对于一些只记录和保留了有限视频资料和音频资料的事件,CG技术可以通过后期制作来模拟和再造“现场”。此时,VR已并非用光影来记录“现场”,而是模拟一个全新的“现场”和“现实”。
2.“身体的在场”:沉浸体验
除了模拟“现场”之外,VR纪实影像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场感”。利用VR进行新闻报道和影像创作的逻辑,不是将“现场”记录展现在观众眼前,而是将观众置于“现场”之中。因此,VR所创造的影像空间,更加接近于戏剧舞台。从技术上来说,VR影像颠覆了电影蒙太奇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表现技巧,“戏剧导演所具备的叙事方式和调度习惯更加适合VR影片的创作”⑦。VR电影与舞台剧的一个共通之处在于两者都致力于空间的营造,而这种空间的营造和“在场感”不仅只局限于“眼睛和耳朵的在场”,更需要“身体的在场”。
目前,很多VR纪实影像都采用了360度全景视频,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动头部来观看四周的环境,从而有置身“现场”空间中的体验。但是如果观众四处走动,显示器上的影像并不会随之而改变,久而久之,反而会产生不适。也就是说,360度全景VR只是实现了观众“眼睛的在场”,而不是“身体的在场”。而要实现“身体的在场”就需要结合CG技术和传感器技术。新闻纪录片《洛杉矶的饥饿》(Hunger in Los Angeles,2012年)模拟还原了一个糖尿病人在洛杉矶食品银行排队等候时,由于饥饿而倒下的真实故事。观众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需要带上VR眼镜和传感器,通过走动和变换姿势,观众将看到不同的景观,真正感受身临现场的效果。《格林兰在消融》(Greenland Melting,2017年)是结合了CG 、360度全景视频、摄影测量(Photogrammetry)和摄像测量(Videogrammetry)制作而成的纪录片。观看的时候,观众可以蹲下身看冰面下的水底世界,也可以走出低空飞行的机舱从半空中观看冰川。
这种让“身体在场”的VR 也被称为“漫步”VR(Walk-Around VR)。“身体的在场”是一种深度的互动,需要传感器实时传输观看者位置的变化,进而与模拟的“现场”产生互动和交流。从“眼睛的在场”到“身体的在场”,观众从被动的观看中解放出来,与虚拟环境互动,真正地实现了“在场”。而VR也不再是记录“现场”,而是重新构建了一个“现场”。
3.第一人称叙事:情感移植
VR对现场的重构,一方面体现在对环境和空间的营造,另一方面体现在情感体验的移植。也就是说VR不仅实现了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还有感同身受的共情效应。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源自人们一直以来对观看的迷思,而感同身受的共情效应则是一种观看的快感。de la Pea认为她的作品是一种“沉浸式新闻”(Immersive journalism),能够让观众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体验新闻故事。⑧主观体验成为VR纪实的一个重要特征。虚拟现实“传播的不再是信息,不再是观点,而变成一种体验植入你的身体,这就是传媒作为人的延伸的重要体验”⑨。从Emblematic制作的VR影片中不难发现,它们大部分是关于遭遇不幸的人的故事,战乱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一些我们平时无法感知的事实,例如冰川融化等。沉浸式新闻和纪录片能在受众与故事之间建立一种独特的情感联系,让受众切实的感受社会问题。
在观看了《洛杉矶的饥饿》之后,有感于其强大的感染力,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提议拍摄一部关于叙利亚难民的影片,希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这个议题。于是就有了VR纪录片《叙利亚计划》(Project Syria,2014年),该影片在多个世界会议和筹款活动中被多次播放。“身体的在场”和“情感移植”是VR 技术模拟和重构“现场”的重要特征。
四、思考:从表征到拟像
1.VR纪实:主观真实
从记录“现场”到重构“现场”,VR纪实影像一方面继承了长久以来人们对观看的迷思,另一方面,它又解构了这个迷思。VR纪实影像通过360度立体呈现“现场”和营造“在场感”将“再现现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超越了之前摄像机镜头的限制,让现实不再局限于边框之中,而是以空间的形式得以呈现。从“眼睛的在场”到“身体的在场”,VR纪实影像赋予了观看新的功能,让人们从“眼见为实”到“眼见即所到”。但同时,VR纪实影像并不是记录“现场”或者“现实”,而是模拟了“现场”,并且强调第一人称的情感体验。因此,VR纪实影像中的“现实”不同于巴赞“完整电影”的理念,其更加接近于维尔托夫“电影眼睛”(Kino-Eye)理论中所表述的“主观真实”。
情感体验既是VR纪实影像的一个特征,也是其诉求之一。de la Pea认为沉浸式新闻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体验他人的故事,引发共鸣。VR纪实影像不再让观众抽离于所呈现的“客观事实”,而是让观众投入到其中。VR纪实影像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观赏的过程中,都注入了“主观”和“情感”的色彩。
此外,VR影像除了在内容上表现为第一人称叙事外,在观看情境上也凸显了“以个人为核心”的传播模式。从电影到电视到手机再到未来的VR,可以发现,影像观赏的物理空间在不断地缩小。电影院是一个公共的空间;电视是属于家庭的观影会,是家庭活动的一部分。手机更多的是一个人的观看,而VR则更是如此,一个头显仪器就可以将观众从现实的空间中剥离出来。换句话说,电影是一群人的观看,电视是一家人的观看,那么VR则是一个人的观看。伴随着虚拟空间里的连接的是现实空间里的孤独。而这样一种个人化的观影体验也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VR影像的“主观真实”。
2.VR“现场”:心理变量
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VR纪实影像实现了“身体的在场”,而事实上这个“在场”的实现是基于两个错觉:位置错觉(Place Illusion)和合理可信错觉(PlausibilityIllusion)⑩,同时,观看者对影片中自己的虚拟身体有感知(virtual body ownership)。也就是说观众产生处于虚拟场景中的错觉,并且选择相信错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VR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变量(Psychological variable),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人产生在场(feel present)的心理错觉。当“现实”以“心理错觉”的方式被感知,我们又将如何理解“现实”?
关于现实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媒介研究的母题。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介对现实的再现。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意指媒介对“客观现实”进行选择和加工之后呈现出来的“象征性现实”。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介高度发达,并渗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象征性现实”已经逐渐超越了现实。鲍德里亚在《拟仿物与拟像》(Simulacres et Simulation)一文中认为,在信息爆炸的年代里,符号已经取代了现实,成为印证现实存在的标准,而现实则沦为一个巨大的拟仿物(A gigantic simulacrum),一个虚拟的环境。拟像(Simulation)与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有着本质的不同:表征的基本原则是使符号和现实等同(尽管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想法),而拟像则是在这个乌托邦之上,将符号从现实的注脚这一角色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不再依附于现实。由拟像构建的新现实(neo-real),鲍德里亚称之为“超现实”(Hyperreal)。而如今,VR技术正是致力于打造一种新的“超现实”,一个现实与虚拟完全融合的新时空。VR所构建的“超现实”成为一种比现实更加真实的存在,进而取代现实。VR实际上是一个基于错觉的心理变量,当错觉真实到让人难以分辨,现实是否被谋杀了?我们又将如何区别“错觉”和“现实”?
3.VR的“沉浸感”:与受众的磨合中建立
正因为VR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变量,“沉浸感”并非仅由VR影像本身所决定,而是在与观众的互动中才能建立起来。有研究显示,VR并非如同业界所说的那样神奇。事实上,沉浸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端的模拟效果,还取决于受众个体的认知模式差异,个人喜好和需求,以及所处的社会语境。例如,喜欢高度沉浸模式的受众更容易从高仿真的虚拟场景中获得观看的满足感,而不习惯高度沉浸模式的受众则相反。因此,Shin和Biocca提出,沉浸效果应该是基于用户体验的一个概念,而非VR与生俱来的特质,它是在VR和受众的不断磨合与互动中建立的。也就是说VR的受众并非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讯息和被沉浸,相反,受众可能会对虚拟的场景产生疏离和不适感,并且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知识背景去解读讯息。目前,VR技术尚在发展阶段,很多方面还有待改进,例如观众需要佩戴笨重的头显仪器和传感器,高质量的VR影像创作依旧缺乏等。在研究上,也需要有更多的关注投向受众体验,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角度探讨“沉浸感”的建立。
注释:
① [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 Bazin,Andre.WhatisCinema.Volumes2,trans.ed.by Hugh Gra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3-27.
③ Fan,Victor.,CinemaApproachingReality:LocatingChineseFilmThe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5.
④ Bruni Barbara,JeanRouch:Cinéma-vérité,ChronicleofaSummerandtheHumanPyramid.Senses of Cinema,March 13,2002,http://sensesofcinema.com/2002/feature-articles/rouch/.
⑤ Vertov,Dziga,Kino-Eye.TheWritingsofDzigaVertov.Edited by Annette Michelson,translated by Kevin O'Brien.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17-18.
⑥ Robinson,Luke.IndependentChineseDocumentary:FromtheStudiototheStreet.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3.
⑦ 孙略:《VR、AR与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⑨ 史安斌、张耀钟:《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的兴起与传统新闻业的转向》,《新闻记者》,2016 年第1期。
⑩ Slater M..PlaceIllusionandPlausibilityCanLeadtoRealisticBehaviorinImmersiveVirtualEnvironments.Philos Trans R Soc Lond B Biol Sci,2009 (364),pp.3549-3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