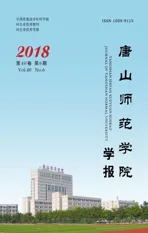论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估
2018-01-29郝晓霞
郝晓霞
论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估
郝晓霞
(忻州师范学院 公共外语部,山西 忻州 034000)
教学评估包括终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形成性评估的促学作用已获得国内外许多综述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支持,在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有效的学习能力、培养教师探究的思维习惯以及提升师生间的良好互动等方面产生了良好影响。相比较国际上形成性评估的发展并不均衡、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我国高校外语教学中形成性评估应在目标的具体化、体系的针对性、评估的融合度以及教师的职业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在教学中贯彻形成性评估的理念。
高校外语教学;形成性评估;教学过程;学习能力
1 形成性评估的概念
评估历来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科学的评估结果是教学的有益反馈,对于实现课程目标至关重要。它不但能够帮助教师全面了解教学效果,及时改进教学方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还有助于学生客观评价自身学习状态,有效调整学习策略,积极改善学习方法,切实提高学习效果。教学评估既包括以标准化考试为代表的终结性评估,也包括以学习为目的、注重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估[1]。终结性评估(summative assessment)大多是在每学期末或某一个学习阶段结束后进行,主要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评估对象,为学生这一阶段的学习提供鉴定性评估。虽然终结性评估是检验教学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不能评估教学过程。而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assessment)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运用形成性评估的手段和方法,教师不断获取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过程或方法,促进学生高效学习。时至今日,形成性评估已有40多年的历史,它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促进作用已得到了研究者、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一致认可。
Frederich Taylor在书中首次提出了教学评估的理念。该理念强调考试的意义,目的是了解学生学习的进步程度[2]。率先使用“形成性”这一术语的学者Scriven给出了如下定义:当教育者对一个成熟的、已经完成的教育项目的价值进行评估时,他所进行的终结性评估,其目的是评判,帮助决策者做出关于教育项目是否合格的决定;但当教育者对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教育项目进行评估时,他所进行的则是形成性评估,其目的不是评估,而是修正,即找出项目中潜在的问题,并作出如何改进项目的决定[3]。
20世纪60年代,评估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课程设置人员所关注。继Scriven之后,Bloom将“终结性”和“形成性”两种评估方式引入教学评估领域。Bloom认为形成性评估是在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提供反馈和纠正措施,是教师和学生通过小测试进行的评估[4]。但当时的评估注重的是教育工作核定或教育责任制,以便帮助改进教学设置。正如Lynch强调的,20世纪60-70年代的评估仍是注重结果的终结性评估,形成性评估只是其辅助或补充教学过程[5]。在之后的20多年中,形成性评估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逐步关注终结性评估与形成性评估的区别,如Bachman认为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估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实施目的(前者是课程发展,后者是课程效果)和时间(前者是教学中,后者是教学后)不同[6]。Pilliner认为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的区别在于评估对象是“你正在做的?”还是“你已经做的?”[7]。王华和富长洪则从目的、时间、发生环境、侧重点、参与者、结果公布形式、结果公布手段和影响等方面总结了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区别的具体表现[8]。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才开始重视形成性评估对教学的影响。Black和William开始对形成性评估进行综述研究,才又掀起了形成性评估研究和实践的热潮。Black和William继承了Bloom从目的或功能的角度定义形成性评估的传统,将其定义为所有教师/学生进行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提供的信息将用于反馈,以调整随后进行的教与学的活动[9,p97]。Weirtc提出教师应采用形成性评估,这样就能有效调整教学各个环节和学生的学习行为[10]。Bachman和Palmer则基于考试的视角探讨形成性评估,提出形成性目的的考试不仅帮助指导学生学习,还有助于教师调整教学方法和教材,而终结性评估提供的是学生课程学习成绩,对教学过程缺乏指导作用[11]。Harlen & James强调形成性评估的关键是认清学生现有水平和学习目标之间的差距[12]。Heritage等将形成性评估定义为:在教学过程中连续收集学习证据、提供学习反馈的系统化的过程[13]。罗少茜在梳理了形成性评估的特征和侧重点之后,将我国二语课堂中的形成性评估定义为:以评估为导向的课堂活动范式,以评估者的判断能力为核心,要求评估者(教师、学生)采用、调整、设计各种适当的任务(课堂提问、任务、纸笔测试、档案袋等),系统地收集学生信息(包括学习产品和学习过程),并用适当的评估工具(检查表、评分准则等)对信息进行评估分析和阐释,再反馈给评估者(教师、学生)用于调整教与学的过程,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14,p13]。
2 形成性评估对教与学的影响
目前,形成性评估的促学作用已获得许多综述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支持。它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作用巨大,而且可以帮助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和自主学习能力,为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它应该成为任何致力于促进学习的政策的中心,同时也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15]。
2.1 提供学生安全的学习环境
Knight认为形成性评估的利害程度低,所以学生更愿意实验、冒险[16]。学生更愿意在评估活动中学习,并不用担心失败的风险。因此,学生更愿意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担忧和弱点,与教师或同伴展开真诚的交流。形成性评估鼓励学生去尝试,不怕犯错,从错误中学习,反思和反馈也为纠正错误提供了机会。Race发现,允许学生在建设性的环境中犯错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性评估在这方面有巨大的潜力[17]。为建设和维护安全有效的学习环境,有必要平衡终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并积极改进反馈的质量和时间。
2.2 培养教师探究的思维习惯
形成性评估不仅要求教师转变角色,也对教学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要求。因此,它对教师和教学都具有重塑作用。在形成性评估中,教师能够清晰明了地看到教学意图和教学效果间的差距,及时采取建设性措施以弥补这种差距。教师还可以随时关注学生学习的行之有效或者收效甚微的方式和活动,并收集和利用这些有效信息,转化成改进教学的有力依据。优秀教师每天、每堂课、每次与学生互动时,都会批判性地考查自己的知识和工作假设,他们具有探究性的思维习惯,敏锐地意识到教学中哪里需要改变,哪里需要提供反馈或信息,从而帮助学生推进学习[18]。
2.3 提高学生有效的学习能力
形成性评估过程之所以能促进学习,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能让学生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在形成性评估中,学生主动收集自己的学习信息,通过分析所收集的信息决定自己采用何种学习策略,以获得学习上的进步或成功。也就是说,形成性评估帮助学习者成为自我调节的学习者和数据驱动的决策者。学生不仅学会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学习,而且其自主性、自信心和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这些学习因素的结合增强了学生学习的韧性,可以更好地处理学习中的逆境和起伏,更可能将学习上的成功和失败归结于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并相信自己有能力调整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以获得学习上的改进。另外,形成性评估能够缩短学生之间在学习上的差距。Black和William的研究发现,虽然形成性评估对所有学生的学习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它对于落后学生的帮助要大于其他学生[9,p64]。
2.4 提升师生间的良好互动
高质量的形成性评估模糊了教学、学习和评估之间的关系,在课堂中创造了合作探究和推进学习的文化。在形成性评估中,教师和学生形成了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随着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愈发紧密,学习对话成为最重要的课堂准则。教师和学生互相交流,共同计划和协商学习目标,收集分析关于学生表现的信息,为课堂学习提供指导。
Knight认为好的形成性评估意味着循序渐进地设计学习,为良好的学习对话提供大量的机会,而这种对话来自于与课堂学习目标相匹配的高质量任务的反馈[1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形成性评估可以彻底改变教师和学生之间互动的质和量。
3 形成性评估的现状与未来
3.1 国外形成性评估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教育评估较为发达的国家中,政府不仅高度重视,还大力资助研究项目,大量专家参与形成性评估的研究与实践,许多高等学校设立专门研究中心。目前,英国在世界语言测试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曼彻斯特大学设立了形成性评估中心(The Center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布里斯托大学设立了评估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ssessment Studies);Black等著名评估专家组成的“评估改革小组”(Assessment Reform Group, ARG)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推广工作。而美国一贯重视标准化测试,形成性评估也获得深入研究和发展。如ETS从2002年开始在全球招聘形成性评估优秀专家,研究运用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形成性评估项目,已研发出“形成性评估题库”(the ETS Formative Assessment Item Bank)。但国际上形成性评估的发展并不均衡,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美国在联邦和州政府财政拨款的资助下,几乎所有的州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形成性评估应用于教学中,美国州立学校主管官员委员会(CCSSO)开展了“课堂评估与学习者标准跨州合作”项目(SCASS)。从2006年起该委员会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形成性评估,并从各类教育机构中选择知名教育和评估专家成立了“学习者与教师形成性评估”委员会(Formative Assessment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FAST)。夏威夷、北卡罗来纳、密歇根、肯塔基等18个州参与了2007-2008年度的大规模形成性评估联合项目。CTB/McGraw-Hill在21世纪初为小学和初中学生研制的基于课程标准的形成性评估网络工具“Yearly Progress Pro”,在6、7年间推广到了25个州。
1992年,葡萄牙政府立法,规定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中都把形成性评估作为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学生进行自我评估,让学生参与评估过程,详细了解评估的标准。研究发现,尽管多数教师认识到形成性评估的重要性,但其课堂评估仍过多地模仿外部的总结性评估[19]。在2005-2006年,英格兰75%的中学参加了政府资助的形成性评估,英国威尔士地区从2007年取消了11-14岁学生的标准化测试[20]。芬兰政府通过立法规定,对学生学习的评估只能使用教师设计的测试,不允许使用外部的标准化测试,评估要做到既评估学生的学业,又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对学生的成绩评定只能提供描述性的反馈,不允许打等级。芬兰的教育评估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政府为教师提供了充足的培训机会,而且教师们也愿意接受终身教育[21,p199]。
加拿大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在课堂评估和大规模测试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大规模评估的结果也要“形成性”使用,以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从20世纪90年代起,加拿大开展了省级规模的评估,形成性评估成为评估改革的重要内容[22]。
此外,法国、德国、希腊、西班牙、瑞典、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进行教育评估改革。改革是为更好地推行学习性评估,但改革意图与课堂教学实践间的差距,迫使教师们仍更多关注评估的问责作用而忽视评估的促学功能。在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考试文化根深蒂固,尽管政府花大力气推广评估文化,试图推进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但教育改革政策与评估实践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21,p211]。
在形成性评估研究领域,教育界的著名期刊,如,,等积极倡导形成性评估;语言测试领域的代表期刊和等刊载越来越多的形成性评估研究的论文,还以专辑形式发表形成性评估的研究成果。
3.2 我国形成性评估现状
从政策层面看,目前形成性评估已经被正式写入《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2003)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教育部给予资助并扶持形成性评估的研究和推广。如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的评估研究”项目组主持的“新课程与教育评价改革译丛”(2003-2005)引介了一系列教育评估的力作;另有2008年国家精品课项目“扬州大学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北京外国语大学承担的2009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形成性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等等。调查也发现,学者们对形成性评估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但在现实中形成性评估的实施并不理想。一是形成性评估对教师和学生的素养和技能提出的要求高,教师的评估素养能力却有待加强。二是在终结性评估上学校和教师投入了大量时间,形成性评估的发展空间却被挤压。三是尽管形成性评估能促进学习,但在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决定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因此,学生和教师投入形成性评估的动力不足[14,p167]。
我国香港地区在教育评估改革方面也取得了成效。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改革——“目标为本的课程”(The Target-Oriented Curriculum)倡导的形成性评估,并没有得到广泛执行[23]。2009年,香港政府课程发展议会(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发布评估改革指导意见,推行针对小学教育的基础能力评估(the 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和面对中学教育的基于学校的评估(School-based Assessment)。这些项目力图推行“为学习的评估”,从2007-2008学年起,基于学校的评估部分取代外部大规模考试的作用[24]。
3.3 我国高校外语教学中形成性评估未来展望
3.3.1 形成性评估目标要具体化
各级二语课程标准都提出了以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模式,一般由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构成。这些成分为我国高校外语评估的设计和使用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但关于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行为目标,课标中的描述不够详细明确。针对课程标准中目标描述问题,教师需要提高标准的解读和具体化能力,能够将课程标准中的目标分解成具体的每一堂课的教学目标。考虑到我国外语教师水平的局限性,完全依赖教师本身的评价素养提高以解决目标描述不明确的问题并不现实。更为可行的做法是在提高教师评价素养的同时,研究人员应尽力使目标描述更为系统化和具体化。
3.3.2 形成性评估体系要有针对性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形成性评估需求,不同的课程对形成性评估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从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形成性评估论文来看,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大学英语的口语和写作课程上。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其他课型的形成性评估实施和研究的难度较大。在我国,英语作为二语的课堂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它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作为自己的学术基础,应有国家统一的课程标准或要求,身处独特的考试文化之中,对不同课型的形成性评估体系是形成性评估在二语教学领域中需要研究和开发的一大重点。
3.3.3 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要有机融合
高效学生应使用任何可以得到的信息,包括终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所提供的信息。由此,建议终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在课堂层面实现融合。未来研究应侧重于这种融合如何发生以及教师如何在课堂中融合终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信息,探索各种实践方式对学生的成就、动机和学习信念的影响[14,p274]。
3.3.4 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要有职业发展
形成性评估是外语教学的一部分,评估的设计、实施和结果的使用等工作大都由教师完成,所以教师应具备开发高质量评估的能力和使用评估结果的能力[25]。而形成性评估大多发生在教室这样的小环境中,同时也存在于社会文化,特别是教育系统这样的大环境之中,因此,许多社会因素制约着教师的教学与评估行为,校长等教育管理者应掌握一定的形成性评估知识[26]。如前文所述,很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推行受阻,主要原因之一是教师缺乏培训的机会,得不到足够的帮助。如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学负担过重,教师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备课与课堂教学上,对评估往往重视不够,几乎没有时间反思自己的评估实践[27]。教师教育和培训项目应为教师提供相关讨论课程或工作坊,使他们能充分反思并扬弃其学习经验和教学经验,创造性地贯彻形成性评估的理念。学校应为教师创设平等、互助、合作的工作氛围,为创造性的评估提供舞台,使教师能够在安全的专业情境下追求和实现其专业发展。
[1] Leung C & Mohan B. Teache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Talk in Classroom Context: Assessment as Discourse and Assessment of Discourse[J]. Language Testing, 2004, (3): 335-359.
[2] Taylor F.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11: 6.
[3] Scriven, M. S. The methodology of evaluation[A]. R. W. Tyler, R. M. Gagne & M. Scriven (Eds.). Perspectives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C]. AERA: Monograph Series 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1.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7: 39-83.
[4] Bloom, B. S. Learning from Mastery[J]. Evaluation Comment (UCLA-CSIEP), 1968, 1(2): 1-12.
[5] Lynch B K. Formative Program Evalu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2.
[6] Bachman L F. Formative evaluation in specific purpose program development[A]. Mackay R, Palmer J D (eds.). 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Program Design and Evaluation[C]. Rowley, Mass: NewburyHouse, 1981: 106-119.
[7] Pilliner A E G. Evaluation[A]. In Heaton B (ed.). Language Testing[C].Oxford: English Publications/ Macmillan,1982: 2.
[8] 王华,富长洪.形成性评估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综述[J].外语界,2006,(4):67-72.
[9] Black, P. & William, D. Assessment and classroom learning[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1998, 5(1).
[10] Weir C J.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ing Language Tests[M].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1993: 167.
[11] Bachman L F & Palmer A S.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8.
[12] Harlen W & James M.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1997, (3): 365-379.
[13] Heritage, M., Kim, J., Vendlinski, T., et al. From evidence to action: A seamless process in formative assessment?[J].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2009, 28(3): 24-31.
[14] 罗少茜,黄剑,马晓蕾.促进学习:二语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15] Black, P. Testing: Friend or Foe[M].London: Palmer Press, 2002: 96.
[16] Knight, P.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criterion and norm-referenced assessment[EB/OL]. LTSN Generic Centre, Assessment Series No. 7. http://www. heacademy.ac.uk/assets/documents/subjects/swap/key-concepts-formative-summative. pdf, 2014-10-06.
[17] Race, P. The Open Learning Handbook: Promoting Quality in Designing and Delivering Flexible Learning [M]. London: Kogan Page, 1994: 102.
[18] Moss, C. M. & Brookhart, S. M. Advanc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Every Classroom: A Guide for Instructional Leaders[M]. Alexandria, Virgini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 Curriculum Develop- ment, 2009.
[19] Fernandes D. Educational assessment in Portugal[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2009, (2): 227-247.
[20] Leung C & Lewkowicz J. Expanding horizons and unresolved conundrums: Language testing and assessment[J]. TESOL Quarterly, 2006, (1): 211-234.
[21] Berry R. Assessment trends in Hong Kong: Seeking to establish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an examination culture[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2011, (2).
[22] Friesen S. What Did You Do in School Today?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 Framework and Rubric[M]. Toronto, ON: Canadian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09: 63.
[23] Berry R. Assessment for Learning[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4.
[24] Davison C. The contradictory culture of teacher-based assessment: ESL assessment practices in Australian and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J].Language Testing, 2004, (3): 305-334.
[25] Stiggins R J. Essential formative assessment com- petencies for teachers and school leaders[A]. Andrade H L & Cizek G J (Eds). Handbook of Formative Assessment[C].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42.
[26] Schneider M & Randel B. 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of 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for enhancing educators’ skills in formative assessment[A]. Andrade H L & Cizek G J (Eds). Handbook of Formative Assessment[C].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56.
[27] 李清华.形成性评估的现状与未来[J].外语测试与教学,2012,(3):1-7.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AO Xiao-xia
(Public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Xinzhou 034000, China)
Assessment, including summative assessment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education system. Numerous studi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have been conduct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Formative assessment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udents’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ability, teachers’ thinking habit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fter reviewing the status quo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pecification, pertinency and combina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implement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teaching process; learning ability
H319
A
1009-9115(2018)06-0125-06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6.028
2018-06-11
2018-08-08
郝晓霞(1983-),女,山西原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
(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