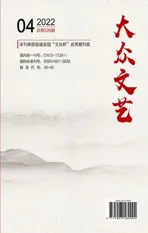知青小说叙事的整体性建构
——评韩少功小说《日夜书》
2018-01-28吴大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411105
吴大平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411105)
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知青小说还是伤痕小说,关于知青体裁的处理都有着较为相同的写作范式。无非是经历的回忆,历史伤痛的不堪回首以及当下生活的聊以慰藉。这种模式形成的思想含义是深刻的,似乎饱含着这个国家民族关于某一段历史的文化自觉和道德伦理判断。一般意义上而言,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观念历史上却造成了某种断裂,且这种一直延续的文化判断,逐渐形成了似乎成为两段历史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整体社会历史图景的构建也存在着弊端。
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作品,只要作者依照某一准则将零星的材料或感受组合成一个可理解的连续体,叙事的整体性问题便出现了。就小说故事本身而言,《日夜书》的内容依然是一个知青体裁的文本,且内容都来源于韩少功极为珍视的知青经历。所谓的知青小说叙事的整体性建构,就是打破原来一直延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书写,呈现知青作为“一代人”的整体性精神图景以及国家一脉相承的整体性社会历史和文化风貌,最终通过文学叙事的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世纪史和当代史。
一、颇具意味的文体实验
《日夜书》与传统的或者经典小说叙事不同,它从古典历史的撰述中获得滋养,开创了一种以人物为核心,串联小说故事的仿纪传体文体。中国古典历史的撰述体例,有纪事本末体,有纪传体,也有通史式写法。各种撰述体例都有着各自的优势与特点。《日夜书》从这些体例上受到启发所进行的文体实验,是非常具有选择智慧和创新才力的。以突出“主线”为特点的通史式写法,可以很好地描述出以自然时间为顺序的叙事脉络。而韩少功通过仿纪传体的写法,让小说人物入传,突出了人物塑造在叙事中的作用。另外,又因为人物之间各有关联,常常故事会出现重叠。韩少功因此在小说中将互见法引入进来,使人物故事上下勾连,不至于独立无依。
更值得一体的是,小说没有主要人物。即使是“我”,也是作为一个叙事者和思想者出现。正是如此,所以以知识青年为代表的小说人物纷纷被纪传叙事,从而构建起了知青一代人的“代际史”。以人物的成长发展构成小说的总体脉络,人物本身的性格和特点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的核心动力,社会环境则成为不是必要的外因。由此,就打破了原来知青小说一直延续的两个时代对比式的写法。从而在文体的实验创新上,推动了叙事整体性的构建。
作为一部典型的知青小说,往事回忆是主要的结构特点。在以人物为核心的章节叙事中,往往牵涉到他的过去和现在。但韩少功又很好地避免了两个时代故事的简单对比,因为在整个小说知青人物群的叙事中,多个人物的故事使得过去与现在重叠出现。正是因为文体的特点,回忆与现实的交叉叙述构成了一种颇具意味的张力结构,使历史现实融为一体,增强了叙事的整体性。
二、审慎克制的价值立场
知青小说体裁的价值判断往往有一套自觉的模式,至少不会缺少对过去的回忆与控诉。这样在文本的价值立场上,就造成了两个时代的断裂。韩少功在《日夜书》的价值立场上是审慎克制的,通过克制的理性,对人物、时代、生活、传统等等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
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对知识人物的塑造。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知识人物群在小说中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韩少功并没有以知识人物为核心,来描述两个时代的变化以及控诉过去的伤痛。恰恰相反,他谨慎地刻画这一类人物,甚至有时采取了反思式的否定态度。马涛这个人物是知识人物中的代表。韩少功的刻画凝聚了他对知识人物的某种普遍性的价值态度。他们有知识人物的应有的知识和智慧,但作者也深刻地写出了他们的缺陷。这种对核心人物充满反思的否定,对于知青小说叙事整体性的建构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他打破了原来因为社会时代的伤害而对从此类人物采取的同情和肯定,更是建立了对于这样一代人的文学创作应有的客观真实的态度,进而深刻地推动了知青体裁的小说叙事整体性的建构。
在另一方面,《日夜书》对于乡土人物、知青生活等等方面却也有着值得关注的价值立场。在此之前,很多代表性的知青小说往往对落后的乡土传统习俗以及愚昧的农村人物有着鄙夷、嘲笑等否定性的态度。正是这样一种价值立场,再结合前面对知识人物的肯定性态度,如此便促成了叙事的断裂。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与知青小说体裁相结合,必然使前后两个时代的叙事的断裂更加明显。而韩少功却对此进行了矫正,这种矫正出于克制的理性,也出于对于美好人性的深度关切。通过《日夜书》的描写,很多知识青年都对白马湖的生活充满了不舍与眷恋,对于朴素的乡土传统也饱含着敬意。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莫过于对秀鸭婆这个人物的塑造。
韩少功在小说的价值立场上避免简单的二元分化,破除政治史、社会史的迷信,从更加普遍的人性意义上去描述这一代人及其所经历的生活和所接触的人物。应该说,这样的一种相对柔和的立场,缓解了知青小说一直以来存在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冲突,从而推动了小说的整体性叙事。
三、两代人和两种视角
《日夜书》致力于描写一代知识青年的整体图景,但却不是简单的一代人的描写。小说通过两代人的故事来着重描写知青这一代人,避免使知青一代人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消解了叙事的整体性。这种两代人的故事,强化了人物性格在人物成长的中影响,也强化了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影响,更降低了社会环境和时代历史对人物言过其实的作用。两代人的故事与知青历史紧密结合,使关于社会时代叙述的转换更为自然。
这种例子生动地体现在了郭、杨两家人身上。郭丹丹是郭又军的女儿,在小说后段逐渐成熟懂事。恰恰与之相反,马家的女儿马笑月最后的命运是自杀的悲剧,也成了整部小说让人唏嘘喟叹的一章。马笑月的问题,根本上是源于家庭的分裂和亲情的缺失。如此,对一代人的刻画通过两代人的故事进行了很好的推动。而且,知青这一代人不仅因为社会历史对自己造成了影响,形成了这一代人的代际特征。同样这一代人,由于自己的个性特点,对第二代人也产生了影响。
在小说知青一代人的刻画中,“我”无论在小说形式和内容上都非常值得注意。“我”是小说知青人物之一,是关联马、郭两家的人物之一。从小说结构上而言,“我”牵涉到了小说的叙述视角的问题。作为一部在形式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小说,《日夜书》在叙述视角上也基于叙事整体性做了有价值的探索。不难发现,韩少功在《日夜书》的创作中很自然采用了两种叙述视角。首先,“我”作为小说人物陶小布,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在形式上,通过“我”陶小布为线索串联起了各个故事,同时也使以人物为核心的仿纪传体文体创新成为可能。在内容上,“我”做为一个知青,那么以“我”为视角的知青生活叙述则更为真切。
所以,以“我”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对小说叙事的整体性建构而言,是作用巨大的。另一方面“我”也作为一个全知视角出现在小说中。以“我”作为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弥补了第一人称进行仿纪传体叙事的不足,使时代情绪和代际历史更加统一,更具整体感。另外,作为全知视角的“我”也是小说叙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者。小说中关于“我”的深刻思考,蕴含了小说的内在意义,是小说文体实验的思想保障,避免了形式创新堕入思想贫乏的窠臼。也正是由于“我”作为全知视角的哲学思考,使小说更为全面地展现了生活历史的复杂性和辩证法,从根本上让人性在知青小说中代替了政治性,促使充满政治意味的两个时代的叙事融为一体。
[1]韩少功.日夜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2]陈鹭.《日夜书》:“后知青文学”的当下书写[J].文艺争鸣,2013(8).
[3]黄灯.《日夜书》:整体性叙述背后的精神图景[J].小说评论,2014(1).
[4]马新亚.韩少功的现代主体建构及其精神寻根——以长篇小说《日夜书》为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5]张柠.论叙事的整体性[J].文艺理论研究,1998(1).
[6]方维保.论左翼“革命文学”的历史整体性叙事及其价值内涵.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5(10).
[7]沈闪.日有所思,夜有所书——关于韩少功《日夜书》的研究综述[J].名作欣赏,20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