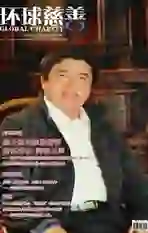阅尽千帆仍少年 天地之中画大牛
2018-01-03张翼飞
张翼飞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的人把自己标榜得很传奇,但其实很是一般,甚至欺世盗名。有的人看着一般,却非同凡响,有着真正传奇的经历。在艺术的世界里更是如此,为了成名成家,各色人等使出浑身解数,千奇百怪,无所不用其极。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真正做艺术的人,是恬淡宁静的,是不争不吵的,是耐得住寂寞的。机缘巧合,郑报融媒记者最近遇到一位少林寺的艺僧,惊异于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震撼于他胸怀万壑、大气磅礴的绘画作品。因为低调内敛的性格,和对自己“依然在路上”的艺术高标准,他很少参展参赛、拍卖作品、出席活动,甚至连得意的作品都很少示人,所以知道他的,多是圈内的行家。
一位优秀的画家,应该被及时认识和发现,他同样优秀的作品,更应该被广泛地传播和欣赏。正如千年古刹少林寺,不仅可以是隐藏在嵩山幽谷中供僧人们清修的禅宗祖庭,也可以是供善男信女、中外宾朋前来膜拜、参观,在天地之中共享的世界文化遗产。
虽然已经五十有六,并且贯通道家和佛家,游走艺坛和禅堂,但他依然保持着一颗热爱生活、怡然自乐、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童心,正如目前流行的一句话“愿你阅尽千帆,归来后仍是少年”。是的,他饱经沧桑,依然少年。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责诚法师,老家在信阳罗山县,1961年出生于新乡市,1968年随父母调动工作移居郑州。1973年,在郑铁四小小学毕业。他从小便是个不安分的孩子,爬树上墙,追鸡打狗,但唯有一件事能让他安静下来,那就是画画。在河边看水中的游鱼,他能一动不动地看一两个小时,肚子里面打好了腹稿,回到家里画得活灵活现。1975年,他考入郑铁六中,这所学校的美术教学当时就已经颇具特色。
那时还属于“文革”动乱时期,学校的教学很不正常,经常以工代教。一次,学校组织学生们挖防空洞,个性鲜明的责诚法师,在老师的评定中属调皮鬼之一,和几个男生一起被禁止参加劳动。他们百无聊赖,只能在学校操场嬉戏打闹。正巧被比责诚法师大三岁、也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哥哥看到了,问他怎么不去上课。责诚法师说今天劳动,老师不让参加。哥哥一听就明白了,说你又调皮捣蛋了,然后给他一张十六开的素描纸和一本小画册说,别乱跑了,你回家吧,画张画给我,学校组织美术比赛呢。
画画是责诚法师喜欢的事,他拿着纸和书就回家了,用铅笔临摹了一幅海军士兵像。不久,这幅画在全校的绘画比赛中获奖了,他也很快被选入了学校的美术组,从此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
当时学绘画的人很少,等上一届学生毕业后,整个学校学画画的,就剩下责诚法师和一个低一届的学生两个人。但他们仍然坚持。让责诚法师得意的是,当时的美术老师怀孕了,他每天都要去找她要美术室的钥匙。美术老师因即将临产,嫌麻烦,干脆就把美术室的钥匙交给了他,告诉他只要不把石膏头像搞脏弄坏就行。
这一下小小少年如鱼得水,从1977年到1979年的3年时间里,责诚法师几乎每天都把自己浸泡在美术室里,把里面的石膏从几何到头像反复画了个遍。这中间,他很长时间都是孤身一人,但从来没有感到过恐惧,感到过寂寞,反而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画得不过瘾。因为还处于“文革”尾声,物质匮乏,很多美术用品市场都买不到,油画颜料种类少,就连调色油都买不到。
这种情况让以西画为基础的责诚法师,决定放弃画油画改学中国画,此后,他开始从古画特别是宋代名家的作品入手,从画作临摹到理论学习,系统地了解了中国画的发展和传承。
1981年,责诚法师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铁路职工,但他对绘画的热爱有增无减,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看画、学画、作画,发了工资,也都买成了与绘画有关的书籍。令他不快的是,因为看不到原作,购买的古代名画的复制品,总是有隔靴搔痒、未见其神的感觉。
1982年,发生了两件事,对他的绘画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当年夏天,轮到休班,几个同学相约出去玩,有人提议去华山,大家一致同意。当时责诚法师没有什么准备,身上只揣了4块钱,脚上穿的是人字拖,但从来没有到过真正大山的他,二话不说,立刻跟着大家动身了。当他们费尽周折,终于登上这座“天下第一险”的名山,站在最高峰向下俯视时,责诚法师真的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
不仅如此,他之前临摹古人画了那么多山川,却总感到画出来的是僵的、是死的,登上华山,亲身感受,才顿时明白了自然之浩瀚,山水之俊秀,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心宽了,人小了。”责诚法师开悟了,他懂得该怎样画出山水的灵魂了。
这一年的另一件事是,当年10月份,他第一次来到北京,走进故宫。也真是缘分,当时恰逢难得一遇的“晒画”,也就是故宫博物院把馆藏的历代名家绘画精品,都拿出来进行展示,面向社會开放。对于一直想看原作而不得的责诚法师来说,真是得偿所愿,大开眼界。
从早上进来一直看到闭馆,他看得聚精会神,看得如痴如醉,看得热血沸腾,很多之前临摹复制品时没有弄懂或者一知半解的问题,看到原作时茅塞顿开,迎刃而解。这次在故宫看画对他的深刻触动,若干年后,依然令他心潮澎湃,坚定了他也要画出可以流传后世杰作的决心。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从1983开始,责诚法师对范宽、郭熙、董源、巨然、李唐、马远、夏圭等唐宋名家,进行了原大绢本的临摹,又对元明清到当代著名画家的各类风格的作品,夜以继日地进行临摹学习。后来他着重笔墨,又下大功夫对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钱松喦、宋文治、黎雄才等先生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看自然山水,阅故宫真迹,使他开阔了眼界,理解了“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的涵义,而从1979年到2004年之间的勤学苦练,又让他对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等,都有娴熟的掌握和独特的呈现。
这些年间,他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不少坎坷和变故,痛定思痛之后,他辞去公职,远离俗务,更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
2007年,责诚法师有一个学生,在中岳庙搞了个道教乐团,邀请他去看看。到了那里以后,看到这么大的庙宇,晚上那么安静,三人甚至五人才能合抱的大柏树,都有成百上千年了。有时候,寂静得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得见,令人感到庄严肃穆,有一种心灵的震撼。这种感觉,和他刚参加工作时,到北京故宫,看到古代著名画家们流传下来的力作真迹的感觉,异曲同工。
在这个幽远宁静的大庙里,远离尘嚣,弹着古琴,品着茶,那种逍遥自在,难以用语言形容。待了几天后意犹未尽,责诚法师萌生了一个想法,想在这里长住一段时间,于是通过小道士向主持禀告。中岳庙的主持,是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至杰师父。他知道责成法师的意愿后,专门把他叫过去问:“你为什么想要出家?”责诚法师很自然地回答:“没有什么,就是喜欢道。”
其实,虽然之前未曾谋面,但黄至杰师父听小道士说起过,庙里来了一位朋友,古琴弹得好,画画得好。见面之后,很喜欢他,没有多说,就让他留下了。只需要他回郑州,到派出所去开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证明。
在中岳庙入住有3个月左右,恰逢中国道教协举办一个活动——道教协会成立50周年首届书画展。中岳庙作为著名的庙宇,也接到了让提供参赛作品的通知。这件事很自然地就落在了责诚法师身上,他很高兴,用了4天时间,画了一只大牛,起名为《清和当春时》。画好之后,邮寄到了中国道教协会。作品寄出去的第三天,道协相关负责人专门打电话过来,感谢责诚法师对活动的支持。后来知道,这幅画在此次书画展中荣获全国一等奖,并且是一等奖的第一名。
有人问,责诚法师喜欢画牛,是不是因为喜欢道,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经常就是骑着青牛有关系?他说,这倒不是,他画的多是水牛,其实是他童年记忆里的东西,是一种乡情。因为自小在河南的南方信阳长大,耳濡目染,对水牛有着特殊的感情,水牛成为他和世界对话的重要载体,也是他赤子之心的直接呈现。
当时在中岳庙入道后,责诚法师不仅潜心研习书画,还深入学习了道教的思想文化,对周易、六爻、风水等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感知到了天地自然的奇妙,以及未知宇宙的神秘。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一年之后,责诚法师离开中岳庙,出去云游,四海为家。冥冥之中,自有造化,缘分到时,不请自来。2010年的一天,有朋友邀请责诚法师到离中岳庙很近的少林寺去游玩,因为当时少林寺管理很严格,或者买票,或者要有寺院里的人领着才能进入。当时,责诚法师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总有一天,我要把少林寺变成自己的家。”
因为当初责诚法师修道也是为了艺术,是为了把画画得更好,但此时他修道达到一定层次后,感到进入了瓶颈,难以突破。所以,他想换一种方式,就像达摩祖师面壁九年图破壁一样,想以参禅的方式,到佛家去寻求新的灵感。
后来,少林寺举办“机锋论禅”,责诚法师前去聆听,结识了少林寺禅堂知客永了法师。在永了法师安排下,他在禅堂小住了几日,发现禅堂里空荡荡的,连一幅画都没有,于是挥毫泼墨,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给永了法师画了幅牧牛图,这是一幅近3米长的大画。永了法师看了十分喜欢,觉得他的画里有禅意,与佛家有缘分,问他是否有意到少林寺参禅,希望他能留下来。
责诚法师不置可否,顺其自然。永了法师便向永信方丈做了汇报。一个月后,永信方丈有时间,请责诚法师过去面谈。见面后,永信方丈问他:“你在中岳庙修道,怎么又想到少林寺来出家了?”责诚法师说:“参禅问道,师出同源,要想参禅,不到少林这禅宗祖庭,还能到哪儿去呢?”永信方丈点点头。喝了茶又聊了会儿,永信方丈说,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在这里住下吧。
于是,责诚法师便在禅堂长住,写生嵩山,后来,少林寺成立艺僧院,他又成为艺僧院的院长。在少林隐居的时间里,他学佛修禅,登山探幽,胸怀万壑,笔下有神,境界更加空灵超脱,而且偏重于对水牛画法的提升和超越,创作出一批尺幅大、格局大、视觉冲击力大的大作品。
责诚法师画的大牛,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他于古人基础上加入现在写实手法,勾勒出了牛的骨骼转折,筋肉缠裹,笔法老练流畅,线条富有力度。牛的眼睫毛、口鼻处的绒毛,以及身上的根根细毛,清晰可见,笔笔入微。每头牛都目光炯炯,通过对其眼神的着力刻画,将牛既温顺又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活灵活现。而且雖然牛是主角,但每一幅都在丈八以上画纸上,近处的草地树木,远处的山峦叠嶂,浓淡相宜,层次分明,情景交融,相得益彰,特别是竖立起来看,画上的牛神采飞扬,仿佛呼唤一声,就能迎面走出来。
虽然画的都是牛,但又各具性格:有的公牛抬头扬角,威风凛凛,霸气十足;有的母牛俯首帖耳,目光温柔,舐犊情深;有的小牛天真浪漫,无忧无虑;有的两牛相斗,难解难分……
责诚法师的牛不但画得逼真,更可贵之处是,在画出了牛的神态又加入了人性在里面,每一头牛都令人印象深刻。
笔端金刚杵,在脱尽习气
几年前,河南省美术馆副馆长、著名画家于会见一次偶然见到责诚法师画的荷花,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人画荷花已经画了一两千年了,你依然能杀出一条路来,画出你自己的味道,画出禅的味道,太不容易了!”
当时,责诚法师画的水牛他还没有见到。后来,见到责成法师画的一些大牛后,于会见不再做评论,而是表示,应该尽快办一个画展,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现在,于会见的办公室里,只挂了两幅画,一幅是自己的,一幅就是责诚法师画的牛。
但责诚法师并没有忙着办展,虽然已经创作出不少让专业人士为之折服的作品,他仍然感到有所欠缺,一定要厚积薄发。因为在少林艺僧院,已经有人不断找上门来求画,令他不胜其扰。最近,他索性“大隐隐于世”,躲在郑州高新区易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全学为他提供的工作室里,每天修炼、作画、遛狗、弹琴,生活简朴,乐在其中。
刘总虽然不太懂画,但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他和责诚法师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别的忙帮不上,就为他创造了这样一个离城很近、离尘很远的环境。他说:我觉得责诚法师是一位惊世骇俗的艺术家,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无论褒贬,责成法师都泰然处之,他觉得,一个画家,还是要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但谈到艺术,他就不再沉默,愿意表达自己的见解。
有人问:您的艺术追求是什么?
责诚法师: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这正是我绘画的追求。艺术永远没有穷尽,但中国画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链条,不能偏离,凡是有成就的画家,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不是随心所欲,肆意妄为。
我认为,画家个人的发展,要遵循历史的规律,符合时代的潮流,既不食古不化,又不自以为是,顺应发展的需要而发展,就是最好的结果。我喜爱的清代杰出画家王原祁,自题《秋山晴爽图》卷略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笔端金刚杵,在脱尽习气。”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有人问: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虾、黄胄画驴,堪称一绝,雅俗共赏,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专属标签。您专攻画牛,是不是想让后人记住,自己是画牛画得最好的画家?
责诚法师:你说这个太小气,不是我要的。这些给画家贴标签的情况,在民国之前是没有的,近现代以后,才有了这种倾向。一个好画家,都是多面手,拿起笔来,应该什么都能画,什么都能画得好。像我们熟知的,宋代的戴嵩擅长画牛,李公麟擅长画马,但他们的其他画作也都是神品;唐代的吴道子,擅长画人物,但他的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也都无一不精。所以,至于有没有人给我贴标签,或者说我担不担得起什么标签,这都是后人的事,我只要画好我想画的画就可以了。
有人问:您怎么给自己定位呢?是画家,是僧人,还是其他?
责诚法师: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回答是与不是,因为画家和僧人是两个载体,我学道参禅绘画弹琴,不只是简单地做个画家和做一个道士或是僧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会拘泥于形式教条。《易经·系辞》有一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是无形的道体,形而下是万物各自的相。被万物各自的形象与用途束缚,就不能领悟、回归到无形的道体之中。
梁武帝问达摩,我自从当了皇帝后,写佛经,造佛寺,培养发展僧人,不可胜计,同时还多做善事,广结善缘,净身持戒,敢问有何功德?达摩竟说:“这些并没有什么功德,真正的功德是净慧智圆、体自空寂,就是说能自见真如自性就是功,能视一切众生平等就是德,念念之间没滞碍,常见真如本性、本自具有的真实妙用,这就叫功德。”得道为功,行道为德,我并不在于画家或僧人,那格局太小,我只想通过这几十年学道修道悟道,再通過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让世间的人通过绘画感知到禅、道、自然的神奇,这才是我要做的,也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