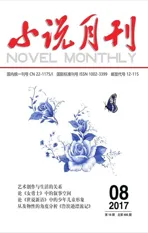孙惠芬小说的空间诗学探略
2017-12-01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00)
孙惠芬小说的空间诗学探略
王颖异刘扬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400000)
孙惠芬作为乡土作家的代表,是忠实的乡土守望者,在她的小说里始终存在着辽南这样一个大的乡村地域空间,其作品也几乎围绕这个空间进行书写,其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空间的诗学”,她将主体的情感寄托于空间想象之中,从现实空间跳出来往回看,童年的人与事、苦与乐,童年的见证让她构建了“歇马山庄”系列小说,同时,这个空间也带来了她的文学表达与文学想象。然而,孙惠芬作品中空间诗学的表现形态不仅在于将并置的场景放入虚实结合的论述框架中,更在于她把对乡村诸多空间的书写还原到“日子”的日常化写作中,将人物放置于时代变革的大潮中,追寻其人性及命运,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孙惠芬;空间诗学;歇马山庄;表现形态
1982年,孙惠芬在《海燕》杂志上发表《静坐喜床》,从此走向文坛。随后,带有鲜活的辽南乡村日常生活气息并引起一定反响的《小窗絮语》、《闪光的十字架》、《赢吻》等作品相继问世,但真正标志她的创作进入成熟期且被更多人熟知的是199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这部作品反映了乡村农民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内心的焦虑、躁动以及对希望的找寻,紧接着作为延续她创作了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将写作视角再聚焦,集中体现乡村女性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近年来,更是佳作不断,创作了《上塘书》、《街与道的宗教》、《台阶》、《吉宽的马车》等作品,可以说她是一位生在乡村的歌者, 一位迁徙到城市却把根留在了故乡的歌者,更是忠实的乡土守望者。
“空间”是孙惠芬小说里十分重要的概念,甚至于,她的部分小说直接以空间命名,如《灰色空间》、《伤痛城市》、《歇马山庄》、《上塘书》、《后上塘书》等等,而作品中老宅、院子、后门等富于空间感的图景更是不胜枚举,在孙惠芬的小说里,她更看重瞬间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往往在不期然间与故事相遇,并掀起波澜。
诚然,地域文化对孙惠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她自觉地选择了并精心守护着这“瑰宝”似的土地,以平实、质朴的语言,真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辽南清新自然的风景,记述了民间古朴的地方民俗,并勾勒出具有自身意味的乡村空间,同时,以其对地方的亲身体验,自己的生活,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借助小说了解想象的地方,或领略用文字描绘出的地方,深深地感受并在作品中书写对地域空间的独特理解,其中包括对乡村场域中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人物心理空间的关注,而作者的这种“主观性”事实上也言及了空间的社会意义。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1]认为空间并非是均质的、空洞的、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而是内置于个体体验和想象之中,是人类意识幸福的栖居之所,他将意象进行诗意观照,从而建构出“栖居的诗学”观:作家在书写自身经历时往往回到怀揣着爱意的,尤其是童年时期的空间场域,童年时代所见证的人与事,以激发起空间想象的诗意表达。巴什拉所关注的是“内部的空间”,这个空间被想象力所把握,被人所体验,并从而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它已然不是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冷漠无情的空间,而是被主体想象力所构建的一种相互融入、彼此交融的形态:人通过想象力诗意地建构空间,而空间也充满灵性地在建构着人。因此,巴什拉认为,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空间,更是一种精神空间,它被人所想象、所体验,人在空间之内,空间也在人之内。
而孙惠芬的小说无时无刻不渗透着这种“空间的诗学”,她对空旷孤寂有着独到的感受与表达,也对乡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深深的爱恋,固然,实实在在的乡村带给孙惠芬创作的源泉,但这种纯粹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内置于她的想象之中,通过这种想象,诗意地构建出自己的文学表达、人生理想,当她迷失在城里的家园时,就回到了童年的家园,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开启了构建自己独特的反映乡村、日子和人的小说的想象空间。
1 地理空间:“歇马山庄”的空间构建
孙惠芬的作品几乎是围绕辽南这个空间进行书写,从而构建了一个“歇马山庄”世界,这也几乎成为其作品的代名词。然而,山咀子和青堆子是作者“所生长的地方”,只是现实的物理上的空间,并不是她真正想要回去的故乡,于是,孙惠芬将这种主体的情感寄托于空间想象之中,从现实空间跳出来往回看,童年的人与事、苦与乐,童年的见证让她构建了“歇马山庄”系列小说,歇马山庄、上塘等空间才是它真正想回去的精神家园,并且,这个空间带来了她的文学表达与文学想象。
1.1 家宅:内心存在的地形图
《空间的诗学》中言及,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是人们认同感产生的地方,是最主要、最可靠、最直接的幸福感萌生的空间。在家宅诗学中,它是人类最初的宇宙,人在其中得到庇护的存在,更是梦想的空间。从内心的角度看,只要愿意梦想,哪怕是最简陋的居所也是美好的,没有它,人就只有流离失所。而且,当新的家宅中重新出现过去的家宅的回忆时,就来到了恒久不变的童年的国度,并且体验着安定感与幸福感,这种对旧日居所的回忆被人们重新体验时,仿佛过去的居所在我们心中是永远无法忘却的梦想。
孙惠芬就是这样,在她的内心深处,总是有着这样一个存在,它让自己看到在这个世界最初的模样,看到与这个世界最初关系的缔结与形成,无时无刻不在怀想它、思念它。尤其是当她走出家宅,走出乡村,以城市人的目光往回看的时候,这种梦想更为强烈,某些时候,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在梦境中,孙惠芬时常回到自己童年的家宅,甚至害怕午睡惊醒了这个与童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梦。家宅就是有着一种强大的融合力,把人的现实、回忆和梦“化”在一起,当她经历了城市的迷茫与惶恐之后,是家宅在自然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她,在这个曾经体验过梦想的地方进行自我重组,构建自己的文学想象与人生理想。当然,在孙惠芬的作品里,家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院子、前门、后门、场院等空间不仅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也共同构建了她内心存在的地形图,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记忆和想象。
1.2 街与道:“向外”的宗教
在辽南乡下,街和道最不易区分,“有住家的地方,街就是道,没住家的地方,道只是道,却不是街”[2]71,但它们始终都通着外边,连接着外面的世界,而在乡村,外边首先就是小镇。因为小镇是相对开放与活络的,与外面的世界息息相关,不仅对父辈们很重要,对于乡下孩子来说,崇拜外边也首先是从崇拜小镇开始的。孙惠芬的祖辈、父辈以及乡亲们“很早就信奉外面,凡是外面的,就是好的,凡是外面的,就是正确的,从不固守什么,似乎只有外面,才是他们心中的宗教”[3]28。所以,“向外”是孙惠芬父辈们的宗教,是乡村每一个人的宗教,也是街与道的宗教,更是孙惠芬心中的宗教,对于乡村的“逃离”让她领略到通向外边的澎湃与激荡,因此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逃离乡村的书写,其实,这“向外”的宗教也源自他们对于“外面”的空间想象,来自主体的内心深处对外边世界的崇拜与美好想象。
正因为街与道代表着“向外”的宗教,同时也让房子形成了新与旧的区隔,被进行切割,区隔成不同的版块,既展开自己的理性逻辑,也展开它的神秘想象,既表达清晰的农村生活,也藏着隐秘的“政治”,乡村的家长里短、琐碎生活在这里生动地还原。《上塘书》中的“上塘”就分为前街、中街和后街,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建筑风格,也代表了不同的阶层,更隐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味,前街历史悠久,多是长者居住;中街晚于前街,多为在困窘与无奈之下另立门户的前街儿子一辈人修建;后街则代表新富,他们带着城市气息,将城市的住房格局带入自家房屋的修建中,刻意模仿。三条街,三个群体的争斗在孙惠芬笔下进行空间化的演绎。
2 社会空间:“关系”的意义建构
社会空间,其实就是关系空间。在孙惠芬的作品中,这种社会空间是一种“关系”的建构,人在自然中自在地栖居,从而构建一套属于这个空间的自我的生存法则,而人与人之间也微妙地发生着关系。
“歇马山庄”是孙惠芬精心营构的乡村空间,在这个场域里,时间仿佛是凝滞的,人们怡然自得,安适宁静,街道、房子、场院、生活自得地存在着,也是在此空间中,人们建构了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有着属于自我的、伦理的、约定俗成的世界。对于空间里的一切,他们有着自己的标准和理解,从而形成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而这套空间的生存法则融入到人们的乡村生活里,从中体现着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情感以及生存的意义。正如《空间的诗学》里所言:人诗意地建构着空间,空间也灵性地建构着人。《上塘书》里,对于“上塘”这个空间了的地理、政治、交通、文化、历史等,上塘人都构建了一套自我的空间生存法则,每条街、每条道、每种仪式以及精神世界都是独有的,而人与人也发生着微妙的关系。
孙惠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书写乡村生活,她擅长在文本中展现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而这种微妙也恰恰是其最为关注、最善于捕捉的,同时也是她对小说最崇高的追求。在世纪转型之交,时代变革的大潮下,乡村固有的男耕女织的秩序被打破,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孙惠芬在此大背景下,她的小说往往不追求事件的完整性与逻辑性,而是将乡村置于开放的结构中,在这样的语境下探寻人物之间的细密心思与微妙状态。《燕子东南飞》的燕子老人天天坐在门口往东南方向望,不回娘家也不让儿子回,孙惠芬一点一点探进老人的心灵世界,不断追问“为什么”,探寻一个属于东南方而又无法言说的秘密,燕子老人每一次心灵的震颤都融进了别人所未见的微妙里,最后终于明白,她的儿子是小日本的后代,她渴望回家,又不能忘却耻辱;她想拥抱儿子,却不得不冷酷;她看似疯狂,实则理性。这是孙惠芬作为作者,作为创作主体,与其创作对象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其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的微妙形态更是值得细细品味。《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与潘桃、《女人小米和女人林芬》的小米和林芬、《歇马山庄》里月月与买子之间,以及“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之间等,孙惠芬将叙述视角延伸至乡村,进一步拓展到乡村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关注更广阔的生活,对人物的生存现状、命运的揭示是生动、真挚的,且反映其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时期的所思、所感,也是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
孙惠芬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有着特有的情绪,而她又善于抓住这种心灵的瞬间情感,观照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在创作中,她尤为注重并擅长在文本中创造这种瞬间的历史,总能“把撼人心魄的心灵瞬间描绘成瞬间的历史,雕刻成微妙的情绪之城,从而延展文本的审美空间”[4]180。她对于乡村人的书写看似简单平凡却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抓住了时代的特征,反映了时代变革给这些普通人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他们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有被城市无情拒斥后的心酸历程,也有诗意的人性复归,有追逐青春理想的渴望,也有无法言说的迷茫与困窘,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与帮助,孙惠芬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发出声音,给予这些人们更多的人文关怀,正如她自己所说:“世界发生变化,文学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作为文学,有一点必须坚守。那就是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探索,对人的生存奥秘、人性奥秘的探索,因为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的历史,是作家永远的职责。”[5]这不仅是她创作的目的所在,也是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更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3 空间诗学的表现形态
3.1 场景并置
尽管孙惠芬的作品之间存在一定的连续性,《秉德女人》以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为线索,并反映出辽南乡村社会从清末民初、东北沦陷、抗日战争、解放区土改以及政治风云变幻的建国时期百年的变动,《歇马山庄》描述改革开放背景下辽南农村的巨大变化,《吉宽的马车》则关注的是在城乡之间游走的乡民夹缝中的生存状态,而《上塘书》则以平实、自然的清丽语言书写辽南乡村的日常生活。但是,她的辽南乡村小说多是展现乡村的横截面,都是放置在“歇马山庄”(辽南)这个大的乡村空间加以论述的,不同小说的不同时间片段的拼合,不同时空、不同场景的人和物,糅合在这个总体的空间框架之中,加上历史向度的挖掘与时间长度的延续为这一系列小说在空间上建立起一个独特的乡村世界。《上塘书》便是一个个独立的版块之间的空间组合,孙惠芬围绕着“上塘”这个大的生存空间,设置了地理、政治、交通等九个小空间,书写和诠释了乡村以及人的命运;《街与道的宗教》每一章节都以场景命名,作者关注空间场域的延展,并在共时性的敞开的空间中描绘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乡村画册;《城乡之间》第一部分“创作与生活”也将其文学自述和生活影像以小节的形式呈现,有着素朴的,略带原始色彩而又弥漫着现实生活芬芳的美学意味。
而且,这种并置的书写是嵌入虚与实的论述框架之中的。首先,孙惠芬的作品中总是自传的真实,非自传的虚构并存,在《街与道的宗教》、《上塘书》、《秉德女人》以及《一树槐香》等多部小说中,不管是小说中的“我”还是其他人物的经历总与作者的经历有着一定的同构性,她所创作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原型”,所以,她的小说既虚构,又带着真实;其次,对于人物的刻画,她尤为注重其在空间场域中的生存状态,而虚化故事背景和人物轮廓;再者,小说中不时贯穿着童年的回忆性的叙事,偶尔又穿插着作为叙事者“我”当下现实的时空里,过去和现实两个时空在文本中不断交叉、融合。
3.2 还原到“日子”的日常化书写
“日常里蕴含着最奇崛的波澜。”[6]乡村有着自己的日子,这里没有大事,四时轮替,春种秋收,一句话、一只鸭子就是大事。因为物资短缺、精神匮乏,因为日月漫长、人居散落,一只鸭子、一句话就是乡下人们精神中的形而上。辽南的乡村也是如此,过着没有变化而又漫长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里,最根本的日子就是过日子,过日子的气象透露着主人内在的东西,是兴趣、心情、精神。孙惠芬所描绘的乡村空间也是由无数个普通的“日子”组成的,她认为“日常,最具有极端的质地,人类精神的真正挣扎,正是在日常的存在里”[7],因此,她笔下的辽南儿女不像鲁迅作品中麻木不仁的国民形象,也不像萧红东北地域中有着原始蛮荒生命状态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真实细腻的存在,并以朴实的笔调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娓娓道出。
但是在对乡村空间最普通的“日子”的日常化书写时,她没有完全执着于对生活的平庸式的描写,而是从中观察,看似日常,其实暗藏波澜,有着其对人性、对命运的思考。她写日常生活,表现笔下人物的平常“日子”,用真实细腻的笔触捕捉到乡村青年,不刻意凸显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不是单纯的平铺直叙,仅仅表现那些日常生活细节,而是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农民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所思所感。她不刻意表现世俗人生,虽写日常生活却不给人“世俗”的感觉,《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乡村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呈现出“男工女耕”的普遍现象。因此,孙惠芬在文本中自然而又“刻意”地表露出乡村潜移默化的深刻变动,将人物放入时代浪潮之中,从而引发对其人性及命运的思考。
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空间是最为复杂的。孙惠芬作品中对乡村空间的诗意想象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深深的“家园”的烙印,充满着她对童年的美好想象,也代表着自己的文学表达。确实,对于乡村以及生活在乡村场域的人和事,孙惠芬都有着自己独到的感受和理解。辽南这个地域空间给予她创作的源泉,成为她童年美好记忆的承载物和文学想象的空间,而她自觉而灵性地将其构建为自己的“歇马山庄”世界,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以“往回看”的方式书写乡村,她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始终抓住其瞬间的心灵变化,除此之外,她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大主题,观照乡村主体在空间迁移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并给予其人文关怀,从而体现出其空间小说的文化想象。本文从空间的角度对孙惠芬的小说进行诗学研究,不仅可以从中探究作家的文学想象和文学表达,也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其个案研究,目前空间问题也是孙惠芬小说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因此还值得深入地挖掘与探究。
[1]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 孙惠芬.街与道的宗教[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
[3] 同上。
[4] 吴玉杰.文化场域与文学新思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 孙惠芬.在街与道的远方——乡土文学的发展[J].朔方,2010(12).
[6] 孙惠芬.让小说在心情里疯长[J].山花,2005(6).
[7] 张赟,孙惠芬.在城乡之间游动的心灵——孙惠芬访谈[J].小说评论,2007(3).
王颖异,女,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扬,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