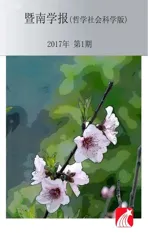论中古诗歌私人化空间的建构
——兼论诗歌新标准“诚”的提出
2017-11-13胡大雷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国古代文学】
论中古诗歌私人化空间的建构——兼论诗歌新标准“诚”的提出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先秦两汉重视诗歌的讽谏与移风易俗作用,用“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看待《诗经》、汉乐府作品的私人化抒情,诗歌中的私人空间被漠视了。屈原作品结合政治事件叙说了私人之“怨”,虽有刘安、司马迁高度赞扬,但遭到班固的批评。汉代楚歌在叙说公共化政治事件的同时,又表达私人空间的个人化情感,被当作事件实录。汉末无名氏“古诗”兴起,或假托公众人物苏武、李陵的赠答,或借助“游子、思妇”的赠答,虚拟的“赠答”为诗歌叙写私人空间提供了形式。汉末正式形成、至魏晋时呈发达之势的“赠答”诗作,诗歌有了确定的读者,与特定对象的交流,使诗歌抒发个体私人空间的情感有了文体保障。随着诗歌私人化的进程,诗歌标准除了“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外,又提出了“诚”,以张华“写心出中诚”为倡导。自此,无论在观念还是创作实践上,诗歌自觉地追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两个天地的互动与交融,使其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公共生活; 私人化; 赠答体; 诚
此处讲的诗歌“私人化”,是指私人生活,是以公共生活为对照的私人空间。诗歌的“私人化”,首先,就文本而言,是指诗人的体验方式或写作方式、作品的经验类型或写作内容,是与诗人私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其次,就理论观念而言,是指读者的阅读,是否把作品当做诗人的私人生活来读。《文选》诗分二十三类,“赠答”自成一类,“赠答”从类别名上就体现出诗歌是想对自己熟悉的人说些什么,要表达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本文从诗歌“赠答”的视角,讨论中古诗歌私人空间的问题;并期望通过这种讨论,探讨中古诗歌除“发乎情,止乎礼义”标准外,诗歌在私人化的进程又提出了怎样的新的标准。
一、民歌作品的私人空间被公共生活化
宋代人朱熹在《诗集传序》里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经·国风》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朱熹称为“淫奔期会之诗也”。但汉代人们对这些吟咏男女私情的作品的
阐释,往往赋以公共生活的性质,《毛诗序》即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把属于个人的私情称为“刺时”。又如《诗经》首篇《周南·关雎》是一首男女恋爱的诗,但《毛诗序》则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毛传》、郑笺也大致如此繁衍。人们重视诗歌作为讽谏工具的作用,所谓“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故有“诗谏”的说法。汉代或以寻绎法来解说《诗经·国风》“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作品的讽谏意味,如《鲁诗》称《关雎》: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
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机而作。
《毛诗序》中多有附会史传的情况,而尤以韩诗、鲁诗为重,这些本事大都是推演出来的,并无历史史实的根据。这种寻绎、推演甚或发展成为不是对《诗经》的解释和论述,而是讲一个故事,发点议论,然后引《诗经》的诗句为证,如汉时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均为如此。
就文本实际而言,诗作具有私人化体验生活的方式以及个体空间的写作内容,但人们却以公共生活来解释它,也是事出有因。其一,民歌本来多为集体创作的写作方式,于是人们认为,《诗经》某些作品虽然有私人化口吻,但就其作为《诗经》作品的文体特征来说,个人是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来抒情的,此即《毛诗序》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孔颖达《正义》曰:“言《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谷风》、《黄鸟》,妻怨其夫,未必一国之妻皆恐夫耳。《北门》、《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举其夫妇离绝,则知风俗败矣;言己独劳从事,则知政教偏矣,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一人言之,一国皆悦。”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作为诗人个体在抒发内心情感,又是作为社会某个集体在抒发内心情感,且以后者为重,于是,这些诗歌的私人化性质被漠视了。
其二,诗歌由私人空间的活动进入公共生活空间,如此的转换是由“采诗”制度所规定的诗歌接受目的及接受过程而决定的。何休称: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汉书·艺文志》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孔丛子·巡狩篇》:“命史采民诗谣,以观民风。”“采诗”活动“以观民风”的目的,决定了诗歌性质转变为非私人化。
其三,某些《诗经》作品私人化性质的转变,又是与当时的“用诗”分不开的。孔子所说诗歌发挥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用诗”是诗歌进入公共生活空间的途径之一,倒过来讲,诗歌只有具有充分的公共性,才能发挥“兴、观、群、怨”以及“称《诗》以谕其志”的作用。
其四,诗歌如此由私人空间的活动进入到公共生活空间活动的转换,又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郑玄《诗谱序》曰:“《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孔颖达《正义》:“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于此,非初作讴歌始于此也。”这是说,“初作讴歌”原生态的诗歌,当然应该是体现出更多的个体空间的私人化意味,而以诗发挥“诵美讥过”的作用,是以后发展起来的。
于是,《诗经》中诗歌的私人化事件、情感被阐释者所忽略,其中的赠答现象也是如此,如《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应该是新婚之夜对新人之咏,则被视为“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大雅·崧高》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抑》称“无言不雠”,旧时阐释者也称其是涉及了政治事件,而削弱了读者对私人化情怀的接受。
汉乐府兴起,“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因其社会所认定的功能与《诗经》作品相同,所以汉代乐府诗亦具有私人化抒情被公共生活化的情况,汉代官员治理地方,有“问以谣俗”以判断风俗的职责,而朝廷亦“广求民瘼,观纳民谣”并“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即有以民谣为黜陟的标准;因此,如《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等,虽然诗歌本身私人化事件的性质依旧存在,但却以“观风俗”而作为公共社会现象被关注。
二、诗歌私人化抒情与其特定的抒情对象
接受是以读者为主体的,这是一种能动的阅读和再创造活动。先秦到汉初的读者,视民歌作品的私人生活的意义小于其公共生活的风俗的意义,因此,就从观念上漠视了作品抒发的是个人情感,而是强调诗歌对社会公共事件的表达。如此在接受方面的社会风气,对汉代文人的诗歌创作自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如承袭《诗经》作品是文人四言诗,西汉韦孟《讽谏诗》的主旨为“讽谏”,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诗中先述祖上: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旂。彤弓斯征,抚宁避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由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坠。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厄此嫚秦,耒耜斯耕。
为什么讽谏楚元王子孙的作品有此一大套叙述自己遥远祖上的文字?这是以自己祖上深重的历史责任来表明如今讽谏话语的分量。诗中“我邦既绝,厥政斯逸”下李周翰注曰:“言绝我国之后,王政放逸,遂至微弱。”这是说前世统治者未听从或未听到自己祖上的讽谏而招致衰弱,这是以历史经验表明当今的讽谏之正当与必不可少。因此。这样的述说自我并无私人化的意味,而是说要为楚元王负责。又有韦孟后辈的韦玄成,其《自劾诗》因自己有过错而作,“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玄成自伤贬黜父爵,叹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诗自劾责”;诗中自述祖上辉煌历史,落脚于“赫赫显爵,自我队(坠)之”而“自劾”。这是“无后”“有后”的问题,即后代是否能够继承自己的爵位官职,是否可以永远享受着祭祀。因此,这不是自己单个人的事,而是家族的公共大事。
对私人化抒情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汉代有过一场争论,这是围绕着屈原《离骚》进行的。先是刘安《离骚传》称: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又有司马迁所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充分肯定屈原是为楚国而作《离骚》,这是就公共生活而言的;但又充分肯定屈原诗歌所谓“盖自怨生也”,这是就其私人化而言的。但《离骚》中如此私人化的情感抒发,受到班固的批判: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认为面对国家大事的诗歌抒情,不应该具有偏向于私人化的倾向,所谓“露才扬己”、“愁神苦思”、“忿怼不容”云云。
但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诗歌毕竟是诗歌,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个人的遭遇完全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的,因此,“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它还是表达着个人情感,其中还是具有私人化的内容。汉初最早显示出私人化倾向的是楚歌,虽然是围绕着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但也有着浓郁的私人化抒情。如楚汉争霸项羽被围,垓下四面楚歌,项羽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有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又有美人相和。又如《鸿鹄歌》的诞生:
(刘邦)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
这是太子之争,以其公共生活的性质被载入史册的,但又是刘邦个人的刻意为诗,他为自己与戚夫人之子哀叹,也是私人化的事件。又如塞外李陵与苏武相别所唱:
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又如刘旦谋反,被诛前夕,其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坐者皆泣。”又如刘胥谋反,被诛前夕,其自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皆涕泣奏酒,至鸡鸣时,即以绶自绞死。”这些诗歌都是政治事件中的一个环节,但从诗歌本身,我们又知道它们是有充分的私人化抒情的,尤其这是有关个人生死的。这些“歌”私人化的抒情,证明了这是诗的本质特征“诗言志”所决定的,诗是表达自己的志意的。汉时又有抒发诗人日常生活的私人化情怀的诗歌,如杨恽自称:
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虽然说是抒发政治牢骚,但就诗歌本身看,完全叙写个体空间中的私人活动。
这些诗歌的私人化抒情,起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促进。一是遵循“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诗歌自身的创作规律,以私人化的抒情展示着自身的魅力。二是这些作品都有一个特定的抒情对象,如屈原作品的楚王、刘邦作品的戚夫人、韦孟作品的楚元王,又如诸藩王临诛前对着属下或妻妾的咏歌;尤其上述的这些“歌”,歌者,“歌咏其义以长其言”,歌必须是唱出声的,唱出声的歌对接受者的需求更为迫切。但是,汉时是以四言诗为诗歌正宗、正统,所以,刘勰称韦孟《讽谏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歌”并不作为诗歌正宗,因此,这些情况只能说是歌对特定接受者的需求而对诗歌私人化的发展有所促进。
三、假托公众人物的赠答以抒发世俗化个人情怀
诗歌创作者以与自己关系密切者为确定化的接受对象,促进了诗歌私人化,这种进程还表现在汉末“古诗”。汉代末年时有一个文人诗创作的高潮,或许正由于诗歌的个人性受不到重视,这些诗作是无主名的,故历代称之为“古诗”。“古诗”最可著称者为《文选》“杂诗类”所录的《古诗十九首》,抒发的是文人们以自我群体生活为基础的情感,是当时某些文人们共同情感心理的表现。体现在《古诗十九首》中的这些情感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感伤知音难会、慨叹年华短促、不满时俗现实、忧伤离别相思等。这些古诗之所以“无题”,就是因为其抒发的私人化情感并不是由某一特定人物或某一具体事件引起的,私人化情感是由针对某种社会现象、针对某一反复出现而久久经历的事件、针对人生、针对社会而抒发的,不能以某一有具体含义的内容来限定它。《古诗十九首》不大涉及具体的公共生活化事件,只是以私人化情感抒发来打动人、感染人了。马茂元称其“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如《文选》所录的前两首: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前一首可谓“游子之歌”,是诗人的群体自述;后一首可谓“思妇之词”,该是诗人代思妇立言,正是为了使自我群体的情感抒发有对应点。“古诗”巧妙地设置“游子之歌”与“思妇之词”来对应抒发私人化情怀,这应该是准赠答诗。
“古诗”中的另一大类型为“苏李诗”,题作苏武、李陵所作者,这是假托作为公众人物的苏武、李陵的口吻的抒情,一般视其为赠答,如《文选》诗“杂诗”类所录,直题其名为《李少卿与苏武诗》,余冠英称:“相传苏武和李陵相赠答的五言诗,《文选》卷二十九有七首。”《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全为写送别,其一写清晨路侧的送别,诗曰: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直接是当前的送别所言。其二写河畔的送别,其三写河梁蹊路的送别。人们认为,这是李少卿向苏武叙说相别之情。“杂诗”类又录苏武(子卿)《诗》四首,全为写相别,其一写兄弟相别,其二写客中相别,其三以夫妻生活写相别,其四写挚友相别,这些都是表现私人化的文人生活;人们认为,这是苏武向李少卿叙说相别之情。有了实在的叙说对象,抒情自然更为真切动人。
最早考证这些作品本非苏李所作的是颜延之,他在《庭诰》中说:
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
此后,考证其本非苏李所作的甚多,理由甚确,遂成定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代苏李立言之作呢?之所以要借苏、李之事来抒发感情,是因为他俩的事迹太特殊、太令人激动了,钟嵘称:“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翁方纲说:“而苏李远在异域,尤动文人感激之怀。”确实是如此,诗人们在寻求一种他们认为满意的抒情方式,想要以自我抒发怀抱的方式直接投身作品、个体直面读者,要在诗歌中表现出个体空间。他们体验着苏李“远在异域”的遭遇,又掺入自己远离家乡的世俗经验,他们吟咏诗句时,似乎变成了苏李,而苏李也仿佛变成了他们。梁启超称苏李诗中有“俯观江汉流”、“山海隔中州”、“送子淇水阳”、“携手上河梁”“等句与塞外地理不合”,以及“行役在战场”、“一别如秦胡”、“骨肉缘枝叶”、“结发为夫妻”等句“与陵、武情事不合”,但文人是借助于公众人物的赠答表达他们别离时的相互情感,以实现其进行私人化、个体化的抒情。
春秋时有以《诗经》之作相赠答以表达自己的外交辞令,“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古训亦有“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的说法,相传孔子见老子,告辞时老子相送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外交场合的赋诗是文人所向往的才能,赠人以言是文人个体间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因此,汉末的文人们以赠答来推动诗歌的私人化的情怀表达,也是可以想见的。
四、赠答体:诗歌确定个体空间的私人化读者
汉末正式出现了赠答诗。蔡邕《答卜元嗣诗》曰:
斌斌硕人,贻我以文。辱此休辞,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赋诵以归。
诗人在诗中点明是对“贻我以文”“酬答”。汉末秦嘉徐淑夫妇间的诗歌是完整的、完全的个体空间的私人化的赠答,《玉台新咏》称:“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秦嘉《赠妇诗》其一云: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
秦嘉妻徐淑《答诗》云: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沈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明人胡应麟所说:“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秦嘉徐淑夫妇间赠答诗的意义,并不在“托兴”,而在于诗歌可以完全是个体空间的私人生活的体验与叙写。
文人的私人生活,并不单单只是夫妇之间,更在文人彼此之间。魏晋的许多赠答诗,也是多有公共生活的政治化的内容,如开“赠答”风气之先的王粲,其《赠蔡子笃》,诗末云“何以赠行?言授斯诗,中心孔悼,涕泪涟洏;嗟尔君子,如何勿思”,述其作诗的私人化目的与情感;而诗中又述“悠悠世路,乱离多阻”,王粲与蔡子笃同避难荆州,现在一个要回去了,一个回不去,诗中自然就有对世路的艰难的咏叹。其《赠士孙文始》,称“无密尔音”,要对方多来信来诗;但其首称“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师。宗守荡失,越用遁违。迁于荆楚,在漳之湄”,讲战乱中来到此地,又称“瞻仰王室,慨其永叹。良人在外,谁佐天官?四国方阻,俾尔归蕃。尔之归蕃,作式下国”,讲士孙文始归还的政治意义。其《赠文叔良》,称“惟诗作赠,敢咏在舟”,指患难与共,一切尽在诗中;李善注称“详其诗意,似聘蜀结好刘璋也”,出行是一次政治性的活动,那么,诗中的勉励之语如“二邦若否,职汝之由”云云,严羽说“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相勉之词”中就多有公共生活的内容,文人之间,最为看重的还是其政治前途。但我们看到,上述文人之间的赠答,在述说公共生活的同时,又具有非常浓郁的私人化的情感表达,这一方面表明,赠答体兴起的特殊意义,在于诗歌创作前就有了确定的读者,非自说自话的,这就为诗歌私人化提供了一个文体依据,即诗歌的交流性质显示出来了,也就是说,诗歌的个体空间的私人化程度加深了。另一方面,上述文人之间赠答中的私人化的情感表达,在表达公共生活的政治化内容的同时,更强化了诗歌的情感力量;而且,这些私人化的情感表达,是能够与公共生活的内容表达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后人对这些诗作中情感表达的赞赏,实际上就是对诗歌私人化而言的,如王夫之评王粲《赠文叔良》“思深言静,得《小宛》之髓”;陈祚明评王粲《赠蔡子笃》为“情至语反质直”,评王粲《赠士孙文始》“宛转入情”,如此“思深”、“情至”,是与诗中的私人化情感抒发分不开的。
于是,诗歌可以有着特殊的私人化目的的观念深入人心,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如司马彪(绍统)《赠山涛》,张铣注曰:“初,山涛为吏部侍郎,而绍统未仕,故赠以此诗,欲涛荐也。”晋郭泰机《答傅咸》,诗称“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喻有才德而不见用;称“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喻自己被弃不用,那么,赠诗的目的就是想让傅咸举荐自己。这些诗是请求荐举的,起码这个请求是属于个体空间的、私密化的,或许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的。更有纯粹化的、更隐秘的私人空间的情感表达,如徐妃之作,“时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表达的是个体空间的私密化的约会。
所谓“赠答”,指从诗歌可以有特定读者,而特定读者可以有特定内容的需要这一方面,奠定了诗歌个体空间的私人化倾向的合理性。没有任何诗歌,像赠答时那样渴望着与对方的交流并期待反应的,视对方为知音而企盼着理解的。由于赠答诗有着确定的读者,使诗歌的意义指向也更为确定,使诗歌个体空间的私人化的倾向有可能更为明确。
于是,诗歌可以表达其他场合或不能或不愿表达的情怀,如张华论诗歌个人性,其《答何劭诗》,先说“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缨纟委为徽纟墨,文宪焉可逾。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称“吏道”使人不自由,而“吏道”正是张华在那个社会安身立命之物。其诗又云:“洪钧陶万类,大块禀群生。明暗信异姿,静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虚恬窍所好,文学少所经。”这是说,自然界赋以人们各种不同的禀赋才能,自己的志向与才能不在“功名”,自己的爱好喜欢在于“文学”,这是自己从小就曾努力的。但假如私人化的抒情被漠视,读者阅读时或许会只见政治性的个人,见不到个体空间的个人,显示出个人私权力的被忽视。
五、诗歌新标准“诚”的提出
当诗歌强调公共空间的政治性时,诗歌的标准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理由即“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那么,如果诗歌属于个体空间而趋向私人化、个人性,其标准又是什么?
汉代王符《潜夫论·务本》曾批评诗赋助长了社会的“不诚之言”:
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那么倒过来讲,王符提倡的是诗赋的“诚”。至今留存最多的赠答诗是两晋时期的作品,细读之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诗中所述“诚”者最多。如张华在《答何劭诗》其二说到:“是用感嘉贶,写心出中诚。发篇虽温丽,无乃违其情。”他把文人间赠答诗作的“缘情”与“写心出中诚”联系起来了,提出赠答的“缘情”应该以“诚”为标准。张华所说赠答的“写心出中诚”并非是空谷足音,此前有孔融《临终诗》“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曹丕乐府《煌煌京洛行》“多言寡诚,只令事败”,曹植《洛神赋》“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称“通辞”以表“诚素”。后更多有响应者,尤其是在时人的赠答诗中,如傅咸《赠崔伏二郎诗》“人之好我,赠我清诗”,“诚发自中,义形于辞”;陆机《赠冯文罴》称“愧无杂佩赠,良迅代兼金;夫子茂远猷,颖诚寄惠音”。陆云《答吴王上将顾处微诗》“亦有芳讯,薄载其诚”。陆云《失题》“赠我翰林,示我丹诚”。郑丰《答陆士龙·兰林》“诚在心德,爱结忘言”。郑丰《答陆士龙·南山》“交弃其数,言取其诚”。曹摅《赠王弘远诗》“日月愈久,曾无玉声。倾心注耳,寂焉靡听。桃李不报,徒劳我诚。”孙绰《答许询诗》“敛衽告诚,敢谢短质”。羊徽《赠傅长猷傅时为太尉主簿入为都官郎诗》“孰寄斯诚,实惟旧要”。谢瞻《于安城答灵运》称“行矣励令猷,写诚酬来讯”,颜延年《直东宫答郑尚书》“知言有诚贯,美价难克充”;李善注:“知汝之言,有诚实旧贯,美价难以克充。”
“写心出中诚”继承着孔子“修辞立其诚”,相对于“礼义”是一种外在要求、社会规范,而“诚”则偏重于自我要求。“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并以“自成”达到“成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修辞立其诚”是对“言”“辞”的要求,诗歌,也是一种“言辞”,提出“写心出中诚”也是理所当然的;而比照诗歌在公共空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要求,对诗歌的个体空间的私人化提出“写心出中诚”的要求,也是合乎实际的。
虽然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但先秦诗歌是作为讽谏工具、外交语辞工具等公共化性质著称的。随着中古诗歌私人化倾向的进程,不仅在诗歌创作中不讳避私人化情感的抒发,有些诗歌甚或有过度私人化的表达,如某些宫体诗之类。至南朝时,人们对诗歌兼具公共化、私人化二者有所论述,如《诗品》一方面称说诗歌“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歌叙写公共生活,是诗歌实施公权力的表现,也为诗歌带来了广阔的前景,其政治化的宏大叙事使诗歌的意义有所扩张。《诗品》另一方面称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者,莫尚于诗矣。”所谓“凡斯种种,感荡心灵”者,即是诗歌公共化与私人化的结合。从创作实践上讲,诗歌的私人化至两晋时已基本被认同,而南朝梁时钟嵘又从理论上肯定了诗歌兼具公共化、私人化二者,也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中古时期诗歌的私人生活化,曾经历着两个发展方向与发展阶段。其一,把原属于个体空间的私人化的诗歌被公共生活化,诗歌排斥着私人生活。其二,汉末开始,借助公众人物、群体人物以抒发私人情怀,到赠答体的出现,个体空间的私人化得以立足诗歌,在诗歌的表达空间中突出私人化的意义,成为潮流。至此,在公共生活与私人化之间、在公共空间与个体空间之间追求某种协调、互动,成为诗歌发展的常态。公共生活与公共化使诗歌得以高、大、上,使诗歌体验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宏伟;而个体空间的私人化使诗歌到达各处幽微私密的空间,无所不在。二者的协调、互动,使诗人的社会性与私人性完整地共存与展现,这样,诗歌的“止乎礼义”与“写心出中诚”,又合乎逻辑地构成诗歌内外两大标准,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程。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池雷鸣]
[收稿日期] 2016-04-25
2016-04-05
胡大雷(1950—),男,浙江宁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I206.34
A
1000-5072(2017)01-00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