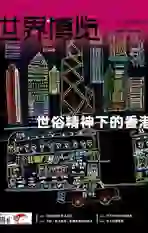抓捕光辉道路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
2017-11-07金·麦夸里
金·麦夸里
在安第斯山脉上,光辉道路的战士们会把那些可能与政府“同一战线”的农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用砍刀或尖刀把他们全杀死。他们最著名的死刑标志就是朝着脑后开枪或是从左到右彻底划开反对者的喉咙。
我在1986年第一次来到秘鲁首都利马,我乘坐的飞机于午夜时分降落在机场。当时正是光辉道路游击队战争最如火如荼的时候。秘鲁政府刚刚宣布首都实行宵禁,时间是从晚上10点持续到第二天早上5点。每到这段时间,城市的街道上都空无一人,只有偶尔驶过的军队巡逻车或突兀的坦克停在某个人行道的拐角。军车里坐的是戴着黑色滑雪面罩,举着M-1式步枪瞄准着街道的士兵。只有持有“安全行为”通行许可的平民才可以在宵禁时段内出行,否则将立即被逮捕。如果试图逃跑,警察和士兵通常会直接开枪。每天早上,薄雾笼罩着这座阴郁的城市,长长的太平洋海岸线上涌起层层的碎浪,利马的居民们起床后翻开报纸,一定会发现头版头条又是关于某辆载满了参加宴会归来的狂欢者的出租车,难免超过了宵禁的时间又没有通行许可,结果就是所有的车窗都被打碎,里面的乘客都已经身亡。这样的报道通常会附有现场照片,然而我读到的这些新闻里没有一辆车里的乘客真的是游击队队员。
到达利马的那一晚,我乘车从市外的机场穿过环绕着城市的一圈圈棚户区前往利马,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乘坐的小货车上插着一面白色的旗子,代表我们是有安全行为通行许可的。街上亮着黄色的路灯,我们能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他们都穿着暗绿色的军装,透过黑色面罩的眼洞紧紧盯着我们。佩戴面罩是为了避免被光辉道路的人认出而遭到报复,然而这样的装扮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在一座死城里巡逻的龙骑兵的幽灵。
“他们遇到什么都会开火,”坐在我身边的秘鲁中年人摇着头说,“因为他们害怕被袭击。”
他指的是被光辉道路游击队袭击。光辉道路是一个起源于安第斯山脉高海拔地区,并迅速向各个方向蔓延,覆盖了秘鲁大面积山地区域之后,又开始像迅速恶化的癌症一样向低海拔地区渗入的运动。游击队战争从1980年开始,最近光辉道路已经包围并渗透进秘鲁的终极目标——生活着三分之一秘鲁人口的首都利马。
整个利马会突然陷入一片黑暗
我到达的这个时候,秘鲁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正经历着类似《人体入侵者》(Invasion of the BodySnatchers)中的场景一般的生活。整个国家就像一个梦游者,不安地想要抵抗不断渗入的游击队运动,然而后者的藤蔓越来越紧地缠绕在这具已經受损的躯体上。他们破坏了高山上的电缆塔,让整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电力瘫痪。他们渐渐地把说盖丘亚语的平民全转变成了说盖丘亚语的游击队队员,还把政府的代表们——包括警察、市长和政治家——都“清算”了,而清算的办法就是朝他们头上开一枪。游击队正在慢慢地把构成秘鲁社会结构的一砖一瓦都替换成他们自己的。
随着光辉道路不断得势,秘鲁政府只得召开越来越绝望的会议来商讨应对之策,最终的办法就是把军队派到安第斯山脉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屠杀。军队使用强制、酷刑和恐惧作为武器,他们无法分辨出说盖丘亚语的农民和说盖丘亚语的游击队员,索性就把整个村庄的人赶尽杀绝。即便如此,“癌细胞”依然在持续扩散,光辉道路的袭击仍在继续,而且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复杂程度上都有所提升。他们袭击的地区范围也在不断扩展,政府的反游击队策略显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我在秘鲁的第一年,有很多个晚上整个利马会突然陷入一片黑暗,然后居民们会收到通知说一队游击队队员又炸毁了一个电缆塔。我很快就学会了像其他利马人一样储备足够的蜡烛,遇到断电就依靠烛光工作,过不了几个小时,电力肯定就会恢复。我像在利马生活的700万居民一样,遇到军事宵禁就留在房间内。偶尔几次迫不得已错过了宵禁时间,我也会非常小心地一直走在无人街道上的阴影中,直到安全返回家中为止。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几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光辉道路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或者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内战。虽然游击队四处设置爆炸装置,但他们很少公开发表什么声明。他们也不像其他游击队组织一样发布公告(communiques)。他们就只是一意孤行地采取行动,有选择地消灭那些妨碍了他们的人,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清楚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有时,鲜红的涂鸦会突然出现在城市和乡村的墙壁上,比如“发动群众战争!”或“秘鲁共产党万岁!”1980年光辉道路发动内战的那一天,利马一些居民早晨起床后竟然发现一些死狗的尸体被吊在路灯灯柱上。没人知道这是要传达什么信息,缠绕在绳子上缓慢转动的死狗似乎并不能预示出未来将会何去何从。
光辉道路最大的秘密之一就是他的创立人——曾经的哲学教授阿维马埃尔·古斯曼(Abimael Guzman)。他从1979年起就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了,但是他一直被怀疑就是秘鲁共产党和他们发动的内战的领导人。古斯曼肤色偏白、个子不高、体格结实,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有人说他藏在秘鲁的偏远地区,有人说他躲在邻近的其他国家。不过也有人相信他已经死了。这个运动中的其他成员也和古斯曼一样神秘,人们只知道他们似乎都说印加帝国曾经使用的古老的盖丘亚语,以及他们都来自安第斯山脉地区。
不过根据截获的文件,人们还是逐渐弄清了这个运动奉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源于本土的,而是毛泽东主义。一些被俘虏的光辉道路成员在受到酷刑折磨之后承认了他们秉承的是毛泽东主义战略和目标:先占领秘鲁的农村,然后包围并夺取城市。渐渐地,秘鲁的警察和军队都意识到,安第斯山脉中被政府宣布为紧急区域的地方越来越多,在城市里发生的袭击也越来越频繁,这个神秘的秘鲁毛派游击队活动的成员们早已进入了他们战略的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
截至1989年,我作为一名作家和人类学者已经在秘鲁工作了三年,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告诉了我秘鲁一个不便对外告知的秘密:有200多名光辉道路游击队队员被关押在利马的坎托格兰德监狱(Canto Grande prison)中。我的朋友还说,被关押的人员当中有男有女,他们已经破坏了监狱内部各个牢房的门锁,事实上控制了监狱内部的一些区域。我对游击队员越来越好奇,也想知道这个国家的前景如何,我确信只有到监狱里探视一些游击队队员才能获得对这个运动的更多认识。endprint
进入坎托格兰德监狱
1989年4月30日星期天,我来到了位于首都东北部破败的贫民窟附近的这间最高警戒级别的坎托格兰德监狱,所有访客都站在高墙之外排队等候。
“留神你要去的是哪个牢房”,等待时,队里的一位老者适时地提醒我,说着他还用手比划了一个扭绞戳刺的动作,那是被用刀袭击或抢劫的意思,说完他就走开了。监狱里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盗窃犯都被关在特定的区域内;光辉道路游击队队员则被认定为政治犯,被关在另外两个区域里。
共和国护卫穿着紫色的制服,头上戴着贝雷帽,脚上穿着皮质的丛林靴。他们在我的小臂上按了几个紫色和金色的圆形印戳,还有几个用墨水印上去的数字。我们这些排队的人被一个一个仔细搜查过之后,才终于进入了监狱的高墙,之后又经过了六个检查站才来到了关押犯人的八个牢房区域。每个区域有四层楼,所有区域连在一起围成一个半圆形。牢房有间隙很窄的栅栏和窗子,有些犯人会从栅栏中间伸出手臂,他们其中一些人就属于秘鲁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
每个牢房区域前站着两名守卫。他们的职责是记录进入牢房探视的人数并确认从牢房里出来的和进去探视的是同一批人。守卫的位置就是国家设立的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走进牢房之后,掌握控制权的人就变成了囚犯们。
由于囚犯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将牢房门锁破坏了,所以他们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区域里随意走动。狱警几乎从不进入这些区域内部,那里面也有严格的“丛林法则”:自制刀具、武器和毒品都很常见,帮派斗争和暴力导致的死亡事件更是时有发生。
光辉道路的成员是按照性别分别关在两个区域里的。此时此地我已经无法知道进入他们的牢房区域是不是比进入其他普通罪犯的牢房更安全。反正按照当地和国际媒体的说法,这种可能性不大。
美国的一份政治性杂志《民族报》称他们是“秘鲁的神秘杀手”。法国的《世界报》称其活动为“这片大陆上最狂热和最神秘的颠覆行动”。《美洲观察》甚至干脆称“光辉道路是整个西半球出现过的最残忍邪恶的游击队组织”。
1986年6月,光辉道路的囚犯在利马的三所不同的监狱中导演了一场同时进行的暴动。他们劫持了一些人质,但基本要求只是改善监狱环境。暴动选择的时机恰巧是一次国际性共产主义者会议的举办期间。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Alan Garcia)只与在押人员进行了简短的协商,就将问题移交给军方处理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大概算得上是所有监狱冲突解决办法中最残忍的一种。共有超过250名囚犯被杀,其中很多甚至是在投降之后被朝头部近距离开枪射杀的。暴动被镇压之后,少数幸存者被转移到了新建的最高警戒级别的坎托格兰德监狱中,不过他们仍然扬言要为被屠杀的囚犯们报仇:一个囚犯的死,要由十个政府官员来赔。我此时走进的就是这座坎托格兰德监狱。
来探视的人员必须提供确切的被探视人姓名。我询问了一位监狱的托管人并且获得了一名女囚犯的姓名。两个守卫打开了关押女性光辉道路战士的牢房区域大门,我走进去之后,金属大门又在我身后被锁上了。
三个最弱势的群体:印第安人、女性和年轻人
走进牢房区域后,我发现这里的空间十分巨大,天花板上有混凝土梁架。每根梁架上都贴着红色的标语。一个写着“欢迎来到明亮的坎托格兰德战壕!”另一个写着“秘鲁共产党万岁!”整个房间里还装饰着许多红色的三角旗,每面旗子上都有白色的斧子和镰刀的图案。很多年轻的女子在四处随意活动,她们全部都有黑色的眼睛和头发。
这些女性就是光辉道路招募策略成功的体现:在一个阶级意识突出的社会里,光辉道路为三个最弱势的群体——印第安人、女性和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摆脱地区性也经常是宿命论式的贫穷的出路,只不过这同时也是一条暴力之路。据估计,秘鲁全国人口为2100万,武装的光辉道路游击队队员有2000~5000名,其中75%的队员年龄在25岁以下,至少25%的队员是女性。
从传统上来说,光辉道路依靠的是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上贫困的当地农民的支持。这些说盖丘亚语的农民都是印加帝国的后裔。自从西班牙人征服这里之后,这些农民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一直受到剥削,靠在仅有的一点点土地上耕种来勉强维持生计。在安第斯山脉上很多地方,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9岁。大多数安第斯村庄中识字的人只占50%,对于自来水、供电和医疗服务更是闻所未闻。
很多观察者都认同,过去500年中的西方式“进步”只是进一步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更是成为一片第三世界国家包围中的第四世界,无怪乎这里会成为光辉道路运动的誕生地和根据地。
20世纪70年代,光辉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它为那些被忽视、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穷人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生存之道(即武装斗争)和一种新的远大前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将秘鲁看作革命之前的中国:一个半封建的殖民地国家,这里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是在为那些恶名昭彰的非印第安精英群体创造财富。
都市与乡村,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北部和“受剥削”的落后的南部之间的财富分配越来越向两极化发展,这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光辉道路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耐心的劝导和说服工作。56岁的秘鲁哲学教授古斯曼在1970年发起了这个运动,运动的宗旨是创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并建立受到农民支持的农村根据地。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他们就会依据毛泽东在中国的成功战略将运动推进到第二阶段,即先占领农村,最终包围并夺取城市。
1980年,古斯曼曾主持了一次光辉道路的委员会议,为了这个特殊的场合,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贡萨洛同志(Comrade Gonzalo,这个名字来源于日耳曼语中的“Gundisalvo”,意思是“斗争的天才”)。在会议上,贡萨洛宣布党已经做好了“推翻城墙,迎接黎明”的准备。推翻“资本主义”秘鲁的战争就此打响了。endprint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拯救我们
在坎托格兰德监狱内,到处都是混血女子和悬挂的红旗。我站在牢房区域内等候,直到一位年长的女性微笑着朝我走来。这位女士的头发已经斑白,向后梳起在脑后盘了一个发髻。她穿着运动衣和长裙,看上去就像一位邻家祖母,实际上她是秘鲁最伟大的记者之一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的遗孀。阿格达斯出生于城市,他的父母是混血(mestizo),但是他从小是由说盖丘亚语的女仆带大的。1969年时阿格达斯自杀身亡。很多人将他的自杀归因于无法协调安第斯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至今仍然令秘鲁深受其害的问题。他的遗孀西维拉·阿雷东多被怀疑是利马郊区游击队的领导之一。
“下午好,”她愉快地向我打招呼,“你想探视谁?”
我告诉她我希望能和党代表谈谈;她点点头,于是我跟着她走出了这个房间。这里关着的都是一些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出头的年轻印第安姑娘,她们大多来自安第斯山脉地區,我经过的时候,她们都带着好奇的眼光盯着我瞧,有些还会羞涩地朝我微笑。
房间外面是一个很大的水泥院子,至少有1000平方英尺,周围是高耸的监狱砖墙。光辉道路战士们在院子里十字交叉着悬挂起长长的红色横幅。院子正中有一根姑且作为旗杆的木棍,上面系着一面巨大的有白色斧头和镰刀图案的红色旗帜,它偶尔会随着微风缓缓飘动。
四周的高墙上都写着醒目的标语:发动群众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拯救我们!
唯一的形式——群众战争!
唯一能领导我们的党——共产党!“你要坐会儿吗?”阿格达斯的遗孀友善地问我。于是我在两个“党代表”旁边的一个水泥矮墩上坐了下来。一个年轻的光辉道路战士很快给我们送来了果汁饮料,阿格达斯的遗孀也礼貌地离开了。
我对这两名妇女说我想问她们一些关于政治理念、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她们微笑着点点头,但是她们想先听听我对于进入监狱后看到的一切有怎样的看法。我看看周围这些穿戴整齐的妇女们,随处可见的旗帜和标语,仔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再想想其他牢房区域内透过窄窄的栅栏盯着我的普通罪犯的脸,我坦白地告诉她们,我稍微放心了一些。
事实上,看看监狱里的这些妇女,我实在很难把她们和光辉道路的那些举世闻名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在安第斯山脉上,光辉道路的战士们会把那些可能与政府“同一战线”的农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用砍刀或尖刀把他们全杀死。他们最著名的死刑标志就是朝着脑后开枪或是从左到右彻底划开反对者的喉咙。
我看着这两位代表,她们都是二十多岁,有棕色的皮肤和接近杏仁形状的黑色眼睛,她们都耐心地向前倾身细听,脸上也挂着礼貌的微笑。
“为什么是政府官员?”我问,“为什么要杀他们?”
她俩其中一人这样回答:“夺取政权的方式就是摧毁政府的纵向层级制度。我们袭击的就是这个制度结构。”另一个人也向前探身对我说:“看看牛奶的价格已经涨到多高了,官员们的性命毫无价值。”
这两名妇女的回答恰恰体现了光辉道路战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极端的。依据光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世界观,人类被严格地划分为农民、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如果一个人被贴上资本家的标签,那么他就是剥削人民的人——在极贫困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一个人哪怕拥有几头奶牛或是雇用几个帮手就会被认定为资本家——就应当受到无情的讯问和审判,然后被处以死刑。
另一个最常见的光辉道路袭击目标就是安全部队的成员,比如公民警卫队队员。这些公民警卫通常是年轻的混血男子,他们的工资其实很低,还要养活老婆和孩子。就在不久之前,在安第斯山脉一个叫万卡约的镇子上,几个姑娘主动跟河边站岗的两个公民警卫热情攀谈。在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之后,两个男人从背后突然冲上来,直接朝两个公民警卫脑后近距离地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一个公民警卫倒下前还死死抓住了岸边的一根杆子,而那两个跟他们调情的姑娘,实际上也是光辉道路战士,则飞快地拿走了公民警卫的手枪,然后逃跑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