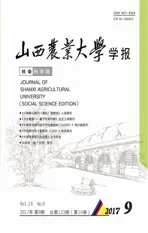农村精英的回归与转化对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若干个案的分析
2017-09-22郭占锋吴丽娟
郭占锋,吴丽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农村精英的回归与转化对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若干个案的分析
郭占锋,吴丽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外流精英逐渐回归农村,他们为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资源。对陕西省若干村庄回归精英的访谈资料表明,乡土情结的吸引力及城市机会的排斥力,二者的结合促使外流精英“归根”与“淘汰”,回归农村。回归精英主要通过家族资源和自致资源,通过示范性和权威性的形成建立声望,从而获取信任,转化为政治精英,为社区谋发展。他们在农村建设方面与普通精英存在共性,同时又具备个性差异。
农村精英; 回归机制; 转化机制; 个性贡献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度推进,中国农村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催生出农村结构空心化、农村留守人群以及失地农民等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进行农村治理,如何定位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广为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而研究此类问题必然离不开对农村本身所具有资源的梳理,农村精英是其中举足轻重的资源之一。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扮演着精英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精英逐渐演化为在农村社会发展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群体,他们活跃在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精英的分化日益明显,陆学艺把农村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1]。金太军把农村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2]。学界对农村政治精英地位与功能的研究理论可以总结为:“双轨政治”、“士绅操纵”、“经纪体制”、“主人——代理人”理论、“边际人”理论、“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庇护关系”理论等[3]。强调农村政治精英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中介,起到缓冲国家权威的压力、保护地方民众地位的作用。农村经济精英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起到技术示范作用,可以带动村庄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并进一步带来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村域经济的发展[4]。他们是农村发展的“领头人”和“经营者”[5-6]。农村文化精英则主要在农村的传统风俗习惯、解决农民纠纷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7]。可见,农村精英的作用渗透于乡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然而,精英的不断流失也是农村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李培林认为“农村精英的流失历史上自古有之,但却因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加剧了[8]”。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的农民或创办乡镇企业、贩运经商,或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他们绝大部分是村庄的青壮年人群和精英阶层。精英流动为乡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割裂了村庄的精英资源,对农村整体的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组织建设、文化承袭等都产生负面影响[9],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质量和绩效,导致乡村社会自我更新、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缓慢甚至停滞[10]。近些年,部分流出精英逐渐回归农村,并在村两委中担任职位。谢秋运把这类人称为“城归”精英,即“一些村庄成员在村外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返回乡村社会,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资源,诸如经济资源、知识技能等,通过竞争选举走上村庄政治舞台,成为掌握村级公共权力的核心人物[11]”。这些“城归”精英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资源。然而纵观已有研究,以案例为基础,对精英的回归机制和转化机制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对陕南漫川关镇,陕北延安川口乡、榆林三村,咸阳市旬邑县马栏镇等地区的若干回归精英进行访谈,旨在对农村精英的回归机制和转化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精英的回归与转化对农村社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归根与淘汰:农村精英的回归机制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单向转移的“民工潮”现象,使得农村社区的发展愈显没落。“农村精英外流是民工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流精英则更有可能因其在城市职业的固定化而产生从农村流失的现象[12]。”精英流失是在利益导向下农民在土地附加值与务工收入、农村生活现状与城市容纳力等方面双重博弈的结果。随着精英的流失,诸多农村陷入空心化、老龄化、妇孺化的困境,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然而,事实上,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从2000年左右开始,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开始回流,其中包括部分外流的农村精英,他们逐渐回到村庄参与新农村建设。除去政策导向因素,如图1所示,从农民自身的原因出发,回归乡村是“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从外界因素来看,则是由于农村精英在城市中没有找寻到安身立命之本,被城市所淘汰。

图1 农村精英的回归机制
“乡土意识是指农民对于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乡村生活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依恋心理[13]。”农村特有的乡土性吸引着流出精英返乡,随着早期外流精英的年龄渐长,潜在的乡土意识上升为一种乡土情结,他们的家庭和生存印迹在农村,这种归属感吸引着他们回到农村“归根”。如个案1中的村长苏某,早年在外务工近20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家庭和村庄的依赖愈加明显,乡土认同感有增无减,归根的意识也愈浓。
个案1:榆林市南丰寨村村长苏某,男,64岁,小学文化程度。在1992年前后离开南丰寨外出务工,2010年返回南丰寨村,2012年当选为村长。“当时是条件越好的人越不会外出,条件差的才会出去。我们南丰寨离镇上比较近,条件比较好,所以出去的人不多。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特别差,我才会出去的。出去以后什么都做,都是苦力活。就在周边几个县城打工,最远只到榆林。后来年龄越来越大了,家还在这里,就回来了。现在年轻人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逢年过节还是会回来,红白喜事也基本会回来参加,毕竟挣够了钱,最后都是要回来的。”
农村精英外出务工多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在城市中寻求机会改变自身与同村人或者城市居民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然而,在人才更新换代迅速的城市地区,只有极少数农村精英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在城市中有稳定的工作并安家,脱离农村。大多数农村精英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生活不稳定,他们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城市亦对他们没有长效的容纳力,他们不得不面对被城市淘汰的命运。如个案2中的会计李某,因为学历与工龄的原因在体制改革时被淘汰,迫于无奈回到农村。农村精英分子在城市里主要属于次属劳动力市场,长期总体上被划入“底层精英”行列,在社会分层上遭受“集体排他”的际遇,缺乏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14]。
个案2:董家湾村前村委会会计李某,男,65岁,小学文化程度。1998年之前在榆林供销社工作,1999年供销社改制时因工龄不够而回到董家湾村务农。“我以前在供销社工作,算账比较在行,所以村民选我做村里的会计。以前总想着可以留在城里,没想到制度一变,自己就被辞退了。”“现在村里搬到榆林市的人很多,只要有钱就不回来了,暂时出去打工的每年会回来几次。”
农村精英的回流可以看做是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主要体现在:自身心理发展和家庭需要的内在因素构成农村精英的乡土情结,城市排斥和村民选举的外在因素构成农村精英的回归渠道,这二者的双重作用促使精英回流。然而可以发现,在此机制下回归的农村精英普遍存在年龄大、学历低的特点,与普通农民相比,他们仅仅存在阅历更多,经验更广,能力较出众的优势。尽管农村精英的回归充满着被动的意味,且并不是绝对优质的回归,但是也契合了农民的心理需要,对农村社区的发展意义深远。
二、资源与声望:农村回归精英转化机制
外流精英回归农村后,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他们多是从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或者由普通农民在经过“外流”与“回归”的包装后转变为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旷宗仁、杨萍认为精英的本质属性是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 而其社会属性则是能够作为村民的榜样和模范, 给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15]。促成他们转化的条件则是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家族资源和通过自致性努力获得的经济资源,以及由于其财富的示范性和年龄所赋予的权威性给他们带来的声望。通过资源和声望的双重推力,回归精英获得村民的信任,进而通过选举的渠道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

图2 农村回归精英的转化机制
回归精英的转化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利益的需求,或谋求更可靠的经济利益,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村民将回归精英推向“台前”。除去因为自己的父辈或亲朋曾经是村干部,为少部分回归精英的转化提供了家族资源外,大多数回归精英与普通村民相比,在外务工的经验为他们的转化增色不少,务工的经历让他们拥有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也锻炼了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如个案3的高某,在外近二十年的务工经历使其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和经济资源。通过自致性的努力,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积累,这成为他们转化无可替代的资源。
个案3:榆林市子洲县苗家坪镇董家湾村书记高某,男,52岁,小学文化程度。高某从1984年开始外出跑运输,去过定边、石家庄、内蒙古等城市,2004年返回董家湾村担任书记。村民张某说:“他并不是主动要求当这个书记的,我们都认为他有这个能力,纷纷劝他担任这一职务,并且他自己也有为这个村子做出一点贡献的想法,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好的村干部。村委会修建的时候书记垫了很多钱,也没有让大家平摊。他找政府部门还有其他在外经商的村民共同投资,像村庄道路硬化、绿化、路灯、村口风景区等等都是现任书记上任后修的。”
村民普遍认为村庄治理的权力核心是村长或村书记。而村长或书记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他所处的位置赋予他的本身的权力,还源自于他在村民间的声望以及他本身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即为村庄争取资源项目的能力和其人际关系网络。村民的个人利益与村庄的整体利益是相互捆绑的,村干部通过实现村庄的整体利益而完成了自身与村民个人利益的捆绑,换言之,形成了村民的共同意愿,即支持村干部就会实现自身利益,村民对村干部产生依赖。由此,村干部的声望提高,村干部的声望越高,共同意愿越强,村干部与村民间联结的纽带越牢固,他所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多。
个案4:陕西省延安市川口乡刘渠村书记崔某,男,大专学历,58岁,连续担任村长和书记34年。崔某并不是单纯的政治精英,在80—90年代的中国农村,大专学历的他属于文化精英,24岁成为村长之后响应国家号召退耕还林,引进技术种果树,通路通电,为村庄建设做出诸多贡献。1994年,他认为“村子要发展,就得自己出去看看”,于是便赴延安市做建设工程,逐渐形成一家企业,并带动村民包工程。随后,崔某返回村庄担任支部书记,继续为村庄的建设做贡献,而他也鼓励村民走出去,“人出去了,才会给村子带来新的技术,新的东西”。
通过个案4可以发现,转化的精英多为复合型精英。村干部本身即为经济基础较强或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并非单一类型的精英,而是经济、政治或者文化的复合型精英。他们的声望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通过文化资源获得优势,再者通过在村庄建设中身先士卒的示范作用,以及以身示范的模范致富作用逐渐形成自己的权威,加之通过为村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以及年龄与阅历的增加,使村民对其产生一种依赖和信赖,成为自己声望的可靠来源。
农村精英的转化可以由普通农民转化为政治精英,由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由单一精英转化为复合型精英。回归农村精英的转化基本不依靠本土资源,而是通过在外务工时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经济资源等外界资源发展自身,回村后成功实现身份的转化。同时,通过资源累积建立起来的声望,让他们可以在转化之后拥有权力与权威,全方位影响村庄的建设。
三、共性与个性:回归精英的带动作用
农村精英的转换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都产生了影响[16]。在人才普遍外流的背景下,回归精英与普通农村精英一样,在农村的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同时,由于是回归精英,他们在建设农村社区的时候会有意加入自己在外的生活阅历,通过借鉴别的地方的经验,促进新农村更好发展。
与大多数村庄的政治精英一样,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马栏镇后义阳村的政治精英致力于新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1997—1999年期间,以焦志宽为代表的回归精英与留守精英响应新农村建设的号召,首先对整个村庄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并做了一些宣传以及村民的思想工作,为接下来的正式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3-2004年期间,以焦海民为代表的第四届回归精英和原有精英发动村民建设了文化广场,并且对整个村庄进行了绿化,修建水泥路。2006年,新建村委会办公场所七间,村办小学教室15间,教师宿办用房6间。2007年继续完善村小学建设,修建了围墙、厕所和校园绿化美化工程。村委会、学校、以及旧村改造一共耗资300多万,而国家投资不足50万,余下的钱都是第四代村干部以卖地收租金、运用资源筹集资金等形式凑来的。可以发现,后义阳村的发展主要依托这一群政治精英的领导。
传统农村精英在村庄管理中扮演守护者和传达员的角色,他们的工作就在于保证村庄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冲击,比如征地时代表村民与外来利益进行谈判,同时他们需要将国家的意志传达到最基层,比如最新政治思想的宣传、政府惠民项目的争取等等。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治理村庄,村庄只是按照自有的逻辑和规则运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农村精英管理者的角色更显重要,他们主导着农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因此,农村精英自身的能力因素制约着其对村庄产生的影响。如个案5所述,回归精英因其特殊的务工背景,在农村的发展与规划中视野更为开阔,更具现代化意识。
个案5:陕西省延安市王庄村村主任王某,39岁,中专学历,1998年离开村庄在外务工,2013年他回到村庄,被村民选举为村主任。“我之所以回来,是想给村庄带来新的变化,实现自己的抱负,带动村民探索出一条致富的道路。”由于在外务工期间接触社会较多,王某的思想较为活跃,并将这些思想融入到自己对村庄规划的想法之中。以土地流转为例,王某通过借鉴袁家村的成功经验以及利用王庄村210国道横穿的先天条件,把村庄限制的土地加以利用,引进大棚产业,种植反季节蔬菜,发展农家乐,以改变村庄产业单一的现状。“如果实行土地流转、果树流转,一方面可以让想出去打工的人有时间和精力出去,另一方面,让掌握果树蔬菜种植技术的村民有机会将种植面积扩大,既便于管理,又利于增收。”而他也认为:“村民不离开村子很难接触到新的东西,只有出去了才可以慢慢转变观念。”
回归精英与普通农村精英阶层在对村庄影响方面存在共性,即他们转化之后首要的事情是对村庄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改造。但是他们与普通农村精英阶层相比,又存在个性,即个人经历的丰富,以及经济基础的牢固,社会网络关系的丰富将开阔他们建设乡村的眼界和思维,使新农村的建设更具可行性。
四、结论与讨论
外流的农村精英逐渐回归农村,于农村而言利大于弊。不论是由于“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还是被城市所淘汰的生活曲折,“外流”就如同“出国”一样,为这些农民镀上一层金,而“回归”如同“海龟”一样,使他们拥有其他人没有的资源和声望,让他们更易于在农村社区中转化为政治精英。而他们也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一角色,为自己的发展,为乡村的发展谋取福利。
农村回归精英早年经历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曾外出务工,并且绝大多数在50岁以后选择回到村庄,这就意味着多数回归精英的年龄在50—65岁之间,虽然算不上年富力强,但仍有余力来管理村庄。同时,这也是村庄“空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另外,从各个方面来看,农村精英群体内部同质性较强。比如,这些农村精英是村庄中掌握有较多资源和声望的群体;他们的权力来源不仅是体制赋予的显性的职权,还有村民对他们的依赖及信任这种隐性的权力。
在村庄治理中,乡村政治精英是治理核心。要建立村民对领导核心的依赖更多取决于该核心的自身资源的多寡而非其外在具有的职权。在农村精英回归并转化为村庄治理核心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新的共同意识来将每一个个体连接,这就不得不依托于其特殊的资源与声望。农村精英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和观念作为一种资源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凭借这两点,他们可以为村庄争取资源,帮助村庄发展。在现有的村庄结构中,农村回归精英是拥有较多资源和威望的人,他们的权力更具合法性,在这一领域也更容易有所作为。
然而,不难发现回归精英在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存在角色冲突。许多农村回归精英在社会中都扮演着多种多样的角色,他们不仅仅转化为政治精英,也是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承担每一个角色的要求和能力都不同,这就很有可能产生角色冲突,使得回归精英往往难以平衡他的各种角色,多重角色冲突引起的角色扮演失败,往往阻碍着乡村治理和村庄建设的发展。
[1]陆学艺.内发的村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71.
[2]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105-114.
[3]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0(3):101-108.
[4]陈莉,左停.农村经济精英与村域发展[J].乡镇经济,2008(11):74-79.
[5]刘德忠.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经济精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6(4):23-29.
[6]郑明怀.农村经济精英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和意愿探析[J].农业考古,2011(6):39-41.
[7]张润君,刘红旭.村庄精英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以甘肃定西市Z村婚嫁丧葬仪式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1):108-112.
[8]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4.
[9]任敏.流出精英与农村发展[J].青年研究,2003(4):8-12.
[10]林修果,谢秋运.“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23-28.
[11]谢秋运.走上乡村政治前台的“城归”精英[J].社会,2002(2):41-43.
[12]张英魁.农村精英人才流失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再造的路径选择[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2):6-10.
[13]邢克鑫.农民乡土意识的历史嬗变与思考[J].学习论坛,2001(3):18-19.
[14]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4-142.
[15]旷宗仁,杨萍.乡村精英与农村发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5-49.
[16]刘路军,樊志民.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15(2):109-113.
(编辑:程俐萍)
Studyontheinfluenceofruralelite'sreturnandtransformationonthecommunitydevelopment
Guo Zhanfeng, Wu Lijuan
(CollegeofHumanities&SocialDevelop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712100,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exodus elite gradually return to rural areas, and they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The interviews from several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show that the attraction of the local complex and the city's rejection promote the elite return to rural area. The returned elite transformed into the political elite through family resources and self-made resources and the reputation establishment by their demonstration and authority. They hav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 the ordinary elite in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elite; Return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C912.82
:A
:1671-816X(2017)09-0001-05
2017-05-10
郭占锋(1977-),男(汉),陕西彬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与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2017年度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7C062);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项目(2016RWYB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