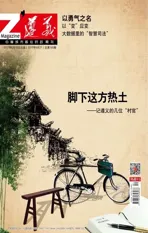民国才女凌淑华
2017-06-22文丨
文丨 琼 娱
民国才女凌淑华
文丨 琼 娱
“埋首书卷,曾几度梦回民国,最惹人迷恋处,莫过于那一群女子。她们生如夏花,淡雅婉丽,却比烟花寂寞;她们温润如玉,爱恨倾城,却难免幽闺自怜。她们风华绝代,芳心悠悠,却一路颠沛流离……凌叔华就是这样的女子。”80后作家欧阳德彬如此形容民国女作家凌叔华。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凌叔华的个性和故事显然都不够重口味。至于文学上的成就,在文采斐然的民国,很容易就被几位领袖人物掩盖过去。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她是民国女作家的一个独特存在,实在不能轻易绕过去。

凌叔华和陈西滢新婚照
大宅门里的生活
1900年,在北京史家胡同的一个富贵人家宅院里,一个小女孩降生了,此后,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她凭借自身的才华成为一代名媛;90年后,经历过战乱流离,并在异乡漂泊多年之后,这位女子重新回到出生的宅院,在这里安详地走完了一生。
这个宅院就是史家胡同24号,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座胡同博物馆。
这里便是凌叔华的故居,也是她出生的凌家大宅的后花园。凌家大宅是一座有99间房子的豪华院落,前门朝着干面胡同,后院相接史家胡同,凌叔华26岁出嫁时父亲把这座有28间房子的后花园给女儿做了陪嫁。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1895年和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名字被列于北京孔庙的石碑上,这资历使他得以进入翰林院任职。他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等要职。凌叔华是凌福彭与第三房姨太太李若兰的第三个孩子,家中共有15个孩子,她排第十。
从凌叔华的作品中,可以窥探到她在这座宅院中度过的童年生活中,有很多快乐的记忆。她的父亲饱读诗书,爱好绘画,家中文人墨客、丹青雅士络绎不绝。凌叔华7岁开始拜师学画,老师是著名的画家王竹林和宫廷女画师缪素筠,而父亲请来教授凌叔华古诗和英文的是被称为“清末怪杰”的学者辜鸿铭。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20年代,史家胡同24号院门口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的很多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名人。因为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小姐家的大书房”的沙龙聚会,汇集京华名流,沙龙的女主人便是凌叔华。
凌叔华很早就显露出写作和绘画方面的才华,这使父亲把她看作掌上明珠。凌宅是京城文化名家经常聚会的场所之一,20岁出头的凌叔华很快成为聚会中引人注目的女孩。
1923年凌宅的一场书画名家的聚会盛况空前,“小姐家的大书房”因此名动京华,它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早了近10年。
那时,凌叔华在燕京大学读书,大半时间花在书画上,父亲介绍她认识了收藏家吴静庵的夫人江南萍,在江南萍的画室中她结识了陈半丁、齐白石等名家。1923年,凌叔华和江南萍以苏东坡诞辰886年为由,在凌家大宅组织了一次聚会,齐白石、陈衡恪、陈半丁、王梦白等著名国画家都参加了,还邀请了美国女画家玛丽•奥古斯塔•马里金。当天,众大师合作一幅《九秋图》,成为凌叔华的珍藏之作。
后来,马里金把这次聚会写进文章《在中国的一次艺术家聚会》,她提到聚会的主人凌叔华,“是位很有才华的画家,她贤淑文静,不指手画脚,也不自以为是,客人有需要时她就恰到好处地出现,说起话来让人如沐春风。”
凌叔华在《回忆一个画会和几个老画家》一文中也提及布置这次聚会的情景:“北窗玻璃擦得清澈如水,窗下一张大楠木书桌也擦得光洁如镜,墙角花架上摆了几盆初开的水仙,一株朱砂梅,一盆玉兰,室中间炉火暖烘烘地烘出花香,烘着茶香……”
“小姐家的大书房”光临过很多名人,包括印度诗人泰戈尔。那是1924年,泰戈尔到北京访问,住在史家胡同的西方公寓,北大负责招待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陈西滢,几个人一起受邀来到书房举办“北京画会”。
这段日子,似乎是凌叔华最快乐的一段人生,回忆文字中充满了闲情逸致,也让人从中领略民国时代的文化风气与名士风流。正是从这一时期,她开始创作并发表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新月派”最主要的小说家。
在物是人非的史家胡同24号院里,遥想凌叔华很多小说中关于这里的描写,眼前似乎百年前的情景重现。这所宅院是凌叔华小说创作的源泉,因为这是她生长的环境,里面生活着她最熟悉的人,她记录下这里的快乐美好以及高墙里的无奈和悲哀。
文学之路
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后便有志于写作,当时,她给到燕京大学讲授“新文学”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誓旦旦地说:“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1924年,凌叔华在《晨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此后写作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古韵》等多部小说,从这些小说中,习惯于“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凌叔华难得地展露出她的内心世界。
凌叔华的创作源泉是她自身的独特经历,是北京大宅门中不为人知的生活。她作为父亲第三位太太所生的三女儿和大家庭中众多姐妹中的“十姑娘”,她对大家庭妻妾子女间的纷繁扰攘,闺阁绣帏中的风云变幻,自小体验独深。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评价凌叔华的小说作品“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沈从文认为凌叔华的小说是“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的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
燕倩是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中的女子,她扮作丈夫的情人和丈夫约会,调皮地向丈夫发问:“……我就不明白你们男人的思想,为什么同外面的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对自己的夫人讲,便没意思了?……”这样的发问让男人无地自容。燕倩为追求爱情主动出击,展示了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体现了“五四”以来现代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燕倩开始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并对男性特权质疑和颠覆,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动和觉醒。
《春天》中的霄音在凄恻的音乐中忐忑不安,“……唉,不晓得怎回事,这样天色,使得你在屋里不是,出去又不是,浑身不对劲儿。”“她不满意这支曲子,她恨那个作谱的人。”“她的心空得难过。”因为这勾起了她不愿想起的往事。她流着眼泪读着远方男人的来信。那个男人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曾经深深地迷恋着她。她决定坐下来回信,可是刚写了一行,丈夫回来了。此时,她抓起信纸揉成团子,用来擦拭桌上的水。显然,她对远方男人的感情让位于妻子角色。虽然霄音没能完成回信,但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内心的挣扎,听到闺中少妇女性意识压抑的呜咽。她对爱情有着美好的憧憬,婚姻却剥夺了她享受被爱的权利,心灵仍然束缚在封建的旧道德中。凌叔华以幽默机智的笔触,描绘出了游荡于新旧道德之间的知识女性的尴尬。
诚如鲁迅所言:“……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即使间或有出轨之作,那是为偶受文酒只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到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决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凌叔华在“五四”时期走出闺门,开始以崭新的眼光审视周遭世界。她与生活优裕、高扬“爱的哲学”的冰心,以及沉迷自我、以“恨的哲学”著称的庐隐截然不同。她以细腻别致的笔触,深入中国女性的内心深处,写出了那些独特女子的心潮起伏。在这一点上,凌叔华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无疑比单纯的爱恨情仇更具艺术高度。
凌叔华小说典雅秀丽,被称为“闺阁派”。但是从她某些作品,例如使凌叔华成名的《酒后》和被胡适赞扬备至的那篇《上元夜》来看,她对人生的激情,尤其毁灭性的激情,很有体验。可能由于富家小姐出生,“教养”太严,她的个性一时被遮蔽而已。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恋情让她发现了自我,也不能说绝对是坏事。可惜30年代中期,凌叔华创作已经停笔,一心临摹宋元古画,陶冶性情。
在陈学勇的《论凌叔华小说创作》中,将凌叔华的创作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细细点评,得出了一个结论:综观凌叔华小说创作,她以不容忽视的成就垂名中国现代文学史。它们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经验,也折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政治理想、文学观念。凌叔华堪称“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的重要作家。贯串先后接连出现的这三个文学流派,并且是每一个流派的代表,只有凌叔华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