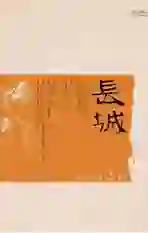贬抑与狂欢
2017-06-01李姝
李姝
在以中国当代作家的“流氓书写”为视点,进行文学形象的梳理与打捞之前,有必要对“流氓”进行一个界定。从广义的词源学角度来看,流氓指居所不定的流浪者。《中文大辞典》中指出:“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可视为对流氓的狭义定义。历史学、民俗学学者完颜绍元在《流氓的变迁》中将“流氓”一词界定为“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更侧重流氓的社会学意涵。本文将要探讨的“流氓书写”取狭义的“流氓”概念,意在考察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作家如何进行“流氓书写”,从而呈现文化价值体系内的思想逻辑、文化心理和生存哲学。
在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前二十七年,对流氓的书写,主要表现在无产者或敌对阶级的不良行径特别是性行为上,人物形象以政治流氓、市井流氓为主;新时期文学中,流氓形象的道德定义逐渐淡化,人性之恶被深入挖掘,文化流氓形象涌现,流氓书写得到了脱敏和狂欢,“流氓”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心理和美学风格。以当代作家流氓书写为视点,考察文学叙述中錯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更具有福柯所说的“讲述话语的时代”的意义。
阶级符码:宏大叙事下的流氓书写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以宏大叙事的概念来把握叙事与知识的关系,可以提供一个关照“十七年”文学的视角。在流氓无赖形象的书写上,作家试图建构一种新政权宏大叙事的总体性、进步性,以党和国家代言人的身份和姿态,为流氓形象包裹一个阶级属性外壳,作为贬抑或改造的对象。
《创业史》是一部想象并展现新生政权革命热情和历史激情的作品,梁生宝“入党-认父”的政治“成人仪式”可以看作入伙仪式经意识形态淬火后的合法化、光荣化。姚世杰是一个富农,一个破坏互助合作的坏分子。考虑到民间的文学接受,政治道德化符合民间伦理中重道德的部分,也是流氓书写得以实现的前提。作者只能把姚世杰的流氓话语和强奸行为放在宏大叙事消灭阶级敌人的话语框架内,才安全合法。而肉欲书写又暗合了民间文化心态,具有官能刺激作用。类似的还有冯德英“三花”系列《迎春花》中孙若西对淑娴的诱奸、孙承祖冒充独臂英雄江水山,强奸进军属桂花屋里,并栽赃嫁祸给江水山的情节。性暴力的书写必须和阶级仇恨粘合在一起,这就是流氓话语的生成机制。
在“十七年”文学回顾新生政权的历史时,几乎从不缺席“牺牲”一词,在“三红一创”等红色经典文学中,作家把含有“流血、暴力、杀”等流氓语汇改装写成“牺牲、殉国”的国家主义话语,进入左翼文学之后新一轮的宏大叙事浪潮。
文革时期,柳青面临政治压力不得不对初版《创业史》的性书写进行删改。这几乎是一代作家的尴尬命运。与此相对的是,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将坏分子的流氓行径进行了放大和消费。如赵振开《波动》中流氓头目白华蛮横地侵占了小四的身体,像对待物品一样视为己有,最终又像对待物品一样交于他人,无不是民间伦理中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身体想象和欲望表达。
《芙蓉镇》中的王秋赦是一个流氓无产者“运动根子”的形象,随时势而动,获得了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土改时期看守浮财,王秋赦像阿Q一样,“一头栽进象牙床”,和地主的小姨太太寻欢。他的三个外号就揭示了其无赖特质。据《当代》的老编辑龙世辉回忆,王秋赦这一形象在《芙蓉镇》初稿中并不存在。古华的原本设计是黎满庚从一个正直的军人转变成一个投靠了当权者李国香的狗腿。编辑部认为这一转折在艺术上不免牵强,读者无法接受。于是就从黎满庚形象中单拎出来,便有了流氓无耻的王秋赦。在这里,流氓书写的主要限制不再是国家意志政治施压,而是艺术规律和读者接受。
王秋赦这类政治投机分子在伤痕、反思文学中十分常见,其革命性本质上是一种封建主义和流氓主义,打着革命旗号做违背革命初衷的恶行。王秋赦构成了极左思潮最基础的恶势力,最后又悲哀地成了极左路线的牺牲者。《芙蓉镇》触及了革命、历史与个体的悖反关系的命题,这与先锋文学相似。
人性探索:现代性命题下的流氓叙事
如果说,前二十七年文学,当代作家在书写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对流氓话语还处于一个贬抑、阉割的状态,那么在《芙蓉镇》中,已有所缓释;在《古船》《米》等深入历史和人性腹地的作品中,则更显示出流氓书写的脱敏状态。
伴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文学创作被置于一个突出的现代性命题中。在《古船》中,老庙烧毁、三桅船搁浅、城垛坍塌,几乎是现代性入侵的强势符码。在洼狸镇的现代化过程中,赵多多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经济头脑迅速成为每个历史阶段的先锋。孤儿身份、一穷二白,在土匪教唆中成长起来的赵多多,对含章图谋不轨时,将自身的流氓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迅速嫁接——“资产阶级小姐就是臭美,嘿嘿嘿”,“你还跑?革命人民一下就能把你干倒”等等。张炜在叙述上省检克制,读者大可以想象赵多多那副猥琐阴险又道貌岸然的表情。在担任民兵团长时,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脱光了衣服,放到一个土堆上冻了半夜”,并用香烟烫他们的下部。面对反抗的麻脸,赵多多麻利地将“麻脸的脑壳给砍碎了半块”。在隋家媳妇茴子濒死之际,当着隋抱朴的面,对茴子施暴。和王秋赦一样,流氓小丑最终只能走向主体身份的丧失——精神失常。赵多多的结局是张炜试图解决现代性焦虑的方法。新时期流氓叙事的正常化书写,既是国内思想解放、政治松绑之后作家对历史的真诚反思,也是对现代性命题的冷峻审视。
在先锋文学实验中,流氓形象抽空了政治身份,获得了具有人性深度的书写。《活着》中富贵从无赖败家子在历史和命运的激流中升华成一个和蔼温情的平民,《许三观卖血记》是对市井流氓的弱智化、喜剧化、温情化;苏童的《米》是一则流氓哲学的生存寓言。五龙既是“流氓”原初意义上的失园者,又是“流氓”社会学诠释上的作恶者和性侵犯者。作家将五龙的生存本能置于悖谬的现代性场域——从“前现代性”逃离出来、进入“现代性”,最终返回“前现代性”而不得。连接“枫杨树”和“城市的北端”的是五龙从家乡带走的最后一把米。生的欲望是五龙流氓主义的原初动能和最大正义。
被饥饿经验深深缠绕的五龙,开始了他作为失园者的流浪。正如16世纪中期西班牙流浪汉文学《小赖子》一样,活下去,就是要把人变成无赖。看看大鸿记米店里崩坏的家庭图谱就可以知道:在城市,乡村以血缘为支点的伦理和经验全部宣布失效。五龙接受了城市的法则,其内核就是流氓精神——遇强比下贱更下贱,遇弱比狠毒更狠毒。正如“项羽吃肉、刘邦分羹”的流氓逻辑一样,五龙为了权势夺下六爷的地盘,狠心烧死媳妇织云,为钱出卖一帮兄弟。从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变成一个乖戾阴狠的流氓头目,五龙永远铭记着曾被人欺辱的仇恨。“身份性仇恨是流氓赖以生存的首席秘密。”仇恨背后,是五龙向城市进发的野心、自尊、自卑和不适感,这种混合情绪甚至是现代性过渡的必要心理阵痛。他在城市永远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只有米——这种作为乡村根基和生命的农产品,才能给他安全感。因此五龙寻花问柳的怪癖是在女人的下体塞上一把米,这既是一个乡村青年对城市的畸形反抗和示威,更是一种难以有城市认同感的漂泊者的极端自我保护。
除了与城市的隔膜,五龙的现代性遭遇在于城市对他的侵袭。花柳病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病。在濒死的五龙带着城市的恶果逃离现代性之路时,梅毒和金牙,连同他衣锦还乡的夙愿,一并夭折在火车上。而火车,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和一个鲜明的现代性意象,宣布了五龙的尴尬身份和黑色幽默般的命运。正如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所言:“从一次与土地家园实施分离的运动开始,越过无限的苦难与惊惧,在世界的其他地点与家园重新汇合,流氓的生命周期就是如此。”
精神狂欢:90年代以来流氓话语的变异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探讨了士大夫(儒)和侠(墨)变成盗最终流为奴隶和流氓的过程。他对于知识分子(儒)与流氓关系的阐释目光精准而狠毒。《米》中织云和阿保的私生子抱玉验证了这一点。抱玉看似是一个谦逊有礼的绅士,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勾引嫂子后不认账;流利的外语成为他的知识话语权,使他投靠日军成为汉奸,以此残酷报复姨夫五龙。到了80年代末,王朔笔下的顽主削去了流氓的罪恶属性,却保留了“身份性仇恨”,他们用流氓话语完成了一场轻盈谐谑的话语复仇。
90年代以来,作家的流氓书写变得更加轻松酣畅,达到了精神狂欢。贾平凹嗅到了知识界的全面溃败,在饱受争议的《废都》中,一批庄之蝶式的知识分子在遭遇文化危机而无法获得生命激情之后,只剩下了一身流氓文人多余的荷尔蒙和多巴胺。贾平凹在书写庄之蝶的文化流氓行为时,基本支点是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唐婉儿、柳月、阿灿等女性之所以心甘情愿委身于他,不过是对他名人作家身份的崇拜,其背后是对庄之蝶操持的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崇拜。在极具《金瓶梅》风格的性书写上,贾平凹自恋地建构起社会对知识分子“广场”地位的召唤态度,但又自省地意识到知识分子地位和精神的丧失。庄之蝶这一传统士大夫和文人流氓的合体形象具有一定的镜像性和警示意义,但是,即使它击中了知识分子的痛点,在普通读者那里,恐怕更多的还是一场流氓主义的话语狂欢和身体狂欢。
对比贾平凹将流氓话语进行雅化,王小波的写作姿态更像是他笔下那个黑夜里挥舞着阳具,孤独思考并且自我狂欢的男人。他触及到了流氓书写中性变态的极端,与妻子李银河的性学者身份构成了某种巧妙的互文关系(李银河曾自曝她与王小波的性虐经历)。在《兄弟》中,李光头靠贩卖他的流氓经验发家致富,余华凭借流氓书重新找到了大雨滂沱般的写作快感,并抵达了叙述的精神高潮,读者则从中获得了巴赫金意义上的人体学的解剖、窥探或自慰式的閱读体验。
在清点不同时期的流氓话语之后,我们发现,作家与叙述话语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奇妙的变奏。有趣的是,如果将问题扩大到文化领域,话语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流氓”的不道德面容和文化反叛姿态被冲淡,而变成一种轻快的娱乐和消费;同时,流氓书写的写作者也在泛化。在文学接受上,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宅文化、二次元文化、同性恋文化等所谓的亚文化实际上已在一代年轻人中获得了某种内在合法性。那么,在一个人人都是写手的时代,在一派开放而混乱的文化和美学氛围中,是否会有作家捕捉到这种极具当下性的言说方式,是否会延展严肃文学的边界,进而为当代文学的流氓书写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将成为一个很有考察价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