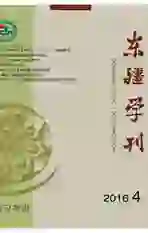朝鲜使者笔下的台湾原住民贺寿朝觐活动述略
2017-04-15刘耀陈文新
刘耀++陈文新
[摘要]清代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曾两次前来大陆参加贺寿朝觐活动。在这两次活动中,朝鲜使者都曾与之接触,并留下了相应的文字记录。其中关于台湾原住民历史及其参加贺寿朝觐活动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国传世文献的不足;而朝鲜使者对台湾及台湾原住民与中国大陆关系的辨析,则从一个特殊侧面展现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以及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一员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朝鲜使者;台湾原住民;贺寿;朝觐
[中图分类号]K3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0706
[收稿日期]2016-07-05
[基金项目]第5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6M592369。
[作者简介]1刘耀,男,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人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2陈文新,男,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武汉430071)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归福建省管辖,台湾被正式纳入清朝的行政区划。在清朝治理台湾时期,其重要的事务之一便是处理与台湾原住民的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理番”。“番”在古代泛指中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或外国部族,在台湾地区,“番”主要是指当地的原住民。根据台湾原住民的归附程度,清廷又将台湾原住民分为“生番”与“熟番”两类,即“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1](154~155)在清廷的“理番”政策中,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是极具特色的事件,以往学者已有相应的研究,并将台湾原住民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的缘起、过程及意义做了详尽的考述。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林衡立:《清乾隆年台湾生番朝贡考》,《文献专刊》第4期第3卷;郝时远:《清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事迹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戚嘉林:《台湾史》,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然而,前人的研究在关注台湾原住民赴内地贺寿朝觐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中国国内的文献,而未涉及域外文献。
清代的贺寿朝觐活动,并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庆典,它更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除了本国的纪录外,外藩使者也留下了不少的文献纪录。对于台湾原住民的贺寿朝觐活动,朝鲜使者也有相应的纪录,由于观察视角的差异,朝鲜使者的纪录不仅可以补域内文献之缺失,还可以更好地了解台湾原住民贺寿朝觐活动。
一、台湾原住民赴内地贺寿朝觐概述
清代台湾原住民赴内地贺寿朝觐共有三次,分别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乾隆五十三年(1778年)以及乾隆五十五年(1780年)。
雍正九年(1731年),台湾北路彰化县大甲西社爆发抗官事变,也是清代台湾较大规模的“番乱”之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才告平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出现了“番民赴省庆贺万寿”之议。雍正十二年,台湾原住民庆福等人由台湾渡海前往福建,在大陆停留二十余日后返台。雍正帝虽然同意了台湾原住民赴省贺寿之事,但他却对福建官员关于台湾原住民赴省贺寿的溢美之词大加贬斥,反映了其对臺湾“理番”事务的失望。[2](115~128)然而,这一事件开启了台湾原住民通过官方渠道赴内地参访的先河,为乾隆朝时期台湾原住民两次赴大陆贺寿朝觐提供了借鉴。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事件”,这是清代台湾历史上最大的民变之一。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廷调陕甘总督福康安赴台平乱,在台湾“义民”与原住民的协助之下,福康安迅速平定了“林爽文事件”。在这之后,福康安着手调整台湾的“理番”政策,并提出让台湾原住民赴京贺寿,“酌令生番头目数人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进京瞻仰天颜”,[3](209)乾隆帝应允了这一提议。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台湾原住民三十四人与“义民”首领八人,共计四十二人,由台湾前往北京,并与外藩使者一起参加了年班朝觐活动。次年四月,原住民返抵台湾,历经八月有余的朝觐活动才告结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值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了展现清帝国的强盛,同时也为满足乾隆好大喜功的心理,清帝国的官员们准备了隆重的庆典。这次庆典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在北京紫禁城结束,长达数十天。是年三月,台湾提督奎林等奏称,台湾“生番”头目十二人希望进京叩祝万寿。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同意了台湾原住民的请求,“于七月二十日以内前赴热河瞻觐,俾与外藩蒙古同与筵宴。”[4](72)而此次前来内地的十二名原住民,分属台湾南北中三路十二番社。这次的贺寿朝觐活动一方面是台湾原住民朝觐活动的延续,乾隆五十三年的朝觐活动后,乾隆帝曾应允“其他未及进京者”陆续进京;另一方面,这些番社也均是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出力的主要番社,因此乾隆帝同意他们前来热河贺寿朝觐,亦有褒赏之意。
虽然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活动只有三次,但却是意义非凡。而在这三次活动中,乾隆朝的两次贺寿朝觐,台湾原住民都与外藩使臣有着近距离接触,“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朝鲜、暹罗国使者,台湾生番等宴”,[4](855)这也让朝鲜使者有机会去观察台湾原住民,并留下了相应的记录。
二、初见台湾原住民
对于台湾,朝鲜使者并不陌生。早在清康熙六年,朝鲜就通过台湾漂流民了解了关于明郑台湾的情况。[5](970~972)在这之后,朝鲜都有留意台湾情形。其中前来中国的燕行使,更是通过中国士人进一步了解到了台湾的情形。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事件”,朝野震惊。次年,朝鲜派往中国的燕行使李正臣留意到清廷内部对于台湾的讨论,故询问了当时的朝鲜译官金庆门,“吾问金庆门曰:‘所谓台湾在何处,而台湾见失颠末,可得闻欤?庆门对曰:‘上年海贼窃发,贼魁有朱一未者,犯台湾,五月杀总兵以下大小官并五十余员,而入据之。皇帝命发江南浙江福建三省水军,往讨之,今方出师。而人谓此地异他郡邑,急攻诚难,以此骚屑。”[6](149)这里的“朱一未”应指的是朱一贵,也正是因为“朱一贵事件”才让李正臣注意到了台湾。
金庆门通过曾前往过台湾的“清差黄仪”了解到了关于台湾地区的详细情形,“台湾者,即一岛名,在福建海中,长八百余里,广半之,幅员几二千余里,四围以高山悬壁峻崖,飞鸟不得过,而但于北面开一门户以导水,其中则为沃野,且多宝产,人蓄甚繁,即所谓别乾坤者也。”[6](149)这段记录对台湾地理的认知十分精准,非亲历台湾而不能知。
除此之外,黄仪海对台湾的历史情形也十分了解,“皇明起自南方,江浙闽广次第平定,而至于此地,则官军不得入击,以是不入于版图。逮至甲申,天下皆薙发,而独有红毛遗孽郑锦,留发自在,不肯归顺。淸朝乃于其对岸澎台,置水师营,厦门置按察司,以备其侵掠而已。康煕癸亥,海溢而潮入水口,平地水高数丈,浸没人家无算。而水不退者凡八日。澎台官军,乘时进船击之,郑锦之裔克塽,穷蹙请降。今皇帝封克塽,为汉军一等公,移置京师。台湾置一府三县,岁课地丁额银万余两,解京又置总兵一员,军三千以镇之。兵官自总兵以下,有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千总、把总等官。民官则有知府、知县、同知、县丞、典史等官。”[6](149~150)在这段文字中,作者除了对郑经的出身来历有所误解外,可以说是朝鲜燕行使关于清代台湾早期历史、制度最为详尽的记录之一,但这一纪录中并未涉及台湾原住民。在此之后,虽然朝鲜燕行使也曾留下关于台湾的纪录,但因台湾地区在较长时间内未发生如“朱一贵事件”这样的大事,所以朝鲜燕行使也未留下李正臣般详细的纪录,更枉论谈及台湾原住民。
乾隆五十三年(1778年),对于赴北京朝觐的朝鲜使者而言并无特别意义,只是依例朝觐,但就是在这次正常的年班朝觐活动中,朝鲜使者第一次见到了台湾原住民。对于这支陌生的朝觐队伍,朝鲜使者十分好奇,因此留下了他们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观察纪录。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乾隆帝在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4](847)在这次宴会上,朝鲜正使李在协与副使鱼锡定二人与台湾原住民使者同居左翼。在此之后,朝鲜使者多次与台湾原住民同宴。正是一次次近距离接触让朝鲜使者得以借机观察台湾原住民,并获得与之相关的信息。
虽然李在协与鱼锡定并没有留下“燕行”纪录,但李在协在给朝鲜皇帝的奏报中提到了台湾原住民,这一奏报被保留在了朝鲜的《李朝实录》中:
生番即岛夷之别名,而在于极南海洋,与中国绝远,而羁縻于台湾者也。昨年春林爽文之败亡也,逃命于生番,生番人诱以擒之,纳于大军。皇帝嘉其功劳,使之来朝。而言语不通,故令台湾稍解其音者,领赴京师,其数为四十四名,别无君长,只有头目四人。而面貌皆如小儿,又无须髯,剪断头发,才覆衣领,或于额上口下黥作卦样。闻其性嗜生鱼秦椒,惯于水上,如履平地。[7](4798~4799)
在朝鲜文献中,李在协的奏报是第一次提及台湾原住民的官方文件,虽然只有一百多字,但其中却涉及了此次台湾原住民朝觐的原因与朝觐人员的样貌特征等。
李在协并不清楚此次朝觐的台湾原住民的具体身份,而是将他们简单地归类为“岛夷”、“生番”。实际上,此次朝觐的台湾原住民属于“归化生番”(輸饷不薙发),[2](115~128)有别于其他台湾“生番”。虽然不了解此次朝觐的台湾原住民的具体身份,但李在协十分清楚台湾原住民与中央王朝间的关系,“羁縻”之说多见于清代台湾的理番政策,“羁縻于台湾”更说明了台湾原住民归台湾府治理,而有别于外藩的情形。
上文已经提到,乾隆五十三年的台湾原住民的朝觐活动是因帮助清廷擒拿林爽文有功,李在协在其奏报中提到了这一情况。而对于“林爽文事件”,朝鲜使者一直都有所关注,在《李朝实录》中曾三次提及,[7](4797)但均未涉及台湾“生番”。因此,李在协的奏议是首次谈及台湾“生番”擒获林爽文有功的朝鲜官方文件。
对于台湾原住民朝觐队伍的人数,朝鲜使者指出有四十四人,但据《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及《嘉平二十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的记载,此次前来北京的台湾原住民朝觐队伍只有四十二人,其中包括“生番头目四名、番目二十六名、通事四名、社丁八名”[8](1029)。因此,关于“生番”人数,朝鲜使者的纪录有所偏差,但他指出,“(生番)别无君长,只有头目四人”,反映了朝鲜使者注意到台湾”原住民”的社会形态,也说明朝鲜使者收集情报之认真。
关于台湾原住民的样貌,中国的文献中多有纪录,明代陈第的《东番记》中便有关于“东番夷人”样貌的记载,“男子剪发、留数寸,批垂”,[9](25)这一记载与朝鲜使者“剪断头发,才覆衣领”的观察相合。此外,关于台湾原住民纹身的情况,巡台给事中六十七在其所著的《番社采风图考》中曾指出:“番俗文身为饰,男则墨黥眉际,若卦爻然,”[10](89)此处朝鲜使者所见则是“于额上口下黥作卦样”,可见,台湾原住民纹身的范围并不仅限于眉际。关于乾隆五十三年的台湾原住民朝觐队伍中原住民的样貌,中国的文献并没具体记载,而朝鲜使者的纪录正可补中国文献的不足。
此外,李在协还指出台湾原住民“性嗜生鱼秦椒,惯于水上,如履平地”,这一说法应来自清朝士人,因为这并不是依靠观察可以得知的。而关于台湾原住民,“性嗜生鱼秦椒”的说法,在清代的台湾文献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惯于水上,如履平地”则多见于台湾文献。可见,台湾原住民引起了李在协的注意,所以他才会去询问当时的中国士人。
虽然朝鲜很早就知道与台湾相关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涉及台湾原住民,而乾隆五十三年的年班朝觐活动,让朝鲜使者得以初见台湾原住民,并得到了与之相关的情报。遗憾的是,由于李在协的奏报属于官方文件,其内容较少,且未能超过中国传世文献中的相应记录,其价值也就仅限于一份少见的观察记录而已。然而,可喜的是,就在朝鲜使者回国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五年,台湾原住民再次启程前来内地,参加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盛典,这让此次来华的朝鲜使者有了观察台湾原住民的第二次机会。
三、文献与现实的交织
乾隆五十五年,为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朝鲜派出了以黄仁点、徐浩修为正副贺寿使的使团,该使团还包括书状成种仁,朝鲜著名文人朴齐家、柳得恭等。在避暑山庄,朝鲜使者遇见了前来贺寿的台湾原住民队伍,这次相遇,与乾隆五十三年的不期而遇不同,朝鲜方面早在一年前便从李在协处得知了台湾原住民也要参与贺寿朝觐的消息,这让朝鲜使者有了更好的准备与更多的机会来观察台湾原住民,并留下了相关的纪录。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朝鲜使团得知台湾原住民的贺寿队伍已抵达热河,“台湾府生番,是月旬前到此”,[11](422)但还未得相见。第二天,在参与朝觐活动时,徐浩修第一次见到了台湾原住民的贺寿队伍,也正是在这一天的纪录中,徐浩修留下了一大段关于台湾及台湾原住民的纪录。这也是朝鲜汉文文献中关于台湾及台湾“原住民”最为详细的记载之一。在这段文字中,徐浩修首先谈及了台湾还未纳入中国版图时的情形:
台湾,即明之鸡笼山,在彭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地多深山大泽,聚落星散。无君长,有十五社,多为千余人,少或五六百人。构屋以竹,覆以茅,不知历日文字,以草青为岁首。不食鸡雉,但取其毛为饰。俗尙勇习走,足皮厚数分,履荆棘如平地,日行屡百里。性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与邻国往来。[11](472~473)
在这里,徐浩修指出了台湾地区之前的数种名称以及原住民的社会形态,其关于“生番”只有十五社之说见于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一书,“鸡笼山、淡水洋,在彭湖屿之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云。深山大泽,聚落星散,凡十五社(《名山记》云:‘社或千人或五、六百)。”[12](83)关于“(生番)不食鸡雉,但取其毛为饰”的说法,则来自于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惟不食鸡。相传红毛欲杀生番,俱避祸远匿,闻鸡声知其所在,迹而杀之。番以为神,故不食。”[13](81)而对于台湾原住民的生活习惯,徐浩修指出,“(他们)性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与邻国往来”,这一说法与上文李在协的记录恰相反,而台湾原住民畏海之说也多见于明清文献。可见,徐浩修在写作这段文字时应已阅读相关著作或采访了当时的清朝士人,否则很难描写得如此清楚。
在此之后,徐浩修谈到了台湾与内地间交流的历史以及台湾被纳入中国版图的过程:
明永樂间,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避不至,和恶之,家贻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其后火反宝之,富者至缀数枚曰:此祖宗所遗。嘉靖间,为林道乾所据。万历末,为红毛荷兰所据,通市舶,设阛阓,筑赤嵌城,始称台湾。清顺治间,郑成功逐荷兰,伪置东都僭王。康熙癸亥,靖海将军施琅,平定郑克塽,设台湾府,隶于福建省,军民皆薙发从满洲冠服。[11](473~474)
徐浩修将台湾与内地的交往追溯到明永乐年间,即郑和下西洋之时,但实际上台湾与内地交流的时间要更早。关于“郑和贻铃”之说,最早见于明代陈第的《东番记》,后又出现在《东西洋考》及《明史》诸书中,然其真实情形当非如此,而只是部分台湾原住民固有的风俗习惯。[14]随后,徐浩修简述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的过程,这一部分没有出现李在臣般将郑成功称作“红毛遗孽”的错漏,且在徐浩修看来,台湾是确凿无疑的中国领土。
在前文中,徐浩修简述了台湾在未纳入中国版图前的情况,其中谈及了台湾原住民,但并不详细。因此在后文中,徐浩修专门描绘了台湾原住民的分布情况:
而如傀儡山,在凤山县东南界,土番所居,呼为加唠,重岗复岫,人迹所不到。山朝山,在彰化县东北,山南为生番三十六社居。蛤仔滩地,人迹罕到,又南为崇文山,内有生番十社。浪峤南屿,在凤山县南,土番所居,多瘴气鬼魅。南谥东屿,在凤山县东南,亦土番所居。等散处之番人,各自从其旧俗。[11](474)
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来自《清一统志》中台湾府的“山川”条,[15](8~24)但徐浩修并没有全文摘录,而只是选择了其中与台湾原住民有关的内容。由此可知,徐浩修在写作该处时,其关注点是台湾原住民。
接下来,徐浩修谈到了台湾的地理位置:
其疆域自府治,东至大山番界五十里,西至彭湖岛海五十里,南至沙马矶头海五百三十里,北至鸡笼城海二千三百十五里。其水程自台湾港西至彭湖屿,顺风四更,自彭湖西北至泉州金门顺风七更,自木冈山东至日本顺风七十更,东北至我国湖南界,顺风四十更。海道不可以里计,舟人分一昼夜为十更。[11](474~475)
在这段描述中,关于台湾府治的情况,也是摘自《清一统志台湾府》。而台湾岛到澎湖、日本等地的航海距离,史籍多有记载,但徐浩修所说的“东北至我国湖南界,顺风四十更”,并无相关史料记载,应是其从他人处得知。
除讲述了台湾及台湾原住民的基本情况外,徐浩修还谈及此次台湾原住民贺寿朝觐的情况:
乾隆丁未,林爽文败遁于台湾,生番等邀击擒献,事具热河文庙纪功碑。是月生番十二人,到热河,其冠服翦发覆额,刺卦文于眉间,或颐上。戴红质靑绣冠,穹窿如覆盆,四围有檐,上加龃龉梁,梁上插饰鸡羽,即鸡笼十五社旧俗。檐左右各悬小铃三枚,即三保太监所遗也。里着狭袖右袵绿长衣,表着狭袖中袵红罽金线缘短衣。项悬木牌,书所居社名及人名,有曰:中路多萝大埔社投旺、南路望仔立社均力力、北路末笃社啰沙怀、祝路屋鳌社也璜哇丹与、北路狮子社怀目怀,其余不记。所着冠服,皆自台湾府,仍渠本俗而制给云。[11](475~476)
从这一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徐浩修并不知道台湾原住民已于乾隆五十三年前来北京参加过年班朝觐活动,将此次台湾原住民的贺寿朝觐归结于擒获林爽文。同时,徐浩修对台湾原住民样貌及服饰的纪录较之李在协更为仔细,他所提及的“生番”人数及番社、姓名皆能与清廷的官方文献相合,从他只记录下五人的姓名可知,这应是他在与台湾原住民接触时记下的。
此外,与之同行的朴齐家、柳得恭二人,也都留下了相应的诗文。“三十六生番,齐眉发辄剪。衣襟系木牌,耳朵穿铜圈。”[16](549)朴齐家的这首诗主要是从台湾原住民的样貌出发,是“在场”的描绘。柳得恭则是结合台湾原住民贺寿朝觐活动写作了相关诗作,“画冠鸡羽插毰毸,铃子郞当步步催。湾府生番生也好,内山才缚匪人来。”[17](25)这两首诗都不能算是佳作,但朝鲜使团中有三人留下了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作品,由此可见朝鲜使团对他们的兴趣。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朝鲜使团与其他各国使团一起拜谒文庙,在大成门外西墙上,朝鲜副使徐浩修见到了《平定台湾纪》,摘录了部分内容,中间便有林爽文被“生番”擒获一事:
闻林爽文计穷欲逃入内山,而生番狙犷,未必能喻利害。预命福康安,既怵以威,复赉以惠。生番等果倾心效命,协同官兵、社丁人等。竟于正月初四日,在老衡崎之地,将林爽文生擒解京。[11](493~494)
徐浩修所见的碑文应是乾隆帝在乾隆五十三年所撰写的《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他只摘录了其中关于最后擒获“匪首”的部分,这也是他所撰写的《燕行纪》中再次谈及台湾与台湾原住民。此时,徐浩修虽已见过台湾原住民,且知晓林爽文之事,但他仍摘录《平定台湾纪》,在侧面反映了他对台湾及台湾原住民的关注。
结语:意外的缺席
台湾原住民参与了乾隆万寿庆典的饮宴、朝贺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参与了其他的一些活动。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迴跸圆明园”,当时中国官员与各国使臣都有在路旁候驾,而唯独缺了台湾原住民,“留京王公,大臣以下及回子,安南,南掌,缅甸从臣使臣,皆已先至,惟生番不在。盖闻贺班、宴班以外,如接驾赐游等处,皆令生番勿参。”[11](21~22)在徐浩修的纪录中,“生番”特指台湾原住民,可见,此次活动并不包括台湾原住民。由于台湾原住民参与了之前的诸多活动,他们的缺席才让徐浩修颇感意外,因此留下了这段纪录。
台湾原住民的缺席乃是清朝官员的有意安排,而对于朝鲜使者而言的“意外”,恰说明了清廷并没有将臺湾原住民视为“外臣”,而将他们与其它使团相区别。清代台湾原住民三次前来内地参加贺寿朝觐活动,均是嘉恩特赏,是清廷对台湾原住民帮助清廷“平叛”的奖励,而绝非将他们视为可与朝鲜诸国等同的使团,所以没有让他们参与接驾赐游等活动。
梁启超先生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18](11~12)朝鲜《燕行录》史料的挖掘正可以展现“亚洲之中国”的景象。虽然朝鲜使者对台湾及台湾原住民的记录并不多,但这些记录仍有不少有价值的内容,恰可以补域内文献之缺失,也让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到当时亚洲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台湾及台湾原住民与中国的关系,这一视角展现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以及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一员的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1]周钟瑄:《诸罗县志》,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
[2]郝时远:《清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事迹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68)》,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8年。
[4]《清实录(2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方豪:《明末朝鲜对台湾的注意》,《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
[6][朝]李正臣:《燕行录(栎翁遗稿)》,《韩国文集丛刊(425)》,坡州:景仁出版社,1993年。
[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8]《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
[9]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
[10]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
[11][朝]徐浩修:《热河纪游》,林中基编:《燕行录全集(51)》,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
[12]张燮:《东西洋考》,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
[13]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
[14]葛坤英、周文顺:《郑和台湾“贻铃”原委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15]《清一统志台湾府》,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
[16][朝]朴齐家:《贞阁集》,《韩国文集丛刊》(503),坡州:景仁出版社,2013年。
[17][朝]柳得恭:《热河纪行诗》,林中基编:《燕行录全集(60)》,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
[1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责任编辑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