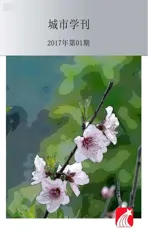“利出一孔”:从理论构建到制度实践
2017-03-28龚郑勇
龚郑勇
“利出一孔”:从理论构建到制度实践
龚郑勇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江苏南通 226000)
“利出一孔”是以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提出的确保君主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主张,随着秦汉以后国家一统的完成,这个理论得到了真正实践并不断被完善,使“利出一孔”的手段确保了“利归一孔”的最终目的,不断塑造着后世国民性格,影响极为深远。
利出一孔;理论;制度
一
“利出一孔”是指国家——确切地说是君主垄断一切资源,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政治观点是主张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他们著作中多次被提及,《商君书》:“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1]80“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1]125《韩非子》基本上直接沿用了这个原文,“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2]471
也有人认为“利出一孔”的观点最早由管仲在《管子·国蓄》中提出,“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3]1262罗根泽认为《管子·国蓄》当为西汉武昭之世的文字。[4]83-87-88
马元材认为“商、韩所谓‘利出一孔’者,盖欲一民于农战,乃从政治军事上立言者也……(《管子·国蓄》)乃从经济上立言。盖即所谓国家垄断经济政策者也。”[3]1263——不过笔者以为,这两者其实无质的区别,因为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经济,其最终目的皆为确保君主各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战争频发时期更多地表现在军事方面,而在相对和平时期则体现在经济方面,这两者不过是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不同侧重点而已。
事实上,在真正的管仲年代,并不具备实行“利出一孔”政策的条件,受限于生产力及交通工具等,不可能真正做到“如胸中使臂,臂之使指也”[3]1443的理想状态。不仅如此,按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的说法,管仲为政,“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5]2132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就更证明管仲其实并没有真正有效实行该政策,因为除君主以外的一切人都不会欢迎该政策的,这对于经历过人民公社及“文革”的国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管仲才拥有“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5]2134的特殊待遇而非商鞅式地受到除国君之外社会各阶层一致反对的下场,尤其是日后的齐国才可能出现学者齐聚稷下学宫的学术盛况。
所以,在大一统尚未真正完成的中国早期,“利出一孔”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实践,它只是对于“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6]994文学化政治理念的具体表述;但这种政治理论为日后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国家提供了治国的理论依据与操作指南,并且也塑造着未来的国民性格,影响至今。
二
“利出一孔”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鉴于春秋尤其战国时期恶劣的“上下一日百战”[2]50-51、“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2]116政治生态环境的担忧——当时的谚语称之为“厉怜王”,[2]106即连麻风病人都同情君主的命运,荀子还专门总结出“性恶论”的伦理观点。现实中,传统相对温情的“礼”已经让位给了严酷的“法”了。
基于“性恶论”的理论基础,法家人物首先推导出了君臣(民)具有天然的对立性:“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2]447“君臣之利异……故臣利立而主利灭。”[2]239“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2]115“臣主之间,非兄弟之亲也……群臣皆有阳虎之心,而君上不知。”[2]380韩非子总结出君主周围的“八奸”: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2]53-58——从所爱到所亲所敬者皆被君主列入了防范的范畴,传统宗法制社会的温情荡然无存,君主对周围一切都保持着警惕,“所谓治主,无忠臣……皆以法相司也”[1]112、“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2]430
所以,处于斗争一方的君主为了自身安全,必须最大可能扩大自身实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压缩作为对立面的臣民的力量:“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1]122“任吏责臣,主母不放。礼施异等,后姬不疑。分势不贰,庶適不争。权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门,大臣不拥。”[2]430尽管韩非子也批判儒家的治国理念,但在现实的等级制度维护上,他却与儒家惊人地相似。——所以,钱穆就认为“(法家)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7]264
与近代西方社会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故设计出了一套防范政治人物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物的制度不同,传统中国是以君主利益为本位的,同样基于人性“恶”的理论,所需防范的对象非但不是最高领导人物,反而是君主基于人性恶的理论对于除他本人以外一切人的防范。这样两者的起点不一,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也是南辕北辙。
三
为了确保“利出一孔”的最佳效果,法家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做法,倡导国家——其实是君主——垄断一切的资源:名、利、资源(人力、物力)等等,“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1]97而且,这种垄断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需要国民或哪个行政机关的授权。
首先,法家已经认识到个体理性对现实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2]397“故治民者,禁奸於未萌。”[2]472因此,首先要在作为源头的思想上进行“愚民”:“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1]7“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1]47“国乱者,民多私义”[1]111同时,为了确保“愚民”的最佳效果,法家认为将有理性判断能力的群体与普通的国民相隔离,这样普通的民众就会被置于人造的“真空”包装环境中永不变色,“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1]15“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1]11-12“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1]13“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2]35
当然,法家的“愚民”并不仅仅因为认识到民智的巨大破坏力,有时也是出于一种政治精英的自负,认为民确实是愚的,故必须为民做主,“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2]462在法家理论精英看来,普通民众的人性永远是好逸恶劳的,他们一旦丰衣足食以后,肯定会走向违法堕落。所以,重赋敛、剥夺国民多余的生活资料对于民众而言恰恰是一件好事,“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於用力,上治懦则肆於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已明矣。”[2]418“刑者,爱之自也。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2]472-473“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1]36这一点上,法家精英与儒家的“民可由使之,不可使知之”[6]5401本质无异。这样,“利出一孔”、让国民赤贫在他们看来恰恰是一种爱民爱国之举。
其次,在物质上“弱民”。物质上“弱民”在法家看来除了让君主直接获得最大利益外,更为关键的是国民为了最底线的生存只能听从君主的操纵,除此以外别无他途,“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1]39“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1]12“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2]349-350“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3]1262“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2]315
这样,民众也包括官吏,既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也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资料,“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1]31一切的生存只能依附于君主,黄宗羲指出其本质:“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8]18被动或主动地成为君主手中的一个工具,“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1]115“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普世原则为“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政治原则所代替。
四
在韩非子的论述中,通常法家讲究“法”、“术”、“势”三者。其实这三者可分两个层面,即“法”与“术、势”之分,粗略地说,“法”是君主用相对公开的手段进行统治,而“术、势”则是利用较为隐蔽但更为卑鄙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2]378“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2]385这两个层面构成了一个硬币的完整两面,而这两面的指向是同一个目标:为“利出一孔”的君主专制服务。
与儒家“仁”、“仁政”、墨家“兼爱”等人治政治主张不同,法家明确标榜出“以法治国”的“现代”法制理念:“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2]31“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1]106“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2]30
然而此“法”非彼“法”,现代社会的“法”是一种社会各阶层利益博弈后的契约,其适用的对象具有普遍性;而法家的“法”适用的对象却是君主以外的一切人,它只是君主掌控一切国民与资源的工具。“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2]201一句话,“法”是君主的工具:“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3]906“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1]145“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2]37君主的法是刑法而非民法,百姓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而进行的法律诉讼行为是受到其排斥的,“朝甚除也者,狱讼繁也。狱讼繁则田荒”[2]153
黄宗羲总结这种“法”的本质及其后果:“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8]23-24因此,《说文解字》对“法”的定义是,“法,刑也”。[9]820
所以,尽管法家提倡公平,但其本义并非为了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而仅仅是为了激起国民对于君主的更有效效忠,“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38“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2]201“法平,则吏无奸……”[1]77甚至为了维护这种“法”的尊严,君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韩非子笔下的卫嗣君愿以五十金甚至一个都邑的高价来交换一个逃魏的胥靡。[2]227——但这种法律的本质,如黄宗羲所言,“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8]8因为君主以外所有的国民都不是独立的被尊重的个体而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他们没有主动参与的权利而只有被动被支配的命运,所以顾准就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连在一起的。”[10]276——除君主以外,一切国民包括高官皆是平等地成为编户齐民,其本质是“以法治国”而非“依法治国”。
即便如此,一旦相对有文明底线的“法”依然不能确保其利益的最大化时,那么,他们就采用更为卑鄙的“术”与“势”,“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势不足以化则除之。”[2]306所以,齐田氏施惠与民,在法家看来景公君臣不知用势及时除去是个失策——此时,连他们自己制定的“法”都可以公然不遵守了。[2]310在一些极端的特殊时期,可以先刑后赏甚至只刑不赏,“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弱国刑五赏五。”[1]31其效果更为有效且成本节约。
当然,法家也并不是主张只罚不赏,它也对国民诱以官禄德。在法家看来,天下之人对于君主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追求,所以只要用利益就可以引诱到一切,“民利之所凑,则民道之”[1]46“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2]39“明主之为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材劝有功也。”[2]57“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2]456这样就达到了“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1]20的理想状态。
但是,一旦还有人不为名利所动,不愿自觉成为君主手中的工具,君主则会毫不犹豫将其除去。所以,伯夷叔齐在法家看来,“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2]106韩非子笔下的姜太公上任伊始便斩了齐国两个居士,仅因为“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2]312-313
所以,无论是“法”还是“术”与“势”;也无论是“赏”还是“罚”,其本质皆无异,都只是确保“利出一孔”的工具,这一点早在韩非子时就已明白,他说“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2]406传统中国没有哪一家思想学派像法家那样高度重视法律的制定尤其是执行的;但也没有哪一家思想流派像法家那样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在他们身上,这种悖论如此鲜明地同时并存。
五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利出一孔”的理论出现在经典政治理论著作中,如上面所提及的《商君书》、《韩非子》及所谓的《管子·国蓄》,其最晚截止在西汉武昭之世的《管子·国蓄》(按罗根泽的考证),再往后的政治理论著作中,这个词汇不再被提及;与之相反的是,在后世,“与民争利”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政治不道德行为,也常易招来政治对手的攻击。
但这并不说明“利出一孔”理论的消失,而恰恰相反,也正是这个历史阶段以后,“利出一孔”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付诸实践的机会,也即意味着“利出一孔”已经完成了理论的构建而到了制度的实践层面。
首先,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消灭了各种政治对手的同时,也消灭了国民迁徙的自由——这种对人身自由的控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越发成熟;而且,某种程度上,国民们也不需要迁徙,因为,整个国家的高度同质化导致了故乡异乡的无别,“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百县之治一形”[1]16在秦汉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真正成为了现实。以前曾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政权不下县。但事实上,秦汉时期国家机器依然强有力地延伸到了最底层的乡村,乡村所设的“亭长”“三老”等都是纳入正式的国家官职体系,这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明确记载,[11]742他们负责村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11]1121——这种描写也许有夸大成分,但至少也是政治追求的理想模式;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竹简也告诉我们即便是所谓聚族而居的魏晋年间,它也依然不是宗族自理的血缘社群而是国家强有力控制下的编户齐民。[12]2-44不仅如此,从秦国的什伍连坐之法开始到宋代保甲制、明代“出百里即验文引”制度等,让民众既接受着国家机器的有效监督也接受着彼此甚至是至亲的互相监督,“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藏)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1]136“天地为牢”至少部分地成为了现实。——“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2]97告密也成为了获得“一孔”利益的重要途径。
没有迁徙自由意味着国民劳动力(包括体力与智力)市场的唯一性与垄断性,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纵横在各个敌对国之间角力斗智的热闹成为了绝唱,稷下学宫“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5]2346的盛况再也不复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国民被封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丧失了获得多元信息的可能,只能被动地接受官僚机构的人身控制与思想灌输。秦晖考证出“汉之一里为户仅数十,而以上三系统(里、社、单)设职的就不下20个。”[12]94顾炎武考证乡村严密的机构组织时说,“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夫唯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13]362-363
其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使国民自觉地接受了思想上的“一孔”。事实上,汉代的儒家思想已经与早期的原教旨主义儒家有了很大的差别,早期孔子对“君君臣臣”的行为规范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激进思想在汉代以后渐为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叔孙通的仪式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大一统”说——新儒学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六经注我”的功利主义出现,也意味着儒法的同流合污,使“利出一孔”成为了一种国民思想文化上的自觉。这一点,黄宗羲看得很清楚,他说:“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8]9
不仅如此,后世君主更自觉地运用韩非子刑、德二柄术,汉代的征察制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更是自觉地将修正后的儒家思想打造成通往爵禄的“一孔”之途,这也就是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自负——常有人将其理解成将天下英雄尽纳入囊中之意——事实上,“彀中”是箭所能射及的范围,它更显示出残酷性的本质。所以,秦晖将赶考的举子比作待选的秀女,[14]201认为其本质无异。——甚至更有学者认为科举制那种“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的做法恰恰就是科举的“非儒化”即科举的法家化。[12]206-207
如果还是有人不为所动,不愿通过这相对文明的“一孔”,那么君主们的狰狞一面就显露出来了,他们不用法,而用更为卑劣的“术”与“势”,朱元璋提出的大诰十条之一:“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15]2284——“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2]466韩非子还未意识到,“术”与“势”其实是可以光明正大地以“法”的形式出现的,其间可以无障碍切换。
所谓“儒表法里”,其实是儒法一体。这一点,政治家们的眼光比一般人看得更为清晰,汉宣帝直白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1]277王安石说,“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16]22“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16]212-213因为“百代都行秦政法”,所以要“劝君少骂秦始皇”。甚至,当君主所倡导的“儒”可能损害到其利益时则毫不犹豫地以“法”制“儒”,所以,他们一方面鼓励儒家血缘宗亲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又不断借故进行“毁祠追谱”。[12]98-99
那么它们可相应地施行酉算子I(3)⊗ ⊗⊗I(4)和 ⊗I(4)之一,就能以的概率成功交换他们的量子态。
所以,“利出一孔”从字面上的消失并不意味它从政治现实中的消失,恰恰是以一种更为强势的姿态渗透到政治现实和国民性格中间,成为了一种政治与文化的自觉,上下阶层位置不同、利益各异,但思维结构却惊人地相似,社会结构呈现超稳定性,“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钱锺书称这种现象为“东西背驰而遵路同轨,左右易位而照影随形”。[17]261
六
长期的“利出一孔”政治实践,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首先,“利出一孔”政治环境下,扼杀了地方及民间经济的任何发展可能,获利最丰的盐铁自古就是官营,其他亦如黄宗羲所言,“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8]98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社会丧失了一切活力,由于对潜在风险的防范,传统社会中,任何社会组织的出现都会导致君主的猜忌,“结党”必然意味着“营私”,“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2]51甚至普通人之间的日常聚会都被猜疑,汉初《汉律》就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11]110——汉初政治上采用的是“无为”的黄老之术,尚且如此。长此以往,和体制的密切程度成为衡量一切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否则既不能获利也缺乏安全感。
由于社会组织的丧失自然就导致社会舆论的丧失,“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1]97“国乱者,民多私义”[1]111“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2]449——既丧失了独立社会存在的空间,也导致了国民理性判断能力的丧失,“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3]80所以,国之蠹虫只能是和珅而不是乾隆,从而实现了“愚民”的最佳目的。
其次,愚民者亦自愚。韩非子在探讨各种可能的亡国症状后,不经意流露出这样的一种可能后果,“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2]113当传统政治对手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环境中逐鹿天下的时候,民众只能被动地在两桀之中选择一个非最坏的结果,所以,中国的史书常常赞颂“不嗜杀”的君王,因为,我们的政治理念中,“不嗜杀”对于统治者而言,已经是一个最高政治道德标准而非底线要求。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发生碰撞时,长期愚民的最终结果不仅是民愚更是国弱,1900年夏,势如破竹的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北京时,郑孝胥感叹“自古亡国未有若是之速也。”[18]760这就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结局了。
不仅如此,“利出一孔”的政治实践也让君主处于众矢之的。仅远超常人的物质享受就能激起市井小人项羽刘邦的觊觎之心,韩非子早就意识到这点,“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2]441丰厚的物质享受与为所欲为的权力任性其本身就给君主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安全隐患,“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8]11况且越是完备的制度防范设计其最终效果只能让后来的大盗获益更多,“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19]255反正,“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19]256
“利出一孔”政策最严重的后果是让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君主本身也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只有私产的意识,所以,王良爱马与勾践爱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2]116况且这种资源是免费的,如果没有被君主耗尽反而是一种过错,“若夫转身法易位,全众傅(传)国,最其病也。”[2]404-405勾践式怒蛙[2]229-230的本义并非是对爱国者的尊敬而只是为了培养无理性判断能力的作战机器。一切只以君主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样又强化了君主对于国民的猜忌与防范。
由于历朝统治者忽略了国家利益应由各阶层均沾的常识,没有意识到民贫的国富与无自由的国家对于国民的无意义性甚至悲剧性,这样又自发形成了另一个层面,即君主以外一切臣民的无国家认同感。韩非子似乎预见到了这点,“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妇人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尽管韩非子也已经认识到了“今人臣之处官者,皆是类也。”[2]181-182但是,他也说不清身为这种国度里的国民其理性的出路在哪里,甚至连高官也缺乏安全感,“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的历史悲剧不绝于史。——韩非子更没有意识到,一旦具备“乘桴浮于海”的可能,大家会选择用脚投票,这在春秋战国就开始了。
[2]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 黎翔凤. 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4] 罗根泽. 管子探源[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5] 司马迁. 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6]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Z]. 阮元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7]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8]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9] 许慎. 说文解字注[Z]. 段玉裁注.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5.
[10] 顾准. 顾准文集[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11]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2] 秦晖. 传统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13] 顾炎武. 日知录校释[M]. 张京华校注.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14] 科举百年[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6.
[15]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6] 王安石. 王安石集[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4.
[17] 钱锺书. 管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8] 中国历史博物馆. 郑孝胥日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19]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责任编校:彭 萍)
From Theoretic Construction to System Practice Based on Chinese Proverb Theory of Benefit from One Venue
GONG Zhengy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Nantong Normal College, Nantong, Jiangsu 226000, China)
The ancient proverb that “benefit can be obtained from one venue” becomes one theory of controlling the country. This old theory keeps the most benefit of the monarch, This theory was proposed by Shang Yang and Han Feizi who were the most reformist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theory keeps all benefit that can only be attributed to the ultimate goal of one place. This view is continued for thousand years in the field of nurs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ities.
benefit can be obtained in one place; theory; system
D 092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1.010
2096-059X(2017)01–0056–06
2016-12-19
龚郑勇(1975-),男,江苏海门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