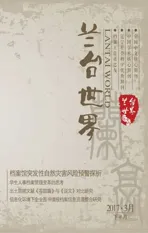《沧浪诗话》的审美思想研究
2017-03-11邓依晴
邓依晴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 100048)
《沧浪诗话》的审美思想研究
邓依晴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 100048)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部体系化的诗论作品。《沧浪诗话》提出了“妙悟”“、兴趣”、“入神”等一系列美学范畴。严羽将禅宗的顿悟与中国传统意境说相结合,创立“妙悟”说,并将其引入诗歌理论之中,创造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严羽将禅宗的“见性成佛”心体论与中国传统的比兴说相结合,创立“兴趣”说,并将其引入诗歌理论之中,推动中国古典美学在对韵、味、神、趣的追求中走向成熟。严羽将禅宗的“真如佛性”精神本体说与中国传统的老庄易三玄之神妙说相结合,创立“入神”说,以“妙悟”为径,以“兴趣”为法,最终达至诗歌之最高境界。
《沧浪诗话》 审美 妙悟 兴趣 入神
在中国文学评论走向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的过程中,《沧浪诗话》从审美视角总结了唐代诗歌的卓越成就,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代诗学进行了中肯地批评,并且提出了“妙悟”、“兴趣”、“入神”等一系列审美范畴。严羽将禅宗的顿悟与中国传统意境说相结合,创立了以“妙悟”为主题的审美体验论,以心对佛教的外象与内识二元体系结构进行创造性转换,建构起了象心境的三元谱系结构,并将其引入诗歌理论之中,创造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严羽将禅宗的“见性成佛”心体论与中国传统的比兴说相结合,创立了以“兴趣”为主旨的审美感兴论,试图通过直觉思维在心物之间建立起一种类比关系,从而达到心物一体的幻化境界,并将其引入诗歌理论之中,推动中国古典美学在对韵、味、神、趣的追求中走向成熟。严羽将禅宗的“真如佛性”精神本体说与中国传统的老庄易三玄之神妙说相结合,创立了以“入神”为宗旨的审美境界论,以心在内在的观念世界达到物我合一的神秘状态,成功地将老庄易之神妙与佛禅之般若融合,并将其引入诗歌理论之中,从而以出神入化的诗悟来表达人生的理想境界。
一、以“妙悟”为主题的审美体验论
《沧浪诗话》中的“妙悟”说,是严羽审美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1]12严羽不仅将佛教禅悟思想应用于诗歌理论之中,而且还对诗道中的禅悟进行分类:有限之悟、透彻之悟,一知半解之悟。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曰:“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1]12不仅如此,严羽还指出了妙悟的实现路径,作为顿悟的妙悟,必须建立在渐修的基础之上,通过学识的积累来通达妙悟之境。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谓:“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1]1在某种意义上讲,“妙悟”不是基于逻辑思维的理性能力,而是基于意象思维的感受能力;“妙悟”不是基于概念思维的理性抽象,而是基于经验思维的直观体验;“妙悟”不是基于生活的现实关怀,而是脱离现实的逍遥精神。
针对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提出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时代风气,严羽将禅悟引入诗歌之中,倡导以禅说诗,将禅悟作为诗歌创作、文艺批评、文艺鉴赏的基本要求。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言:“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於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1]26将禅悟引入诗论之中,的确有利于形成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意与境浑的审美思维方法,在审美思维中,“通过感观而可观之外显,如言、形、秀、韵,与通过心灵而体悟之内蕴,如意、神、隐、味,相互衬托、相互关照,达致言与意、形与神、隐与秀、韵与味的浑然为一,文章家于虚实的回旋往复、联动会通中空纳万象,以虚无衬实存,于有限见无限,引发无尽想象”[2]33。但是,禅悟毕竟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觉体验能力,致使中国诗论更多是经验的而不是理论的,更多是抒情的而不是思辨的,更多的是意象思维的而不是逻辑思维的。从根本上讲,这种禅悟式思维方式妨碍了思维之网上概念纽结的清晰性、精确性、确定性,不利于中国诗论的抽象理论思辨和严密逻辑论证。依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原则,实践设计优先于理论设计,那么,合乎逻辑的必然结局就是,中国诗论要对中国现实文艺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回答,就必须实现从意象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转型,这是中国诗论不可逆转的发展走向。
严羽引禅悟入诗论与佛教中国化所带来的文化转型相始终,对妙悟的解读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传统的意境说和佛教的妙悟说的融合,即须回归佛教中国化的语境。中国传统的意境说主张心入于境,意会于心,意明于境,心意境相交融的心——意——境三元谱系结构。“佛教追求虚幻的身外之象,转化为真实的身内之境,将身外之境转化为身内之识的境界观念,属于外境与内识的二元谱系结构。”[3]179在某种意义上讲,“严羽以佛学的外象转内识的妙悟来指称唐诗的妙处莹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但是又不同于佛学的妙悟观念:佛学妙悟的外象转内识境界,属于外象与内识的二元体系结构。而严羽所谓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悟境界,显然属于言象意,或心象境的三元谱系结构”[3]180。严羽的妙悟说正是在佛教的外象与内识之间加入心的中介,以心沟通意和境,像心如意,心入于境,心意境相交融,从而创造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悟境界。无论是佛教的外境与内识的二元谱系结构的禅悟,还是严羽的心——意——境三元谱系结构的禅悟,都更多地强调直觉感悟能力,不利于理性能力的成长,历史事实也是这样,严羽之后直至明清,中国美学始终停留于描述性、点悟性、经验性上,始终没有激发出严密逻辑论证的美学思想体系。从这个角度讲,严羽还是要承担一定历史责任的。
二、以“兴趣”为主旨的审美感兴论
《沧浪诗话》的“兴趣”说是严羽根据前人对“兴”和“趣”的阐述的基础上而凝合成的独具特色的审美范畴。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言:“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1]26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兴趣”包括层层递进的三个层次:其一,悦耳悦目,审美主体从直观感相的渲染来传达愉悦情感,在感知的基础上,再加上想象、情感、理解等因素的渗入,悦耳悦目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生理快感之内,而是陶冶性情的身心愉悦。其二,悦心悦意,“当外界事物有何自己意趣相通之处,便激发了感情,引起感兴,是由于内心之兴发感动所产生的一种情趣”[4]62。这种情趣就是从心与物的关系角度来审读兴趣,即审美主体因外物触发而在心灵深处产生的一种愉悦情感,达到理与诗的统一,心与理的统一,理与意的统一,情与意的统一,意与兴的统一,物我一体,情景交融。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所云:“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1]148其三,悦志悦神,审美主体在创作或鉴赏文艺作品之时,凭借直觉能力,捕捉灵感,获得一种似真切又虚空、似确切把握又无法言说的清空悠远、幽深隽永的审美体验,从而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妙悟境界。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所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26在某种意义上讲,“兴趣”不只是情感体验,更是渗透着学识的积累;“兴趣”不只是直觉体悟,更是渗透着经验的积淀;“兴趣”不只是想象的审美趣味,更是渗透着社会知识的践行。
严羽针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文风针锋相对地提出“兴趣”说。诗歌不能将语言技法作为其核心要素,兴趣才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本质特征,即“诗歌不以知识学问为具体内容和表现对象,而以‘吟咏性情’为根本”[5]47。诗歌要以有利于性情的抒发为本根,而不能咬文嚼字、凿文雕字、锤词锻字。“诗歌只有空灵剔透,不粘不滞,不即不离,才有诗意、有兴致,才算是本色当行。”[6]90严羽的“兴趣”说将诗论与“吟咏性情”联系在一起,以诗歌抒发性情不能用直来直去、平铺直叙的语言来表达,而应该借助艺术形象来表达,对艺术形象的塑造不是矫揉造作的,而是要不留雕琢痕迹,具有含蓄蕴藉之美,才能达到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审美境界。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言:“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26严羽的“兴趣”说还将诗论与“妙悟”联系起来,以“妙悟”为实现路径,来追求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在严羽看来,作为一种审美感受力,“兴趣”不能通过语言形式来加以表达,只能通过非语言的形式来体悟,让人们透过这有限的画面,去领略、去体味、去把玩那无穷的意趣。只有这样,诗歌才能“避免出现了江西诗派的创作弊端,并非僵硬、刻板;它保持了自然生命活泼的灵性,具有鲜活生命的流动性,让人可以从中体味到一唱三叹、余味不绝的诗性韵味”[7]19。应该承认,严羽强调“诗者,吟咏性情也”的诗论命题,并且高度重视诗歌的兴趣,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的确符合诗歌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但是,以吟咏性情为本,并不必然排斥文字的挺拔刚健;以兴趣为诗歌创作之旨归,并不必然否定才学的高深;以妙悟为诗歌创作之路径,并不必然取消议论的论辩。
严羽“兴趣”说源于禅宗的“见性成佛”心体论。禅宗六祖慧能把“心”直接提升为佛教的精神本体“真如”,既然“真如”本体原本就在人的心中,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主体如能当下敞开“真如”,即是明心,即是见性,即是成佛,即是涅槃解脱的圆满境界。因此,禅不可用语言形式来表达,更不可用义理形式来解释,而是只能通过意会的形式来体悟。因此,无论是以禅入诗,还是以禅说诗,抑或以禅论诗,都是强调诗歌的艺术思维形式非关书、非关理的特征,而应该追求别才、别趣,也就是说,将诗歌所要歌咏的性情熔铸于整体形象之后所形成的那种浑然天成、无迹可求而又蕴藉深远的艺术境界。中国儒家传统诗学的感兴论经历了从物感说到比兴说的发展过程。物感说就是将物和心连接起来,建立起某种微妙的联系,物感包括从生理层次的感官接受到心理层次的感受、感悟、情感等方面,物感说奠定了中国审美思维的感性原则,成为审美感兴理论的思想源头。比兴说是物感说的感性原则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兴抛弃了物感说中可能存在的义理思维,弘扬与义理思维对应的直觉思维,试图通过直觉思维在心物之间寻找、建立一种比类关系,从而达到心物一体的幻化境界。“兴趣说则是这两种分别来自儒佛两家理论相互联系的过程和融合的外在烙印。兴趣说的一个‘兴’字道出了妙悟说这种来源于禅宗的诗学理论对儒家传统诗学的无意识继承。不承认物感说、赋比兴说等儒家传统诗学理论,妙悟说就显得单薄、突然,它就成了严氏个人的独特趣味和偶然之论;而承认了传统感兴理论与妙悟说的内在联系,则以禅说诗的妙悟说便成了整个感兴理论发展过程中瓜熟蒂落的成果和最高表达,就成为感兴理论自然发展的逻辑必然。”[8]117在某种意义上讲,佛教的禅悟与儒家的比兴相融合而生成的“兴趣”说,在禅心与诗心、禅观与诗观、禅悟与诗悟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推动中国古典美学在对韵、味、神、趣的追求中走向成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兴趣”说是佛儒两家理论相契合之处的融合,而不是相异之处的互补。如何在佛儒理论的互补中寻求中国美学的创新就成为时代发展的重大课题。
三、以“入神”为宗旨的审美境界论
严羽认为,“入神”构成诗歌的最高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言:“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1]8在严羽看来,“入神”是诗歌经“妙悟”之路,承“兴趣”之法,而达诗歌之最高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谓:“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1]7也就是说,诗歌的审美风格有九种,而这九种审美风格又大致可分成“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两大类,要达到这九种审美风格就必须符合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等五种审美标准,必须运用起结、句法、字眼等三种审美方法,才能达到诗歌审美的最高境界“入神”。在严羽看来,纵观诗歌发展的历史,能臻于严羽“入神”标准的也只有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从诗歌的审美风格来看,李白的诗歌豪放飘逸,杜甫的诗歌深沉忧郁,然皆如“金翅擎海,香象渡河”,两种诗风都臻于“入神”境界。从诗歌的审美体制来看,李白的诗歌创作往往天马行空,富于变化;而杜甫的诗歌创作则是有章可循,中规中矩。从诗歌的审美题材来看,杜甫诗歌取材于六朝,充分汲取了六朝人在意境渲染、词句锤炼、格律推敲方面的优长,李白诗歌取材宽广,具有抱负宏大、气魄豪迈、胸襟开阔的审美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入神”是一种物我未分的境界,然而只有对物我未分的否定之否定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入神”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直观体验,然而只有在理性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直观的高峰体验;“入神”是一种远离现实世界的逍遥状态,然而只有对现实生活深切的关怀才能获得真正的“入神”状态。
针对江西诗派将注重诗歌艺术形式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泛滥,严羽提出“入神”才是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在严羽看来,诗歌要达到“入神”境界,就不能单纯凭借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等的形式技巧,而是要自由自在地将自我生命体验以合适的形式表达出来。为此,严羽将“入神”与“妙悟”相连,要充分体现出描写对象天然具有的神采,既无法单凭感觉器官的直接感知,也无法通过义理的分析来理解,而只有通过直觉体验、神思妙悟才能把握那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意。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云:“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1]11严羽还将“入神”与“兴趣”相接,诗歌要达到艺术创作出神入化的境界,就不能拘泥于外在形式的束缚,要突破“五俗”,“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1]108。要力避“五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1]122。要坚持“四个不必”,“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1]114。弘扬“两个倡导”,“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1]119。严羽还将“入神”与“气象”相联,诗歌创作要达到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就不能过度追求辞藻的外在形式,突出强调诗歌的“气象”,“气象”是“诗歌的各要素构成的整体境界,表现为一种感性风采”[1]90。诗歌只有具备了“气象”,才能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深厚的意境。“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1]144就实而论,严羽的“入神”说对于矫正诗坛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入神”说毕竟是一种意象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体思维对客观现实及其映像的确认,不易于对感知对象进行分析、整理、抽象、演绎”[9]147。最终致使中国诗论无法对现实文艺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也就无法演绎出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入神”是禅宗妙悟的极致境界,禅宗的妙悟极致境界“反映了禅定时静坐入神、内观冥思中意识失去控制并产生幻觉和联想的状态,表达的完全是一种神秘的、直觉的、超越现象界束缚的、离言绝象的宗教体验”[10]114。禅宗的“入神”将“心”直接提升为佛教的精神本体——真如佛性,成佛修行,达至入神境界,无须外求,只须内在的观念世界达到物我合一状态就能够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讲,禅宗的“入神”超越了物我相分的状态,物我完全合为一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禅宗“入神”就是对物我一体神秘境界的直觉体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入神”是一种用直觉体悟到的神圣境界,老子主张以“玄览”的方式来达至与“道”合一,庄子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来达至同于大通、通天下一气、从而与道为一的“入神”境界。《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所云“神”者,既指神秘之境界,也喻指思维之直感,即直觉思维。《文心雕龙》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刘勰所言“神”者,则是融和了老庄易三玄之神妙,即以直觉方式体悟神秘的境界。严羽《诗说杂记》言:“万事皆以入神为极致。……一技之妙皆可入神……魁群冠伦,出类拔萃,皆所谓入神。”[1]9可见,“《沧浪诗话》所标举的妙悟之说、入神之论,在思维方式上则是成功地兼容了老庄易之神妙与佛禅之般若。严羽在阐说诗歌创作的妙悟思维之时,借用了禅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象喻”[11]151。严羽诗学的“入神”说沟通了禅悟和诗悟,诗悟即是禅悟,禅悟即是诗悟。历史事实证明也是这样,只有物我分离的充分发展,人性能力才能真正超越物我分离状态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也才能真正达到严羽所云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入神状态。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夏静.对待立义与中国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J].文学评论,2010(6).
[3]徐扬尚.中国文论的意象话语谱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魏彩云.严羽“兴趣”说研究综述[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8).
[5]吴建民.严羽诗歌理论述评[J].徐州师范学院(哲学社科版),1996(1).
[6]朱志荣.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经典阐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宋冬莹.《沧浪诗话》的主要艺术观念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3.
[8]薛富兴.感兴:意境创造的艺术思维形式[J].东方丛刊,1999(4).
[9]王玉德.文化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10]刘达科.金诗中的佛禅意蕴[J].齐鲁学刊,2011(1).
[11]李建中.两爻之间的诗性诉求:以周易、老庄、孔孟的诗性言说为中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6.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KS017)。
邓依晴,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I206.2
A
2016-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