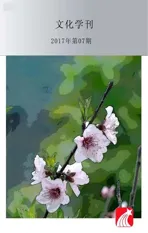误读他者与建构自我
——从翻译角度看晚清民初时期“《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
2017-03-11任宋莎
任宋莎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文学评论】
误读他者与建构自我
——从翻译角度看晚清民初时期“《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
任宋莎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晚清民初时期,学界对拜伦诗歌的翻译经历了一个高潮,其中,《哀希腊》的翻译最为典型。本文以拜伦《哀希腊》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汉译为例,具体分析了晚清民初时期“《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的原因,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哀希腊》在中国汉译的影响。
晚清民初时期;《哀希腊》汉译;爱国主义情感
一、《哀希腊》及其汉译背景简介
晚清民初时期,不少文人学士都受到充满反叛个性和革命精神的拜伦作品的影响,拜伦诗歌在此期间经历了一个翻译高潮,其中,《哀希腊》(以下简称为《哀》)的翻译最为典型。《哀》诗所属《唐璜》第三篇章,共16节,每节6行,原诗主要是一个游吟诗人所唱之歌,意在激起当时被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人民的奋身反抗,以重获自由。此诗情境在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和胡适等文人看来是十分契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地,便无一例外地都想借此诗当一回中国式的“游吟诗人”。《哀》诗的翻译被认为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此处援引邹振环所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它在当时中国所受到的欢迎更是被认为是一种“幸运”。*“拜伦《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的章名。
二、晚清民初时期“《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的原因
《哀》诗受到诸多文人的翻译,如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和胡适都对《哀》诗进行了翻译,这实属“幸运”。这四位译者在翻译时,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各位译者对此诗的改写,其目的旨在给中国人民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中国正如诗中的希腊一样,处在灭国的威胁之下;中国人民,要像诗人拜伦一样,应意识到这种威胁,努力开展“救亡图存”运动。
翻译是最易辨、最具影响力的改写,改写者们(或译者们)*根据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这些改写者们包括译者在内。自己创造了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某个时期或某种题材的种种形象,有时甚至是关于整个文学系统的,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都在目标文本中得以体现。[1]翻译的改写过程主要受3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包括文学批评家和评论家,他们的点评将影响一个作品的接受程度;其次是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包括特定历史时期影响力和权力大的个人,出版商、媒体或政党等团体,以及掌控文学分布的机构;最后是“主流诗学”,包括文学修辞手法和文学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赞助人”施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此处的“意识形态”是指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社会中可接受的种种观点和态度组成的观念网格,读者和译者通过这样的网格来处理文本。[2]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受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制约,其翻译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被“操控”的改写,译文中的改写部分亦是对原文的一种有意误读行为。
“西学东渐”使在中国介绍异国古典文学变为可能之事,这可能之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为之。在中国,拜伦有极好的声誉;而在其故乡英格兰,他并没有取得很高的文学地位。胡适在译《哀》一诗的引语中曾直白地评价拜伦:“在英国文学上,仅可称第二流人物。”[3]胡适之评价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其和其他译者翻译拜伦的诗歌并不是因其文学特质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拜伦的诗在异文化语境可执行的政治功能。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曾这样描述过拜伦:“在俄国和波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精神生活中,他如此慷慨地到处播下种子都开花结果了——从种下龙的牙齿的地方跃出了披盔戴甲的武士。”[4]勃兰兑斯所言道明了其他国家对拜伦赞扬和尊敬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和近代中国一样都曾遭受外敌入侵,而拜伦诗歌中的主题正是他们所急需的,于是他们借拜伦之诗来传递爱国精神,而近代中国对拜伦诗歌的翻译亦是和中国内忧外患的近代史紧密联系着。
晚清时期的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遭受着“国之将亡”的危机,中国人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救国的思想逐渐深入民心,当时的政治权力掌控者清政府首次提倡“西学”,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对此反应强烈,而中国的学者们也开始翻译异国文学,冀望在异乡寻求落败故国的重生。文学是语言艺术和话语实践的重要形式,话语体系建构着语言表达的价值和规范,话语权力使文学充满着控制人民的力量,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颇为类似中国“文以载道,文以治国”所表达的意思。晚清时期的政治话语允许西方思想的传播,因而翻译在此时期扮演者关键角色,当时时代的内涵即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和其占据主流的地位,而《哀》诗的翻译正是应此时而生。意识形态不仅操控了译者对原作的选择和翻译策略,而且操控了译作的接受。[5]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占据所有影响因素级系的最高位,而首要翻译标准——“忠实”,不再处于支配地位。
例如,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和胡适四人都无一例外翻译了《哀》诗,他们四人将译诗与“救国”这一主题紧密相连,旨在激起人民的爱国精神。《哀》诗在中国的翻译和重译绝不仅仅是一场“偶然的邂逅”。《哀》诗被引介到中国之际,正是中国经历社会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经受了种种国耻的中国人会尽其所能挽救已处于困苦情境的中国,这也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励的;而《哀》诗恰似为当时中国情境所作,呼吁着中国人民去战斗,这也符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想要在一个社会系统内引起注意,那么对于其主题的选择就必须与这个社会系统相关联。[6]拜伦最开始便是以一位革命先锋的形象被介绍到中国,其诗歌在中国的改写是为了重构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可见,改写和重构一个国家的文化受主体社会的意识形态制约,而主流意识形态又是由其所在的历史状况和政治话语所决定的。
三、误读拜伦与建构中国文化
拜伦在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英雄、一位自由战士、一位爱国主义者,换句话说,即一位中国式的拜伦。他们翻译拜伦的诗歌并不是出于审美需要,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满怀美好愿望,希望通过翻译拜伦,能够启发到中国人民,促使他们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者。然而,真正的拜伦并不是国家主义者,而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是一位爱好希腊的浪漫主义者,他的自由精神和希腊情节都促使他自然地向受压迫的希腊伸出援手。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拜伦被改写了,他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被重构,并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正如霍斯曼特瑞(Justa Holz-Manttari)曾指出:“翻译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受目的驱动、结果导向的行为,译者便是以救中国为目的而翻译拜伦,期望着中国革命即将胜利这样一个结果的到来。”
可见,在那个时代,“启蒙的目的,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7]《哀》诗被反复翻译这一现象便是呈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对它的有意误读行为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规范,拜伦被改造成了中国式拜伦——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被有目的地翻译,这些都被当作“他者”被中国文化观照着,为的是重构本土中国文化。
[1][6]Lefevere,A. 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9.26.
[2]Bassnett,S. & Lefevere,A.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48.
[3]胡适.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94.
[4]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徐式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53.
[5]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18-25.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16.
【责任编辑:王 崇】
I206.6;I046
A
1673-7725(2017)07-0069-03
2017-05-10
任宋莎(1989-),女,四川阆中人,助教,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